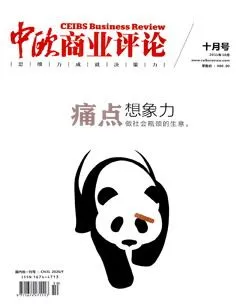2011-12-29王婷
中欧商业评论 2011年10期
惠源制药集团自主研发的新药已经完成了在中国与新西兰的临床Ⅱ期试验,但遭遇资金困境的董事长李国辉却不得不考虑将它卖给跨国药厂。不断重演的研发困境,已变成中小药企不能承受的负担。“卖还是不卖”的抉择背后,是否有第三条供养研发的道路?
“眼前的困境,让我们不得不考虑是否要将‘诺雷它安’卖给跨国药厂。这个选择太艰难了,就好像将自己的孩子送人。但为了项目能够维持下去,有时候又不得不痛下狠心。”惠源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辉说这番话时,会议室内在场的人似乎看到这个一向冷静的中年汉子的眼眶湿润了。
这些天,李国辉几乎没有合过眼。他做梦都在想,到哪里去筹3亿元,好让惠源度过最后的艰难时期。今天在会议室内,他对公司所有高管的这番话,几乎浇灭了大家对诺雷它安十年来的热情。
仅仅是一年前,李国辉还曾在业内知名的“中国创新药物研发战略”研讨会上自信满满地对外界介绍惠源制药集团自主研发的重磅新药——“诺雷它安”的最新进展。该药是国内少有的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药,已经完成了在中国与新西兰的临床Ⅱ期试验,在国际抗老年痴呆症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性进展。当时,李国辉表示,诺雷它安将会成为中国医药产业一个划时代的突破。但如今,这个被寄予厚望的产品可能又要成为跨国公司的囊中之物了,这真是切肤之痛啊!
其实早在三年前,诺雷它安Ⅱ期Ⅱ临床刚刚启动之时,就有一家来自挪威的国际大型制药企业出价3600万美元与惠源接触,承诺提供给惠源全球销售T+OKhbzwHWiRxjClCsDga7hqw/WvjIERYtNVFPlEbfo=额10%的分成,以收购诺雷它安的全球市场销售权,但李国辉拒绝了。如今Ⅱ期临床结果宣布在即,已是胜利在望,李国辉实在不忍心将胜利果实拱手让人。但另一方面,为了研发该药,惠源却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存粮”。不久前又有一家英国药厂接触惠源,希望收购这一新药,卖还是不卖?李国辉遇到了自己经营企业以来最大的难题。
万难之事
惠源是华南一家知名的中型制药企业,李国辉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惠源时,手中只有一个口服抗病毒药物的配方。如今惠源已经发展成为一家集制药、生物医学工程、药材种植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生产口服液、胶囊剂等中西药制剂80多个品种。
企业越做越大,但是李国辉却感觉路子却越走越窄了。
困难的“供养”“李董啊,听说最近你又遇到资金难题啦?”会议后的第二天一大早,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郑天成副局长就打来电话询问李国辉。郑局长和李国辉是老朋友了,正是依靠郑局长的推动,诺雷它安已经投入的3亿元研发资金中的1亿元才得到了国家支持,分别从国家“863”计划、市“科教兴市”重大产业科技攻关项目以及“重大新药创制”专项首批项目中获得。
“可不是吗,承蒙领导关心,这次又需要领导支持了。不知道目前还有没有其他的支持创新药物研发的基金,可以给我们拨一些救救急啊?”李国辉急切地问。
“国辉啊,你也知道,就算有,也还需要按规定审批。而且你也很清楚,之前诺雷它安入选国家重特大新药创制科技专项,但整个专项国家预算投入70亿元,有1200多个项目共同分享,分摊下来,每个项目也就不到600万元,惠源也是一样,这区区几百万元还是不能解决你们的大难题啊。我觉得你还是需要从其他方面想想办法。”郑局长说。
“是的,谢谢领导的指示,那我再想想办法。”李国辉颇为沮丧地放下电话。
李国辉明白,对于中国众多研发型中小药企而言,国家专项资金对于企业的支持通常都是有限的。尽管国家已出台了不少鼓励政策,发改委、科技部等有关部门每年均要提供数额可观的资金扶持药企研发项目,但由于这些资金发放通常采取“撤胡椒面”式的做法,靶向性差,对促进企业研发水平的提高、解决真正的资金难题效果并不明显。而在申请国家经费的过程中,企业还需要经历漫长的新药审批流程,研发进度一拖再拖。比如,惠源曾与国内一所知名科研院所合作研发的另一新药品种,申请国家专项基金过程中,仅仅听证就耗费了半年时间,审批至今还未结束,研发进度也因此不得不放缓。即使是申请下来了,也确实像郑局长所说,对缓解企业的巨大资金压力而言,只是杯水车薪。郑局长哪里知道,李国辉早已想了很多办法,该找的关系都已经找了。
这时,电话声又响起来,是安达创投的合伙人秦红。“李董事长,我是秦红,很抱歉,安总让我转告您,这次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拿出这么大的一笔钱了。真是对不起了。”秦红无奈地说。
听了秦红的话,李国辉并不吃惊。过去几年来,惠源用于诺雷它安的3亿元研发经费中,有2亿元就来自安达创投等创投机构的股权投资,安达创投的董事长安涛和李国辉是校友,一直对李国辉的研发事业很支持。但目前,惠源再引入新战略投资者的可能性已不大,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安达创投这类国内专注于生物医药的VC资金规模都不大,且多数都缺乏专业的风险评估认识,投资额度偏小,难以提供项目长期的资金保障。“如果我再逼促,恐怕也是给安涛出难题咯。”李国辉知趣地对秦红说。
“您有没有与国内一些具有投资实力的企业接洽过呢?”秦红问。
李国辉明白,秦红是希望惠源“傍大款”。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大型制药企业通常与研发型中小企业合作,结成战略联盟,利用自身充足的资金和丰富的I临床研究经验,快速完成新药的研发和上市。
但问题是,国内大型药企根本没有收购惠源的能力和魄力。由于中国的大型医药企业普遍自身盈利能力低下,靠的是一些市场仿制药和抗生素销售,这些产品的泛滥使得制药厂家的利润率较低;此外,许多药企还需要花大量的营销推广成本,要“搞定”各级分销商和各家三甲医院,很少能具备“供养”一个耗资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新药开发的经济实力。
虽然心中早已有数,惠源在国内是“傍不上大款”了,但他还是客气地对秦红说:“我们还在积极联系,秦红,请转达我对安总的谢意,让他费心了。”
拼的是综合实力创新药物的发现和研发是一个复杂精细有机结合的系统生物工程,大概平均需要10~15年,花费约3亿~6亿美元,并在每个阶段都需要整合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技术、仪器设备、试验场所进行配套。按照李国辉的话说,就是“新药研究是涉及多学科和领域的系统工程,是知识技术高度密集和资金密集的耗时工程,如果能成功,很大程度上拼的是这些方面的综合实力,是万难之事”。
在科研压力、人才、管理和资金等挑战中,目前对中国企业而言,最难的恐怕是资金一项。李国辉曾经算过一笔账:在中国这样成本较低的国家,新药研发的成本大约在4亿美元左右,比欧美便宜不少。但4亿美元对普通的制药企业来说仍然是个很大的数字。以“诺雷它安”为例,研发已经用了10年时间,预计到成功上市还需要2年多,临床费用已经耗资3亿元左右。
而如果要在全球上市,惠源还需要到其他国家做国际临床试验,还要做国际市场开拓,因此还需要2亿~3亿元。而惠源就是勒紧了裤腰带也再筹不出这笔钱了,上至管理层,下至其他股东,都只能望“钱”兴叹。
巨大的科研挑战和资金压力,让几乎所有的中国药企都只能凭借生产国际上专利过期的仿制药来积蓄实力,而不敢望“研发”之项背。相比之下,李国辉是难得的理想主义者,作为惠源的领军人,李国辉一直抱有着产业理想,毕竟背靠全球第二的医药消费市场,中国制药企业的未来机遇充满了想象空间。
然而不断重演的研发困境,在诺雷它安上重现。“卖还是不卖”成为让李国辉寝食难安的问题,“如果不卖给英国人,惠源还有什么办法?我的新药梦就真的这样破灭了吗?”李国辉几乎天天自问。经过一天的高层领导人会议,大家都对诺雷它安的命运感到惋惜,但也都感到“无力回天”。
自主研发:输在最后一公里?
“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发一代”是惠源的生存之道。近些年来,惠源一直在围绕着新药开发做工作,已经做好了短、中、长期发展规划。短期主要立足于支柱性产品、治疗冠心病的“托安酚”和口服抗病毒药物“利康”口服液两个产品的二次开发。目前利康口服液已经获得了治疗结膜炎的临床试验批件,治疗手足口病的临床试验也正在审批过程中,一旦审批通过,该药品的发展后劲相当乐观。
诺雷它安则是惠源的中期发展规划药物。同时,惠源还有几个储备项目已纳入长远规划项目,其中与国内一所知名科研院所合作研发的一种抗心肌梗死的新药很有进展,但由于缺乏后续研发资金只能暂停。它与另一所知名科研院所合作研发的另一新药品种,也因为国家支持经费迟迟申请不下来而举步不前。原本对“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发一代”战略寄予厚望的李国辉,却因“缺钱”陷入了万般愁苦。如果诺雷它安被卖掉了,惠源不知何时才能开发出能够全球上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要想摆脱靠老药维持经营的现状,站在产业价值链的顶端,更是不知还要“熬”多久?
惠源在华南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研发型药企,它遭遇的种种问题折射了中国医药企业的典型困境,其中资金问题就是不断打乱药企研发安排的重要困扰之一。
医药行业研发周期较长,一款创新药的研究,从科学家的实验室开始,在取得基础的研究成果之后还要历经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等环节,要经历一个10年左右的漫长研发周期,可谓“10亿美元10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各种实验失败的可能性,更需要企业持续投入资金和人力。正是这种资金和技术的门槛,使得医药研发成为跨国医药巨头们的寡头俱乐部,中小企业根本“玩不起”,也“伤不起”。最终,跨国医药巨头们垄断了全球创新药的市场,分享丰厚的收益。
跨国制药企业之所以愿意在研发上投入重金,看中的正是专利药背后巨大的利润空间。一般来说,一款原创新药的利润率在40%左右,而靠仿制药生存的大部分中国药企利润都十分低下。
而有了诺雷它安的惠源的命运很可能会不同。经过10年的艰苦研发,如今诺雷它安已经申请国际与国内发明专利62项,获得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地区的专利保护。据估算,一旦审批通过,其未来在全球的销售额将达到60亿美元左右,年利润或达25亿美元。作为一款拥有全球专利保护的原创新药,“诺雷它安”被认为将面临一个仿制药无法想象的巨大市场,让中国药企真正攀至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如果它能够实现全球同步上市,则意味着中国也能培育出年销售额几十亿美元的专利药。
纠结的未来
这次李国辉之所以有点万念俱灰,除了资金链的绷紧之外,还有研发团队的动荡和国家政策等各种烦扰。
人才保留战药物研发企业需要在人才、实验设备上投入大量资金,从药物发现到开发的各个过程都需要建立不同专业部门,部门内部又要配备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才。所以,整个新药研发是一场艰苦卓绝的人才战和心理战。即使小小一片“诺雷它安”,为了它,惠源已经支出了巨额人力成本。
比起实力强大的跨国医药巨头,本土公司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本就欠佳。而且研发团队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累积,也就需要本土药企在研发上持续投入。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让惠源备感成长的艰辛。首先,企业缺乏足够的优秀项目储备,在研发上的投入和支持也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甚至有的时候因为经费紧张,不得不压缩研发人员的工资,一些研究人员为此干脆离开了企业。
李国辉已经认识到,诺雷它安要想最终在国际上市,惠源需要具备丰富的资本运作经验。适时圈到钱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也需要在政府中获得重要人脉,帮助惠源在药物审批中得以过关斩将。但长期搞科研的李国辉现在转型做政府公关和投资者关系管理,显然并不擅长。
雪上加霜“限价令”,“以药养药”无法为继 “董事长,刚刚得到消息,国家基本药物最高零售限价(指导价)将于本月底公布,这对于我们可不是个好消息啊。”
李国辉还在纠结的情绪中,秘书张凡又匆匆地走进会议室,告诉了他一个新的消息。最近正值国家医疗改革政策密集发布的时期,此次将颁布的基本药物最高零售限价(指导价)也是医改政策之一。这个政策的公布对广大患者而言是一个好消息,对整个医药产业来说却五味杂陈——医药制造商、医药流通商甚至医院这些产业链利益共同体,都被一个透明而不可穿越的天花板限制了。这意味着药企利润将被摊薄,那些“以药养药”的研发型药企的资金将更加吃紧,也许将有更多制药企业会降低新药研发的积极性。
“这样一来,我们的两种主打药品的定价可能都会受到影响。现在药材价格飞涨,我们还能挣多少钱啊!像我们这样的研发型药企积累资金搞新药研发就更困难啦!”财务总监谭致远担忧地说。
2006年,中国生物制药研究院研制的治疗老年痴呆症的新药“石山碱甲衍生物”,就是在欧洲6个国家完成了Ⅱ期临床试验后,因无力加大后续费用而以800多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德国安道森公司。“中国医药市场上超过97%都是仿制药,大部分所谓的新药都不是真正的新药。像我们这样苦苦研发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成功了,难道就把胜利成果拱手让人了?新药研发本来就要巨额资金为助推器,现在药物限价政策一出,我们怎么还有生产新药的动力啊?难道也要走其他企业生产仿制药的老路?但那也是个价格战的死胡同啊。如果我们的新药成果被外资收购了,对整个中国的自主创新药物研发而言,将不啻为一个大悲剧。”研发总监薛建平愤愤不平地说,“想当年,我可是放弃了海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跟了李董事长来创业的,没想到,第一个新药研发成了这个结局。”薛建平不由地异常苦闷。
按理说,制药行业现在正面临着大好的发展机遇。从2002年开始,跨国公司就因为专利到期、研发效率低下、价格竞争等因素,开始纷纷关闭国外的研发中心,转而在中国建研发中心。它们看中的就是在中国研发新药成本较低(包括物美价廉的科研人才)、丰富独特的疾病资源以及广阔的市场空间。惠源本指望通过诺雷它安为中国研发型制药企业打入一剂强心针,激发制药企业的研发热情,对抗跨国巨头,没想到荆棘重重。
晚上回到家,李国辉窝在沙发里,听电台《新闻播报》中的一条消息:“2000~2010年间,中国医药行业销售额的年复合增长率超16%,约为中国GDP增速的两倍,远快于同期1O%的世界药品市场增速。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新医改及基本医疗保障的全面覆盖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将推动中国医药健康产业未来10~20年持续增长……”李国辉不禁摇头,关上收音机,喃喃自语道:“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新兴市场中,能有几家中国药企分得大部分的羹?看来,‘中国培育不出年销售额几十亿美元的专利药’的说法还得继续盛行。”
面对英国医药巨头伸来的橄榄枝,李国辉依然难下决心。推出本土自主创新药的理想真的又一次幻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