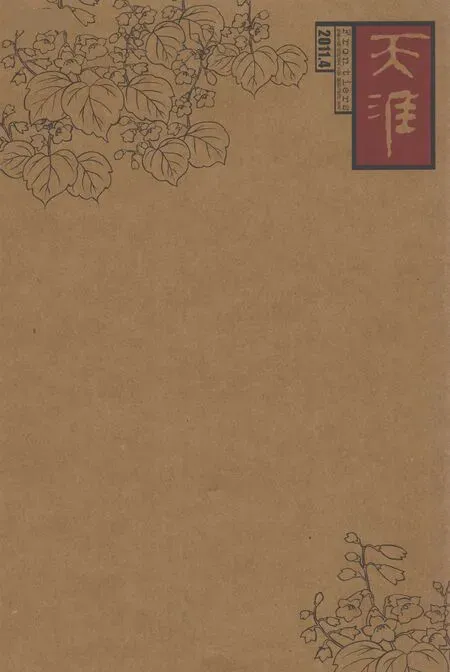在西藏长大
2011-12-25凌仕江
凌仕江
在西藏长大
凌仕江
我停止写作,对着窗外喊他名字的时候,他正蹲在那棵唐柳下逗一只睡在阳光上面的猫,许久才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站起身,跑着步答应我:来了,来了。他还不敢随便跑进我的房间,也不知该怎么称呼我才恰当,因为和我还没打熟。他怯生生地站在窗前,看着我桌子上刚冲好的一杯速溶咖啡,他的嘴唇动了几次,终于没能说出话来。最后,看我哈着气,抿了一口,他才带着惊异和一脸傻笑指着那棵唐柳说:“你快看!”
我终于甩过头,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一只拳头大的老鼠正躲在那只猫的耳际窃听。猫是白色的,雪一样的纯白,老鼠是麻灰色的,像乡下人养的麻麻兔,它瞻前顾后,贼心不死,走起路来大摇大摆,它的得意是偷窃到猫的隐私了吗?难道它还想跳到猫背上舞蹈不成?这真是阳光下面难得一见的新鲜事——这是我抵达硬雪包裹的哨所一周后发生的事。之前的几天,他一再让我看这看那的,我从不感兴趣。他肯定认为我是个不太好相处的人,我以为我早已熟知哨所的一切,他反复对我指点的那些事物已经提前疲惫,甚至麻木。在喜玛拉雅的那些时光,我去过的哨所太多太多——雪莲花开我见过,狼群侵袭我遭遇过,与鹰共舞我参与过,捕猎者卖熊掌我买过,牧羊人追赶野牦牛奔入哨所我解围过,但我从没在哨所看到猫和老鼠如此亲密,太不可思议了。这两个死对头真要抛弃曾有的恩怨,构建和谐社会了吗?我摇摇头,心里在说,看不懂,真是看不懂呀。他只顾笑,腰如弹簧弯上弯下的,双手捂着嘴,小小的脸蛋盛开出那么多惊艳的豌豆花,但他最终没有发出一丝笑声,他抽动的脖子生怕惊散了哨所里最动情的故事。那一刻,我脸上除了比地上的硬雪僵硬,什么表情也没有,更不可能有豌豆花开了。我知道再精彩的故事也不会带领我走出此刻的哨所。老鼠把猫惊醒之后,猫“嗖”的一声便跃上了唐柳。他的脸很不甘心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就像故事在一瞬间回到了最初的地方。接下来,他提着水壶摇摇晃晃打水去了。我又回到了一个人的世界,面对稿纸发呆、忍耐、孤独和痴狂,上帝送我一双翅膀,我也没有胆子飞走。
因为来这个哨所体验生活是上级指派的工作,而我深知,作为一个写作者,其实这更是我生命的另一种突围和需要。
我更愿意和眼前的他散步。他的表情和几天前的机警相比,与我已经算打得很熟了。那天,他叫来了哨所的另一个人。原本哨所的人也不多,除去班长休假,就只剩下他们二人。我们从哨所下来,下八百多级台阶,在乱石丛中没有方向地往前走,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走,也不知能走向何方,脚下的路太多,风把我们的影子吹得东倒西歪。经过大大小小八百多座墓碑,天色一下子像被关闭了白天的世界,但墓碑在星空隐约的折光下有些微亮。我望着远处闪光的河面,想了又想,我们是不是该折回。西藏的许多夜晚,天边总是有星星在旷野铺出闪亮的大道,那可是银河?我对着那些闪烁的波光忍不住歌唱:“冰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当我离开它的时候……”刚唱两句,便被他俩的声音止住了:“求求你,换一首吧?”他们应该是睁大眼睛看着我的,但是夜幕越来越深,我们都看不清对方的脸。“怎么了?难道我唱得很难听吗?”风过无声,有星星像一颗宝石飞过天边。“不是的,千万别误会,其实在哨所,我们也是很爱唱歌的,只因几个月前,一场雪崩洗白了我们的三个战友。”
“你看,那就是他们仨合葬在一起的墓碑。”我再无心唱歌了,真想不到事情会是这样的。什么也看不清,大地一片沉静,只有野草在疯长,伸手摸到草尖尖,草结穗了,野草也有春天,可野草有过爱情吗?我知道他们仨同我身边两个活着的小弟兄一样年轻。尽管他们已经死去,可走过他们身边,我从不胆怯,他们也都只有二十来岁,名字叫磊磊、鑫鑫、小辉。
而陪我走在一前一后的,前者云濡,陕西人;后者穗良,江西人。他们注定要成为我此文的主角,他们更能代表哨所兄弟的形象。
又一个寂寞的夜晚要降临,我们用虚弱的笑声提前骗走了无聊这个强大的天敌。挥着翅膀的雪花,它们摇摇晃晃是要为我们送来欢乐吗?我们照常散步到了墓碑前,像是去看一群老朋友。回来的路上,雪越下越大,棉花糖一样给大地投掷无限甜蜜。他们仍然一前一后地走着,把我夹在中间,耳边一直回响着大雪拍打狂风的声音。雪团砸在我们厚厚的大衣上,丝毫没有什么声响,因为它太轻柔了,风似乎更有力量,风常常可以打败阳光,但它却打不过此时的雪。“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好像那雪崩飞滚万丈,啊,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可爱的脸庞……”突然,穗良大声唱了起来,我甩过头,看见他停在那里,双手痛击风雪,他是想赶走风雪的寒冷吗?他的腰被风吹得比哨所里晒衣服的铁丝还要弯曲,那是他在用尽全力歌唱,不光我诧异,就连走在前面的云濡也被惊呆了。云濡顺着风跑过去,猛烈地把穗良摁倒在雪地。原以为穗良只是在和大风雪斗气,哪知他在雪地里翻了几个滚之后,却站在原地不动,唱得更疯狂。此时,狂雪在舞蹈,雪地很快就硬了。穗良的脚在硬雪上跺了一个洞,他在挣扎。而毫无办法的云濡,彻底被这突如其来但却没有理由的歌声震得不知云里雾里,刹那间,他手足无措,似乎忘记了眼前的人到底是谁,也不知道穗良到底想做什么。如果我没记错,上次我在墓碑前唱这首《怀念战友》的歌完全是因为想起了刘欢那宽广又深情的嗓音,绝非触景生情。我想穗良歇斯底里的呐喊,一定有着比我更为复杂的情绪。他的声音里含满了比雪更晶莹的水。虽然,我在风雪中容易想起女人的温暖,可我根本没有资格让他换一首《真的好想你》。
云濡无可奈何地等待了一阵子,穗良终于唱完了。我们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前走,没有说话,耳边回响的仍然只有雪拍打风的声音。我不曾问穗良突然唱起歌来的原因。但我知道,就在他歌唱之前,我走着走着就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墓碑前的野草,想起了远方的白桦林,想起了《真的好想你》和一段不堪回首的爱情。最后,当我们爬回哨所,雪早已挡在了门槛。在我的小屋前,看得出来,穗良是想了又想,终于,转过身,他在烛光下告诉了我:“你们不知道,去年今日的晚上,他们仨还在围着烛光为我过十九岁生日呢。”
这一点,云濡看来并不知道。云濡比穗良晚来哨所。但云濡却比穗良早入伍几年。现在我知道了,大雪一般不会给哨所带来什么欢乐,它更多的是在昭示,昭示悲伤的来临,昭示回忆,或不可预知的结局。我想我应该更加懂得原谅,原谅大雪覆盖的真相,原谅非正常的死亡,或逃之夭夭的宣告;在原谅别人的时候,首先应该学会原谅自己。烛光熄灭前,我唱了一支歌送给穗良,祝他生日快乐。
我想起十天前的那个下午,我穿上迷彩服,带上厚厚的一叠稿纸,从财务室预支了二千块钱,提着简单的洗漱工具和换洗衣服,一个人走出领导的办公室。刚走几步,他的门嘎吱一声被风关上了。闷雷般的一声巨响,把哨所和哨兵的期待交给了我——那个下午,我的心犹如一扇门挡不住风的侵蚀。
云濡在一个起风的黄昏从我这里拿走小说后,几天也没出门。我猜测他消失在小说里了。那是一部长篇小说,是我这回出门带在身边唯一的书。
我每天除了在哨所构思哨所和哨兵,就是同他们聊天和散步。好像在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年代,就只剩下这样的事情可做了。老鼠和猫的故事不可能天天都上演,哨所也不能单靠一些笑声就能让一个写作者成熟,更不能让一个哨兵成熟,哨所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我和穗良、云濡共同栖身的地方竟然成了我背着他俩追问烛光的背景?而我是可以在一定时间之后离开哨所的,至少可以回到有人烟的地方,可他们还要继续守在这里,他们是在守候战争吗?没有谁回答我。在许多风雪吹灭烛光的夜晚,我已经听云濡说起过穗良的来历:中学毕业之后,他从南昌的一个小村庄里跑出来,到北京投奔舅舅。舅舅是军队里的职工,认识那些部队当官的,也深知穗良从小就喜欢部队,喜欢打仗,于是设法将他这送那送,最终送到了西藏。可到部队三年了,也没打过一次仗,于是穗良好不容易犯个低级错误才从连队来到了哨所。他以为哨所就是战场,至少它离战争更近了,毕竟哨所的位置在敌我交界线上,但他没有发现敌人。他发现的只是敌国职业军人朝他友好地笑,有时还甩一支香烟给他。他们的牙齿在阳光下比他的要白得多,看得出他们的表情也比他开心,只是脸像抹了油似的黑。刚到时他拼命地给人讲哨所真新鲜,不到半个月,他又对人家说不如连队新鲜了。但他很快通过敌国军人的表情学会了自己安慰自己。这样的地方,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地方,既然来了就得适应下来,除了适应你别无选择。
连队有连队的好处,哨所有哨所的好处。不新鲜的生活,转瞬便是半年。
半年里,穗良没离开过哨所半天,也没有人上哨所来看过他半天。每隔半个月,会有藏族老阿妈给他捎来可以随时放在嘴里嚼的饼干和饮不尽的啤酒——那可是他提前付款托老阿妈从遥远的喜玛拉雅山侧带来的尼泊尔啤酒。每隔两月半,那些看不见的战友还会为他返还借用后积存的津贴。在我来之前,他已经身无分文了。原因据说是连队的战友都参加演习去了,没时间管他在哨所的事情。如此,他和云濡的内心荒芜了好长时间。但是,他们的一堆问题却不可能指望我给出答案。譬如,找婆娘的事情。云濡是老兵,在连队时,他谈过一个驻地的姑娘,可听说刚到哨所不久,姑娘就被人家谈走了。穗良实际年龄虽然年轻,可他看上去差不多也像一个小老头了,脸上长了“红二团”,再多的洗面奶也洗不尽那两个油漆般的烙印,那是西藏的馈赠?还是高原的施舍?它们早已进入他的血液。他的头发一天比一天细,一天比一天少。我想了又想,他是否早该为务虚的内心种下一颗爱的种子了?穗良,你知道吗?有了这种寄托,你在哨所是可以延缓一些衰老的。可穗良和云濡如今都像两棵空心的草。哨所的天空也常常处于空的状态。空对空的生活,还能指望什么呢?
一个人坐在窗前,我总是两眼苍茫。如果那场雪崩,他们仨都没有死,也许情形会好些,至少穗良不会在大雪里产生如此疼痛的记忆,至少还有人围着他过个像样的生日。
“我明白了,终于明白了。”云濡喊出这句话的时候,风终于安静了,仿佛安静了三天三夜,哨所什么新鲜的事也没发生。云濡终于看完了《沧浪之水》,那是他到哨所接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前他从没有看书的习惯。在书里,他找到了自己在连队时曾有过的心态。也就是说,他明白了自己的弱点,只有明天才能分晓。“明白”对于一个哨兵究竟是坏?是好?对于云濡,明天是可怕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认清并且认同自己的弱点。当雪风再次破门而入的时候,穗良和云濡已经沉睡。哨所之外的许多人和事都已沉睡。面对烛光,我一直是醒着的。这是一种矛盾的活法,让一个人继续沉睡容易,让一个人突然醒来却很难,谁能叫醒沉睡中的人?我无法想到一本书可以叫醒云濡。他在消雪时分呼喊:“我明白了,终于明白了。”可是,我的弟兄云濡,你真的明白了吗?“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关闭书页,世界常常是睡着的,看上去比水更平静,一打开就看见了世界在发疯,雅鲁藏布江在咆哮。我其实没抱什么期望,对于这类小说,云濡看不懂更好,下一个黄昏,当我们把夕阳追赶至墓碑,我会突然问他:“你到底明白了什么?”
云濡说:“我明白了一个年轻人要怎么去讨好领导才能当上领导,其实我们部队的许多军官都比主人公聪明,都知道在关紧时刻该怎么做?那些事儿还用人教吗?从这一点来看,小说创作的出发点是失败的,可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我们部队,又有几人能写出来呢?穿军装的作家们是不是觉得,那样的事写出来没什么指导意义?战士们的军装还没洗白,什么事都看会了。”
过去我总把自己写不出好作品归结为阳光下面无新事,但我没想到一个从不读小说的战士会有这般出人意料的见地,他让我在阳光背后恍然明白:越是暗地里沉默的,越在阳光下清醒,我唯一能做的是离他们近些,再近一些。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哨所是个死囚笼。它能够给人什么?许多时候,哨兵只能面对墙壁上投下的影子,想一想自己的过往。有时,它给你的只有杂草般的一堆烂思想,最终,它不能给你的是外界所有的消息。它,让你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成为自己的遥远,即使这样,它照样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战争伪装的工具,里面有望远镜、迷彩网、来福枪、记录本、圆珠笔、铁钎、水壶、干粮、罐头、电话(线路常被风雪中断),它照样可以成为许多军人的乌托邦或理想国;因为许多军人的一生也没有机会抵达哨所,他们把驻守在里面的人想象得比雪莲花还圣洁,他们多数时候只能让梦去抵达。对于哨所,他们听惯了“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地方”。这句话背后潜藏了多少集体主义下滋生的英雄情结呀。
穗良又开始了他的歌唱。我怀疑,这些日子以来,他已经唱完了自己会唱的所有的歌。无论是在山下背冰,还是在树下逗猫玩耍,他都张开嘴巴唱个不停,但他多数唱的不是军歌,而是几近于《大悲咒》的那种调子。我惊异于他居然能在这样的环境把这样的佛教歌曲唱得像《两只蝴蝶》!他的内心真的开始迷乱了。又一晚,当鸟群从天边黑压压飞过,雪朵,开始以跳伞的姿势降落,我再次被穗良走调的《大悲咒》惊醒。打开窗户,借着雪光,看见他正披着一身雪花紧紧地怀抱着那个心爱的同伴——那只笨猫,连同那些无字的歌词就像一块块玛尼石从他的胸腔里滚了出来,但它们分明又像无影剑刺破了白白的雪光,看上去,竟似一个雪中飞仙。当云濡拉着他赶快回屋睡觉时,他却挣脱说,他看见了磊磊、鑫鑫、小辉,他们没有死,他们在山下等他,他睡不着,他要去见见他们。
我突然感到一阵厌恶,我厌恶地捶打着自身:如果我能哭,我就会哭着告诉穗良,其实,我们都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只是你比我更清醒,你清醒地说出来了,我一直没有说出,这些年我活得太含蓄,但并非糊涂。但是在一天一枯荣的哨所中,当我想起今天的愁云和明天的往事,而你已开始展开了歌喉,我为什么就不能告诉你,其实,从接到上级命令到抵达哨所的今天,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即使从机关逃到哨所,我也还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面对哨所和哨兵的命题剧目,无非是排山倒海的痴心与妄想,还有怀疑与审视,我无法用笔管吸干他们比海水更多的孤独。
而那三个倒下的英雄,偏偏在我思绪泛黄的时候从雪地里伸出手来,他们的样子无泪无悔,满脸金色的阳光,他们的背后是千军万马……我呆呆地望着他们,许久之后,才急急忙忙地问了一句,你们是要我手指上的香烟?还是要我桌子上的咖啡?
“我们什么也不要,如果你要离开哨所,我们也不阻拦你,但请留下你的孤独,请相信我们并没有死,我们都是喜玛拉雅的王子,我们再也不会离开这里了。”这个声音每次都在我熟睡后的哨所响起,它们随雪风来,又随雪风去,直到我不再当它是梦。也就是说,在我离开哨所之后,我接受了一个梦的诞生,并且这个梦还将跟随我走过冰冷的雪坡与墓碑。
在我眼前,或有一片沧海,或有一座哨所,清醒者的肉身与心魄只能任由其包裹与浮沉,即使每一个哨兵都拥有一双翅膀,但他们也飞不过那片森林禁锢的天空。他们到底该怎么办?罗曼·罗兰说,失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得祝福灾难,我们是灾难之子。海德格尔说,人仅有一个世界是不够的。丘吉尔说,最容易通向惨败之路的莫过于模仿以往英雄们的计划,把它用于新的情况中。黑格尔说,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它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泰戈尔说,错误经不起失败,但是真理却不怕失败。唯有他和他,我的哨所兄弟——穗良和云濡,在通往理想的独木桥上,不模仿别人,先粉碎自己。他们在一个远离外部思想的地方获取了来自内心思想的独立拯救。穗良说:“战士到部队是来打仗的!”这就导致了他所犯的那个低级错误,全国人民都解放了,哪里还有仗打呢?于是连队一纸命令把他下放到了哨所,让他自己和自己去打仗。云濡说:“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就是这样,即使在风雪如刀的后半夜,他也可能在用小说抵挡哨所的寒冷与寂寞,厚厚的书页包裹了他明天的梦呓,他祈求过太多,但他拒绝了重复自己。他是我哨所永远的小弟兄,只有他会对我说:“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我说,明白了,就什么都不要说了,来来来,我要我们在一起,大声地喊出来,因为我们是同一条雪线上相遇的小弟兄。虽然我们还未能完全相知。
但风和雪全都知道——
一个以笔为旗的军人接到命令,前往与敌国交界的我军哨所创作哨兵的剧目,(仿若是为了捉拿敌人),殊不料,终其一个半月的生活,他也没见到哨兵惊天动地的感人故事,(就像没有见到敌人是什么样子),在没有故事发生的哨所(如同没有敌人的战场上),他能做些什么呢?他只好像哨兵一样迷恋上了枯荣,并且一再告诫自己,要相信说出“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人是具有崇高信仰的战士。当他最终明白所有的战士都有崇高信仰的时候,年华已老去,雪风夺走了他头顶的大棉帽,连同几根雪染之后的残卷青丝,飘向天外云霄,直至最后被那些先于他脱下戎装的战士如此挥手嘲笑:“他和我们一样,都没遇到敌人,也没有遇到战争,来不及成为英雄,他们却在西藏长大了。”
凌仕江,作家,现居成都。主要著作有诗集《唱兵歌的鸟》、散文集《你知道西藏的天有多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