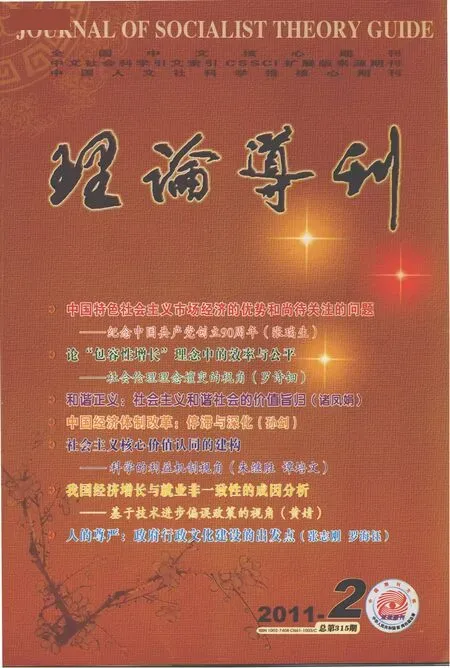政策科学:范式革命、假设转换与关系框架
2011-12-24刘小年
刘小年
(东莞理工学院,广东东莞523808)
政策科学:范式革命、假设转换与关系框架
刘小年
(东莞理工学院,广东东莞523808)
政策科学在创立后形成了一种以科学性为特征的范式,这种范式将政策活动解读成一种解决政策问题的理性程序。因而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成为众矢之的,许多学者投身到寻找替代理论的潮流中,由此开启了当前政策科学范式革命的学术丛林景观。本文从突破这种学术丛林的基本假设入手,以关系人假设代替经济人假设,构建了一个政策过程的关系框架,力图对政策科学理论发展的危机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回应。
政策科学;范式革命;假设转换;学术从林;关系框架
政策科学的发展正处于一种范式革命的时期。因此,总结主流理论演变的趋势,并根据中国的文化与实践来尝试理论创新,对于历经20年左右消化引进工作后追求本土化的中国政策学界来说,无疑是一条重要的学术崛起之路。
一、政策科学范式革命的提出
1.政策科学范式的形成。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等提出了政策科学建构的设想,开启了现代政策科学建设时期。经过70年代德罗尔的发展,形成了学术界所称道的拉斯韦尔——德罗尔的科学传统,[1]即主导政策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
这个范式的基本内容:一是视政策活动为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如拉斯韦尔在开创政策过程研究传统时就主张它有七个功能环节,即:情报、推动、制订、执行、适应、终结和评价。[2]550提出这些功能环节的背景是为了从理论上更全面地探索信息革命等急剧社会变化给整个公民秩序系统带来的适应问题。[2]551二是追求政策活动的科学性或理性。如德罗尔继拉斯韦尔提供的政策模型就是一个最佳决策模型,包括总的政策制定、通常意义上的政策制定与政策再决定等三个阶段。[3]对政策过程的科学性,拉斯韦尔也说:政策分析与法律、法理学、政治理论、哲学等相连时,显示了史无前例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并说,处心积虑地试图澄清和推进这一联系的努力是政策科学方法。[2]566
2.政策科学范式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存在问题,如萨巴蒂尔指出了它的六个方面的弱点,即: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因果模型,没有为经验假设检验提供一个明确的基础,在构建一系列的阶段时存在描述不严谨的问题,受到条文主义与自上而下关注等困扰,忽视了政府间关系系统的概念,没有能够为整合政策分析和贯穿公共政策过程始终的政策取向研究等的作用提供一个好的工具等。[4]30-31二是在应用上存在严重局限。曾任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长的罗伯特·丹哈特教授指出了现有政策范式支配下的政策分析的三个问题:它助长了对现有目标不加批判的接受;对客观性的关注使人们只考虑能对其方法本身进行分析的题目;力图通过强迫实践来回应理论而不是相反的方式解决理论—实践二分法的问题。[5]
3.对待政策科学范式问题的态度。政策科学范式在1950-1970年代形成后,到80年代末期便不断遭到学术界的批评。最早质疑这种传统智慧的是罗伯特·纳卡鲁马。他问道,理性政策过程模式的广泛应用是否意味着政策各阶段都近乎像它们的支持者们所提出的概念界定那样精确,如果不是,他就宣称,过程模式不能被用作某种范式。[4]30萨巴蒂尔更是敏锐地提出,“阶段启发法的积极作用很有限,有必要寻求更好的理论性框架取而代之。”[4]10
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政策科学理论的重建活动,试图以新的理论取代理性政策过程的地位。可以说,政策科学已经进入范式革命的时代,一方面理性政策过程的地位面临被替代的命运,一方面也形成了新的学术发展的空间。
二、当前范式革命的学术丛林
1.丛林景观。主要有两种表现,其一是在政策科学主流理论即科学范式受到日益广泛的质疑与批评后,涌现了许多新的理论。根据萨巴蒂尔的统计,[4]12-18在当前政策科学理论竞赛中占据有利位置的是以下六种新框架,即:制度性的理性选择;多源流分析框架;间断——平衡框架;支持联盟框架;政策传播框架;大规模比较研究方法的因果漏斗框架和其它框架。此外,还有四种一度流行但当前不是很活跃的政策科学模型,即:权力竞技场,文化理论,建构主义者框架以及政策领域框架等。其二,在政策科学饱受批评的过程中涌现的各种新式理论并没有一种形成具有政策主流理论即政策科学范式的地位,在政策科学的研究与应用中,理性的过程理论还是运用最广泛的。国内著名政策学者陈振明指出:“迄今为止,阶段途径仍然是一种整合政策科学知识特别是政策过程知识的方便框架,其他途径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取代阶段途径而成为新的支配性‘范式’。”[1]63美国著名政策学家彼得·德利翁在《政策过程的阶段性方法:何去何从》一文中也说,在“可供选择的模型中,没有一项在根本质疑或甚至强烈要求放弃政策阶段框架”。[4]40他还说,自己对萨巴蒂尔与简金斯·史密斯“所支持的联盟框架是否冲破了由政策过程取向产生的范式有疑问”。[4]34
2.丛林法则:旧瓶装新酒。这是一种变革的方式,但是由于使用的是旧瓶,也会面临变革不彻底的问题。这可以直接解释前面提到的很多新的替代框架,为什么没有一家取代已有的理性模型,而是以一种学术丛林的方式存在。所谓旧瓶装新酒,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些新的模型,仍然在理性政策过程这种科学范式划定的解决政策问题的框架内讨论问题。由此,使得这些雄心勃勃的理论建构,到头来只是对主流理论形成了一种修补功能。
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以前述六种影响较大的政策科学理论新框架为例,分析如下:制度性的理性选择框架,主要是发现了解决问题的政策过程中作为一种理性的装置——制度的层次结构及其作用;约翰·金顿的多源流框架,则是研究解决公共问题的公共政策是怎样做出或到来的。他的基本发现是由于公共政策问题流、政治流与政策流三者交汇,政策之窗的机制开启,公共政策的程序才开始运转;间断——平衡框架,指出了问题取向的政策过程存在连续性与中断性相结合的特点;支持联盟框架,深化了理性政策过程理论关于政策方案形成的子系统的认识;政策传播框架,从政策创新的角度,指出解决问题的政策过程存在政策信息传播机制的重要作用;大规模比较方法的模型,指出了理性的问题导向政策过程中社会经济条件、公共舆论和政治组织的多样性。
3.丛林人:“经济人”。政策科学范式革命陷入学术丛林的困境,在想要替代的范式那种问题导向的框架内打转转。这与这些尝试的基本人性假设没有转换有关。由于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研究社会现象必须以人性假设为基础。不转换研究假设,就难以突破已有的学术框架。
作为范式的政策过程理论的人性假设就是具有深厚西方个人主义色彩的“经济人”假设,正是它形成了问题导向的理性政策过程范式。正如西蒙指出的,在传统决策领域活跃的是“经济人”或理性的“经济人”。这种“经济人”具有完全的认识复杂政策问题做出最佳决策并追求最佳结果的能力。[6]根据这种理论假设,政府是理性的“经济人”——由公民授权组建的、以解决在公民之间发生的而公民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获得满意解决的公共问题即公共政策问题为目标的组织。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必然是回应性的、依靠科学理性解决与公民相关的社会问题的过程。政策过程理论的完善或替代,也只能在这种问题导向的模式下进行,并具体通过对政策过程的问题界定、方案形成、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诸阶段的重新研究与科学发现来实现。
三、走出学术丛林的一种选择:政策关系框架
1.以“关系人”“取代”“经济人”。鉴于在新的政策科学理论框架的建构中,学术界未能走出“经济人”假设的视野,因而在问题取向的经典理性政策过程范式内左冲右突,最终困于学术丛林的现实,这里,根据马克思的开创性思想,提出一个“关系人”的人性假设,并以之为基础,进行政策科学、政策过程理论框架的新建设,以期对政策科学发展中的范式危机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回应。
在“经济人”的理论框架内,人都是全能理性自足的自由个人,只是为了协调这种自主个人之间的矛盾,才需要政府的设置与公共政策的展开。[7]所以,政策只能在公共问题域内发生。不言而喻,这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假设。现实的人,并不是这样的。按照马克思的见解,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8]但这种本性并不能自我实现,一方面需要面向自然进行生产,以取得维持生存的物质;[9]67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活动又必须以社会的形式进行,以克服个体相对自然力的不足。[10]所以,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只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9]56是在人与自然、社会三维矛盾中存在与变化的。因此,人是关系人。作为关系人,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立足需要的生存体,是以社会实践形式存在的。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11]
在这种新的人性假设的基础上,就可以进行走出当前政策科学范式革命学术丛林的理论创新尝试了。
2.“关系人”眼里的政策过程。(1)本质。既然人是一种现实的关系生存体,因此,公共政策活动的本质也只能是一种人的现实生活的一种关系——公共管理关系的写照。这种现实的关系——公共管理就是政府与社会在一定环境下互动,以应对由于人的生存需要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关系。
这样界定公共政策,在坚持政策的活动或过程特征的前提下,突破了现有政策科学理论对政策过程起点的认识,回归人最后的生存需要,为新的政策过程的演绎奠定了基础。同时,从互动的角度阐述政策活动,也回避了作为政策科学范式的主要理论框架的政策系统论忽视政府对政策过程的输入问题。[12]另一方面,将公共政策活动的本质界定为一定环境下的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既真实反映了政策过程的条件性,又内置了政策活动发生的历史背景。即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人的关系生存条件的变化,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的剩余产品的出现与阶级的形成以及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导致政治现象的产生,因而公共政策也首次在历史上亮相。这样,就突破了现有政策理论那种就事论事的问题取向局限,具有宏观性与历史性。
由此也可知,作为有条件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公共政策过程,也包括了复杂的政府内部的互动关系、社会内部互动关系以及在此之上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
此外,由于这里对政策本质的理解是建立在现实的人的基础上的,因而对政策过程的理解也就突破了经典的理性过程的一元科学范式或认识与心智模式的束缚,可以从人的行为的角度全面地讨论政策过程的机制。由于人的现实生活不光表现为一种有意识的活动,还首先是一种人的需要——利益的满足活动,也是人的行为变化的过程,是人的生存关系调节与扩展的过程,因此,关系的政策过程框架主张,政策活动具有五重机制,即认识机制、利益机制、权力或关系机制、制度及政策机制、行为或事件机制,是这五种过程互动与变化的统一。
(2)过程。作为人的关系生存的一种反映,政策过程在前述五大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一种三个阶段九个环节的、渐变与突变有机结合的复杂场景。第一个阶段是表达——整合阶段。一方面,政策主体认识到现有政策过程影响了自我或他人、甚至整个社会的需要的实现,向利益相关方表达;另一方面相关方面进行整合。具体的表达可以是个人向他人或组织提出、组织向别的组织提出,也可以是社会包括个人与组织与政府的互动表达或者在政府内部表达。表达的内容可以是社会问题,也可以是政府问题。在这里,表达为关系政策过程的第一个环节,整合为第二个环节。整合由单一社会组织、政府或个体进行,是利益相关方的一种反应。其结果可以是一种积极的肯定表达,也可能是消极的否定表达。在肯定状态下,利益相关方在既有基本政策框架下进行调适,这也就是关系政策过程的第三个环节;在否定状态下,则表达的一方要进行一个继续行动的综合成本收益计算,如无利可图,则会中断已有行动,此为政策过程的第四个环节。反之,如果经过分析,后续行动存在利润,则政策过程进入第二个阶段。以上论述表明,第一阶段,政策环境基本上是以一种政策场域的形式起作用的。
第二个阶段,即压力——回应阶段。此时,政策主体继续逐利行为,常常越过组织内部整合的边界,形成政府与社会、环境全面互动的态势。其形式,一是从社会向政府求援,二是政府向社会提要求,三是社会向上级政府反映,四是政府部门越级要求自我关系协调,五是环境中的第三方主动介入或传播信息或表达意愿或提供资源等。这些都形成了一种现实的政策压力,是为关系政策过程的第五个环节。由此,感受到压力的一方也要作出相应的响应,即回应,是为关系政策过程的第六个环节。回应,与前面的整合的后果一样,可以是肯定的,因而政策过程一般又会进入到第三个环节,即调适,包括政策执行、关系协调,甚至局部政策变通。回应的结果也可能是否定的,在此情形下,如继续行动没有利润,通常也会由相关利益诉求方中断已有的活动,即转入前面讲过的第四个环节。反之,如仍然存在利润,则政策过程会向后延伸,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即区隔——变迁阶段。由于第二个阶段回应无力,政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际进入到一个僵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政策主体的策略,就是区隔,包括将政策主体从相关的政策问题情境中抽离出来,或者进入一种体制外活动状态。在利润的诱惑下,人们可能采取越轨行为甚至是过激维权,政府在压力下也可能重组或者采取高压姿态控制相关社会主体。这也就是关系政策过程的第七个环节。区隔之下,可能的选项包括,带妥协或让步性质的调适与中断,也可能是一种冲突后在法律上阻断政策过程的情形,如当事人的死亡或刑拘等,就形成了关系政策过程的第八个环节,即终止。区隔之下,由于社会越轨的加剧及政府可能的重组等行动,政策过程发展为第九个环节,即变迁,可以包括基本政策与体制的变化。
在上述过程中,一方面政府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实现了变化,另一方面也推动人们的需要的满足与生存状态的改观。这样,又为新政策过程提供了动力。
(3)方法。前述关系政策框架,主张政策过程是由五种关系机制推动的。因此,在政策分析上,应该进行政策关系的分析。具体有如下方法:一是进行需要与政策阶段的分析,通过调查,了解社会需要,了解现实的政策过程,分析这种过程是否是必要的,是否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同时,进行政策活动的成本收益分析,提升政策过程的效率。二是进行关系与权力的分析,从政府、社会的关系角度来认识政策中的权力分配与变动情况,把握政策进程,具体可采取民意调查等方式。三是政策与制度的分析,研究政策周期与政策变迁问题。四是认知与行为分析,探讨政策过程中相关主体的心理与选择。五是事件与环境分析,研究政策过程的内外条件,通权达变。
总之,政策科学的发展正处于一种范式革命的学术丛林状态。走出丛林生存,需要变更其基本假设。以马克思有关人的关系生存的论述为源头,探索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策过程的关系框架,应该说是一个方向。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5.
[2][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策分析研究:情报与评价功能[M]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M].竺乾威,周琪,胡君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韩]吴锡泓,金荣枰.政策学的主要理论[M].金东日,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13-220.
[4][美]保罗·A·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M].彭宗超,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
[5][美]罗伯特·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教程[M].项龙,刘俊生,译.华夏出版社,2002:107-108.
[6][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M].杨砾,韩春立,徐立,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29-30.
[7][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9-6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1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12][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37.
D035
A
1002-7408(2011)02-0058-03
东莞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策过程研究:以东莞农民工政策为例”(2010RQ18)的阶段性成果。
刘小年(1971-),男,湖南岳阳人,东莞理工学院副教授,博士,兼任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南京大学与中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责任编辑:王润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