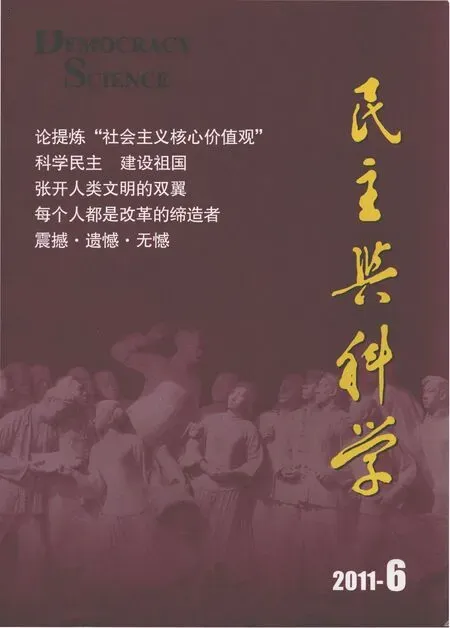以正义构筑道德大厦
2011-12-23■蔡伟
■蔡 伟
近年来,关于道德重建的讨论和报道铺天盖地,连高层也发出“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的感叹。种种道德沦落的事件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事实上,我们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强调道德建设。比如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德便放在首位,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种种举措,在社会大张旗鼓地开展道德教育活动。然而,从现实来看,收效甚微。道德滑坡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是价值信仰危机和社会制度危机,比如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拜金主义,越演越烈渗透于社会各个部门和行业的贪污腐败,公权力对私权的侵犯,“良法”没法得到有效的尊重和执行,投机主义等等。这些形成一个很坏的示范效应,而使得恶人和恶行肆无忌惮,而老实人、好人只能吃亏,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和价值信仰。
道德的现代核心:正义
道德是适用于全族群、对该群体的内在价值和外在生活具有普适性的精神要求。不同人,不同时代对道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要求。
中国历史上对道德有过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三德(礼、义、仁)、五常(仁、义、礼、智、信)等的论述。根据周辅成先生的考证,古代的“义”是指“公正”,“义行”就是“公正行为”。然而,这种“义”与现代社会具有普适性的正义要求有很大的距离。在传统的农耕时代,“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正义的要求和适用在不同人群中也常有不同。于是,我国传统上的道德观,更多的体现为私德。梁启超把中国古代的道德称为“私德”,而把现代道德命名为“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点”。
无疑,人们在不同的时期和社会有不同的道德观,但无论何种道德观它总是要维护某种正当性的价值外观,这种正当性便体现为正义,无论它实质上是否是真正的正义或者是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正义。正义是一种社会道德准则和人们的道德行为规范,自从是非观念产生以来,道德便有了公平公正等正义的理念,虽然这一理念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理解;比如正义有时仅仅在某个特定群体内有效,甚至有时有着根本的对立,但是它却一直引领着相应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发展。
正义的精神内核和核心价值,使得某些道德戒律能够上升成为法律,并得到国家暴力机器背后的支持。当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是以契约为中心连接起来的,每个个体都需要和其他社会个体互通有无,交换产品或者服务,于是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大,每个人的行为也容易影响到其他个体。以传统血缘为纽带的道德行为规范不足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为正义提供了基础。正如亚当·斯密所言,仁爱是为邻里而存在的,它适用的是熟人;而正义则可以适用于陌生人;仁爱涉及私人关怀,是具体行为问题,而正义则要处理的是公众利益问题、普遍法则问题;而仁爱对社会的存在来说不如正义那样重要;以正义为核心的现代道德,能把人们引向合理追逐自身欲望与利益的自由。
现代道德是社会性的道德,是以正义为中心的。(陈赟)而正义正是法律的核心概念和价值追求。《尤士丁尼法学概论》指出:“正义是让每个人各得其所,这样一种始终不变的意图……法律的戒规是:诚实地生活,不加害于他人,让每个人各得其所。”罗尔斯《正义论》也强调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者废除。”于是,在现代,法律与道德的核心枢纽为正义,正义也就成为现代道德要求的核心价值。
不义之下苍白的道德
在社会的调控系统中,道德、法律、文化等各自发挥着它们的作用。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线,如果法律没有实现正义,那么一切的道德要求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而社会正义则涉及法律、分配、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道德提倡“善”,我们的道德教育通常要求无私。然而“社会将公正而不是无私作为它的最高的道德理想,它的目标是为所有人寻找机会的均等”。(尼布尔)
在我国现实中,种种原因之下,不正义广泛存在着,正在不断侵蚀着这个社会的价值基础。比如在经济上,国家在资源分配上倾重于城市,利用产品差价、户籍制度等剥夺农民的利益,使得农村长期以来发展大大滞后于城市;在政治生活领域,农民的声音缺失,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难以有效得到解决;尤其是近来的违法拆迁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种种的不正义,很多还由法律法规直接确定下来,成为法定的不正义。在公法领域,最为典型的就是历史上农民的选举权不均等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曾经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这种1/4选举权的规定深为学界所诟病。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选举法的决定,最终我国农村和城市每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规定为1:1,在规定上实现了选举的正义。
另外,同样受社会关注的还有“同命不同价”的问题。我国法院确定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通过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的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第二十九条还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依据这一司法解释,农民在人身损害赔偿中获得赔偿数额远远少于城镇居民。
面对这种规定在实践和法理中的困境,不少地方在它的适用上都进一步进行完善。如2006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安全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农村受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有正当生活来源的,可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数额。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7条也作出了新的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但这仅适用于同一侵权行为的情形。国务院于2010年12月20日修改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这一规定统一了各地的工亡补助金标准,在全国实现了“同命同价”,为法律的正义迈进了一大步。
对于法律正义,虽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它却是可感知的,在法律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处于弱势、没有话语权的农民能认同这种规定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要使一个人因为社会规范的合理性而遵从它,关键是要向他表明什么是公正”。(约翰·威尔逊)如果不能,在这种赤裸裸的不正义之前,一切的道德说理都是如此的苍白无力。
法律仅仅是社会的一种治理机制,法律的不公正直接影响了法律的权威,使得公民之间难以形成现代契约社会所必需的信任的纽带。正如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春晨所言:“整个社会弥漫着互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在经济领域,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不信任;在政治领域,公众对官员和政策效力不信任;在法律领域,公众对司法不信任。最后这些不信任扩展为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不信任。这样一来,一些基于信任的道德行为,在有些人那里就成了不太可能的事——小悦悦很可能就是这样被漠视的。”
虽然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很多方面在趋向正义,然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正义重建道德
正义并不是平均主义,它是以机会平等为目标的。它要求相同的情况得到相同的对待,公民不论其出生、地位、财富、性别、种族和宗教信仰等情况,能够有平等的机会获得社会和自然资源,不因为家庭等外部因素而失去本应该得到的机会。在政治领域,平等的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经济领域,相应的竞争领域能够向社会公众公平的开放;在社会保障领域,公民的社会保障条件是一致的,不因权位而享有特权;在文化教育领域,每个公民都同等享有同等的受教育和利用文化资源的权利等等。
一旦社会的法律制度对权利、义务、资源等分配不均衡,将为社会不公提供孳生和蔓延的土壤。在一个黑白颠倒、道德沦丧的社会中,个体也难以独善其身,而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中,社会机制本身就能去浊扬清,个体的正义感也随之增强。正义的实现,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意识,还有助于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
正是我国的制度正义远远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导致它非但没能给良性的道德发展提供指引,反而破坏了当代契约社会陌生人之间最应该具有的信任,导致道德的滑坡。“见死不救”的冷漠传染病可怕,“见义勇为”以后英雄流血又流泪更是令人恐惧,因为它扼杀了本来就很脆弱的为善之心。姑且不论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等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隐情和它们的法律逻辑,这些都给社会公众强烈的暗示:小心见义勇为会惹火烧身。在趋利避害的本性驱动下,见义勇为在此背景下难上加难。近期报道的数起市民花费不少时间精力和金钱举报税务违法行为时,却只得到几元或者十几元的奖励,还要举报者申请行政复议和起诉,其中一个案件法院还判令举报人将其获得的1.5元巨奖中的0.5元返还国税局。国家机关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行为和规定实在扼杀了公民与种种“恶”作斗争的“善”心。
因此,与其空洞的道德说教,还不如尽力修补社会的不公之处,并且用制度来引导人们行善。完善每个人的正当权利能够得到保障的制度规范体系,使其能有效调节人的善恶行为,保护人的“正当的行为”,惩罚人的“失当的行为”,提倡和鼓励人的“崇高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完善制度保护见义勇为者,才能让更多的人敢于挺身而出,就像很多国家通过各种制度保护证人一样,让举证犯罪的人无后顾之忧;还可以考虑建立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民事损害时的责任豁免或者自身造成损害时向获利方求偿的法律制度;再比如建立捡获失物上交的奖励制度,对拾金不昧者,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奖励,没法找到失主时,奖励幅度更大,或者直接将全部失物都作为奖励……此等良法将更能引导人们行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迅猛,但同时价值观的迷失、道德失范在很多领域都存在。“在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建设应该与法律规范相协调,其协调的纽带是公正。而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法制,理所当然被视为社会美德的生长点”。正义正是填补道德空白的最主要基石,唯有以正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道德体系才能经风历雨而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