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黑势力与乡村治理内卷化①
2011-12-21耿羽
耿 羽
灰黑势力与乡村治理内卷化①
耿 羽
后税费时代,国家以各种形式向乡村分配了大量的资源,但是资源的很大一部分被基层政权和灰黑势力以合谋的形式截取,资源分配没有引起相应的治理效益,反而出现了新一轮的基层治理“内卷化”。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出现,和灰黑势力、基层政权以及村庄资源分布三者的转变密切相关。要解决基层治理“内卷化”的问题,需要改进基层政府的政权性质。
灰黑势力;基层政权;内卷化;治理;税费改革
村庄的生活图景和政治图景,是村庄中各种权力进行错综复杂的博弈和角逐的结果。当前村庄中的各种权力,蕴含有暴力性的,主要有基层政权和灰黑势力②所谓乡村的灰黑势力,可以借用吴毅的相关定义:这些人 (尤其是那些核心人物)往往有犯罪前科,坐过牢,而现在也仍然在有意无意地借助团伙的力量,在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涉入地方经济与社会生活。详见吴毅:《小镇喧嚣》,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 283页。两种,如贺雪峰所言,灰黑势力与正式制度,构成了乡村治理一阴一阳的两个基础。[1]新中国成立后,村庄中的恶霸和流氓在国家政权的强力打压下销声匿迹,这也基本解决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灰黑势力在村庄中有所抬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灰黑势力的能量虽然有所增长,基层政府对灰黑势力的定性却并未改变,在基层治理中,基层政权大多数时候都是以“一正一邪”来定义自我与灰黑势力的形象的。可是,我们发现,近期的基层治理中,基层政权正逐步放弃自己的政治原则性,基层政权和灰黑势力这两种原本具有相互对抗性的组织愈来愈有合谋和协作的倾向,基层治理正出现新一轮的“内卷化”问题。即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却无法带来治理效果的增长。这种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外在表现、内在逻辑以及其和以前的治理“内卷化”有何不同,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一、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外在表现
我们将以洋镇 Y村来展现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大致状况。洋镇面积 150平方千米,人口 4万,辖 1个居委会和 17个行政村。Y村为洋镇的镇郊村,全村 2 500余人,19个村民小组,耕地 3 790亩 (1亩约等于0.067公顷,本刊注),作物种植以一季水稻为主,兼以玉米等。我们在当地调查时,总是听调查对象说到“王三 ”、“王四 ”、“胡三 ”等“道上的人 ”,灰黑势力人数之多及其在乡村中影响之大可见一斑。我们在调查中搜集到了不少有关当地灰黑势力的案例,其中“王四”围绕村边新修公路而四处强取豪夺的事例 (地点图示见图 1),能够比较细致而清晰地展现出当地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基本样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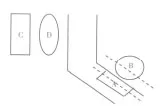
图1
2009年县政府修县级公路的时候,Y村的一段路本来可以笔直地通过,但洋镇政府故意绕了一个弯修,目的是把路边的一块地给顺便征过来,以便留着以后开发房地产。镇政府想“空手套白狼”,用县里的钱来征得一片自己的开发地,但如意算盘在实践中却碰到了困难——在那片地居住的五户百姓不愿意被征地。镇政府在征地中遇到了僵局,镇里领导找来王四,让他去解决,王四上门进行了“劝说”以后,五户人家只得答应搬迁。王四这样的灰黑势力登门,起初是非常文明的,他们常提着水果去老百姓家,说“你给我个面子嘛!”一般老百姓都会顺水推舟,赶快答应,如果不答应,王四这种“大哥”级的人物,就会到镇上找一些“小弟”,再去那家,第二次去就没那么客气了,会直接进行赤裸裸的威胁。
为了安置这五户人家,镇里答应在图中 A地给他们划一块地建房。A地原为 Y村的老村委会,有 10间房子,2007年,由于镇里要修一条新路 (镇里把道路的修建工程也交由了王四负责),老村委会就被拆除了。新路修好后,A地本来是不适宜再建房子的,因为影响交通。但是,镇里还是变通性地在老村委会往后 3米的地方盖了新的房子,新房子的一半地方给了那五户人家作为补偿,而镇里为了感谢王四在征地方面的帮助,就把另一半地方给了王四让其建房开发 (最后赚了 40万)。新房子地处 A地和 B地之间 (图中以虚线表示),而 B地几年前就被王四承包下来了,镇里很感谢王四的配合,为了对王四承包的 B地进行补偿,镇里把王四关于九联水库的承包期 (原本 20年)又免费延长了 10年。该水库是镇里的,面积为 0.9平方千米,水库效益一年有 30万~50万。
地处 A地的 Y村老村委会被拆,镇里说给村里一块新的地方作为村委会,也就是图中的 C地,新村委会需要有一条通道从D地经过,但 D地已经在几年前被王四从村民手上转包过来,村里为通道的事开始和王四协商。由于 C这片地地段不错,王四又想拿走,他和村干部商量,说这片地后面盖 5间做村委会,前面盖 5间房子,送给老书记 2间,送给村长 2间,另留 1间作为通道。老书记没有答应,王四又拿出第二套方案,说把 C地整片给他,他给村委会另找一片好地方,这也被老书记拒绝了,老书记顶住压力,最后终于为新村委会争取到了一条通道,但老书记为这事也得罪了王四,老书记现在挺担心王四用各式手段报复。
这个事例的背景是洋镇的小城镇建设。2002年,洋镇主要领导人决定将小城镇建设作为本镇的亮点工程,当时洋镇城镇面积 1.5平方千米,城镇居住人口 5 000余人,1条老街,而现在洋镇城镇面积有 3平方千米,城镇居住人口 11 000余人,16条街,洋镇的小城镇建设在该市来说是规模最大的。洋镇政府通过小城镇建设,人为塑造起当地的土地市场,城镇及镇郊村庄中的土地价值被大幅度拉高,作为土地市场化的发起者,政府自然要通过征地从中获利,而灰黑势力也敏锐地嗅到了土地中的钱味,在村庄中到处“收购”土地,如王四早几年就将 Y村的 B地和 D地收入囊中等待开发,又如王四目前又试图拿走 Y村新村委会所在地的土地。以上只是基层政府和灰黑势力分别从土地开发中谋求利益,对乡村危害更大的是基层政府与灰黑势力沆瀣一气,互相利用,联手瓜分基层资源。基层政府在小城镇建设中,首要的是收回土地的使用权,灰黑势力可以进行的“支援”,一是让渡自己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权 (如 B地),二是逼迫普通老百姓 (如那五户人家)向政府让渡土地的使用权。作为回报,政府可以将土地使用权收回后再分配给灰黑势力开发 (如一半 A地),也可以将垄断的其它资源(如水库)交换给灰黑势力。灰黑势力和基层政权以相互配合的方式在村庄中谋取各种资源,资源一分配到村庄,就立刻被这两个群体以结盟的形式攫取很大一部分,资源分配不能增进基层治理的效益,基层治理中出现了“内卷化”的问题。
二、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内在逻辑
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出现,和灰黑势力、基层政权以及村庄资源分布三者的转变密切相关。
(一)灰黑势力:从名气到利益
改革开放初,有限度的社会流动、革命理想主义的退潮和村庄集体对农民控制力的下降,改变了村庄秩序,年轻人越轨行为日益增多,这一时期的乡村江湖,盛行的是英雄主义。[2]41-50乡村“混混”在村中多数只是为了拼一个“名气”而好勇斗狠,此时暴力的施展具有率意性和盲目性,乡村“混混”也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多为相互仰慕而聚在一起的“江湖弟兄”。到了 1990年代,乡村“混混”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拼和历练后,变得“成熟”起来,他们不再注重虚幻的名气,而只重视现实的经济利益,“混混”常结成利益团伙,进行各种非法谋利活动,“混混”们通过贩卖自己的身体暴力给团伙,来换取金钱利益,此时暴力的施展则具有市场化和组织化的特征。“混混”们根据组织的严密程度不同,纷纷成为灰社会或是黑社会的成员。
当乡村灰黑势力赤裸裸地以金钱为目的时,便会以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取向,哪里有利益,哪里获取利益的成本最低、风险最低,哪里就会出现灰黑势力。有能力的乡村灰黑势力多流向城市中,经营酒店、夜总会、KTV、游戏厅、迪吧等,或是流向矿产资源区,开采矿产。势力一般的乡村灰黑势力只能留在乡村,以偷盗和抢劫的方式来敛财,这种谋利方式和前者相比较,收入少且遭到政府打击的几率高。总之,进入 1990年代后,乡村灰黑势力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谋取资源上,但此时的村庄由于资源总量和城市以及矿区相差甚远,并不是乡村灰黑势力谋利的首选。
(二)村庄资源分布:从提取到输入
由政府主导分配到村庄中的资源,大致可以分为市场分配型、非市场分配型和半市场分配型三种。市场分配型的村庄资源,实质就是利用国家政策把村庄中的存量资源通过市场化转变为流量资源。这种分配方式中,政府并不直接向下投入资源,而只是利用政策和法律来重组地方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村庄中的各种集体资源如鱼塘、水库等都被相继投放到市场之中,近年,从村集体下放到村民手中的农地和宅基地也逐步被政府收回投入到市场之中。非市场分配型的村庄资源,为自上而下的政府转移支付的一部分,多通过行政渠道直接发放到村民手中,如各项补贴。半市场分配型的村庄资源,如各种工程项目,这种资源初始也来自于政府的转移支付,但并不是直接将资源分配到底层,而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在基层进行招标,由工程的承包人和工程的享受者 (如广大村民)共同获取转移支付资源。
改革开放后,首先在村庄中释放出来的资源是市场分配型的村庄资源,尤其是村庄中的集体资源,如鱼塘、水库、厂房、滩涂、山林等。村集体资源市场化,既是国家政策调控的结果,也是村集体的要求。由于要完成税费收缴任务,村干部试图以额外的收入来填补村民欠缴的空缺,因此,从1990年代甚至 1980年代起,各村集体都迫切地将村庄公共资源承包出去以“资源租”的形式变现。这批原来由村集体垄断的资源投放到市场之中后,灰黑势力很快接替村集体成为了下一个垄断集团。灰黑势力承包这些公共资源具有天然的优势,一是其在投标时能利用显性的暴力来耍横式地取得承包,或是利用隐性的暴力即将混过灰黑社会经历作为符号性的“资本”来耍赖式地取得承包,而且,他们也敢于用非法手段如行贿等方式拉拢村干部等招标人;二是承包后由于灰黑势力掌握暴力资源,管理成本也将大大降低,如王四在洋镇承包了 6~7处水库、200多亩林地,从来没有老百姓敢去他的水库中偷鱼,也没有老百姓敢去他的林地中砍树、放牛。村集体资源是村庄中出现的第一批比较诱人的经济资源,这吸引了一部分乡村灰黑势力把“生意”重新投注到村庄之中。
村集体资源的释放,没有改变国家对于农村的整体资源分配策略。我国自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以来对农村实行的都是“资源提取式”治理,1990年代中后期,乡村两级组织出于上级政府任务的压力以及对自身财政的追求,对于农民资源的提取,数量上又多、手段上又暴力,农民对于沉重的税费负担怨声载道,农民和基层政府关系极度紧张,农村随时有爆发危机的可能。中央政府看到这种局面,开始不断减少对于农村的提取,税费改革意味着国家对农村“资源提取式”治理的终结,同时中央政府提出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要反哺农村,农村开始进入“资源输入式”治理的时代。各上级政府向农村输入的资源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非市场分配型的资源,如粮食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业保险、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等,这些资源通过行政渠道层层转移下来,直接打到村民个人账户中,这类资源在政府官僚系统内部传递,有时候可能被官僚克扣和贪污,但灰黑势力并不容易插足其中参与资源的瓜分①这类资源中,最有可能被灰黑势力获取的就是退耕还林补贴,但退耕还林补贴也是灰黑势力借助大面积承包山林得到的,并非直接从发放渠道中截取。。上级政府向农村输入的另一种资源为半市场分配型资源,即各种工程建设项目,如公路建设、水库建设、安置房建设、绿化工程、自来水工程等,这类资源由政府向社会招寻“代理人”来进行具体建设实施,这很有可能出现招标人与投标人勾结在一起共同瓜分大头资源的现象,此时灰黑势力便重演起承包村集体资源的故伎,通过恐吓、行贿等各种灰黑手段,软硬兼施地拉拢政府人员,目的是取得工程代理人这个合法的身份从而大幅度截取上级政府本意是补贴到农村的资源。承包工程建设项目,相比较承包村集体资产,投资少、收益快、利润高,因此更受目前灰黑势力的青睐。
税费改革后,农村的资源分配政策由“提取”走向了“输入”,各级政府向农村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灰黑势力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钱味,摇身一变成为工程承包人,截留了大量的上级资金。在村集体资源对外发包和国家工程项目资源下乡的过程中,“官黑勾结”主要体现为灰黑势力单方面地努力拉拢基层组织的官员,基层组织对于灰黑势力的依赖并不明显。基层政府主动寻求灰黑势力的支持,更多体现在基层政府经营土地资源之中。政府经营土地的实质就是把土地商品化,将原来农业用途的土地转化为非农用途的土地,然后投放到土地市场中获取高额利益。农地市场化,同样是将村庄资源进行市场式分配,农用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本来也能为农村注入一笔资源,但这笔资源的大头却被基层政府和灰黑势力联手汲取。基层政府之所以热衷于经营土地,并在经营土地时寻求灰黑势力的援助,都和基层政府的性质密切相关。
(三)基层政权:从治理到维稳
乡镇政府之所以要求助灰黑势力,是因为其面临着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问题。乡镇政府的行动逻辑取决于以下几种资源的调配:“财政资源”、“政界资源”、“治理资源”、“合法性资源”。
乡镇政府自 1990年代实行“分税制”以来就面临着财政紧张的压力,因此乡镇政府一直以来都有强烈的谋取“财政资源”的动力。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政府的“财政资源”主要从提取村庄中的税费而来,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由于没有了收取税费的动力,其逐步退出而“悬浮”于村庄,[3]乡镇政府把营利的方式转向了招商引资和土地开发,土地财政成为了各地基层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经营土地,对乡镇官员谋求“政界资源”有利也有弊,由于官僚体系中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是GDP,乡镇政府的“财政资源”就极有可能转化为乡镇官员晋升的“政界资源”。但是,在“稳定”和“和谐”的大政治环境下,乡镇政府在土地开发中一旦出现了“反弹”如群体事件和暴力事件,无论对错,都会给乡镇官员的“政界资源”带来负面影响。上级政府对“维稳”的要求越高,乡镇政府越是缺少“治理资源”。1980—1990年代,乡镇政府掌握着强大的“治理资源”,配合其强烈的谋利动机,造成了严重的农民负担问题,中央政府看到这点,对乡镇政府关于“稳定”和“和谐”的要求越来越高。在 1990年代末,当地相继下达了上级关于收取税费的“十四不准”以及关于计生工作的“七准八不准”、“联防队”等原先正式的暴力资源被取缔。“治理资源”削减但上级分派的任务未减,乡村两级组织只能寻求一些非正式的资源,如利用私的个人关系来做公的收税工作,又如利用灰黑势力去收缴税费。这时基层政府已经主动地去请求灰黑势力参与基层的治理,这种情况虽不普遍,但基层政府在“治理资源”匮乏困境下“急病乱投医”的行为逻辑已经凸显出来。税费改革后,上级政府对于“稳定”和“和谐”越来越重视,一有影响稳定的事件出现,乡镇政府无论对错都要受到惩罚,加上乡镇政府失去了提取税费这块财源,由于财政的压力政府机构被“倒逼”缩编,在这二者的共同影响下,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越来越弱。如在拆迁方面,乡镇政府并没有足够的“治理资源”来完成,因为不管是有合理要求的老百姓,还是无理取闹的老百姓,乡镇政府都没有办法去应对,老百姓稍有异动,基层政府在“维稳”方面就要忙得焦头烂额。乡镇政府没有足够的合法暴力资源去完成治理,就只能放弃政权自身的正义性和原则性,抛弃“合法性资源”,去寻求非法的暴力资源即灰黑势力。让灰黑势力去做工作既能达到治理效果,又不会破坏“稳定”和“和谐”,因为灰黑势力在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方面的威胁给老百姓的压力是巨大的,在灰黑势力面前,一般老百姓根本不敢不表现出“稳定”和“和谐”,就算有的老百姓敢于反抗,政府也能声称这并非由“政府行为”引起。
总之,乡镇政府想要获取“财政资源”和“政界资源”,但乡镇政府无论获取合法利益还是获取非法利益都处处受到“稳定压倒一切”话语的阻碍,缺少“治理资源”的乡镇政府只有放弃部分“合法性资源”,利用灰黑势力来趋利避害。乡镇政府在利用灰黑势力方面尝到了甜头,于是灰黑势力越来越成为一支“正常”的治理力量,如镇里搞什么活动、典礼,乡镇领导都会让灰黑势力的“大哥”领着“小弟”去维持治安,完事后镇里再给予酬劳,又如 Y村最近新上来一个年轻女书记,镇里怕女书记掌控不住局面,就让王四去当 Y村的“名誉村干部”,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现在洋镇政府的各种行为,常常需要得到灰黑势力的配合,基层治理的维系,往往伴随着灰黑势力的壮大。
三、三波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比较
杜赞奇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4]51在清朝,国家向村庄提取税收的传统做法是依靠基层的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来实现征税,[4]28这两种“代理人”同时存在、相互制衡。国家遭遇强大的外敌入侵后,为了救国图存,清朝和民国政府都希望改变以往无为而治、“皇权不下县”式的治理模式,通过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裕和强大,国家权力下沉到乡村,一个重要目标是增加税收的征缴,以便为国家的各项新政服务,这打破了基层治理传统的平衡状态,征税任务的沉重把乡绅等保护型经纪排斥出村庄的政治舞台,他们充当国家“代理人”的“精神和物质报酬越来越少,而这一公职所带来的麻烦却越来越多”,[4]157另一方面,地痞恶棍等赢利型经纪却充斥于基层管理职位,他们借着国家征税的名义大肆中饱私囊。国家政权扩张却并未带来政权效益的增加,政权的合法性进一步遭到削弱。
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4]183共产党政权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对乡村的恶霸、地痞、土豪、流氓等原先的赢利型经纪群体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并通过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建立了稳定而可靠的“代理人”队伍,国家政权一竿子插入底层,禁止了贪污和截取等中间环节,国家对农村资源提取的效率大大增加,显著地支援了工业建设,同时国家的合法性不减反增。改革开放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层建制取消,国家对于基层的控制力大不如前,提取资源由基层组织统一核算上缴变为基层组织向千家万户的村民收缴,提取成本大大增加。同时,基层组织也逐渐变得不可靠,1990年代实行“分税制”后,乡村两级的自我营利性质凸现出来,加上革命道德话语的退却,使得很多乡村干部自我约束力下降,借着国家提取资源的名义过度收缴“乡统筹”和“村提留”。国家要向农村收税,需要借助乡村组织这一媒介,但由于乡村两级的营利倾向,国家收税的同时还伴随着乡村两级的中饱私囊和机构膨胀,而且乡村两级在“拔钉子”时还常常使用暴力,这些导致了 1990年代中后期爆发的“三农”危机。这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基层治理出现的第二波“内卷化”,这一波“内卷化”与第一波“内卷化”有所不同。第一波是在国家政权正试图深入村庄提取资源时出现的,国家在基层没有可靠的组织建制,只能依靠地痞恶棍来充当中介;第二波则是在国家政权已经成功占据村庄后需要继续提取资源时出现的,此时国家的权力触角虽已延及基层,但在提取资源方面曾经发挥巨大作用的基层组织遭遇了控制力、财源、道德约束等多方面的削弱,基层组织在提取资源时,无论提取数量还是提取方式都不能令老百姓满意,基层政权合法性下降的同时连累了中央政府合法性。
税费改革,倒转了国家和农村之间的资源分配方式,这让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大幅度提升。但是,税费改革只是取消了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三农”问题背后的基层组织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其控制力和财源等方面的短板不仅未改进,反而由于税费改革进一步被削弱,基层组织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决定了其虽不会再在收取税费这块“作恶”,也会在其他方面“作恶”。“中央是亲人,乡里是恶人”,这句老百姓中的流行语充分显示了税费改革在政治效果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在行政效果方面未有起色。资源下乡的不如意就是一个例证。国家以各种形式向基层分配了大量资源,这吸引了不少灰黑势力的注意,同时由于基层政权的营利倾向和治理手段的缺乏,分配资源的很大一部分正被基层政权和灰黑势力联手瓜分,有些资源分配如村集体资源对外发包和国家工程项目对外招标的过程中,灰黑势力主动拉拢基层组织的官员,而在土地开发等事项中,基层政权反而要向灰黑势力求援。资源每分配一分到基层,都伴随着基层政权和灰黑势力私利的增加,这二者勾结在一起就像一个毒瘤生长在村庄之中,不断汲取输入的养分。资源输入乡村的绝对数量虽在不断增加,但并未产生应有的治理效果,这就是基层治理中出现的第三波“内卷化”。这一波“内卷化”同样会造成资源和合法性的流失,但与之前的流失仍有实质不同,前两波“内卷化”是在资源提取的大背景下出现,而这一波“内卷化”是在资源输入的大背景下出现,在资源提取背景下,每一个村民都是掠夺对象,当地痞恶棍或乡村干部使用暴力征税时,容易引起群体性的公愤。而在资源输入背景下,掠夺对象只涉及极少数特定的村民,如土地拆迁中的“钉子户”才会感受到灰黑势力的欺压,甚至有时候并没有村民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掠夺,如灰黑势力承包山林、鱼塘、工程项目等,这些资源并不从村民的口袋中流出,第三波“内卷化”中,资源的损耗更多指国家分配的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老百姓的被剥夺感并不是很强烈。因此当前老百姓对于政府合法性的评价也很有特点:首先,老百姓肯定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但仍然给基层政权以差评,因为老百姓既看到了中央政府的资源分配政策的转变并拿到了不少类型的直补,也看到了基层政权和灰黑势力联手侵吞上级资源;其次,由于切身利益被直接剥夺得并不多,老百姓对于基层政权的不满意程度并不像税费改革前那样高涨。但是,由于基层政权和灰黑势力的勾结,老百姓对于基层政权的性质越加失望,也就是说,老百姓在这轮“内卷化”中对基层政权合法性的否定,更多地在质而不在量。
“资源输入式”的治理方式,在实践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资源的输入没有改善基层的治理,反而滋养了基层政权和灰黑势力这个结盟群体。从当前基层治理“内卷化”的状况,我们可以反思当前国家对于基层的治理方式:国家仅改变资源分配方式是不够的,无论是提取资源是还是输入资源,都需要有基层政权来连接中央政府和村民,因此改进基层政权这个中介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中央政府经历了世纪之交的“三农”危机,对基层政府能够履行好“代理人”的角色深感怀疑,于是中央政府希望绕过基层政府来亲自治理村庄,方法一是将各种补贴直补到农民手里,方法二是通过各职能部门进行直接治理,方法三是不断缩小基层政府的权力和组织规模。国家目前的这种治理方式,首先忽视了基层政府在提供基层公共服务方面的重要性,中央政府只看到了基层政府做坏事的可能性,没有看到其在做好事方面的不可替代性。其次,对于基层政府的改革也没有改到点子上,目前改革的重点是不断缩小基层政府的权力,却没有将重点放在改变基层政府的政权性质上。这种改革方式造成了,一方面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特别弱小,该治理的事情无法进行治理,手中的强力资源被严格限制,而另一方面基层政府谋利倾向未被改变,而且越来越失去了原则、越来越失去了应有的政权性质,在“策略主义”的逻辑下,[5]201其为了自保或获取资源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要去除当前基层治理中的“内卷化”,不能仅把目光放在灰黑势力上,“严打”等专项整治只能暂时抑制灰黑势力,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改变整个基层治理的结构。而改进基层治理的结构,不能简单地只是弱化基层政府,然后由上级政府不断向农村投钱,这还不能使基层治理达到“善治”。如果要真正让基层政府实现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一是要重视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财政和权力方面为其留足空间;二是要重塑基层政府的“正气”,改进基层政府的“政权性质”[6]374,转变其“自利型”的政权性质,要让其重视并有意识提升自我的合法性,而不仅仅是在治理方式方面做文章。基层政府改革的重点是“权力性质”而非“权力规模”,当下应该重塑基层政府的原则性和正义性,把基层政府改造成“良性政府”。
[1] 贺雪峰.私人生活与乡村治理研究.读书,2006(11)
[2] 陈柏峰.乡村混混与农村社会灰色化.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文论,2010
[3] 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2006(3)
[4]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
[5] 欧阳静.策略主义与维控型政权——官僚化与乡土性之间的乡镇.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文论文,2010
[6] 申端峰.治权与维权:和平乡农民上访与乡村治理 1978—2008.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文论文,2010
Gangland and Rural Governance Involution
Geng Yu
In the post-era of tax and fee refor m,the state allocated the large amount of resources in various forms to the country,but these resourceswere intercepted by local government and gangland in the form of conspiracy.Resource allocation?causes the new rural governance involution?instead of the corresponding efficiency?of governance.The appearance of rural governance involu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followings:gangland,local govern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village resources respectively.In order to?solve problems involved and improve current situations,the author suggested the state needed to improve the na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in certain extents.
Gangland,Local government,Involution,Governance,Tax and fee reform
2011-02-12
耿羽,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2010级博士,邮编:430074。
①贺雪峰教授对本文写作给予了颇多启发和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连丽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