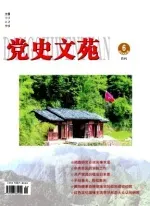陈独秀与刘半农:倾心交往铸就中国革命传奇佳话
2011-12-16■杨飞
■杨 飞
陈独秀与刘半农:倾心交往铸就中国革命传奇佳话
■杨 飞
陈独秀与刘半农,一个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民主革命家,一个是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两人以文相识,随后携手编辑《新青年》,并肩战斗在“五四”运动中,终成至交。陈独秀与刘半农的交往,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传奇佳话。
上海初遇,二人相见恨晚
1915年9月15日,怀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的念头,从日本东京归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一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刊物——《青年杂志》。《青年杂志》创刊后,为了提高刊物的知名度,扩大杂志销路,陈独秀开始“招兵买马”,四处邀集名家加盟。一开始,求贤若渴的陈独秀便想到了活跃于上海文坛,有着“江阴才子”“文坛魁首”美誉的刘半农,但无奈与其素不相识,初创的《青年杂志》影响力又不大,陈独秀才怅然作罢。
就在陈独秀为办好 《青年杂志》而绞尽脑汁之际,191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闻名已久的刘半农。
刘半农原名刘寿彭,后改名刘复,字伴侬、瓣秾、半农,号曲庵,1891年5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今江阴市)澄江镇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1907年11月,刘半农以江阴考生第—名的成绩考取由八县联办的常州府中学堂。他天资聪慧,在常州府中学堂每次考试几乎都名列第一,被学校“列入最优等”,一时间“才子”的美誉不胫而走,“同学争以一识刘寿彭为荣”。然出于对学校保守的教育体制的不满和失望,在毕业前一年,刘半农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放弃唾手可得的大好前程,毅然从常州府中学堂退学。此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就任民国大总统,倾向革命的刘半农大受鼓舞,决心离家做革命党。怀着这一愿望,他只身来到江苏省清江市(今淮安市),在一位军官手下做文案。但时隔不久袁世凯再度夺权,军队内部亦陷入混乱,失望至极的刘半农遂愤而辞职,于1912年3月前往上海另求发展。
初到上海,刘半农做过短期杂工,又做过开明剧社编剧,最后在朋友徐半梅的介绍下,到中华书局编辑部做编译员。在这期间,他笔耕不辍,先后在《小说月报》《时事新报》《中华小说界》和《礼拜六》周刊等杂志上发表译作和小说多篇,被读者捧为“江阴才子”“文坛魁首”,成为上海滩文坛上一个十分活跃的小说新秀。
相见之前,文人出身的陈独秀与刘半农两人都听说过对方的大名,只是无缘一见。此次见面,陈独秀那乐观大度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让刘半农深为叹服。而英姿飒爽、思想进步、富有文采、充满活力的刘半农也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两人一见倾心,均有相见恨晚之感。陈独秀与刘半农都很健谈,从文学到时事,再到社会生活,他们好似有说不完的话。陈独秀对刘半农作品中的诅咒旧社会昏庸黑暗、同情劳苦大众的涵义的理解,以及对其译著在开拓国人视野、吸收外国文化、针砭时弊、讨伐封建腐朽、启迪民众智慧等方面作用的较高评价,都让刘半农甚为感动,刘在心中已开始将陈引为知己。而刘半农对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及其倡导的新文学的理解和支持,也让为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而竭尽心力但却收获甚少的陈独秀深感欣慰。那时《青年杂志》已易名为《新青年》,发行量和影响力都有所增加,但以启蒙青年思想为己任的陈独秀对此并不满意,认为还远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全国青年热烈反响的状态,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在为《新青年》寻求优秀稿件。趁此机会,陈独秀诚意向刘半农约稿。
从这开始,《新青年》便开始刊登刘半农的文章和译稿,刘半农逐渐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之一。陈独秀与刘半农两人还常聚在一起切磋文学,交谈时事,发表对时局的一些看法,感情日渐深厚。在陈独秀支持下,刘半农后来还第一个在 《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新诗和随感录,对民主主义的传播和青年一代的文化启蒙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北大,刘全力支持陈的文学革命
1917年1月,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力荐下,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随即利用蔡元培赋予他的人事和行政权,延聘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学者到北大任教。中学肄业但富有才华的刘半农也在陈独秀的考虑之列。陈独秀力劝蔡元培破格聘用刘半农,蔡元培便于这年夏天向刘半农发出了聘书。
收到蔡元培的聘书时,刘半农正在江阴老家赋闲。当时,由于没有固定收入,刘家几近穷困潦倒,有时还不得不靠借贷度日。蔡元培的聘书对刘家来说简直就是喜从天降。但刘半农知道这一切都是老友陈独秀对自己的照顾,患难见真情,他为能拥有陈独秀这样的朋友而自豪。随后,带着对陈独秀的感激之情,刘半农接受了北大的聘请,于这年秋天出任北京大学法科预科教授,讲授范文和文法概论。
未到北大任教之前,倾向于文学革命的刘半农就于1917年5月1日在《新青年》杂志三卷3号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的文章,率先支持陈独秀提倡的文学革命。刘文从文学的界说谈起,就散文、韵文、文章形式等方面提出了改良意见。刘半农认为:“欲发起新文学,须从散文改革做起。第一曰破除迷信,如不顾自己只是学着古人,便是古人的子孙。第二曰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持的地位,二者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处,未能偏废。第三曰不用不通之文字。而新诗的创作第一曰破坏旧韵重造新韵。第二曰增多诗体。第三曰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之位置。”刘半农的文章受到陈独秀的赞赏,一时间影响很大。
当时,北大在陈独秀等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下,已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新文化思想的中心。进入北大后,刘半农在陈独秀的支持下,以《新青年》为阵地,先后发表《灵霞馆笔记》《小说精神上的革新》等译作、杂文和评论,宣传新思想,抨击保守派,倡导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赫赫有名的闯将。
在陈独秀提倡的文学革命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诗歌革命方面,刘半农在新诗理论和创作实践上贡献出色,他先后创作了《相隔一层纸》《学徒苦》《铁匠》《敲冰》等新诗。其中,受陈独秀的影响,刘半农在《相隔一层纸》《学徒苦》等诗中着力揭露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鲜明地体现了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民主主义倾向,在“五四”时期的诗坛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时的刘半农,就如鲁迅先生在《忆刘半农君》中所说的那样:“(刘半农)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

1917年8月,《新青年》的另一重要撰稿人钱玄同首倡《新青年》发表文章应“渐渐改为白话”,并表示从此时起自己一切文章通信都将躬身力行,并敦请他人用白话作文。陈独秀十分支持钱玄同的所做所为,他不惧压力,在其主编的《新青年》三卷6号上刊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即钱玄同与陈独秀的通信。为了支持陈独秀,刘半农公开发出论调:“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么人再写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话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写白话文的,就是活人。”寥寥数语,其情却深。刘半农对陈独秀的理解和支持之情,尽显其中。
当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还在北大酝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推动新思潮的传播,陈独秀鼓励和支持文科师生成立各种进步的学术文化团体。刘半农积极支持陈独秀,他同胡适、周作人等一道,于1917年底成立了北大文科国学门研究所小说科研究会,并先后演讲了“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和“论中国之下等小说”,要求创造平民派新小说。刘半农的演说和研究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发展,在客观上也支持了陈独秀在北大的各项改革活动。
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
1918年初,鉴于自己已就职于北大,为方便《新青年》的编辑,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了北京。其时陈独秀正忙着进行北大文科学制改革,一个人办《新青年》有点忙不过来,便将《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由钱玄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刘半农6人轮流编辑。
新年伊始,《新青年》六大主编之一的刘半农便发表了《应用文之教授》一文,表达自己文学改革的愿望。经过再三斟酌并与陈独秀商量,为与自己先前略显香艳媚俗的笔名“伴侬”相区别,刘在文末署名“半农”,以示自己与过去决裂之决心。从此,“半农”变成了他正式的名字。刘半农还同钱玄同一道,受陈独秀之邀为《新青年》向鲁迅频频约稿,催促鲁迅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杰出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
为寻求扩大《新青年》的社会影响、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斗争的良策,《新青年》的编辑们几乎绞尽脑汁。刘半农由于曾在上海开明剧社做过编剧,所以他首先想到了双簧戏。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同为《新青年》六大主编之一的钱玄同。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他虽旧学根底深厚,但却十分讨厌旧文学的做派和风格,曾经骂他们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刘钱两人性情相近,在北大的教授圈子里一向过从甚密,无话不谈。刘半农提议两人合演一曲双簧戏,—个扮演顽固的复古分子、封建文化的守旧者,一个扮演新文化的革命者,以记者身份对他进行逐一驳斥。他们期望用这种双簧戏的形式把正反两个阵营的观点都亮出来,从而引起全社会对文学革命的关注。当时,这种不入流的炒作手法使两人一度有所顾忌,但为了斗争的效果,斟酌再三他们还是决定实施。
《新青年》有一个“通信”专栏,专门发表读者来信,来信后面附有编辑回信。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3号上“通信”专栏刊发了一篇4000多字的读者来信,信是写给编辑部的,署名“王敬轩”。其实,王敬轩本无其人,此信纯由钱玄同综合当时旧文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谬论写成。在编辑回信部分刊发了洋洋万言、署名“半农”的杂志社记者的回复——《复王敬轩书》。“半农”便是刘半农。
王敬轩的信用文言写成,不加一个标点,通篇都是对新文化运动所提倡观点的攻击,他说:“贵报大倡文学革命之论,权舆于二卷之末,三卷又大放厥词,几于无册无之。四卷一号,更以白话行文,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罗织新文化运动诸多罪状,攻击主张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
在《复王敬轩书》中,刘半农以新文人形象出场,对王信中内容一一驳斥,针锋相对。刘半农素以幽默、诙谐的文风和流利畅达、泼辣尖锐的语言受到人们的称誉。在这封信里,其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高屋建瓴,条分缕析,切中要害,又旁征博引,于嬉笑怒骂中将王敬轩代表的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和封建国粹派一伙人的谬论批判得体无完肤。在信中,针对王敬轩提出的“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刘半农起句即以“闲话少说”回敬之,接着展开阐述:“句读之学,中国向来就有的;本来采用西式句读符号,是因为中国原有的符号不敷用,乐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来用用。”对王敬轩所论的“钩挑”是代圈点的说法予以讥讽:“知识如此鄙陋,记者惟请先生去读了三年外国书,再来同记者说话;如先生以为读外国书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不愿下这个功夫;那么,先生!便到了你‘墓木拱矣’的时候,还是个不明白。”对王信中所提出的“能笃于旧学者,是能兼采新知”说法,刘半农答复道:“记者则以为处于现在的时代,非富于新知,具有远大眼光者,断断没有研究旧学的资格。否则弄得好些,也不过造就出几个‘抱残守缺’的学究来,犹如乡下老妈子,死抱了一件红大布的嫁时棉袄,说它是世界间最美的衣服,却没有见过绫罗锦缎的面;请问这等陋物,有何用处?”等等。
这两封信发表后,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热烈争论,并迅速演变成新旧两派的激烈对骂,陈独秀希望之轰动局面随之形成。它不仅引来了“王敬轩”那样的卫道士如林纾(林琴南)之流的发难,更多地却引起了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鲁迅后来在《忆刘半农君》文中也称这场论战是一场“大仗”。双簧戏的结果是“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一些原来还在犹豫的人也开始倾向新文化。
陈独秀对刘半农与钱玄同策划的双簧戏的结果十分满意,以至于一个月后,当一位自称“崇敬王敬轩先生者”写信质问《新青年》编者为什么对王敬轩的议论肆口谩骂时,陈独秀还复信说:“对于违背常识,闭眼胡说的妄人,不屑与辩,唯有痛骂一法。”陈刘两人的知己相交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面对封建守旧势力,二人并肩战斗
由于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同时也由于旧的传统势力根深蒂固,任何微小的改良和进步,都会引起激烈的反对。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文化狂风暴雨般的冲击,新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的结合并进一步深化,引起封建势力的惶恐和仇恨,他们对以陈独秀、刘半农为代表的新派势力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和残酷的诬蔑。
1919年2月17日,封建卫道者林纾在上海 《新申报》发表用文言仿聊斋体写的政治小说《荆生》,恶毒诋诬新文化运动。小说中的“三人称莫逆”的田其美、金心异和狄莫,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而那个名为荆生的“伟丈夫”,则是代表封建主义旧政治旧伦理旧文化的卫道者。小说写道:当上述三人聚谈抨击孔子的纲常伦理时,那个随身携有18斤重的铜筒的荆生,“……指三人曰:‘汝适何言?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荆生说罢,还对正欲抗辩的田生“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这些话,把封建卫道者对新文化运动的仇恨心理和盘托出,可谓写得淋漓尽致。很显然,该小说的用意在于鼓动北洋军阀政府对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采取政治上的高压措施。
与此同时,《神州日报》发表了北大法科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兼北京《神州日报》记者张鹆子(张厚载)的《半谷通信》,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因思想激烈,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已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张厚载发表《半谷通信》源于其对北大关于文理合并改革的不满,加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曾反驳过他1918年关于新文学及中国旧戏问题的来信,张因此在心中对陈落下芥蒂,不希望“本科”学长落到陈独秀头上。3月初,张厚载第三次在《神州日报》发表通讯,造谣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这样的谣言,使蔡元培及陈独秀等人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3月19日至23日,林纾再次在《新申报》发表类似的文字,题为《妖梦》,把陈独秀的影射之名改为田恒,胡适的影射之名改为秦二世,蔡元培的影射之名改为元绪。整篇文字以荒诞的故事,表达了以作者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卫道者对于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极端仇恨心理。在这前后,北洋军阀政府中依附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安福系的喉舌——北京《公言报》,也直接攻击陈独秀、刘半农等人,并于1919年3月18日除了发表林纾的《致蔡鹤卿书》外,还发表题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况》的长篇评论,再次攻击陈独秀等人“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诽孔孟”的言论,并说其“祸之及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企图唆使北洋军阀干涉新文化运动。
在北京大学内部,守旧派们也开始了对陈独秀、刘半农等人的疯狂攻击。辜鸿铭以宣扬“尊王尊孔”大义和新文化运动对抗,他指出“中国优秀的文言文的特点是优雅,非白话文可比”。指责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可笑的,伪善骗人的”。黄侃在其所编《〈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梁漱溟在北大积极宣扬孔子哲学,组织“孔子研究会”,与陈独秀、刘半农等人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相对抗;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及北大学生陈钟凡等数十人,还“慨然于国学沦夷”,出版《国故》月刊,宣扬旧文化、旧道德,反对新文化运动。
针对这些居心叵测的谣言和无端的攻击,胡适和陈独秀、刘半农等人予以坚决还击。3月10日,胡适即致函《北京大学日刊》:“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还说陈先生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越传越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这月中旬,陈独秀还在其与刘半农等一些有谈政治愿望的朋友于1918年11月27日成立的 《每周评论》杂志13号上发表署名“只眼”的文章——《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中,说:“张厚载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作对,这事尽可从容辩论,不必藉传播谣言中伤异己。若是无心传下来,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针对林纾,陈独秀说他的小说也不会受到旧文学家欢迎。因为荆生正是孔夫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林纾是翻译家,陈独秀对他和对张厚载不一样,称作“林先生”。胡适和陈独秀公开驳斥张厚载谣言后,蔡元培亦发表《致神州日报函》,替陈独秀“辞职”辟谣,并依据大学规程,令张厚载退学。
钱玄同对林纾使用的卑劣手段甚为蔑视。那时,钱玄同有很多笔名,但他却常以“金心异”自称,使用“金心异”这个名字来写文章,“回敬”林纾的诽谤、攻击。
而刘半农也以自己的文采,写了多篇令人叫绝的文章对林纾之流的诬蔑和攻击进行回击。就在这段并肩战斗的时日里,他与陈独秀的友谊更上一层楼。
终因政治理念差异,二人分道扬镳
陈独秀和刘半农等进步知识分子对于那些使用“依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的人的反击显得苍白无力。在封建势力的残酷打击下,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不久便被免去了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黯然离开了北京大学。从这以后,陈独秀的思想更加“左倾”,他日益接近马克思主义,为其以后与李大钊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打下了基础。
1919年5月4日,陈被免职后不久,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陈独秀是这场运动的“总司令”,而刘半农亦作为北京大学教授临时会议干事负责人,于“五四”运动当天“坐守北大指挥部”,组织社会支持,声援被北京政府监禁的学生和教员,成为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齐名的“五四”运动四台柱之一。不久陈独秀因在“新世界”娱乐场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进步传单而被反动政府逮捕,刘半农还为营救其出狱而四处奔走呼吁。
两年后,《新青年》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胡适因不满《新青年》越来越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强烈要求陈独秀改变宗旨,否则就停办,或者另办一个哲学文学刊物。生性倔犟的陈独秀既不愿改变宗旨,也不愿放弃《新青年》。于是,他同意胡适等人另外去办刊物。从此,陈独秀与胡适等《新青年》大多数同人分道扬镳,将《新青年》迁回北京独立编辑。《新青年》实现了由编辑办刊向政治家办刊的转变,不久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而在这之前,刘半农便于1920年由教育部公派出国留学。政治理念的不同,使得陈独秀与刘半农两人的关系已经开始疏远。
再往后,陈独秀思想日益激进,他于1921年7月一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领导了波澜壮阔的国民大革命,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而刘半农则潜心学术,于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被外国以国家名义授予最高学衔的中国人。回国后,刘半农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世界日报》副刊编辑等职,继续以一个学者和诗人的身份活跃于中国文坛,在文艺批评、语音学、文学、乐律、古代音乐史以及摄影艺术等诸多艺术领域中,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成为蜚声中外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
刘半农常自诩其“正业”为音韵学,但在从事“正业”的同时,他从没有放弃过《新青年》时代的战斗精神和人文追求。他爱国正直,不畏邪恶,勇于揭露军阀政府屠杀爱国青年的罪恶,坚决主张抗日。1933年4月,刘半农还不顾白色恐怖,与钱玄同等12人联名在报纸上发出为李大钊烈士举行公葬的募款书,并书写墓碑墓志。甚至在其去世前的两个月即1934年5月13日,他还在南京《民生报》发表杂文《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针对国民党考试院长戴季陶“将令全国百姓心,不愿为人愿为鬼”的倒行逆施,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1934年6月19日,刘半农率助手白涤洲、沈仲章、周殿福及工友梅玉等,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赴西北地区考察方音民俗,不幸于7月8日感染回归热,返回北平后于7月14日病逝于协和医院,享年43岁。遗体葬于北平西郊香山玉皇顶南岗,蔡元培亲自为之撰写碑铭。胡适在给其挽联的上联中写道:“守常惨死,独秀幽囚,如今又弱一个”,高度地评价了刘半农,认为其历史地位可以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相比。
刘半农去世时,于1932年10月在上海病榻上被捕的陈独秀,正被国民政府判刑后监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闻知刘半农去世,他许久无语。陈独秀生性倔犟,喜怒哀乐从不轻易外露。但是,又有谁能体会得到一生笃信“世无朋友更凄凉”的陈独秀此刻失去挚友心中的悲痛呢?
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后来曾这样比较过刘半农与陈独秀、胡适的区别:“如果将韬略比作武器仓库的话,陈独秀的风格是仓库门大开,里面放着几支枪几把刀,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外面则竖一面大旗,旗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胡适的做法,是库门紧关,门上贴一张小纸条,说‘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两位都是高人,一般人见了,望而生畏,不上前。可刘半农没有什么韬略,他没有武库,就赤条条的一个人,冲锋陷阵,愣头愣脑。所以,陈胡二位,让人佩服,刘半农却让人感到亲近……”
或许就是刘半农的容易亲近,才使他与陈独秀等由相识到相知。他们用其诚挚交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永恒的乐章。

题图 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刘半农(左),青年陈独秀(右)
西安工业大学)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