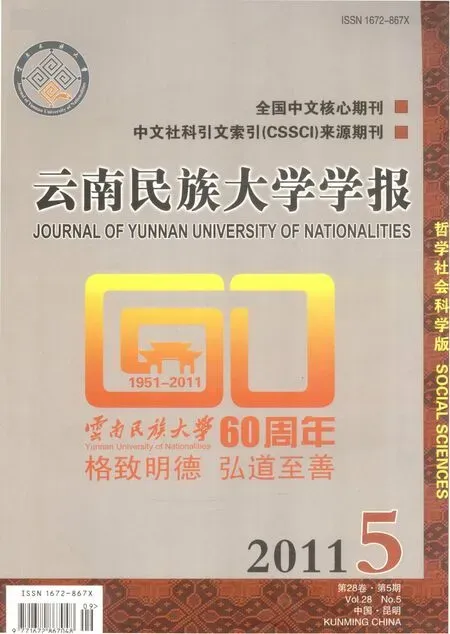老挝Lanten人的度戒仪式
2011-12-09袁同凯
袁同凯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中国 天津 300071)
一、引言
在老挝,Lanten人是老松族 (Lao Soung)的一部分,属苗瑶语系、勉门语支。Lanten人有自己的语言,像苗、瑶和贺人 (汉人)一样,他们来自于中国,其传统文化、宗教信仰、语言以及日历即是最好的佐证。而且,瑶人和Lanten人是本语支中惟一保留汉字的族群,但现今能够识读汉字的人已经不多了。根据Schliesinger的研究,老挝的Lanten人是从中国和越南迁移过来的,时间上可能要比瑶族的其他支系如Mien晚得多,大概在20世纪初期。[1](P274)据老挝政府《2005年人口与家庭统计结果》统计,老挝共有瑶族 (Mien和Lanten) 27449人。[2]
与其他苗-瑶语族的族群一样,Lanten人信奉多神与道教。他们既祭拜家神和祖先,也崇拜诸如天神、土地神、水神、树神等自然神灵。Lanten人普遍相信,无所不能的神灵掌控着人世间万物的命运,规定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每一个神祗都有其各自的保护作用,人们必需无条件地尊重神祗的习性。冒犯了神灵的人必需举行仪式来进行赎罪,以免当事人或他的家人乃至他所在村落遭受灾难。人和神灵之间的媒介是鬼师,当地人称莫公,他的角色是将人们的愿望上传给神灵,并传达神灵的旨意。在Lanten村寨,最重要的神祗是寨神和家神,每一个Lanten家庭都设有供奉家神的神龛。与其它信奉多神教与道教的族群一样,仪式活动是Lanten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生活中但凡遇疾病、灾祸或重大事件,通常都要请莫公前来主持仪式活动。每当此时,村寨里的人们总会聚集在举行仪式的人的家里或院落里,在沉闷的木鼓声中一边观看仪式一边闲聊;小男孩们则夹杂在大人中间,在玩耍过程中习得一些有关仪式的基本知识。
本研究是2006年笔者在老挝北部田野调查的成果之一。在老挝调查期间,笔者考察了老挝北部3省的12个Lanten村寨,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参与他们的日常活动,尽可能地体验和感悟他们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在这期间,共走访235户家庭,访谈了1602人,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基于这些数据和资料,本研究试图阐释和解析Lanten人的度戒仪式及其蕴含的象征寓意,为我们理解Lanten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点依据或者一种视角。本研究主要以垄南塔的Lanten人即Kim-Di-Mun为主,通过一个比较微观的视角,阐释Lanten人的度戒仪式及其象征寓意。这是男性Lanten人生活中需要经历的最重要的仪式活动之一,也是一个唯有男性参加的仪式活动。
二、度戒:男人的仪式
结构-功能主义大师Radcliffe-Brown认为仪式行为是社会秩序的展演,对社会结构的构筑有不可缺少的作用;象征主义大师V.Turner则认为宗教仪式行为是社会通过对自身的反省建构人文关系的手段。[3](P145)但对于大多数人类学者来说,神灵信仰和仪式活动构成了文化的基本特质,也构成了社会形态的象征展示方式。因此,无论采用何种解释体系,人类学者在进入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与论文写作时,信仰与仪式向来是主要的观察点和论题。[3](P144)因为仪式,用 Monica Wilson的话说,“在最深的层次上体现了群体的价值,人们在仪式中表现了他们最为之感动的东西。我认为仪式的研究是理解人类社会基本构成的关键所在”[4](P420)。因此,研究一个社会或文化的仪式活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该社会或文化中“最为之感动的东西”。
据V.Gennep和V.Turner等人类学家的研究,生活在不同文化尤其是那些传统社会中的人,在其生命过程的重要转折点上或者当人们的角色和地位发生较大的变化时,通常都要举行一些过渡性仪式活动。[5](P513)
在老挝北部的Lanten人中,一个男人一生中一定要举行一次度戒仪式。通过度戒仪式,他投胎再生,获取一个法名,死后莫公方能为其举行丧葬仪式,使其躯体入土安息,亡灵投胎转世。可以说,度戒仪式是老挝Lanten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通过仪式,含有浓郁的宗教意味,关系到他来世能否投胎转世。因此,对于一个 Lanten男人而言,无论其家境好坏,其家人一定要为他举行一次象征“再生”的度戒仪式。家境好的,父母可以在他孩提时期为其举行度戒仪式;如果家境穷困,父母无法为其举办度戒仪式,那么,等他结婚后,如果女方家境好,也可以帮助他完成这个重大的通过仪式。①举行度戒仪式开销很大,往往需要花去人们多年的积蓄。以下是B.Nam Ke Noi一个男子举行度戒仪式的具体开销:半大小猪6头、公鸡4只、大米约300公斤、啤酒 (Beerlao)20瓶。另外还有请莫公的费用:三个大莫公每人50000kip(约合5美元),两个小莫公每人30000kip(约合3美元),共计210000kip(约合21美元)。
2006年3月笔者在陇南塔的一个Lanten山寨调查时,正好赶上一场度戒仪式,受戒者是一个26岁的已婚男子。这个仪式整整举行了三天三夜,本村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参加了仪式活动,妇女不能参加,但可以到主家协助主妇准备众人食用的饭菜。仪式由一位70来岁的老莫公主持,另外还有五个小莫公作助手。受戒者在仪式期间必须静卧在床上,不能下地,在床上接受各种神祗的旨意,完成“再生”的一系列程序。
按照常规,需要度戒的男孩子的父母,要在举行仪式的头一年就请莫公查看经书,选定受戒的日子。首先要举行小度戒仪式,通常要杀4只鸡,敬献4位鬼神,摆法坛,给孩子起法名,然后再举行大度戒仪式。举行大度戒的具体日子,通常不确定,要看孩子哪一年走好运就定在哪一年。受戒者要亲自逐个去拜请莫公为自己主持度戒仪式。临行前,他要梳洗得干干净净,剔好头,在家人的陪同下,从法力最小的莫公saaiwickdy开始依次逐个烧香拜请莫公。当天晚上,法力最小的莫公先来到小孩家准备仪式用的字符,村里人也纷纷来受戒者家里帮助剪纸、布置法坛。为此,整个村寨要闹热几天。村民们尤其是村里的男人们在这几天几乎都不出工,汇集在法坛周围聆听莫公的唱词或围坐在院落里谈天说地。在举行度戒仪式的三天里,村里所有的成年男子都会前来参加仪式活动,可以免费享用一日三餐。
传统上,那些爱学习、能够记得住经文的人,受戒后就有可能成为Saaimen(莫公的一种)。Saai men(Lanten语)或mogong(老语)是“做鬼”的莫公。在Lanten村寨,莫公又分为Saaimen和Guamen。Guamen是不识字、经过学习成为莫公的人;而Saaimen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要懂得汉字,要会念经,是可以主持各种治疗疾病仪式的人。
生活在老挝北部丰沙里的Lanten人 (即Kim-Diang-Mun,意思是“住在山顶上的人”)的度戒仪式略有不同。通常情况下,那里的男孩10岁开始受度戒,他们认为男人在8岁以前是没有“道”的。因此,8岁以后,只要家庭条件允许,就要为孩子举行度戒仪式,使其重新投胎再生。在丰沙里,Lanten人的度戒仪式一般要做一个星期。在这期间,受戒者每天只能喝一点水,吃一点饭,睡觉时不能俯卧,也不能仰卧,只能侧着身子睡觉。否则认为对天地不敬。外出解决内急时,眼睛不能远视,只能看自己的脚下,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大,也不能坐凳子,如果要坐,要莫公将凳子在火上燎一燎,除去邪气方可坐。受戒时,将一根筷子折成两截,师父拿大头一端,受戒者拿另一端,筷子象征利剑,如果受戒者不遵守戒规,师父可以用“利剑”杀死受戒者。一周之内,要杀6头猪、10只鸡,全寨子每家来一个男子参加聚餐,妇女通常也不得参加此类度戒仪式。
三、木鼓声声:度戒仪式的过程及其象征寓意
老挝Lanten人的度戒仪式的具体过程极为繁杂,在老莫公的主持下,要先叩请玉皇、雷皇和盘皇,再拜请他们的师父 (也是神灵),三请家神,把受戒者引介给这些神灵。在度戒期间,受戒者要遵守许多禁忌行为。首先,受戒者要静卧在床上,不得随意下地和出门,非要出门时也得打着雨伞。第二,受戒者每天都得有人尤其是老莫公的陪同,在守护他的同时向他传授某些知识。第三,受戒者不能吃饭,只能喝一点水。等仪式结束后,他们才能吃东西。三天仪式之后,师父们先吃,随后受戒者才能吃。吃饭时,每位师父给他夹一点菜,由他的家人把饭菜端送到床上,让他一人独自在床上吃饭,随后便躺下睡觉。也就是说,受戒者在“阈限时期”内基本处在禁忌和隔离状态之中。受戒期间,外人不能有意去探望他,他要与外界保持一种“隔绝”状态,受到许多约束。如不能见光,不能出远门,出去大小便时,要请别人先出去看看道上有没有猪粪或者牛粪之类的不洁之物,如果有,必须清除,受戒者非常忌讳碰见这类他们认为不洁的东西。受戒者出门大小便时,要打雨伞,不能抬头向远处看,只能看自己的脚下;受戒者除了下地大小便外,必须整日整夜地要躺在床上,如同新生儿童一般。此外,受戒后三周之内,受戒者不准杀生,不准与女人讲话,更不能与女人同房。他们深信,如果受戒者犯忌,尤其是与女人同房,他们会生病,甚至丧命,因为在这期间诸位莫公还都在向他施法。
象征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Victor Turner在其名作《象征的森林》一书中认为,对于那些通过象征表述其情感、道德和价值观的人们来说,象征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意义。[6](P44)从Lanten人的度戒仪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禁忌行为所蕴含的象征寓意。根据V.Gennep的研究,通过仪式是伴随着地点、状态、社会位置、年龄的每一变化而实施的礼仪,认为通过仪式通常分为三个时期或阶段,即分离、阈限和整合。在分离阶段中象征行为意味着仪式主体 (接受仪式的人)离开了他以前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或离开了一种“状态”①这是V.Turner的概念,指一个人的为社会文化所承认的成熟状况,如“已婚状态”或“单身状态”或“婴儿状态”,等等。;在阈限时期,仪式主体,或V.Turner称之为“阈限人”的状态含糊不清,他所经过的领域几乎不带过去的或将来的状态的任何特性;在第三个阶段中,转化完成了,这时仪式主体再次处于稳定的状态,从而有一些明确规定的“结构上的”权利和义务,人们期望他的行为符合某些约定俗成的规范和道德标准。[5](P514)显而易见,Lanten人度戒期间的上述禁忌行为表明,仪式主体或“阈限人”此时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模糊状态,正如V.Turner所说的那样,他的状况是含混不清、似非而是的状况,是平时习惯的大混乱。V.Turner甚至认为,在通过仪式的阈限时期,“阈限人”从结构上看是“不可见的”,尽管他在形体上是可见的。[5](P517)
仪式期间,莫公要在受戒者的院子里竖起一根竹竿,上面挂满写有咒符的各色纸条。两个最小的莫公,用芭蕉竿做一支“枪”,腰间挂着装有弹药的袋子,这时受戒者站在法坛中央,这两个莫公端着“枪”绕着他佯装向他射击,以示受戒者生命的终结或“死亡”;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小莫公则在模仿“妊娠”与“分娩”,象征着受戒者生命的“再生”。此时,整个仪式进入高潮,在场观看的人们相互敬酒庆祝,庆贺受戒者获得“新生”。紧接着,莫公要在草纸上写下主持仪式的莫公的名号、受戒者的姓名、生辰八字以及受戒的日期,一式两份,将两份拼在一起,并在拼接处加盖印章,其中一份是给阴曹地府的,这份要烧掉;另一份则由受戒者用草纸包起来细心保管,不能给任何人看,等他去世时,其家人才将其拿出来烧掉,以示能与阴曹地府的那份对上,以证明死者的真实身份。
度戒仪式的最后一天,莫公们的任务主要是教授受戒者一些医病的常识或法术,教导他善待家人,多为百姓做好事。三天之后,受戒者家人杀鸡宴请莫公,拆去专门为受戒者而建的围栏 (一般用布),但他还必须睡在里面。这时,莫公各自回家,理发、换衣服。这期间他们忌讳与女人接触,更不与女人同房。当晚主家要杀一头猪,拜谢luoguan神,庆贺度戒仪式圆满成功。
四、结语
本文概要地介绍了老挝Lanten人的度戒仪式,着重讨论了其度戒仪式中所蕴含的象征内涵。毋庸置疑,仪式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历史长河中所积淀下来的各类仪式活动中所包含的深层寓意往往能折射出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从Lanten人的度戒仪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Lanten人的文化中,这些被V.Turner称之为“阈限人”的受戒者不仅在结构上是“不可见的”,而且在仪式上是“污染性的”,所以他们总是被隔离,部分地或完全地与文化上有规定有秩序的状态和地位的领域隔离开来。[5](P517)仪式期间莫公们不停地击鼓施法,致使整个山寨都浸没在沉闷的木鼓声中。木鼓声为山寨营造了一种超乎寻常的神圣的宗教氛围,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对那些从小听着木鼓声长大的Lanten人而言,这声音无疑使他们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男人们在木鼓声中“脱胎换骨”,获取新的“角色”、“身份”或“地位”,并习得其新“角色”或“身份”所必须的能力和知识。在Lanten人的传统社会,诸如度戒之类的各种仪式,使当地人为了生存所必需的某些知识得以永久传承下去,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Lanten社会或文化中“最为之感动的东西”。
[1]Schliesinger,J.2003.Ethnic Groups of Laos,Vol.3.Bangkok:White Lotus Co.,Ltd.
[2]Steering Committee for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ed.).2006.Results from the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2005.Vientiane Capital,March.
[3]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4]徐鲁亚.维克多-特纳与恩丹布的神秘仪式[A].庄孔韶.人类学经典导读[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维克托 -特纳.模棱两可:过关礼仪的阈限时期[A].史宗.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6]Victor Turner.The Forest of Symbols:Aspects of Ndembu Ritual.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