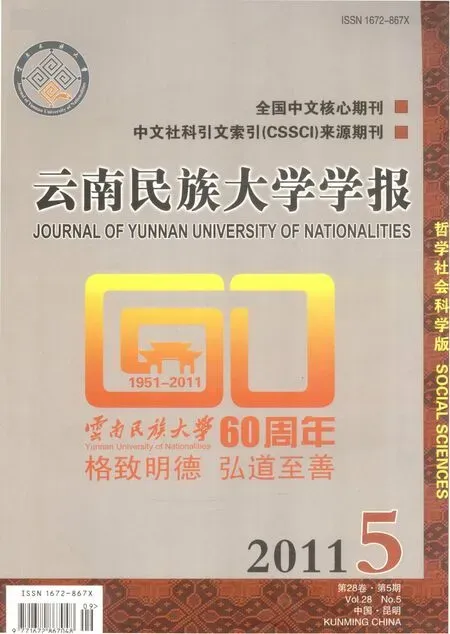桥头堡建设与云南跨境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2011-12-09和少英
和少英,李 闯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31)
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处于联接整个中国西南与南亚、东南亚的关键区域,早就被英国著名地理学家戴维斯 (H.R.Davis)称作“联接印度与扬子江的链环”[1]。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成分最多的省份,在长达4061千米的边境线上有近20个民族或族群 (Ethnic group)跨境而居,它们在对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我国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锦涛总书记2009年7月在云南考察工作时提出,要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这是在新形势下扩大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云南拥有区位条件优越、生物资源富集、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等桥头堡建设的诸多优势,尤其是经过西部大开发十年的发展,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呈现出越来越好的发展态势。近期,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正式出台,标志着国家对桥头堡建设的战略部署进入了全面实施的新阶段。因此,地处桥头堡建设最前沿的云南跨境民族或族群文化的繁荣发展问题,自然而然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一
所谓“跨境民族”一般是指具有共同族源、此后由于迁徙和国界变动等原因分别居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国家的同一民族或族群,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基本相同。云南跨境民族或族群主要有壮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瑶族、彝族、哈尼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怒族、阿昌族、独龙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以及克木人、莽人等近20个,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这些民族或族群内部都有较为通行的自称,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则往往又有不同的他称。
越南的岱依族和侬族与我国壮族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并在语言、习俗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性。其中侬族由于迁入越南的时间较晚,因而与中国壮族的共同性就显得更多一些;苗、瑶等族大致是明代从云南、两广和贵州迁去的,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这一迁徙过程的传说和文献记载;倮倮族与中国彝族有亲缘关系,语言和习俗与彝族也大致相同;哈尼族与拉祜族从我国云南省的金平、绿春两县迁去,距今也不过二三百年时间;布依族祖先则系19世纪从我国贵州省经云南省迁去,由于人数较少和居住分散,越南布依族已逐渐融合于其它民族;此外,还有一些特殊族群如莽人等,在云南省的金平县与越南的莱州一带跨境而居,语言与风俗习惯亦大体相同。
中老两国边界线长710千米,一侧是我国云南省的勐腊县和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有哈尼、汉、彝、傣、瑶、壮、苗、佤、拉祜、回、布朗、白、克木等民族或族群。另一侧是老挝国的琅南塔省、乌都姆塞省和丰沙里省。按照老挝政府公布的47个民族或族群来看,跨境而居的克木人①“克木[khmu]”意为“人”、“人民”,是族群自称。我国与泰国、柬埔寨、缅甸亦均称之为“克木人”。而老挝和越南称之为“克木族”或“高目族”。是老挝人口较多的族群;苗族是老挝第三大族群,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尚勇乡、磨憨镇等地的苗族村寨,据说是从老挝搬迁过来的白苗,他们与老挝境内的同源族群至今交往密切;泰、泐族是云南省勐腊县的傣人在宋末元初道经越南奠边府、勐莱 (莱州)至老挝的勐乌、乌得后流入的;哈尼 (阿卡)族大约在300年前分成多批次从中国南方转移到老挝[2](P52);三岛族即我国的布朗族,分布在琅南塔省和波乔省;归族和木舍族是老挝1995年人口统计表中由拉祜族改称的;瑶族被老挝学者认为是18-19世纪从中国和越南进入老挝的;央族 (即中国的壮族)是从中国迁出,经过越南进入老挝丰沙里等省的;倮倮族是中国境内彝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分布在老挝丰沙里省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自称阿露 (alu)。在我国也有自称阿露 (有人译为阿鲁anu)的族群,分布在云南省的云县、宁洱、新平、墨江、华坪、勐腊、江城等县。除此之外,在我国境内的苦聪人大约是1950年代前后从老挝迁来的,现与老挝同族边民往来密切;1987年,中国境内的苦聪人被划入了拉祜族。
缅甸的民族或族群大多也是从中国迁入的。最早进入缅甸的是定居于我国华南和滇西一带的百濮族群;其后氐羌部落的一支于公元一世纪前后进入缅甸境内,定居在缅甸中部和伊落瓦底江三角洲一带。源自我国百越族系的一些民族或族群先民,则定居在缅甸东部和东南部。掸族是缅甸的第二大少数民族,其自称“傣”,与我国傣族的文化风俗相同;高族即我国的哈尼族,传说他们的祖先很早以前居住在我国,后因生活所迫才迁到缅甸,从他们自称“阿卡”来看,很可能是从今天普洱、西双版纳一带迁徙过去的 (这些地方的哈尼族至今仍被当地人称为“阿卡”);克钦族在我国被称为景颇族,源自中国青藏高原东部,后大批移居至缅甸境内;拉祜族在缅甸也有拉祜纳、拉祜西和拉祜尼等分支;达迈族即我国的阿昌族,近年来德宏州阿昌族的奘房中已没有精通佛教玄机的“萨拉朵”,遇到一些重大的宗教活动,都到缅甸去请和尚来主持;缅甸与我国的傈僳族自称均为“傈僳”,但缅甸傈僳族实行一夫多妻制;缅甸仍称德昂族为崩龙族,分布在毗邻德宏的密支那、昔董、八莫、抹谷、孟密,瑞丽江左岸的果塘、当拜、西保、腊戌、南登尼等地,是滇西南和中缅交界地区的原住民族;拉佤聚居在佤联邦地区,散居于掸邦,操佤语,用佤文;还有从我国迁出的苗族 (蒙族)、布朗族(有的被列入佤族支系)、独龙族等。
此外,在云南的跨境民族或族群中,与虽未接壤、却相距不远的泰国的泰 (傣)、佤、苗、瑶、哈尼、傈僳、拉祜等族具有亲缘关系。其中,泰 (傣)族是泰国的主体民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佤(拉佤)族居住在清迈、夜丰颂、清莱、帕尧、南奔、南邦等地;苗(蒙)族人口的80%分布在清迈、清莱、达、黎、碧差汶等5个府;瑶族主要居住在清莱、帕尧、难府、南奔、清迈、彭世洛、甘烹碧等府;哈尼(阿卡)族居住在清莱、清迈等府;傈僳族居住在清迈、清莱、夜丰颂等府;拉祜族则主要分布在清莱府、清迈府、南邦府、达府和夜丰颂府。据美国人类学家安东尼.R.沃克博士称:“泰国典型的拉祜人称拉祜纳或黑拉祜,拉祜尼或红拉祜,拉祜西或黄拉祜 (又分为邦考、邦兰两个分支),拉祜普或白拉祜,拉祜先勒及拉祜拉巴”[3](P5)。
云南省作为本土文化、中原文化、东南亚与南亚文化的交汇点,独特的地域环境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成了不同“文化圈”与“文化丛”多元并存的格局。同时,历史沿革的特殊性也赋予了云南跨境民族或族群的文化以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积累了大量与其他文化互相交流与和睦相处的经验,当前的桥头堡建设无疑将对境内外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首先,传统文化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不断创新而成,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是很有特色的。强势文化将会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产生主导性作用,而后者对前者也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并会在特定条件下转化为对前者的疏离乃至抵制作用。对于作为本国文化非主流部分的跨境民族或族群文化而言,一方面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由于与境外同源族群的自我认同与频繁往来,也自然而然会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随着边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跨境文化交往也会愈加频繁。如果我们忽视了对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与爱国主义观念的培养,区域性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认同就难免导致其内部自我认同感强于对国家的认同,最终影响到边境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树立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是维护边境稳定、促进跨境民族或族群的文化繁荣发展的有效手段。
其次,保护和传承跨境民族或族群的文化是维护民族平等团结的重要标志。每个民族都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权利,这也是增强各民族相互了解的重要手段。传统文化不仅属于某一族群,同时也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宝藏。例如一些在内地早已消失的礼俗却仍然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中,“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这些“活化石”的存在,对我们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各种观念形态的起源及演化,提供了生动而直观的例证,其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另外,跨境民族或族群的文化中保留着大量少雕饰、贴近自然的原生性文化元素,在经济全球化正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今天,对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也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此外,跨境民族或族群文化不仅有重要的资源价值,同时也具有丰富的经济开发价值。传统文化是宝贵的人文资源,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也就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绿色经济强省以及通往南亚、东南亚国际大通道的战略设想并付诸实践,已经取得了不错的业绩。目前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速度加快,包括人文旅游在内的旅游业获得很大发展,以少数民族加工业、种植业、文化产业为基础的特色产业迅速崛起,在提高跨境民族或族群生活水平的同时,有效的增强了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树立了文化上的自信。要是能够牢牢抓住当前的桥头堡建设的大好机遇,跨境民族或族群文化的繁荣发展就一定能够收到更加显著的成效。
二
对于从各自不同的社会形态经过“跨越式”发展到今天的云南跨境民族或族群来说,当前主要面临着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双重挑战。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导致了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工业文明的强势冲击下,其生计方式、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家庭模式,以及语言、服饰、礼俗等传统文化将如何在新形势下健康持续发展,也就成为关乎跨境民族或族群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跨境民族或族群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其传统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承与保护的同时,随商品化大潮而产生的“伪民俗”等也开始泛滥,给跨境民族或族群的文化繁荣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同危机与主体性意识淡化。对于大多数跨境民族或族群来说,其生活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生计方式的转变直接导致其文化心理面临挑战。克木人是西双版纳州勐腊县与景洪市的土著居民之一,大约有3000余人,分布在10余个村寨中。克木人传统的生计方式是刀耕火种,直到20世纪50年代,族群内部尚未出现私有制和阶级观念。1955年党和政府把克木人聚居区划为“直接过渡”的地区。之后的几十年间,克木人的生计方式经历了从刀耕火种的游耕变为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耕,再到依市场需求种植橡胶的转变,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为了能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克木人开始以破坏热带雨林为代价而扩大橡胶种植面积。这样,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改善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促使曾经以雨林为核心的传统生计和文化观念发生变迁。对于这样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来说,一方面受到区域内处于主流地位的傣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因官方对其族群身份界定的模糊而加剧了认同的危机。这使得克木人对自身生命观念、价值体系、信仰体系、行为模式逐渐质疑,并慢慢否定了传统的观念和价值体系。
与认同的危机相伴而生的,还有民族主体性意识的淡化。这也是少数民族或族群在应对外来强势文化冲击时表现出的另一种状态,直接的体现是政府的扶贫工作落实困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提供大量的经济补贴与发展基金,力图在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百姓生活困难的同时,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状况的改善。然而这种做法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我们在对布朗族新农村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困境的调查中发现,为了改变布朗族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各级党委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帮助这些地区百姓的经济社会发展。但由于布朗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因此贫困的现状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同时,随着政府资金投入的加大,“救济式”的扶贫不但没有唤起他们的主体性意识,反而使当地百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等、靠、要”思想,使本该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未能发挥其最佳效益。
2.旅游业对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冲击。旅游业作为云南省的新兴产业,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问题。如何解决旅游业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和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商业化、庸俗化的倾向该如何调和?对于跨境民族或族群来说,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同样不可小觑——因为这是维系边境社区稳定的重要保障。
以位于云南最南端,与老挝、缅甸接壤的西双版纳州为例,全长966.3公里的边境线占云南省边境线的四分之一,8个民族或族群跨境而居,并与境外长期保持着探亲访友、赶集互市、通婚结亲、节日聚会等关系。随着民俗园、民俗村落成,旅游业带来的收入一方面提高了当地村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传统的生计方式。邻里关系、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民族文化面临着重组。笔者对世代居住在“傣族园”中的傣族百姓调查时发现,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入促使着傣族百姓转向发展旅游业而逐渐放弃了稻谷的耕种,“稻作民族”正在逐渐变成“旅游民族”。生产方式的转变导致其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语言习俗都发生了变化,例如人们对优秀青年的标准已由会纺织、尊重老人、有威望,转变为汉话讲得好、会招揽客人、会做生意赚钱。这种观念甚至影响到了小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出现了男孩子长大后大多想当保安,而女孩子想当导游的价值取向,没有了认真读书的心思。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明显增加,年轻人把更多精力放在赌博和飙摩托车上,由此导致的偷盗和交通事故成了村民最头疼的事情;有的年青人为了跟父母要钱赌博而拿刀威胁,完全违背了傣族的“尊老”传统;还有因争夺游客而产生的不正当竞争,导致亲戚、邻里之间互相结怨。在民族语言的使用与保护方面,由于旅游景区中汉语好的人在经济上的回报更多,因此许多村民开始以汉话说得好为荣,而不再重视本民族语言的学习;有些地区甚至已经出现了年轻人与老人之间因语言不通而无法交流的“怪事”!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方面,商品化和庸俗化倾向也不可忽视。历来喜欢清静的僧侣开始习惯于佛寺里熙熙攘攘的游客,傣族群众最为重视的“赕”也因佛寺收入的增加而变得可有可无。居住在基诺山的基诺族也同样因传统文化的商业化而陷入困境,随着民俗村的成立,半坡村29户基诺族家庭轮流进行歌舞表演并赚取演出费。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传统歌舞已蜕化为商业性的表演,失去了应有的文化内涵;甚至一些神圣的宗教活动也沦为取悦观众的演出节目……这些对民族或族群成员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感情产生的消极影响,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凸显。
3.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云南跨境民族或族群的宗教信仰相当复杂,既有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等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民间信仰,也有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世界性宗教的信仰。这些信仰与文化认同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以普洱市为例,该市东连越南、老挝,西接缅甸,国境线长达486.49千米。全市共有4个县的16个乡镇紧靠边境线,傣族、哈尼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傈僳族、景颇族等许多民族跨境而居,社区成员信仰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异。由于历史上的同源和文化的相近,因而民族或群内部交流频繁,境外的宗教势力在普洱市边境一带的村寨中积极活动,导致当地的社会问题与民族、宗教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突出特点。他们有的动员我方边民到境外参加布道讲经、接受洗礼等活动,有的未经我方允许就带圣经、赞美诗以及其他宗教宣传品入境,在当地传播销售。更有甚者利用边民日常往来的机会,打着宗教交流或帮助我方边民发展经济、开展扶贫工作的幌子深入我方村寨;通过向我方边民赠送收音机、电视机等手段,为其向境内进行传教活动创造有利条件。但当地部分基层干部对这种现象缺乏认识,认为抓好生产是唯一工作的重心,而大可不必去管宗教问题;也有的基层干部片面地把信教群众进行祭祀、祈祷等正常的宗教活动视为搞封建迷信。再从红河州河口县一带的情况来看,近年来越方在边境线上大兴土木修建教堂和庙宇,开辟宗教活动场所,其中在河口对面的沙巴,修复天主教堂一座,每周一、三、五、七做礼拜;在老街修复寺庙及天主教堂各一座,吸引了许多河口边民及省内外到河口旅游和经商的人群出境到越南去参加宗教活动。在中老边境和中缅边境地区,由于我方宗教职业人员的宗教学识不高,宗教领袖人物后继乏人,宗教自养能力有限,因而双方的宗教交流是出去的少而进来的多,外来影响占据优势。由于近年来越南方面在电视宣传上投入了大量经费,因而文山州麻栗坡县与越南相连的8个乡镇、24个村委会可以直接收到境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和布道宣传。越南政府还在边民购买电视机时进行半价优惠,并免费发给收音机,吸引境内外百姓购买电视机,收看节目。此外,境外邪教组织在我国境内的活动也需要重视。这些关乎我方跨境民族或族群信仰文化的安全问题,应当得到学界和相关部门重视。
4.跨境婚姻和人口贩卖的隐患。云南境内外民族或族群间通婚现象普遍。仅以文山苗族为例,从越南嫁过来的妇女据统计有数千人,而且由于边民没有领结婚证的意识,因此形成事实婚姻的数量应远不止此数。有学者估计,云南、广西两省区边疆地区娶了越南妇女、形成事实婚姻的可能有数万人之多。中越边民的跨国婚姻,在云南金平边境一带较为突出,傣族、瑶族、苗族和莽人均有互婚。这是由于境内外历来有同族互婚的传统,如金平傣族与越南傣族在土司统治时期就有傣族土司到莱州娶妻纳妾的习俗,因而这种互婚的传统就一直沿袭下来。据笔者调查,金平县金水河镇中越边境线上的雷公打牛莽人村,共有31户,197人,其中有5户的女主人为越南莽人,嫁到越南去的有2人。这种边民之间的互婚现象在当地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大家都视之为正常现象。跨境民族婚姻主要有以下一些形式:一是自由恋爱,多居住在紧邻边境村寨的年轻人;二是主动或被动介绍的,大都是一般距离边界线有一定距离 (直线距离20公里以外)的残疾人或年纪较大者;三是有跨国民族婚姻的村寨比较对应,往往是对方嫁过来的姑娘,把同一村寨的姑娘介绍出来或连带认识的结果;[4](P200)四是被不法之徒以生活优越为理由哄骗拐卖出入境等。通过调查,笔者发现跨国婚姻可能产生如下问题:
(1)外国媳妇的认同危机。由于很多跨国民族婚姻没有正规的婚姻登记,因此婚后的外国媳妇难以取得中国国籍和当地户籍,从而产生国家认同、群体认同、自我身份认同等三重性危机。这些危机直接导致了作为初级群体的家庭无法正常发挥其功能,并造成家庭对其成员的心理慰藉功能、经济依赖功能、成员的教化功能减弱,从而给当地社会带来隐患。
(2)不关注公共事务。嫁入我国的外国媳妇由于语言、身份等方面的限制,因而生活圈子很小,活动范围往往仅限于与本村本地。一旦到了其他地方,没有护照和合法身份的她们简直寸步难行。没有乡镇选举权、民事知情权,也得不到社会保障,甚至连基本的社会身份都会遭到人们的质疑。由于无法拥有任何政治权利,因此她们对公共事务也并不关心。这就为边境地区计划生育等政策的落实和治安管理等工作的开展等造成困难。
(3)跨境婚姻家庭子女社会化面临困境。跨国婚姻中孩子母亲社会身份不明确,有可能因其自身及整个家庭社会地位较低,由此给儿童成长过程造成阴影。孩子可能会对合法与非法的概念模糊,进而面对非法入境、非婚生子、走私等行为缺乏应有的是非判断。另外,母亲的认同危机和子女能否拥有合法国籍等问题,是否会影响到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的文化认同,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此外,妇女的盲目外流与人口拐卖的现象不容忽视。人口的正常流动本是社会开放和发展进步的标志,但随着妇女大量外流与儿童被拐卖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愈益凸显。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境内外不法分子通过种种手段把边境地区的妇女儿童拐卖到邻近的东南亚国家,还有的则被拐卖到广东、河南、山东、河北、四川、湖南、内蒙古等省区。这就导致村社未婚青年性别比例失衡,适龄男子结婚成家面临巨大压力。这不仅极大地冲击了跨境民族或族群的传统婚姻习俗与家庭制度,而且已婚妇女的迁出导致了儿童被遗弃,并加深了已婚家庭夫妻间的不信任。
5.其他社会问题。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尽管跨境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快速发展,但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使得民族地区的发展仍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特别是边疆跨境民族地区为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生态环境保护日益成为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突出问题。由于少数民族或族群多聚居于经济弱县、财政穷县,因而经济结构单一,财政自给率低,自我发展能力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以普洱市为例,该区域内的拉祜族、佤族和布朗族地区因资金难筹集,达不到上级补助的配套标准,因此得不到切实需要的开发项目。因此,现在还有相当部分村社未通公路,而通公路的村社多数是晴通雨阻,难以满足群众的生产生活的需要。另外农田基础设施差,水利化程度低,仍然处在“靠天吃饭”的状况,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如西盟县仅有高稳产农田2.19万亩,人均不到0.5亩,水利有效灌溉只达到16.3%;①西盟佤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提供。孟连县水利化程度也只达到35%。在教育卫生事业方面的发展同样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为完成“普六”、“普九”和扫盲任务,大都是负债运转,严重影响了“普六”、 “普九”和扫盲成果的巩固,导致边境地区的佤族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4.26年,拉祜族仅为3.82年。②西盟佤族自治县教育局、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教育局提供。医疗条件滞后,初级卫生医疗条件难以保证;有的村寨没有卫生室,有的乡卫生院也缺少必要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医务人员水平低,难以保证少数民族群众初级卫生医疗的需要,少数民族群众看病十分困难。
二是生态的破坏。文化与生态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牺牲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盲目追求数字上的增长,其结果是迫使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随之发生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开始受到市场需求的深刻影响,非强制性的传统生态保护观念在追求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逐渐淡化。以笔者对西双版纳的调查为例,其生物资源的丰富闻名于世,如今,曾经广袤的热带雨林正面临着生物种类减少和水资源危机加剧的困境。究其原因是橡胶的广泛种植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海拔900米以下的热带雨林同时也是橡胶种植的适宜地带,于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近一半的热带雨林被毁,取而代之的是大面积种植的橡胶林。橡胶林在涵养水源等方面的生态效果远不如热带雨林,从而导致了区域内气候的干热化——雾气的减少和旱季的高温是最为明显的例子。[5]但是,在高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却并没有因此而反省;20世纪90年代胶乳价格的上涨再一次掀起了种植橡胶热潮。边民放弃了传统生产方式中蕴涵着天、地、人三者之间朴素的和谐观念,将凡是可以种树的地方都大力培植橡胶树,连不适合橡胶林生长的高海拔地区也都种满了橡胶苗。最终导致水库水位的下降、寨子远处的河水水量减少和寨边水沟的干涸,人们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吸毒与犯罪问题。众所周知,邻近云南的泰国、缅甸、老挝交界处是世界最大的毒品产地之一,毒品走私和毒品犯罪活动猖獗。近年来,跨境民族地区毒品交易、性病艾滋病等问题日益成为公害。首先,男子买不起毒品便想办法去偷去抢,女子买不起毒品就靠卖淫来供养自己吸毒。其次,吸毒和卖淫相结合,贩毒和嫖娼相结合,造成社会风气败坏。其三,由于吸毒者很多,使澜沧人谈毒色变,为社会动荡埋下隐患。其四,吸毒导致的女性艾滋病患者增加。吸毒贩毒、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死灰复燃导致的性病、艾滋病,严重危害着跨境民族或族群的身心健康与社会发展。
三
要实现云南跨境民族或族群文化的繁荣发展,就必须牢牢抓住当前的桥头堡建设这个大好机遇。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笔者认为至少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应当立即启动云南跨境民族或族群文化的繁荣发展工程,利用“软实力”维系边疆稳定。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源动力,是民族保持生命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全球化浪潮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课题。近些年来,云南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脱离文化原生地的保护与传承模式,譬如各类民办的民族文化与艺术的传习机构,以及公办的博物馆、剧团和文化艺术院校等。由著名作曲家田丰先生于1995年初创办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是脱离文化原生地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的典范;此外,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聘请少数民族民间艺人到学校为学生授课的方式,所实践的也是一种“脱离文化原生地”的保护与传承模式。另一种便是不脱离文化原生地的保护与传承模式,即主要在村寨或社区层面的传习。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云南省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目标以及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组织的“滇西北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等项目,均倡导不脱离原生地的保护与传承模式。丽江的宣科等一批纳西族民间音乐家对纳西古乐的传承以及傣族的寺庙教育也可以看作是不脱离文化原生地的传承模式。这两种模式虽各有利弊,但在实际工作中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都是非常有效的。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来自其与现实生活的相互影响,传承和保护本身也是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我们不妨尝试用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天人关系和价值取向来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就采取经济手段解决,文化的需求则采取文化手段进行弥补。我们不仅要通过政策宣讲和行政执法让百姓知道不能做什么,同时还要告诉大家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变强制性管理为积极引导和服务。要把当前已经启动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抢救工程、云南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精品工程等尽量统筹起来,并适当向跨境民族或族群地区倾斜,以尽快实现整个云南跨境民族或族群文化的繁荣发展。
其次,应当坚持以人为本,探索“自治+共治”的新路子。跨境民族或族群由于内部交流频繁,因而其身份认同感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他们会因政治环境、经济机遇和文化传统来选择自己更加倾向于哪一方:中国、外国或者索性是族群内部自我认同。因此,我们一定要营造更加适宜云南跨境民族或族群生存发展的宽松环境,增强其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同时,对目前一些民族身份划定尚存争议的族群来说,不应当急于求成地将其“归族”,否则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以及国际上的不良反应!我们要在认真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础上,坚持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民族区域自治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仅要有“民族自治”的基本立场,同时要有“区域共治”的全局观念。尤其是对那些自然条件较恶劣,生产水平较滞后的跨境民族地区,如果仅仅按照教条的标准 (如民族界限、人口多少等)作为落实政策的依据,不仅会导致我们的工作陷入僵化死板的困境,还会严重制约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基础上加入“区域发展”的维度:凡是有利于维护区域内稳定、有利于解决百姓民生问题、提高生活水平的都要优先考虑;自主创新,因地制宜,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6]。
其三,应当增强跨境民族或族群的主体性意识,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跨境民族或族群主体性意识是维护民族团结与边境稳定的重要因素。只有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他们积极参与到建设当中,才能有效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加快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最终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种主体性意识包括当家作主、自谋发展,更重要的是要树立中华民族的凝聚意识,使边民对中国公民的身份产生文化上的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不仅来自于经济上的优势,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综合体现。如云南跨境而居的苗族,无论是从族群关系、行政区划、还是居住地区的地理环境来看,他们都处于一种夹缝中生存的状态,其文化也带有夹缝中求得生存的特点。[7](P126)随着与其他民族或族群差异性的加大,其出现了逐渐边缘化、少数族群化的趋势。这就需要从实际出发,在政治上充分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或族群百姓的政治权利,使其从感情上确实接受我国的国体政体;经济上要改变以往仅仅依靠“输血”的机制,变政府“输血”为少数民族群众自主“造血”;文化上则需要帮助少数民族群众保护传承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要将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与每个民族或族群内部维系自身发展的地方性知识相结合,将地方性小传统与国家的大传统相结合,以期取得最佳效果!
其四,应当十分重视生态保护,合理开发文化发展的储备资源。随着过度的开发与不合理的利用,云南特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我们应当把民族文化生态建设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认识到民族文化生态建设并不单纯是由“民族”、“文化”以及“生态”三个概念简单地迭加构成,而是由在特定地区居住的特定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社会-文化因素构成的统一体,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制度文化的有机组合。民族文化生态建设就是要让人们在充分尊重自然界万事万物、尊重并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或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终极目的。民族文化中朴素的生态观,对维持跨境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非强制性的约束力,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根植于其价值观与宇宙观中。因此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宣传政策,更重要的是让边民充分认识到环保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使其积极主动的维护生存的环境。而对于已经造成破坏的环境,应当充分整合个人、企业、社区、政府资源进行治理。并根据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建立生态储备机制,更好地促进民族文化生态发展。此外,还应当不断促进文化交流,扩大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既大力弘扬云南跨境民族或族群文化的优秀文化,又要坚持对外开放,大力学习借鉴东南亚、南亚以及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要把云南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提高云南文化产品的知名度与竞争力,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
我国著名民族学、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文化自觉”的理念,主要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8]笔者认为,对于云南跨境民族或族群文化的繁荣发展来说,“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尤为重要。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我们既反对那种对某个民族、某种文化指手画脚、横加干涉的做法,也不赞同那种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漠不关心的态度。应当鼓励对本民族文化进行自觉的理性反思,辩证分析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因发展的紧迫感而探索创新意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打造有利于民族发展的软实力。当然,云南跨境民族或族群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中发掘、整理、保护、传承等方面的工作往往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缺一不可的。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更加频繁;若不把交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弱势文化就难免不被强势文化同化。因此,我们应当在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去理解、接纳、吸收不同的文化,并不断创新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努力形成各种文化之间互相取长补短,各展所长、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1]H.R戴维斯.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M].李安泰,和少英,等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2][越]阮维绍.老挝各族结构(越文版)[M].河内: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安东尼.R.沃克.泰国拉祜人研究文集[M].许洁明,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4]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5]张乃剑.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R].
[6]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5-28.
[7]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8]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