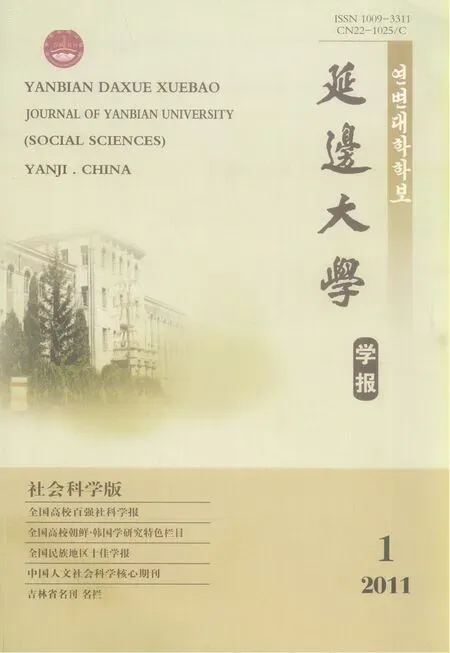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综述
2011-12-08井米兰
井 米 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上海200062)
朝鲜半岛与我国山水相连,借助这一地理位置优势,汉文化及其载体——汉字很早便传到了朝鲜半岛。作为最早进入汉字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以汉字为通用文字。俗字①是汉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汉字产生发展传播过程的始终。[1]而韩国俗字亦是汉字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变异形体之一。开展对韩国俗字的调查研究,运用国内外俗字理论和研究成果对韩国俗字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意义至少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可以弥补国内俗字研究之不足,总结汉语俗字异于国内俗字演变之新特点;二是可以完善汉语俗字理论,从而有利于建立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三是可以探寻出汉字传播发展之规律,推进当前的域外汉字研究、对外汉字教学、国家汉字规范化工作进程。
本文首先介绍汉字在朝鲜半岛传播、使用的状况,然后从当前韩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研究韩国汉字的现状出发,指出两国学者在韩国俗字研究方面的缺失和不足,以期为当前的韩国汉字研究和域外汉字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一、汉字在朝鲜半岛传播、使用的概况
汉字约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传入朝鲜半岛。“汉字正式输入的时间很难做出精确的考证,但公认一般在公元前2、3世纪时的战国时期。”[2]随后,约在1世纪左右,朝鲜半岛就已经出现了记录地名和国名的汉字。而在朝鲜古代三国时期的新罗时代,已经借用汉字来表示国名和官职名称。大约在6世纪左右,朝鲜半岛不仅输入了汉字,而且已经开始使用汉字标记朝鲜语音。“韩国学者普遍认为,汉字、汉文的正式传入时期应为卫满朝鲜建立的公元前195年前后,随着汉四郡的设立,以及汉民族向半岛的规模性移民,汉字、汉文逐渐在半岛普及开来。”[2]从高句丽时代起,中国的一些字书诸如《玉篇》、《字统》、《字林》等已经是贵族子弟的基本教材,而统治阶层的汉字、汉文水平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汉字真正在朝鲜半岛民间普及开来是由于汉传佛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尔后汉字一直是朝鲜半岛的通用汉字。直到朝鲜王朝世宗时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语言和文字不统一的标记方式,于1446年正式颁布“训民正音”,又被称为“谚文”。由此,朝鲜半岛有了自己的文字,但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官府的正式文书等仍旧使用汉语汉字。1895年,朝鲜进行了被称为“甲午更张”的改革,从这时起,其官方文书从专门使用汉字过渡到汉字与表音字结合使用,其后一段时期朝鲜半岛处于汉谚并用的局面。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期间,“训民正音”文字的地位迅速确立起来。1948年至1972年,汉字在韩国基本处于被禁用的时期。1945年,朝鲜半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一些表音字学者提出凡爱国者应全部使用表音字。1948年,韩国政府制订法律,规定公文全部使用表音字,只有公文的附加条款允许汉字与表音字并用。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很多参战青年读不懂混有汉字的教科书,韩国政府便在军队中统一使用表音字。1968年,韩国总统朴正熙下令在公文中禁止使用汉字,强行废除教科书中使用的汉字。从1970年起,韩国小学、中学教科书中的汉字被取消,完全使用表音字。然而,历史影响并不能被轻易抹掉,汉字毕竟已在朝鲜半岛传播了近两千年,鉴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韩国政府开始修改全面废除使用汉字的方针。1972年,韩国文教部颁布“教育法改正令”,规定在初、高中恢复汉字教育,并确定1800个“汉文教育用基础汉字”。1999年韩国的金大中总统在国务会议上宣布《推动汉字并用方案》,规定在政府公文和交通标志上恢复使用汉字和汉字标记。2005年,韩国政府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中国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世界化的时代潮流。近几年,随着中韩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以及“学习汉语热”在全球的演化,韩国年轻人学习汉字和汉语的比例已有较大上升。但由于韩国政府多年来对汉字的忽视,韩国人学习汉字和汉语的能力与汉字文化圈其他地区相比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可以说,汉字问题已成为韩国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现状
根据上文汉字在韩国传播使用的状况,我们可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至1972年韩国文教部颁布“教育法改正令”这一时段为界点,将韩国汉字分为韩国历史汉字与韩国近代汉字。汉字约在汉末传入朝鲜半岛,直到19世纪末,一直是朝鲜半岛的官方文字,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两千年。这其间,中国汉字在书体、书写介质、记录方式、形体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韩国历史汉字与这一时段的中国汉字有着相似之处。其中韩国俗字是韩国历史汉字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1972年韩国文教部颁布“教育法改正令”标志着韩国开始改变全面废除使用汉字的方针,此后出台的一系列汉字恢复政策,为学者们研究韩国近代汉字提供了素材。从地域来看,对于韩国汉字及俗字的研究又可分为中国、韩国两部分。下面我们以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整理研究概况与韩国近代汉字的研究概况两方面为纲,分别介绍韩国学者与中国学者所取得的成果。
(一)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整理与研究概况
1.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整理概况
材料的整理是开展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韩国学者对于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材料的整理,主要集中在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资料的辑录、文本的解读等方面。韩国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汉字为通用文字,因此韩国保留有大量的汉文典籍。原则上说,对于这些汉文典籍的整理,其实就是韩国历史汉字材料的整理。韩国学者对于这些汉文典籍的整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先有《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于 1981年出版,著录了韩国汉文典籍33808种。此后,全寅初教授主编的《韩国所藏中国古籍综合目录》于2005年出版,该书著录了现存韩国各图书馆的中国汉文典籍。另有一些韩国学者编纂韩国现存古书综合目录,并调查海外所存韩国古籍状况,如朴现圭的《台湾公藏韩国古书籍联合书目》、千惠风等的《海外典藏文化财调查目录·日本宫内厅书陵部韩国本目录》等。
与此同时,汉字在中国汉末至19世纪末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从书写介质上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段历史时期汉字的书写介质空前丰富,简牍、刻石、纸张等都已出现,依次充当了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的书写介质,呈现出由简牍向纸张过渡的趋势,而以纸张成功代替其他书写介质告终。同时,汉字在韩国传播使用时,亦在书写介质上有着与汉字在中国相似的变化。而韩国学者亦注意到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书写介质的不同,对不同书写介质的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进行了辑录与释读。如《新罗的文字》收录并释读了朝鲜新罗时期的简牍、金文、瓦当文、陶文、碑刻等书写介质上的汉文汉字资料。李基白的《新罗上代古文书资料集成》(一志社,1987年)较为全面地收录了自新罗到高丽王朝末年的许多古文书资料,而这些古文书资料有的是写在木简上的,有的则是印刷在纸张上的。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对部分古文书资料添加了释文与时代属性。与以上全面辑录简牍、金文、瓦当文、陶文、碑刻等各种书写介质的两部著作不同,亦有不少学者对其中某一书写介质上的汉字资料进行了辑录和解读。对金石文字进行辑录与解读的,如金锡夏的《丹阳真兴王赤城拓境碑解读文》(《史学志》1978年第12期)、南丰铉的《丹阳赤城碑解读试考》(《史学志》1978年第12期)、金煐泰的《三国新罗时代佛教金石文考证》(民族社,1992年)、任昌淳的《韩国金石集成》(一志社,1984年)、金福顺的《新罗石经研究》(《东国史学》2002年第37期)、金昌镐的《六世纪新罗金石文释读与分析》(庆北大学1994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等。对木简文字进行辑录与解读的,如李镕贤的《韩国古代木简研究》(高丽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朴仲焕的《韩国古代木简现状及其形态特征调查》(《鹿园杂集八》,2006年)等。
与以上诸多韩国学者对于韩国历史汉字的整理解读相比,韩国俗字的辑录与整理则显得相对薄弱。对韩国俗字进行专门整理的,如崔南善的《新字典》(大东印刷株式会社,1928年)附有俗字谱,崔南善可谓是对俗字关注最早的一位学者。韩国国立国语研究院在搜集各种传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韩国汉字的略字调查》(1991年)与《汉字略字调查》(1993年),收录包括以《韵会玉篇》(1536年)在内的5类字典以及与《三国遗事》(1512年)相似的一般文献1种,另外还有以《大慧普觉禅师书》(1512年)在内的与佛经有关的资料等写本俗字资料。李圭甲的《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高丽大藏经研究所,2000年)对传入韩国的佛经中的异体字进行了整理与释义,其中辑录了部分韩国俗字。其他另有一些单篇文章整理了部分韩国俗字,如任昌淳的《韩国的印本与书体》(《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4集,(大邱)岭南大民族文化研究所,1983年)辑录了坊刻本《大学》中的部分俗字。柳铎一的《朝鲜文献使用的半字》(《韩国文献学研究》,亚细亚文化史,1989年)在强调对坊刻本俗字进行关注的同时,辑录了部分坊刻本俗字。河永三的《朝鲜后期民间俗字研究》(中国语文学第27辑,1996年)辑录了坊刻本《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中的部分俗字。
与韩国学者相比,中国学者对于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材料的整理则显得非常薄弱。虽然有中国学者对韩国汉文典籍进行了整理,如李仙竹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代朝鲜文献解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黄建国等的《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等对中国所见部分韩国汉文典籍进行了整理,但规模远远比不上韩国学者。另外,几乎没有中国学者专门整理韩国简牍、金文、瓦当文、陶文、碑刻等书写介质上的汉文汉字资料。而对于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进行整理的亦是非常少,当前所见中国学者对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进行过系统整理的仅有台湾学者金荣华先生。金先生对韩国抄本俗字进行整理辑录成《韩国俗字谱》[3],并于1986年出版,该书对韩国的写本材料俗字进行了整理,编者根据33种韩国写本汉字材料,以《康熙字典》为正字,于1712个韩国写本俗字单字之下分列俗字字样3780个。其他单篇文章中亦有提到韩国俗字的,如王晓平的《从〈镜中释灵实集〉释录看东亚写本俗字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提到了韩国俗字,并将东亚写本俗字与敦煌俗字对照来写,但只是摘取部分俗字;吕浩的《〈物名考〉异形字及相关问题》(《韩国汉字研究》第1辑,2009年)亦举出了一些韩国抄本俗字,但数量非常有限。
2.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研究概况
有了材料做基础,开展相关研究则相对来说容易许多。在中国汉末至19世纪末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从书体上看,汉字经历了隶变、楷化等阶段,出现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各种书体,并最终形成了以楷书为主、各书体兼备的局面。从记录方式上来看,汉字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以手写为主,即使是刻在碑石上的文字亦是以书写体为蓝本的,宋元以后,版刻书籍盛行流传,此时汉字的记录方式已经由手写转为版刻。从汉字形体来看,虽然这一段历史时期汉字从未走出异体层出不穷的局面,但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汉字形体趋于整合定型的趋势。韩国学者亦注意到韩国历史汉字与汉字在中国相似的情况,虽然很少有人对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但还是有部分学者对韩国历史汉字的书体及俗字形体进行研究。对韩国历史汉字书体进行研究的,如孙焕一的《新罗赤城碑书体I、II》(《泰东古典研究》1999年第16期、2000年第17期)与《新罗时代书体研究》(檀国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两篇文章专门讨论了朝鲜新罗时代的书体问题。对韩国俗字进行研究的,如上文我们提到的任昌淳的《韩国的印本与书体》以坊刻本《大学》之俗字为研究对象,指出坊刻本所具有的保存丰富俗字材料的重要特征;柳铎一的《朝鲜文献使用的半字》强调了对坊刻本俗字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指出应对坊刻本俗字进行分类,并揭示了其主要特征;河永三的《朝鲜后期民间俗字研究》对坊刻本《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中的部分俗字进行了研究,并总结出坊刻本俗字具有的特征:简化是其最明显的特征、形声结构的兴盛、突出反映朝鲜之文化内涵、反映汉字所依托的独特载体。
与韩国学者不同的是,中国学者较少研究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的书体问题,关注更多的则是对其文字形体的研究。如张成、姚永铭的《〈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文字研究》(《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1期)指出《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中的一些文字字形非常奇特,在分析字例的基础上,指出其文字字形一方面承继汉字在中国的字形而来,另一方面发生了一些异于中国本土汉字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于补充汉语汉字资料,探求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王华权的《〈一切经音义〉(丽藏本)刻本用字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届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一切经音义》(丽藏本)刻本用字的讹误、相混、相通等情况,继而分析该刻本用字的构形类型及特点,指出该刻本用字具有构形异化、无理据性等特点。另有王平教授的《韩国朝鲜时代〈训蒙字会〉与中国古代字书的传承关系考察》(大韩中国学会主编《中国学》第32辑,2009年)将《训蒙字会》置于中国字书的行列之中为之定位,根据其成书于宋本《玉篇》之后、明代《字汇》之前,应与宋本《玉篇》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同时指出朝鲜时代教育用汉字具有字收常用、形从简化、义取通俗的特点。亦有部分学者注意到韩国历史汉字中存在的俗字,并对其进行了局部研究,如上文提到的王晓平的《从〈镜中释灵实集〉释录看东亚写本俗字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提到了韩国之俗字,并将东亚写本俗字与敦煌俗字进行了对照,指出东亚写本俗字与敦煌俗字在字形方面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吕浩的《〈物名考〉异形字及相关问题》(《韩国汉字研究》第1辑,2009年)举出了一些韩国抄本俗字具有异形、异构等特点,在分析相关俗字字例的基础上,得出《物名考》异形字具有字形丰富、主形与异形并存等特点。
(二)韩国近代汉字范围与研究概况
1.韩国近代汉字范围
韩国近代汉字主要指1972年韩国文教部颁布“教育法改正令”之后,韩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针对韩国国内民众使用汉字的方针政策中所颁布的汉字。主要有:1972年,韩国教育部公布的1800个初、高中“汉文教育用基础汉字”及4182个汉源汉字词;1987年韩国文教部选定的教育用《常用汉字表》收录的1800个常用汉字以及韩国工业标准《KSX1001:1992信息交换用字符集》收录的4888个汉字。而中国教育部、国家语委于1988年颁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的2500个汉字及其后附的1000个次常用汉字、2006年颁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7000字等也为研究韩国近代汉字提供了参照。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当前“汉语学习热”的潮流,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来中国学习汉语汉字知识。其中亦有许多韩国留学生,由于这些韩国留学生所学习的汉语汉字知识为中国当前所使用的现代汉语与规范汉字,因此韩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期间所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与规范汉字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对外汉语教学人员所发表的关于韩国留学生汉语汉字教学的研究成果均不属于韩国近代汉字的讨论范围。但将韩国近代汉字的音、形、义与中国规范汉字进行比较研究的一类研究成果是属于韩国近代汉字的研究范围的,而这亦是韩国近代汉字研究的特色。
2.韩国近代汉字研究概况
韩国自1972年以来实行与颁布的一系列汉字教育政策,掀起了韩国国内研究教育用汉字的高潮。如赵国基的《教育用基础汉字研究——以中高等学校教科书为中心》(成均馆大学校教育大学院1987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当前的中高等学校教科书应注重汉字教育,并提出教育用基础汉字的可行性方案。沈庆昊的《关于初等学校汉字教育的当为性研究》(仁荷大学校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当前初等学校开展汉字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韩国政府着力推行汉字教育的基础之上,越来越多的韩国学者将韩国的汉字教育置于汉字文化圈之内进行考察,而这些学者大多是韩国高校毕业生,目的多在于通过考察汉字文化圈内其他国家的汉字教育政策,为韩国当前的汉字教育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如金太汉的《汉字文化圈内教育汉字比较研究》(忠南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比较研究了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中国等国所颁布的教育汉字在字量、字形方面的异同。权善玉的《韩中日常用汉字比较研究:以字数、字意为中心》(庆熙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专门以韩中日三国的常用汉字为考察对象,主要考察了各国常用汉字在字数及字意方面的差异。与权善玉文章相似的还有李允子的《韩中日教育用常用汉字比较研究》(淑明女子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朴贞爱的《韩国教育用基础汉字和中国现代汉语常用汉字比较研究》(淑明女子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此外,还有部分韩国学者专门研究了韩国固有汉字,如金钟埙的《韩国固有汉字研究》(集文堂,1983年)、河永三的《韩国固有汉字的比较研究》(《中国语文学》第33辑)和《韩国固有汉字中“国”字之结构与文化特点》(《韩国汉字研究》第1辑,2009年)等,内容多讨论韩国固有汉字的产生方式、原因以及由此而反映出来的韩国特有的文化历史特色。
与韩国学者不同,中国学者在研究内容方面更加注重对韩国近代汉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的研究,研究时多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因韩国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期间所完成的毕业论文由中国高校教师指导完成,所以我们将其看做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关注中韩汉字形、音、义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朴点玉的《韩国和中国现行汉字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将韩国“教育用基础汉字”与中国《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字进行比较,得出中韩共同使用的汉字为1799个,并将1799个汉字分为三种情况:韩中字形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汉字;韩中字形有繁简差别的汉字;在有异体的字形中,韩中所选用字不同的汉字。此外,亦对中韩两国现行汉字的字形、笔画数、笔顺、部首以及归部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指出韩中汉字字形统一工作有待继续深入进行下去。田博的《汉字在韩国的传承与变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比较了韩中汉字在字形、字音、字义及语素功能方面的差异,并由此总结出了差异特点和规律。另有一些研究成果关注中韩汉字形、音、义三个方面的某一方面。如任少英的《韩国汉字音与普通话声调的对应关系》(《汉语学习》2003年第3期)指出现代韩国汉字音中的次浊入声字与汉语中古音以及普通话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赵美贞的《韩国汉字音中的汉语上古音》(《民族语文》2005年第5期)指出当前的韩国汉字音有些来源于中国汉语上古音。吴海娟的《韩中现行汉字字形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在朴点玉论文的基础之上,摘取两国汉字的字形进行专门研究,举出43组中韩汉字进行字形比较,指出当前的韩国汉字字形多使用繁体或旧体,而中国规范汉字则注重对简化了的汉字的吸收。徐新伟的《中韩汉字比较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对中韩汉字的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共同音节、部首归部等差异进行了研究,由此指出当前韩国学生在汉字字形学习方面的缺点及其改进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亦有中国学者将韩国近代汉字的研究置于汉字文化圈之内进行研究,但目的却与韩国学者不同,中国学者更加注重汉字文化圈内汉字字形统一、汉字简化统一方案以及如何帮助汉字文化圈内中国以外学生学习汉语汉字等问题。如裘锡圭先生的《浅说汉字文化圈内的汉字异形的问题》(韩国汉字讨论会论文,1994年)指出当前汉字文化圈内各国汉字存在异形的情况,应将其置于整个汉字文化圈内予以统一。刘世刚的《中、日、韩三国汉字一体化的初步设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通过中、日、韩汉字的历史沿革和使用现状申述汉字的重要功能及其简化进程的一体性。李炬、李贞爱的《汉字中日韩朝文化之基石》(《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指出汉字对日本、韩国、朝鲜的文字、语言和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金红月的《中、韩、日三国汉字简化字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三国汉字简化字在字形、字音和字义方面的差异,指出三者的差异是造成交流困难的主要原因,由此提出对三国统一规范汉字简化字的愿望。邵文利、杜丽荣的《推动中韩汉字“书同文”的一个重要举措——韩国韩中文字交流协会选用的606个简体汉字》(《学术界》2007年第2期)分析了韩国1800个教育用基础汉字中的606个简体汉字与中国规范汉字的具体对应关系,阐述了韩国学术界启用606个简体汉字对于汉字文化圈国家实行汉字“书同文”的重要意义。另有潘先军的《汉字基础在韩国留学生汉语学习中的负迁移》(《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指出韩国学生本身所具有的韩国汉语汉字基础对于其学习中国汉语汉字具有一定的误导作用。
三、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的缺失与不足
经过韩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韩国汉字及俗字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缺失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不容忽视。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对韩国历史汉字和俗字材料的系统整理。虽然韩国学者对历史汉字资料的整理和辑录成就远远超过中国学者,但韩国学者对于汉文化、汉字知识的缺乏却是其整理研究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中国学者虽具有深厚的汉文化、汉字底蕴,但由于地域、国别等的局限,难以长时期从事韩国古代典籍汉字的整理研究工作。而能够关注到韩国古代典籍俗字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有必要积极推进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为两国学者共同合作完成韩国古代典籍汉字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开辟途径。
第二,当前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的不平衡性。首先,中韩两国学者多注重对现当代韩国汉字的研究,很少有人关注韩国历史汉字材料,特别是对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材料进行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其次,对韩国历史汉字及俗字来说,当前的研究多是对其进行材料整理,缺乏对其在汉字理论基础之上的系统研究;同时当前的材料整理多注重对简牍、金石等载体之上的汉字及俗字的整理,很少有人关注宋元以后版刻汉字及俗字材料的整理。再次,对韩国近代汉字来说,韩国学者多从韩国汉字教育的角度进行研究,很少有人全面关注韩国近代汉字的形、音、义等,中国的学者则缺少从汉语言文字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第三,缺乏在文字学理论基础之上对汉字域外传播途径及规律的探讨。韩国俗字是汉字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变异形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掌握了韩国俗字的主要变异类型及特点,也就间接掌握了汉字在韩国传播的规律和特点,而这些对于弥补国内俗字研究、完善汉语俗字理论、完善汉字发展传播史,都有着积极的意义。通过上文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当前学者对于在文字学理论基础之上对汉字域外传播途径及规律的探讨几乎是空白的。
第四,缺乏对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充分运用。韩国贮存有丰富的古代典籍汉字材料和俗字材料,只有通过计算机技术的运用,才能对其进行完整录入、系统整理、深入研究。虽然韩国政府所推行的汉字政策中的汉字是比较确定的,但将其与中国汉字进行全面系统比较研究之时,亦必须依靠计算机技术进行相关数据分析。
注释:
①根据相关研究,俗字指写法有别于官方制定之正字,乃经约定俗成而通行于当时社会,且易随时、地不同而迁变之异体字。首先,俗字是与官定正字相对而言的。其次,俗字是“经约定俗成而通行于当时社会”的。“约定俗成”是说俗字是与正字写法相异且经过人们传习相效通行于社会的字形。“通行于当时社会”则是说俗字的使用是遍布社会各阶层的。再次,俗字是“易随时、地不同而迁变”的。这里是说俗字的使用是有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的,因此俗字也就随着时代和地域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最后,俗字是异体字。“一切俗字都是异体字,俗字是异体字的主体”、“异体字并非都是俗字”。具体请参阅拙作《俗字之名义及其相关问题》(《岱宗学刊》,2010年第1期)。
[1] 井米兰.敦煌俗字与宋本《玉篇》文字比较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 陈榴.东去的语脉——韩国汉字词语研究[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10.
[3] 金荣华.韩国俗字谱[M].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