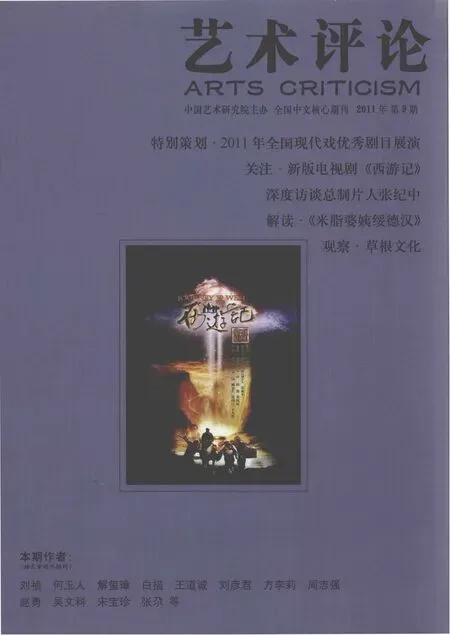“移情”之辨:从“伯牙学琴”说起
2011-11-21丁朝虹
丁朝虹
“伯牙学琴”的故事见于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水仙操》,文为:“旧说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而成。至于精神寂寞,情志专一,尚未能也。成连云:‘吾师子春在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延望,无人。至蓬莱山,留伯牙曰:‘吾将迎吾师。’划船而去,旬时不返。伯牙近望无人,但闻海上汩没崩澌之声,山林,群鸟悲号,怆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之。曲终,成连刺船而还。伯牙遂为天下妙手。”这是春秋时期的著名琴师伯牙学琴的一段经历,老师成连带他到海上进行“移情”,之后他琴艺大长终成名家。这故事自诞生以后引发了许多人的思考,特别是音乐爱好者和创作者,对于这段佳话最是津津乐道。其感兴趣无非在于,伯牙作为一个艺术家,当他的进步处于瓶颈状态时,是经由一种神秘的“移情”而实现了突破,那么究竟什么是“移情”呢?
一
伯牙向成连先生学琴,三年后学有所成。但他的老师认为他还有不足,要带他拜访自己的老师子春先生。成先生到底认为他有哪些不足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伯牙甚至已经到了精神虚静、情志专一的地步,但还是没有学成[1];另一种说法是,伯牙的精神、情志始终未能专一,所以还没有学成。这两种说法显然是对“至于精神寂寞,情志专一,尚未能也”理解不一,前者把“至于”理解为动词“到达”,后者把“至于”理解为介词“关于”,从训诂的角度来看都没有问题。但究竟哪种理解更合乎故事的本义,我们需要联系上下文来考察,因为这涉及到古人对于艺术创作核心的理解。
成连向伯牙推荐子春,原因是他能“移情”,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伯牙尚未“精神虚静、情志专一”,那么这将成为“移情”的目的,也就是说,伯牙“移情”是为了实现“精神虚静、情志专一”。如此看来,对“至于精神寂寞,情志专一,尚未能也”的理解也将影响对“移情”的理解。
那么什么是“精神寂寞,情志专一”?这是源于道家的说法。先说“精神寂寞”,庄子曾说:“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也。”(《庄子·天道》)在老庄看来,心境的空虚和休静是心灵充实和活动的前提,所以“虚静”、“寂寞”等乃是万物的本源。而“情志专一”, 是庄子对“心斋”的解释:“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所以“情志专一”就等同于“虚”,也就是空明的心境。总之,“精神寂寞,情志专一”是指一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心理状态,其特征是“无己”、“丧我”。道家认为,这是领会“道”所必需的心理条件,在道家学说中,与之同义的还有“心斋坐忘”、“虚静”、“涤除玄鉴”等。从美学角度看,这种心理条件又被称为“审美心胸”,是审美发生的前提,“心斋、坐忘,正是美的观照得以成立的精神主体,也是艺术得以成立的最后根据。”[2]因为人一旦排除了实用欲望和道德追求,就能以虚而待物的心态与万物相沟通,达到物我两忘、主客合一的审美境界。
被成连带到海上,经历“移情”之后的伯牙是怎样的心境呢?故事里没有直接形容,只说“但闻海上汩没崩澌之声,山林,群鸟悲号”,这是说伯牙已经忘记了自己,忘记他来学琴的目的,忘记他对功名的渴望,正是这种“虚而待物”的心理,大自然才能无碍地映照入他的心灵。此时伯牙感到海水澎湃波涛汹涌,山林里光线幽暗,群鸟呼号,他看到了一派意象融凝的世界:一方面,自然本身“质有而趣灵”,体现着造化之美;另一方面,大自然被伯牙的心灵照亮,它并不是单纯的海水、山林和群鸟的叠加,而是一个整体的有情的世界,是被伯牙的情改造过的世界。事实上,这只是伯牙眼中的自然,是有此情方现此景,反过来,非面对大海也不会产生伯牙之情,是“情以物迁”,是有此景方有此情,故此刻是此情与此景的高度融合,是物我合一同时也是物我两忘,如果这就是伯牙此时的心境,那么就证明他进入了一种审美状态。据此我们可以判断,“至于精神寂寞、情志专一,尚未能也”,并不是说伯牙已经到了精神寂寞、情志专一的地步,而是指“尚未能”达到这一地步,伯牙到了海上经过移情后才具备了这种虚静的审美心胸。更进一步地,这个故事中的所谓“移情”,就是指改变人的性情,使之进入审美状态。
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内心与外境,非能一往相符会,当其窒塞,则耳目之近,神有不周;及其怡怿,则八极之外,理无不浃。然则以心求境,境足以役心;取境赴心,心难于照境。必令心境相得,见相交融。斯则成连所以移情,庖丁所以满志也。”缺乏审美心胸,就是处于一种“窒塞”的状态,而“移情”的目标是求得内心与外境“见相交融”,实现物我两忘,进入审美状态。庖丁是《庄子·养生主》中的一位厨师,他在宰牛方面技艺高超,甚至能做到“动刀甚微,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其诀窍在于在宰牛时“未尝见全牛”,这样他与牛的对立消解了,内心与外境高度融合,因而能“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他获得了超越心与物对立所带来的充实感和自由感,这就是成连要为伯牙移情的原因,即必当如此才能获得艺术创作的自由感,才能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
二
自西方“移情说”传入中国后,伯牙学琴故事中出现的“移情”引起了很多争论。有人认为,中国没有专门用作审美的“移情”,包括伯牙学琴中在内的“移情”,都是指“转移人之性情”,并特别指出,它与西方“移情说”风马牛不相及[3]。因此,“移情”这个美学范畴,如果从美学体系的角度来考察,应当被划入到作品功能论而不是审美论部分。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移情”说出现得比西方的早,中国很早就把握了审美过程中的特殊心理,比如伯牙学琴中的“移情”就是指一种“心”与“物”相互交融的审美过程[4]。
事实上,中国出现“移情”这个词语确实比较早,比如《后汉书·仲长统传》里的“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意为以教化变易他人的情感心志。梁任《王文宪集序》:“公不谋声训,而楚夏移情”,《文选》张铣为其注为:“言不作声誉教示,而下人感其道德,已移情于善道矣。”指不通过言语,以行动感化人使人向善。就这些“移情”来看,确实不应该看作审美范畴,就“移情”的结果而言,它不以审美标准而以道德标准来判断,指向善而非美。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移情”(它们有时也作“移人心”、“移我情”或“移人情”),或者强调自然山水或者强调文学艺术对人的影响,如唐皎然《观王右丞维沧州图歌》:“丹青变化不可寻,翻空作有移人心”,清代沈谦《填词杂说》:“词不在大小深浅,贵在移情。‘晓风残月’,‘大江东去’,体制虽显殊,读之若身历其境,倘迷离,不能自主,文之至也。”都是指艺术作品使人感动,如使人跨越时空,如使人身临其境;而唐代王勃《武山赋序》有:“怀霄汉之举而忘城阙之恋……泉石移情,秋阴方积,松柏群吟,悲声四起,背乡关者无复顾向时之荣焉。”清代乾隆皇帝《枕峦亭》诗:“岂不在城郭,居然谓林。移情咫尺间,濠濮夫何有?”则是指自然山水对人性情的陶冶,如使人忘却世间烦忧。这些“移情”虽然也是改变人的性情,但它们显然与教化移情有本质区别,因为就“移情”结果而言,它们更看重其使人“不能自主”,也就是进入忘我之态,以审美标准而非道德标准进行评判,最终是指向美而非善或真的。
不过中国的“移情”是不是真正触及到审美心理,还有待存疑。虽然上文提到沈谦将“移情”的过程解释为“读之若身历其境,倘迷离,不能自主”,似乎“移情”过程就等同于审美过程。但是大部分关于“移情”的论述,即使在谈到文艺作品的感人功能时,还是侧重谈它对改变人之功效而不是审美过程。比如金圣叹在《西厢记》中有评点说:“夫枚乘之《七》治病,陈琳之《檄》愈风,文章真有移换性情之力。”西汉赋家枚乘的《七发》治好了楚太子的病,汉末名士陈琳的讨伐檄文也治愈了曹操的头痛,所以金圣叹感叹,好的艺术作品的“移情”功效,不亚于药物对人的改善。由此,至少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移情”说没有自觉且系统地探讨审美的心理,就艺术作品的“移情”而言,它倾向于将有没有“移情”作为一种评价机制,来描述艺术的感人功效;而就自然的“移情”而言,它看重自然对人的人格修炼和艺术修养所产生的巨大的、关键的作用,它不是审美本身,而是审美的前期准备,伯牙学琴中的“移情”就是如此。
宗白华先生在《美从何处寻?》中提到伯牙学琴的故事时说:“伯牙由于在孤寂中受到大自然强烈的震撼,生活上的异常遭遇,整个心境受了洗涤和改造,才达到艺术最深的体会,把握到音乐的创造性的旋律,完成他的美的感受和创造。这个‘移情说’比起德国美学家栗卜斯的‘情感移入论’似乎还要深刻些,因为它说出现实生活中的体验和改造是‘移情’的基础呀!并且‘移易’和‘移入’是不同的。”宗先生认为中国的“移情”就是:“把整个情绪和思想改造一下,移动了方向”,它是审美的心理方面的积极因素和条件,在主观心理方面的准备,而不是审美本身。
三
前文提到,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推论,伯牙当时学琴的困境就是尚未能进入“精神寂寞、情志专一”的状态,而“移情”就是破解这一困境的方法,它要求创作者努力使理性与欲望沉息,从而达到物我合一的状态。其实在中国道家的著作特别是庄子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这一艺术创作的前提。除了上面提到的“庖丁解牛”,“梓庆削木为”、“佝偻者承蜩”、“善泳者操舟”以及“以瓦砾作注”等寓言故事,都是强调需精神集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所以“移情”,也就是梓庆所说“静心”,也就是佝偻者所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这正是伯牙突破琴艺的关键所在。
这一结论对于熟悉西方“移情”说的人来说,是不容易接受的。西方的“移情”,根据立普斯的概念,是指一种过程,是“我们把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的力量感觉,我们的努力、意志,主动或被动的感觉,移置到外在于我们的事物里去。”[5]也是人(自我)作为主体,将自己的情感灌注到自然万物,从而将对象化的自我作为欣赏对象的一种过程。所以从西方审美理论的角度来看,创作和审美的源头在于主体有足够的情可以向客体投射。这样在许多介绍“伯牙学琴”的故事,特别那些是把它当作创作秘诀来传播的解读中,伯牙的困境源于“少情”,故而“移情”就被解释为外物为人赋予情。从一定程度上说,前文提到的将“精神寂寞、情志专一,尚未能也”作“甚至到了精神寂寞、情志专一的程度,也还是没有学成”解的这种说法,对以上误读有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美学的一些区别。由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性质,自然是被看作有情的主体,因而不存在单向的人向物的“移情”,而只有人与物之间平等状态下的交流与感应。另外,在中国传统美学中,被认为是制约创作的重要因素不是来自于审美主体本身有没有情,而是能不能进入审美情境,也就是能不能达到主体与客体(物我)合一的境界,获得创作的自由感。清代刘熙载在《伯牙待成连图题辞》中说:“成连以琴教伯牙,三年。当是时,若惟知有琴也者,然而,伯牙之情未移,是合而未免于离也。及至之海上,忽然别去,当是时,若不知有琴也者,然而伯牙之情移,是离而适得真合也。”伯牙初学琴时,满脑子都是琴,这时他是不自由的。虽然他弹琴的技巧可能很高了,引文说“三年而成”就是这个意思。但只有技巧的娴熟是尚处于低级的“匠”的阶段,因为“巧”不如“拙”,“技要进乎道”,才能为“天下妙手”。而要领会“道”,就得经过“心斋”、“坐忘”,非要经历一个“堕肢体、黜聪明”的阶段,到海上伯牙终于学会了“忘我”,当然也忘记了琴,却因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而不再感到琴对他的限制,所以此时与琴的关系是“似离真合”了。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西方哲学在完成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向后,有不少美学家借用主体间性理论对主体性美学进行修正。其中梅洛·庞蒂就提到,没有创作就没有创作主体,创作主体不能由日常生活来界定,创作主体只是在创作那个阶段的主体,他只存在于那个特殊的阶段。因此既没有创作之前的审美主体的自在自足“情”,也没有独立存在的“景”,它们的意义只存在于创作之中,创作的奥秘就在二者的结合中。而这,也正是伯牙学琴这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
* 此文为2010年度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基于主体间性的中国传统美学研究”(项目编号y201016033)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1]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译注(增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552页。
[2]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3] 分别参见成复旺:《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683页,杜黎均:《中西审美移情比较》,《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3期,黄海澄:《“移情”新探》,《文学评论丛刊》第24期。
[4] 参见胡雪冈《我国古代美学的“移情”说》,《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
[5] [德]立普斯:《论移情作用》,转引自《西方文艺理论译丛》第8辑,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