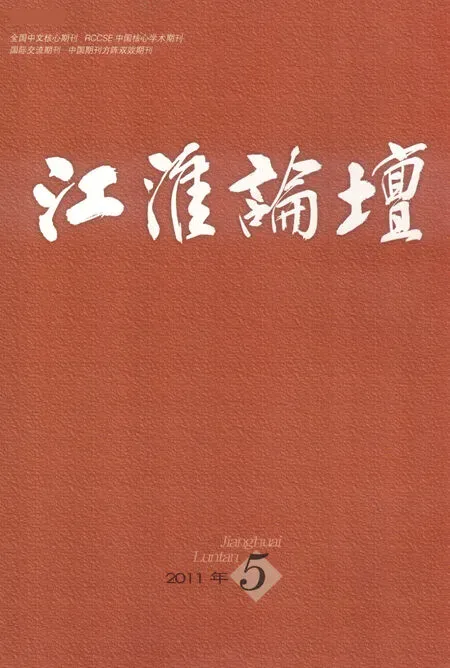方苞的文论思想及其散文创作特色*
2011-11-21江小角
江小角
(安徽大学历史系,合肥 230039)
方苞的文论思想及其散文创作特色*
江小角
(安徽大学历史系,合肥 230039)
方苞作为桐城派的创始人,一生注重名节,身怀天下之志,主张经世致用,体察下情,关注民生,这些对桐城派中后期代表作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也是桐城派之所以能绵延几百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方苞"义法"说的文论思想,为桐城派文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影响久远。方苞的散文创作实践,是以他自己创立的文论思想为指导,体现出文章布局结构严谨,创作内容讲究取材的多样性和典型性。其散文创作特色,主要表现为叙事简洁传神,说理透彻新颖,语言质朴雅洁,写人生动形象。因此,从方苞的创作实践来看,他也堪称为桐城文派之正宗与楷模,为后世桐城派作家树立了典范。
方苞;文论思想;清代散文;创作特色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世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姚鼐说:“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百馀年文章之冠,天下论文者无异说也。”[1]904袁枚称方苞为“本朝古文之有方望溪,犹诗之有阮亭:俱为一代正宗”。[2]因此,方苞历来被认为是桐城派的创始人,对桐城派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人称:“昔有方侍郎(方苞),今有刘先生(刘大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方苞是明初四川断事方法的裔孙。曾祖象乾,官副使,避寇侨居江苏上元(今南京市)。祖帜,字汉树,号马溪,岁贡生,有文名,官至兴化县教谕。父仲舒,字南董,号逸巢,国子监生,诗人。赘于六合吴氏,故方苞生于六合留稼村。其时,方氏家境衰落,因此他说:“余家贫多事,吾父时拂郁,旦昼嗟吁。吾母疲疴间作。”“余先世家皖桐,世宦达。自迁江宁,业尽落。宾祭而外,累月逾时,家人无肉食者,蔬食或不充。 ”[1]504“家无仆婢,吾母逾五十,犹日夜从灶上扫除,执苦身之役。”[1]502他在为胞弟椒涂写的墓志铭中,也道出了其童年时代的家庭环境,他说:“自迁金陵……数岁不瘳,而贫无衣。有坏木委西阶下,每冬月,候曦光过檐下,辄大喜,相呼列坐木上,渐移就暄,至东墙下。日西夕,牵连入室,意常惨然。”“兄赴芜湖之后,家益困,旬月中屡不再食。 ”[1]497
方苞很小就随父迁至上元城内土街。时黄冈杜睿、杜岕兄弟皆寓于江宁(今南京),桐城钱澄之、方文亦时往来,与仲舒常相唱和。方苞说他“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1]174-175方苞20岁左右,外出授徒,往来江淮河济。康熙二十八年(1689),方苞获岁试第一,补桐城县学弟子员,受知于学使高裔。23岁应乡试,即遭落榜。后随高裔去京师,游太学。其文章得到李光地等人的赏识,同时得交前辈学者、史学家万斯同,钻研经学。在刘言洁、刘拙修等人的影响下,读研宋儒之书,遂倾心程、朱之学。以致他在25岁时,与姜宸英、王源论行身祈向时说:“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所崇奉的准绳。此后几年,他在涿郡、宝应等地开馆授经,曾两次参加顺天乡试,均遭落第而南归。康熙三十八年,在他32岁时,举江南乡试第一。次年至京师,后两次参加礼部考试,均未及第。在京城结交思想家李塨,并与李交谈,因学术观点不合,旋即南归。康熙四十五年,即其39岁时,再至京师,应礼部试,中进士,位列第四。就在将要参加殿试授官之际,方苞闻母病遽归,失去殿试夺魁的机会。
康熙五十年(1711),是方苞一生的转折点。这年冬十一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上奏康熙皇帝,以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语多狂悖”为由,弹劾戴名世。方苞因给该书作序,牵连被逮下狱。康熙五十二年,“《南山集》案”狱决,方苞被判死刑,只因“圣祖一日曰:汪霦死,无能古文者。”李光地等人极力营救,因此回答皇上说:“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因而他蒙皇恩赦免释放,出狱隶籍汉军。三月二十三日,康熙皇帝谕旨:“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1]515旨下武英殿总管和素。第二天,方苞被召入南书房,几天之内,先后撰写《湖南洞苗归化碑》文、《黄钟为万事根本论》、《时和年丰庆祝赋》等,每次呈奏康熙帝,都受到赞赏,以为“此赋,即翰林中老辈兼旬就之,不能过也”。[1]515此后命以白衣(即无功名而替官府当差的人)入直南书房。但其家人因受《南山集》案的牵连,仍全部没入旗籍。
从《南山集》案蒙皇恩赦宥,入直南书房,方苞开始了他30余年的官宦生涯。作为皇帝的文学侍臣,他移直蒙养斋,教授诸皇子,编校乐、律、历、算等书,潜心于《春秋》、《周官》研究,撰写《周官辨》、《春秋通论》、《周官析疑》、《容城孙征君年谱》等书。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开始,他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等职达十年之久。
雍正皇帝即位后,对以张廷玉为代表的桐城学人非常信赖,垂爱有加,这也使方苞的政治处境较康熙朝有了进一步改善,方苞合族均被赦归原籍。雍正九年,方苞64岁,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后迁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讲学士,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一统志馆总裁,奉命校订《春秋日讲》。雍正十三年正月,充皇清文颖副总裁;九月,高宗乾隆皇帝继位,有意对方苞委以重任。乾隆二年六月,擢礼部右侍郎,方苞仍以足疾辞;乾隆六年冬,《周官义疏》纂成,进呈皇上,留览兼旬,一无所更,下命刊刻;第二年,方苞年届75岁,以时患疾病,乞解书局之职,回家安度晚年,乾隆帝许之,并赐翰林院侍讲衔。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卒于上元里第,享年82岁。
方苞作为桐城派的创始人,一生注重名节,身怀天下之志,主张经世致用,体察下情,关注民生,这些对桐城派中后期代表作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也是桐城派之所以绵延几百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的文论思想,不仅对后世桐城派作家的创作指明了方向,而且给清初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以“义法”说为核心的文论思想
“义法”说是方苞文论思想的核心,也是桐城派文论形成的基石。他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1]58这里方苞把《易经》作为他“义法”说立论之本,这不仅抬高了“义法”说的地位,而且也明确指出了“义法’说中“义”与“法”的统一,“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即内容与形式要相符合。也就是说“义”包含在“法”之中,而“法”又是“义”的具体表现。因此方苞以“义法”论文,不仅注重文章的义理精当、深刻,而且要求作文必须遵循文章的体例和写作的规则,如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以及遣词造句的要求等问题。所以说,方苞“义法”说的文论思想为桐城派文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影响久远。
第一,方苞“义法”说形成的历史背景。首先,方苞“义法”说的产生,是匡正时代文风的需要。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王朝更迭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学术思想开始剧变的时期。文人士大夫多半经过农民革命和满族入关的巨变,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浪潮的冲击,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或奋起反抗,或归附于清;或削发为僧,隐迹山林,寄情山水。在文学创作方面表现为:一是重道轻文;二是空洞无物,无病呻吟,摹仿之风越演越烈。有识之士或激烈抨击,或忧心忡忡,或无可奈何。如钱牧斋说:“今之人耳佣目僦,降而剽贼,如弇州四部之书充栋宇而汗牛马,即而视之,枵然无所有,则谓之无物而已矣。”[3]黄梨洲哀叹:“世无文章也久矣!”古之文“奈何降为今之臭腐乎?”[4]戴名世对明末以来 “文风坏乱”、“文妖叠出”的现象,认识得更加深刻。他说:“往者文章风气之趋于雷同,而先辈之文世所不好。”[5]107“文体之坏也,是非工拙,世无能辨别,里巷穷贱无聊之士,皆学为应酬之文,以游诸公贵人之门。然必济之以狡谲谀佞,其文乃得售。不然,虽司马子长、韩退之复生,世皆熟视之若无睹。”[5]293因此,戴名世以振兴古文为己任,决心“与世之学者左提右挈,共维挽风气于日盛也”。方苞针对当时的文风,更是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训示门人沈廷芳时说:“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1]890方苞在批评这个时期文坛怪异现象的同时,提出了自己作文的一套主张,即要“言有物”、“言有序”,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义法”说,这是对清初文坛现象的一种拨乱反正,是代表时代和文学创作发展要求的,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其次,方苞的“义法”说是在吸收同时代进步之士文论主张基础上,加以升华、提炼形成的。戴名世、方苞为了振兴古文,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群。戴名世说:“余年十七八时,即好交游,集里秀出之士凡二十人,置酒高会,相与砥砺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 ”[5]73他入京师后,广交宾朋,讨论文章得失。他常说:“余自入太学,居京师及游四方,与诸君子讨论文事,多能辅余所不逮。宗伯韩公折行辈与余交,而深惜余之不遇。同县方百川、灵皋、刘北固,长洲汪武曹,无锡刘言洁,江浦刘大山,德州孙子未,同郡朱字绿,此数人者,好余文特甚。灵皋年少于余,而经术湛深,每有所得,必以告余,余往往多推类而得之。”[5]118这里可以看出,方苞作文及文论思想的形成与戴名世对他的影响和启迪是分不开的。
方苞“义法”说的立论根据就是《易》中的“言有物”、“言有序”。在方苞之前,戴名世就提出:“今夫立言之道,莫著于《易》,《家人》,《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5]6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立论之源同是《易》。因此,“戴名世以‘言有物’为‘立言之道’,是方苞义法说的先导。 ”[6]
再次,万季野、程绵庄等人对方苞“义法”说的创立,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万季野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学家,他曾告诫方苞说:“子诚欲以古文为事,则愿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约以义法,而经纬其文,他日书成,记其后曰:‘此四明万氏所草创也。’则吾死不恨矣。”[1]333程绵庄说:“古先圣贤之论文,大要以立诚为本。有物即诚也。言之中节则曰有序,如是则容体必安定,气象必清明,远乎鄙倍而文之至矣。古之立言者期至于是而止,故曰辞达而已矣。故为文之道本之以诚,施之以序,终之以达。”[7]因此,方苞“义法”说的理论,是在汲取同时代作家、学者文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方苞高人一筹之处,就在于他把前人的理论,予以全面总结,使其具体化、理论化,并在实践中广泛运用。
第二,方苞“义法”说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首先,“义法”是指文章体裁对写作内容的要求和限制。方苞从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出发,在文章内容方面,强调“言有物”,在文章形式方面强调“言有序”,并且认为内容决定形式。他通过评析、考察前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得出各种文体在创作上的不同要求。他在《答乔介夫书》中说得非常清楚。他对写作侍讲公乔莱的表志或家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以鄙意裁之,第可记开海口始末,而以侍讲公奏对车逻河事及四不可之议附焉,传志非所宜也。盖诸体之文,各有义法,表志尺幅甚狭,而详载本议,则臃肿而不中绳墨;若约略剪截,俾情事不详,则后之人无所取鉴,而当日忘身家以排廷议之义,亦不可得而见矣。 ”[1]137他在文中还分别列举了《国语》、《春秋》中列传的例子,加以论述,认为在传志、家传等文体中,不能将奏议收录其中,“以是裁之,《车逻河议》必附载开海口语中,以俟史氏之采择,于义法乃安。 ”[1]138所以方苞在评论前人作品时说:“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每篇文章,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并且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这就是说写作的内容必须符合文体要求,也就是方苞所说的“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1]64。根据这一“义法”说的要求,创作出来的文章就可以戒空戒浮,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其次,“义法”是对文章选材以及材料取舍详略提出的要求。方苞在《与孙以宁书》中说:“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太史公传陆贾,其分奴婢装资,琐琐者皆载焉。若萧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1]136这里方苞明确指出文章材料的取舍以及安排,必须与人物的身份相符,“虚实详略”要因人而异,即由“义”来决定“法”。方苞在《书汉书霍光传后》中说:“《春秋》之义,常事不书,而后之良史取法焉。”还说:“其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如此。”[1]62-63这里方苞明确指出文章体裁的选择以及材料的运用,都是“义法”所要讨论的范畴。方苞在《史记评语》中,也是从繁简详略方面来规范“义法”的。他说:“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锡,粗矿去,然后黑浊之气竭而光润生。《史记》、《汉书》长篇,乃事之体本大,非按节而分寸之不遗也。 ”[1]181这里他显然是对《史记》、《汉书》中的长篇文章予以肯定,因为“事体之本大”,无需用长短去要求它们。他评《史记·项羽本纪》这一长文时,赞赏该文“先后详略,各有义法,所以能尽而不芜也。”[1]850他认为《项羽本纪》中对“高祖、留侯、项伯相语凡数百言,而以三语括之。”是因为“其事与言不可没,而与帝纪则不可详也。”[1]851再次说明作文宜详则详,当略则略,必须符合“义法”的法度。所以方苞说:“盖纪事之文,去取详略,措置各有宜也。 ”[1]851
再次,“义法”要求作文追求言简、雅洁的文风。方苞说:“盖所记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乃得体要。子厚以洁称太史,非独辞无芜累也,明于义法,而所载之事不杂,故其气体为最洁也。此意惟退之得之,欧、王以下,不能与于斯矣。 ”[1]853这里方苞所言的洁,不仅指作文在语言文字方面要简练,而且要在义法的原则下,对文章所要表达的内容有所取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符合他所说的“气体最洁”。方苞特别称赞《史记》行文的雅洁,如在《书萧相国世家后》中说:“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最为洁耳。以固之才识,犹未足与于此,故韩、柳列数文章家,皆不及班氏。 ”[1]56他认为《史记》行文符合义法的准则,就能实现文风“雅洁”。因此他说《史记》“变化无方,各有义法,此史之所以能洁也”。[1]856方苞常常以《史记》等文作为自己创作时的语言典范,旨在提倡典雅、古朴、简洁的文风。方苞在创作中力求实践自己的文论思想,写出了一系列的精美散文,如《左忠毅公逸事》等。
方苞“义法”说的文论思想强调作文在内容与形式方面达到完美统一,并对文学创作上的艺术表现手法提出了一些符合古代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具体要求,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颇具特色,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由于他的文论思想偏重于对古文传统的继承,注重对我国古文创作经验进行全面科学的总结,评斥是非得失,使人们在创作实践过程中便于运用。因此,方苞以后,桐城派文论思想日臻完善,文风大振,作家云集,作品广为流传,一时倾倒朝野,这些与方苞“义法”说的理论容易被人们接受、符合时代发展需要是分不开的。因此后人称颂他有“能集古今文论之大成”的历史功绩。[8]
二、情真义挚寓意深远的散文创作特色
方苞的散文创作实践是以他自己创立的文论思想为指导。他的文章结构严谨,讲究取材的多样性和典型性。其散文创作特色,主要体现为叙事简洁传神,说理透彻新颖,语言质朴雅洁,写人生动形象。因此,从他的创作实践来看,方苞也堪称为桐城文派之正宗与楷模,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首先,方苞的散文创作注重写实,强调详略得当。他说:“吾平生非久故相亲者,未尝假以文,惧吾言之不实也。”[1]201他在《儒林郎梁君墓表》中写到:“余谢以平生非相知久故,不为表志,非敢重要,惧所传之不实也;……君子之善善也,务求其实耳。”这说明方苞把创作的源泉,建立于真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文章的生命力就在于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如他在写《孙征君传》中,就很好地贯彻“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的创作要求。[1]136方苞在该文中,通过写孙奇逢为杨涟、左光斗等人的营葬,上书孙承宗,斥责魏忠贤,入清后誓不为仕等事例,将孙奇逢不阿权贵、嫉恶如仇的高风亮节,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详者略,实者虚,而征君所蕴蓄,转似可得之意言之外”的效果。[1]137再如他撰写的《左忠毅公逸事》,突出重点地介绍左光斗与史可法交往中的几个片断。即初次相识,狱中探视,不忘师训等,表现出左光斗的识才之智、爱才之心、护才之行。同时,方苞的人物描写达到了出神入化、栩栩如生的境界。这也是他写的许多人物传记能被后人传诵的主要原因。他在写史可法打扮成清洁工,冒险入狱探望左光斗,看到他:“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脆,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地何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1]237-238这里方苞通过对左光斗、史可法两人形貌、动作、语言对话的描写,刻画出左光斗身陷囹圄,仍心系国家大事的爱国情怀。同时方苞也深刻揭示了人物内心的矛盾,左光斗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保护人才,让天下事有人来支柱,极力压抑师生之谊,读后令人肃然起敬,振奋不已。此外,他撰写的《田间先生墓表》、《明禹州兵备道李公城守死事状》、《石斋黄公逸事》、《狱中杂记》等文章,无不以形象生动的人物描写而取胜,这也是方苞文名震天下的原因之一。
其次,方苞的散文创作,寓论理于叙事之中。顾炎武在论述太史公作史笔法时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9]方苞继承了太史公的笔法。他在撰写人物传记之类的作品时,往往在文章的结尾或文章中间,插入自己的议论,或加上他人的评述,有的以传赞的形式出现,有的言古道今,讽刺现实,抨击时弊;有的借题发挥,抒发个人情怀,畅言对社会及人生的感悟,或褒或贬,无不暗含作者心志。方苞的《左仁传》,写左忠毅公后代左仁,其祖患了传染病,家人害怕传染,没有一个人敢与之接近。其时左仁才只有十五岁,也知道此病有传染的危险,但为了燠祖足寒,陪居六年,终染病而殁,乡人以为“愚”,而方苞在文末却说:“呜呼!当明将亡而逆阉之炽也,如遭恶疾,近者必染焉。忠毅与同难诸君子皆明知为身灾,独不忍君父之寒而甘为燠足者也。世多以仁之类为愚,此振古以来,国之所以有瘳者,鲜与!”[1]222方苞就是从家庭小事入题,小中见大,广而推及国家大事,从笃于亲人而推之为忠于君父,从而颂扬左忠毅公与同难诸君的孤忠大节和报国之志。又如他写的《辕马说》,文中说“马”,其实处处指人,所写的现象均为当时的社会现实。“呜呼!将车者,其慎哉!”[1]79旨在点出本意,敬告统治者识马用人,不可不慎重。有时在叙事过程中,插入人物对话或人物自白,对某事某人作出评价,点明旨意,起到一针见血的效果。如方苞撰写的《狱中杂记》就是用这种笔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成为传世典范之作。
再次,方苞的散文创作,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力求散文语言的形象、生动。方苞认为文之工致,不在辞繁言冗,而在于“情辞动人心目”,即以真情来打动人心。他写的《兄百川墓志铭》、《弟椒涂墓志铭》、《先母行略》、《书孙文正传后》、《亡妻蔡氏哀辞》、《王瑶峰哀辞》、《仆王兴哀辞》等文章,或讲述家境、叙述兄弟手足之情;或感慨先贤生不逢时,难有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字里行间,或表达兄弟之情;或讲述母子之情;或颂扬爱国忧民之情;或怀念夫妻之情;或畅言朋友之情;或描述主仆之情,言语质朴,情真义挚,读之动人心魄,感人肺腑,回味无穷。
方苞在其写作的文章中,还经常运用修辞手法,以增强文章的活泼性和感染力。他在《书老子传后》里,为了讲述老子确有其人,从老子的姓氏、籍贯、官守到他的子孙后代的封爵、居住等情况,运用整齐的排比句式,不厌其烦,详细描述,旨在加深读者印象,张扬文章气势,增强说服力,同时让读者欣赏起来,有一种美的享受。有时他还在文章中插些比喻,通过形象而又生动的比喻,来阐明抽象深奥的道理。如他在《与程若韩书》中,反对行文繁琐冗长,认为“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锡,粗矿去,然后黑浊之气竭而光润生”。[1]181可谓比喻生动贴切,寓义深刻明了。有的文章他还用比兴手法,如在《题舒文节探梅图说》中,以“芝兰之萎折”,喻舒公遭遇之不幸;以“西山之梅”,喻舒公的人品及其处世原则。又如在《与鄂张两相国论制驭西边书》中,以同样的手法,表达自己对国事的关心和焦虑,他说:“然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庶人。……学先圣之道,仁义根于心,视民之病,犹吾兄弟之颠连焉;祖国之疵,犹吾父母之疾痛焉。 ”[1]637在上述文章中,方苞托物言志,喻人喻己,表现出他仰慕先贤、忧国忧民的人格魅力。
方苞还在与友人书信作品中,夹杂一些对山水风光、自然景色的描写,让人读起来意韵深长、无枯燥之感,别有一番情趣。他在《与王崑绳书》中,就插入了精彩的山水风光描写,他在信中写到:“苞以十月下旬至家,留八日,便饥驱宣、歙间,入泾河路,见左右高峰刺天,水清冷见底,崖岩参差万叠,风云往还,古木、奇藤、修篁郁盘有生气,聚落居人,貌甚闲暇。因念古者庄周、陶潜之徒,逍遥纵脱,岩居而川观,无一事系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郁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这里他既赞扬山水之美,又怀念古人隐迹山林的清闲生活,并生羡慕之情。他说:“使苞于此间,得一亩之宫,数顷之田,耕且养,穷经而著书,胸中豁然,不为外物侵乱,其所成就未必遂后于古人。”[1]667这里他借景抒怀,怀古思贤,表现他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
总之,方苞以他简严精实的文风,在“义法”理论指导下,追求道与文并重,把古文写得清新雅洁、自然流畅,并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在清初文坛可谓独树一帜,开创了一代文章风气之先。尽管后世之人论及方苞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不一。讥之者谓:“先生文,叹其说理之精,持论之笃。……而特怪其文重滞不起,观之无飞动嫖姚跌宕之势,诵之无铿锵鼓舞抗队之声。”“措语矜慎,文气转拘束,不能闳放也”;[10]“旨近端而有时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11]尊之者则谓其文为清代 “百馀年文章之冠”,[1]904“源流极正”,[12]“宋以后,无此清深峻洁文心;唐以前,无此淳实精渊理路。”[1]902实事求是地说,方苞的文章气势略显孱弱,文采略显贫乏,不能说不是其缺陷;然而他的文章精炼平实,澄清淡雅,注重写实,忧国思民,关注民生,寓意深远,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现实针对性,在当时可以说起到了矫正文风的作用。因此刘开评其文:“丰于理而啬于辞,谨严精实则有余,雄奇变化则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 ”[13]此论颇为精当。
[1]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第二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8.
[3]国立编译馆主编.清代文学批评资料彙编(上集)[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9.
[4]黄宗羲著.陈乃乾编.山翁禅师文集序[M]//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370.
[5]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C]//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周中明.桐城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84.
[7]贾文昭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类编[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295.
[8]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34.
[9]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429.
[10]方东树.书望溪先生集[M]//仪卫轩文集.清同治七年刻本.
[11]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M].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212.
[1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4: 1528.
[13]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C]//漆绪邦,王凯符选注.桐城派文选.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306.
(责任编辑 文 心)
I206.2
A
1001-862X(2011)05-0170-006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桐城文派史”(09YJA751002);安徽大学211三期“桐城派研究”及科研创新团队“安徽地域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
江小角(1963-),安徽桐城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清代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