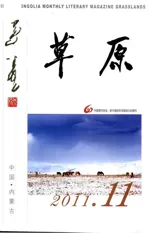在祖坟园……
2011-11-21蒙古族
□云 珍(蒙古族)
父母的坟头已被风雨蚀去大半,只不过七八年的时间。
祖坟园不大,方圆约略两丈,明显的坟头有四五个。园内正中,一棵曾被锯掉的柳树从根处长出两杈,高约丈余,碗口粗细,长得圆蓬蓬的,荫阴很大。坟头间皆为杂草,夏秋季节,坟园周围沙棘林郁郁葱葱,坟树仿佛就是一株最大最旺的沙棘。故土多为平原,祖坟园西南东北向,处在一块略显倾斜的坡地上,前面是一块荒草滩,有点凹。我寻思,我的祖辈在建园初,可能也尽可能地从风水学的角度考虑了一下背山面水的风水学原理,只是地理使然,就只能权且将斜地作山,凹处当水了。我对故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很熟悉,像祖坟园这么极具象征意味的地儿,少有,可见我的祖辈还真不是马虎的人。
幼年的时候,祖坟园前的凹地,荒草萋萋,是蚂蚱和蛐蛐儿叫得最响最稠的地方,由此,那里也成了孩子们经常出没的地方。常常是在中午或傍晚,几个小伙伴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循着那个叫得又脆又高的声音寻去,有时竟至忘了午饭或晚归。大人们着急,担心我们是不是到村里的塘坝玩水,被水鬼捉了去了,就邀了三五乡邻可村可野地寻找,一边找一边吆唤着名字,声音长长的,很哀婉,很绝望。越是这样,小伙伴们越是不敢动弹,因为谁都知道,如果真的被逮着了,等待的肯定是父母亲的一番责骂,就只好静静地伏在草最旺的凹处偷眼看着大人们的脚步匆匆离去。等到实在饿得不行或是黄昏之后天越来越暗,才敢偷偷溜回家去。后来,不知为什么,村里竟至传出,说那里是个阴宅,阴气重,昼夜有孤魂野鬼出没,说不定哪一天谁家娃子不走运,遇上披头散发的吊死鬼,一把擒了去,啖了血、吃了肉也说不定……那时是农业社,生产队里的骡马一大群,牲口们的活又苦又重,秋天更是它们不能歇脚的季节,队里就配了专人,在夜间放骡马抓膘,故乡叫“放夜马”,我家祖坟园附近就成了 “放夜马”最好的去处。凡事一有了开头,就总会有下文的,就说这阴宅的事吧,我就亲自听马倌说,真的呢,夜半三更之际,静静吃草的马儿,会突然一惊之后狂奔起来,那除了是在挣脱吊死鬼抓住的马尾巴外,还能怎样呢……说的人煞有介事,听的人愈发信以为真,我家祖坟园及其附近就被三乡五里的村人定为阴宅了。这之后孩子们是断断不敢再去捉蚂蚱寻蛐蛐了,有时随了劳动的大人们偶尔去一两次,还真觉着阴森森的,仿佛草丛中就藏着厉鬼……
从父母亲的坟头往上数,那些坟头是愈来愈小,到第四个,已不能称作是坟头了,只能说是一块园形的微微隆起的地表,上面的荒草长得比别处旺,两个原因吧,一是村人在割草时肯定考虑如果动了土惹得死鬼生气,是要带来晦气的;这第二,故乡的地下水层浅,墓穴不能挖得太深,那些荒草的根系极有可能就直接伸到已腐化了的血肉上,当然长势就好。这一块微微隆起的地表下埋着的,按故乡方言,父亲应该叫老爷爷,于我就应该是老老爷爷了,怪拗口的,每年逢“清明”、“七月半”、“十月一”及大年三十,我带着儿子烧纸钱,按理我们在叩头时,应同时默诵亲人的名份,这样,死去的亲人才会收到,反正,我是直呼父亲和母亲,最多念一声爷爷或奶奶,而我的儿子,我推想则最多也只呼一声爷爷或奶奶,所指不同,我的爷爷或奶奶在我出生时就已故去了,说白了真是没感情,而我的父母亲则视我的儿子如掌上明珠,曾一同生活了十几年,想来,儿子在叩头时心情还是真诚的。我家没有家谱,祖坟园里到底埋葬了几代人,无法知道。我们村在我们县是个大些的村庄,每年的年三十晚上,有些人家就将族谱专门挂在一间房舍里供奉,童年时,年三十晚上孩子们跑大年,我们总忍不住偷偷爬上窗台往里眊,那幽幽的麻油灯火,那缭绕的香烟以及摆放很整齐的供品所创造出的那种氛围,似幻非幻,充满了诱惑。以祖坟园地理位置的选定来看,我的祖辈不应该不建家谱的,幼年时我不懂,及至现在才明白。我是蒙古族,我父亲五代以上,应该是“土著”,标准的马背民族,其文明程度还没有发展到像汉民族那样有那么多繁文缛节,人死之后一般就地火葬或风葬,死了就死了。至于祖坟园的草创就又当别论,我们村三百多户人家,蒙古族仅我家一户,可以推断,第一代入主祖坟园的我祖上就已经是被汉化了的,他们的生活观念,生存态度,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媾的混血体,实际上就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 “四不像”。到第二、第三代乃至后来,应该说吸收汉民族的习俗更多些,但毕竟还混杂着本民族一些根深蒂固的礼仪,因此,就可能对像修族谱这样的事,是既认真又马虎的,一拖再拖,就搁置了下来。这期间,蒙汉民族的交融是最强烈的,其佐证很明白,我们县及县镇汉语都叫 “和林格尔”,“和林格尔”是蒙古语的音译,即蒙语二十户人家的意思。县镇东南约七十公里处与山西省的右玉县接壤,著明的关隘“杀虎口”就屹立在省界上。中国近代史上同样著名的三次人口迁徙之一的“走西口”就发生在这里。“走西口”滥觞于明朝中期,一直到民国初年,延续了四百余年,无数山西人背井离乡,冲出“杀虎口”来到地广人稀的内蒙古恳荒种地。清咸丰年间,山西省连年荒旱,加之官府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走西口”达到高潮,生存难以为继的关内人民,有的人举家来迁,分布在阴山的南北麓,有的不愿再像候鸟样飞来飞去,就索性定居下来。想来,“和林格尔”就是最初定居下来的二十户人家。山西省及内蒙古西部流传的二人台小戏,就叫《走西口》,说的是新婚燕尔的玉莲和泰春,泰春要“走西口”了,小夫妇俩难舍难分,哭成泪人一对。及至现在,每看此戏,我都会被演员夸张的表情和肝肠寸断的唱词感动得泪流不已……
父亲病重时,最后嘱咐我们两件事,一是要我们修家谱,他说:“请个先生,好赖也得拾掇个家谱吧,像人家李家……”这二,就是要我们将祖坟园里的那株老柳树锯掉。这是父亲纠结最久也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困难最无奈的一个决定。我的老老爷爷辈是当时村里的大户人家,住的是四合院,日子过得很殷实,家道衰落,始于我的老爷爷、老奶奶。时值鸦片战争前后,国人遭受鸦片的荼毒,我的祖上亦在劫难逃。老爷爷和老奶奶竟也染上了毒瘾,在两杆烟枪的喷云吐雾中,四合院被撒了换烟,殷实的日子一时灰飞烟灭。到我父亲时已是赤贫如洗了。一九四九年划阶级定成份时,我们家被确定为“雇农”,这就意味着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我们家因此而分得了“地主”家的一间房子,我就出生在那间房子里并一直生活到十三岁。那房子是地主家四合院中的一间正房,面积不足六十平,虽然屋内陈设一样不少,但也是最简朴的。这房子已是百年老屋,记得每逢淫雨连天,漏雨不断,母亲就取了脸盆、铁瓢之类盛那些漏下来的泥水,一家人真是寝食难安。我的父亲是个犟性子,他私下里多次对我们说,我这一生,没办什么大事,死活也要盖一处像样的房子。这话在当时无异于晴天霹雳,那年月社员们吃的是大锅饭,我们村又是碱性土壤,一个工分仅值几分钱,一家人辛苦一年,居然挣不回应得的“口粮”。我记得我们家“缺粮户”的年份居多,一直到我高中毕业返乡务农,因为新添了个壮劳力,才变成了“余粮户”。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在那样的年月里竟然还积攒下了大约五十条椽檩,做好了盖房子的准备。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五十多岁时,父亲的病重了,整夜整夜睡不稳,五更即起,剧烈地咳嗽,吐痰,喘气,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不说,还需不停地打针、吃药。盖房子的事就这样一直拖下来。可父亲的心不死呀,他虽然人躺在床上,却仍在谋划着全家的大盘子,指挥着我们做这做那,看到我们稍有懈怠,他就嘟囔……可这房子就是一直盖不起来。这件事一直持续到我上初中的那一年,才算有了着落。那年,一个王姓的上门女婿要搬回老家去了,他人是担任过我们村大队支书的,有半新不旧的房子两间,椽檩都是上好的,但这房子是搬不走的,他就找上门来与父亲谈,记得第一次父亲没表态,一直憋着脸大口大口地抽烟袋。那人悻悻地去了。事隔不久,他就又来,如是反复。详情我不了解,听母亲的口气,好像终于定下来了,按理说,这是喜事,一家人高兴才对,可是看着父来阴郁的脸色,听着母亲一下一下戳痛脊梁骨的叨叨,非但不高兴,还凭添了一份羞愧和气愤!母亲说,损德的,换就换呗,还非要锯了人家的坟树去……那树可有灵气哩,它罩着咱家的流年运气,谁家动走它,总会遭殃……后来明白了,父亲与王姓的那人达成的协议是,用我们家已积攒的五十余条椽檩再加那株能做柁子的老坟树换取他家搬不走的那两间房子。父亲去逝后,我们一家终于搬家了,条件是好了,起码不再听见雷声就担心,看见阴云就烦躁,但就是心里犯嘀咕,特别是逢年过节烧纸钱时,瞅一眼老柳树那白惨惨的荐口,就有一种好像被人挖了祖坟的感觉,也就深深地理解了当年母亲的叨叨和父亲一直憋着脸大口大口抽烟袋的心情。
站在祖坟前,我的思维如控不住的野马,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地瞎闯乱撞。一阵北风急剧地掠过,我的头发一奓,我是想,几十年后,父母亲坟头的下面,也就是当下我正踩着的这块土地,就该是我和妻子的最终归宿,以此类推,我的儿子儿媳,儿子儿媳的儿子儿媳……那时,如果传统还在继续,我的后辈如果进了坟园烧纸钱,“我”会不会就仅是一块微微隆起的地表,只不过荒草更旺了些?也许这样的情形也不会有,因为我和妻子都是公务员,按政策是要火化的,就算拐弯抹角将尸体弄了回去土葬,结果也不好说,因为我看见,当下一条崭新的乡村柏油路就已势如破竹般地穿过了祖坟园前所谓“阴宅”的那片凹地,公路的那边,县里新规划的开发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公路上人来车往,好不热闹。童年的乐园是永远不复存在了,弄不好,用不了几年我的祖坟园就会被连根拔掉。想到此,我开始隐隐地悟到,这世上有些事其实是无可无不可越想越复杂的,就说这修族谱砍坟树的事吧,怎么才是个理呢,换了话说,砍了就砍了,不又长起来了吗?修不修族谱又能怎样?我敢断言,即使影响如孔子,形制如曲阜孔林者,也很难预料最终的结果。洪水、地震、战争、外天体的撞击等都可以使其毁于一旦。庞贝、楼兰、吴哥……是如何被时间的奔马一蹄子踹向历史的暗处?这其中人类直接的恶作仿佛更具嘲讽意义和不可思议性,例子多了,譬如二战其间,被盟军炸毁的有世界建筑宝库、易北河上的 “佛罗伦萨”之称的欧洲历史文化名城“德累斯顿”就是之一。据说,作为高棉王国的都城吴哥是经过一次屠城之后突然消失于莽林之中的,柬埔寨战乱期间,没有人保护这些遗址,吴哥窟中价值连城的宝物已经被偷盗殆尽,在邻国泰国的市场上,游客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吴哥窟古物,吴哥古文明的存在不过五百年的时间,再过五百年呢?这是多么令人扼腕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啊!凡事总有完结的时候,人是一定要死的,断子绝孙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谁敢保证几十或几百年后,自家的种族就一定能够延续?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我一直无意张罗修族谱的事,对于父亲,这应是最大的不孝了。
祖坟园周围的沙棘,绿油油地就要压过来了。这沙棘可是一种生命力很强又极富担当的野生植物,其种子随风飘游,不论流落到何种土壤,都可生根发芽。郁郁葱葱地固守一方水土。有资料显示,沙棘的根、茎、叶、花、果,特别是果实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可以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轻工、航天、农牧渔业等国民经济的许多领域。我想,我这大半生,就故土而言,不啻是在漂泊和流浪,竟有点像沙棘的种子呢,但庸庸碌碌的我能比得上沙棘吗?族谱是断然不会去修的了,房子也无需再盖,那么,就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而言,我还可以做出一件其意义相当于父亲为我家换房子的事吗?一阵微风吹过,沙棘林枝头上金色的小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晃,如蜜蜂振翅般嘤嘤嗡嗡,一阵阵轰击着我的灵魂,那,分明是一种平常而独特的自在之物以叮叮当当的金属之响敲击着生命的节奏……突然就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几句诗文:
“苍白的天空没有云影——巨大的生命的空白!
生是一生中无数偶然的开始,死却是一生中唯一的必然。记忆是多么美好,时间又是多么的恐怖。活着就要尽可能好好地活着,非回归泥土不可的时候,就要设法变成树木或植物……
几堆黄土终将被抹平,地平线划了一道长长的休止符……”
然而,什么叫做“尽可能好好地活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