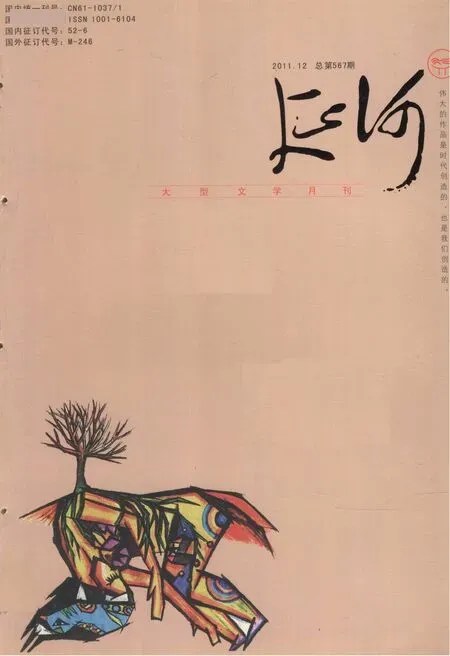活下去的理由和承受力量的村庄
2011-11-20高宏
高 宏
谢谢大家,我今天主要演讲的是活下去,农民的活下去,我们每个人的活下去,包括我高宏在北京10年的经历。我曾经这样描述过我自己,既不像石头一样坚硬,也不像钢铁那样有韧性,我就是陕北高原上的黄土,我有它的坚韧和毅力。
首先介绍我自己。我的家在陕西省横山县一个叫怀远的村庄里,但整个陕北是我的家,那里有信天游,有石狮子,有剪纸,有人们向往的精神圣地,有黄河。我曾经徒步黄河,感到黄河就像中国人一样平静的流淌,它的内心是那样的沉静,那样的富有诗意,当我们站到黄河瀑布前,我看到黄河在壶口瀑布前站着撒了一泡尿,它像我们宣示,我们是有精神性的。就这样一条平静的大河,在这样一个晋陕峡谷,它树立起来,站起来,咆哮着,具有非常强劲的力量,只有你到现场才能感觉到这种气势。我为自己生到这块土地上而庆幸。我曾经抱怨过自己是农民,批判过农民,也讽刺过农民,但今天我要为他们唱赞歌。我为什么要画他们,画农民的什么呢?我对自己说的是:一定要画农民的承受。中国农民具有多么坚强的承受力啊,每一个农民他就像大树上的一片叶子,叶子的生命都给了大树,这棵树才能够长壮,这个根才能扎下去。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根不断扎向深厚的土地,向下,向下,再向下,我们的爱我们的善意才会升向爱的天空。只有这样,这个爱才具有激情,具有理想,具有责任。
我在北京接触过很多知识分子,接触过很多当代的艺术家,也接触过不少归国学子,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性:比较沉默,比较怯懦,甚至失去了理想!我跟他们说:你们活的太幸福,你们只有到陕北,到厚土里看一看,看看农民背着一背庄稼是咋样走向山岗的,那种承受力是如何辐射发光的,才能进入深层的生命的感动!在我的艺术感知范围内,在我的一些画作里,我表现了我的真实感觉:陕北农民的眼睛真的是绿绿的,像光源一样的闪烁,那种光是具有神性的,那种承受力是让人感动的。我通过我的绘画告诉人们——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爷爷,我的祖父,一代一代的,就在这块土地上,就是这样活下来,并且告诉我一个朴素的真理:孩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丢失自己,迷失自己,你只有本着你的心去做事的时候,才会得到爱,得到善,得到关注。
我在这里讲农民,赞美农民的承受力和他们的精神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但我同时还要批评自己身上具有的农民性,那主要是指我们精神深处的某些污渍,我批判这个!有虱子,有恶水(注:在陕北方言里指结成块状的污垢),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抠去这种恶水,让他的光发亮!这是我今天所讲议题的开场部分(同时对鼓掌的听众示意: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说一下我对自己故乡村庄的一个感觉。它和千千万万的农村一样——窑洞是天圆地方式的结构,继承了最原始的美学造型风格,就叫窑洞——有热热的炕头,温暖的人心,充满着善良。在冬天(就像陕北人一样),老远就望着你,木讷,呆滞,但这种木讷、呆滞里头充满对外界的渴望。但我为什么会来北京呢?我觉得我是一条鱼,待在那个村子那么大的地方,当鱼长大的时候就不能活了。北京像一个大海。这是我在北京生存的感觉,纯粹是对比后产生的。
我曾经和北京的一些朋友聊过饥饿问题。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饥饿,忘记饥饿就忘记了过去。为什么说要挨点饥饿呢?还是为了提醒记忆。例如眼前这幅画吧。当我们看到这张画,我们就知道饭的香,知道饥饿人心里的一个记忆。我在北京问朋友们饥饿是什么,他们会说饥饿就是想吃饭。其实不是这样的。
在陕北,饥饿年代的人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人在饿到极致的时候吃了一顿好饭,就那么撑死了!那样的饿在心灵上才是有痕迹的。如果只是想吃饭,还局限于身体需要,它绝对不产生记忆。中国人几千年来对饥饿是有记忆的,而这种记忆在我们的血液里根深蒂固。尤其在陕北,你看到的每一个人,都带着这种基因,文化记忆的基因。我父亲有四个孩子,把我们姊妹三个供到上大学的程度,但有一个二妹供不出去了。我这个妹子活活的急成一个疯子。她看到我爷爷有九个孙子全部在北京的北大、清华、交大上大学的时候,连我这样一个最不成器的哥哥也成为一个大学生,我妹妹就发疯了。当她死在我母亲怀抱里的时候,我意识到:只有真死的是死了,假死的死不了。母亲说:孩子,人就这么回事情,当你醒来你还要过日子,还要念书,活着是最重要的。我父亲掉了两颗眼泪,抹干眼泪就下地劳动。我回去,给我二妹磕了两个头就走了。死了的人死了,她会给你留一个影子般的回忆。在我这样一个家庭里头,看到一个人死亡,会让你对死亡的认识和别人不一样。有的人为日本地震流泪,为汶川地震流泪,我说我也会心痛,但它和我没有关系,那是死亡人的死亡,那是汶川人的死亡,那是日本人的死亡。对死亡有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冷静的去帮助那些该帮助的人,那些等待你帮助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我刚才要讲的——饥饿的意义——一定要记住饥饿!
现在,我们忘记了我们最本质的一个属性:我们忘记了饥饿。当你饥饿的时候你会发现啥都不重要。因为这个,我在我的绘画里头画了很多关于饥饿的环节。画一个乌鸦。乌鸦我认为是有神性的,很多中国人在唾弃乌鸦,乌鸦是知道人的心灵秘匙的,它能闻见你要生,闻见你要死。这往往是与饥饿有关的死。
我是69年、70年生的一个人,按理说不应该对饥饿有这样一个敏感,但我还是遗传了那种文化记忆。即便是在上世纪的进程中,中国农民尤其西部农民整整饿了20年,饿死了很多人,但是他们依然活下来,还不是因为他们有这份刻骨的记忆!我们还需要宗教吗,还需要信仰吗?就像黄土高畔上的那个山芋,那颗黄杨刺,虽然长得曲曲歪歪,很难看,但是他们坚气的活着。他们是一个整体,守望着这片土地。看着鹞鹰在上面飞过,看着孤行、凄凉的豹子(我们那儿叫花豹)。老鹰飞过去的时候,你就会充满着理想,充满对生存的渴望。当你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你就知道啥叫艰难,啥叫蹭挂住。我们那儿爱说“蹭挂住”这个词。给你两筐土豆或者两筐碳,增送给你,让你背你也不会去背,但是陕北人会去背。整天的背!从春季背到了冬季背到了夏季。有一次,因为我挑着一担土豆,没有力气,摇摇晃晃的,把土豆在崖上和墙壁上一碰,把土豆掉沟里头去了,我母亲把我骂了一通:娃娃,这是今天要吃的饭啊。我父亲绑着一根绳,从我的下面,拦裆起身背起来,把我从崖上吊下去,再把土豆捡回来。就这样生活过来了。人在饥饿时期对食物的那种执着看起来可悲,或者说很可笑。但这里边又含着某种悲壮的色彩。
讲一点我刚来到北京的事情。那是个寒冷的季节。我时常以为绿色是假的,经常不由地要手掐一下,就是对那个绿色没有记忆,只有到了夏天这个记忆才会苏醒。陕北更多的像素描,这是我们的家乡毛乌素。(出示画图)它像素描,冬天它寂寥的黄色像素描,夏天它的绿色像素描,夜晚它的黑色蓝色像素描。每一种颜色都具有宗教性,都具有神性,这种神性在指引着我们。陕北有两种颜色是我体会最深的,这在我的画册里我也不断强调。这两种颜色是什么呢?一种就是神秘的蓝色,艳蓝色的、神秘的蓝色,还有一种就是正午太阳照耀下的那种苍劲平凡的白色。这些颜色是具有宗教性的,它非常有力量,非常有力量。这种力量是震撼人心的。夜晚的时候是鬼神出没的时候,人会往回走。就在这人鬼交加的时候,有一种灵性的东西在诞生。正午的时候,就是正午12点到1点的时候,在陕北要出现鬼,干活的人都会回去的。山里头非常寂寥。我确实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实,就叫中邪吧。我和小伙伴去砍柴,背着一背柴,到了十字路口分了家,我回到我的家里,我那个朋友也背着柴回到他家。结果他回到他家就跟家人胡言乱语,说的话都是村子里头前几天死去的一个人说的话。我后来到北京一问,有说法说:这是符合事实的举动。那个人曾经在那活动过,被自然录像录到那了,我这个小伙伴恰好就走进这个磁场,两个磁场一吻合,两个人重叠在一起,叫灵魂出窍。但我们那儿叫中邪,就是被鬼抓了。
现在给大家看一幅画。大家看到的这个人群,是我画的一张大画,4.5米×2.2米,名字叫黑棉袄,一个陕北的特定的时代,叫黑棉袄时代。大家都穿黑棉袄,穿着黑棉袄在前行,穿着黑棉袄在忍耐饥饿,穿着黑棉袄像鬼一样在走向劳动的场面,穿着黑棉袄在集会,穿着黑棉袄在对毛曲,穿着黑棉袄在做着一切一切。黑棉袄在我心中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记忆,这是陕北的一个主要服饰。饥饿的时候,大家很无助地前行,像宗教徒一样,但目标秩序依然没有乱,依然坚定地走向工地。
(又拿出一幅照片展示出去)这是饥饿时候的一个农贸市场,做生意的地方。这个农贸市场,可能照片不太清楚,但能感觉到是土岗的生活。这种生活场景就像……我用一种特定的颜色打比方:黑色,蓝色。把它们禁锢在一个宗教一样的一个东西里头的一种生存状态。当时,我每年在陕北打工,挣来三万块钱,要在北京花5万块钱,每年欠账两万块。我要改变生存的时候已经借下18万块钱的账。这种生活状态让我认识到,无论你是博士,无论你是一个打工的,你来到北京就会像大树里头的一棵小树,你要晒到阳光,你就不可能头顶蓝天,你只能钻着空往外长,就是说避实击虚。这是我自己的一种北京体会。我画的这个叫开会,但大家不觉得这像在讨论战术吗,跟打仗一样激烈。这几个抽烟的就分开了,后面的都不是领导,前面这些是领导,具有决定性的。为啥画两个狼呢,我觉得是狼指引着人,有一种无形的靶子就像狼一样控制着人。我当时是一种反叛心理,很直接的讲故事,让故事具有空间感,有两个狼跪到前面,黑压压的,和这些人进行对话。这种语言形成一种空间,就是人们在生存的过程中的这个激烈感受。我画的当代艺术,还画过红人,整整画了两年,但我发现它不属于我,当代艺术不属于我,为什么?首先它要运作社会关系,我没有这样的能力,不希望在内心屈从于别人。我在清华美院读书的时候,在高美店住,每天晚上骑自行车回家,寒风刮得呜呜呜的。穿一个烂风衣,把脸蒙得严严的,只留两个眼睛,黑的什么看不见,多么渴望一点亮光,结果真的远处就出现亮光。你不敢撞上去,那亮光是机车的光,是火车的光,你撞上去就没命,这个光不属于你。我啥要感谢北京,甚至要感谢陕北这块土地呢,北京让我知道文化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放弃当代艺术。
那种禁锢要不要打破呀?我认为要打破。但这种破除不一定是在衣食、外在等级方面。如果人在农村分三六九等,在延安市就分十八等,在北京人就分九十等。必须要承认这种差距,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真是有差距,但我一直认为人的心灵是没有差距的,还要不断缩小这种差距。
1982年以后,农村陆续放开。一部分人走出山外,那些懒汉二流子先富起来,真正的务实的人没有富起来。凡是文化里头有的,生活里头全有,文化里头没有的生活里头也有。看,在这种屈从里头(指着其中一幅画),82年进城,拉砖的、挖胚子子的人,不都是这样的状态吗?大家到瓦厂去看一看,那些挖胚子的人的状态,汗流的一把,抹着泪按着眼睛,一个眼睛还看不见,这是人的贱化,全在这做碳挖煤的人的神态里。倒小煤窑的一幅画。随时会有人死在煤窑里面,他四体趴下,背着煤在那里头爬,他真的想下到300米深的黑窟窿里头吗?不是,他为了活命。他并不卑贱,只是为了活下去。当你看到这种力量的时候你还能认为这个国家没有希望吗,这个民族没有希望吗!在这个国家复兴的时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承受,去像他们一样去背负,而不是去抱怨。
那时候,父亲逼我念书。我饿得实在不行,从学校跑回来(那阵才16岁)。父亲逼我在三点左右出山劳动,,父亲为的是让我继续上学。赶9点、10点的样子,我拉了17架子车羊粪。每一车都非常重。拉完以后,累得站也站不住。(种地的时候)父亲为了整治我,就跟使驴一样的时不时抽一鞭子。当我把这些地种完的时候我发现骡子哭了。我在想我要念书了,骡子在告诉我,我没有办法转成骡子,连个后代都不能繁育,驴还能繁殖后代,我呢就成了骡子了,连后人都不能留。那时我回到农村连个婆姨都弄不下,是真的问不下婆姨,太穷了。我1990年在西安考美院的时候,在陕师大看到一个女娃,真的爱到淌涎水了,我看见女娃娃的皮肤啊,粉粉的白白的,那个美啊,尔个心里头也打着那种烙印和记忆,让我触目惊心!(哄堂大笑)大家不要笑,这是真的。如果一个男人对美女没有感觉的话,他真的不是人!约束自己控制一下嘛!我并没有像流氓一样抱住大学生去亲嘛,大家就不要笑了。
所以你看这幅画:这个妇女,当然我给压缩了,压缩了才有力量,她顶着几堆金黄的稻穗,她就寄予这种生存和希望,一种信念,这可能不是我母亲,但她就像我母亲,每次卖给别人庄稼的时候,她会把最脏的东西拣出去。她说:娃们,不管多么艰难多么贫穷,我们还是要把好东西卖给别人的。我感觉到母亲的温厚、宽容。她三岁就失去了父亲,她用无言来承受了一切。在中国,我看到女人指责男人抱怨男人,但我没有看到我母亲抱怨过我父亲。其实我父亲没有我母亲宽厚,我就继承了我父亲几分奸猾。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美女,今后不要在生活中抱怨,多鼓励自己的男朋友。真的,中国人爱抱怨,中国女人更爱抱怨。
看,刨挖,大家扛着一把 头,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里头刨挖,你说这里头有元宝有金子吗?不是,抛挖就是一种希望,只要你敢于刨挖,就有希望,这是刨挖希望,但这种眼神里头充满的这种惊悚感、光亮感,就是对生存的渴望。庄稼人确实很悲锵,很憋屈,很窝囊,既没有话语权,又没有生活的平等权,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命交给老天爷,他们每天起来种地,但他们不知道有没有收成,陕北这个地方缺雨缺水,缺水的地方是非常饥渴的。我小时候灌过水,驼过水,驼一次水要走20里路。40里路代表着城里人一个礼拜的劳动强度。庄家人在白天还要去干活去种地,这是一种惊人的劳动强度。我父亲今年67,但却像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我今年42,看上去像52、62,秃顶。我儿子这样描写我:丑陋的父亲,像黄土一样的秃顶,口臭、黄牙、打呼噜,所有的毛病他都具备,但我父亲非常坚强,他在北京能生活了。我在最艰难的时候,我儿子6岁,他写了几个小纸条、小卡片,上写的几个字:请买我爸爸的画,这是我儿子真实的心声,请买我爸爸的画。我妻子曾经说下辈子宁肯嫁给一个驴也不嫁给一个艺术家,这话是真话。选择是要有代价的。我给我媳妇说,你选择我就得付出代价。
看这都是我画的一批画,都是一种生存的状态,我叫他们黄土叶子,也叫土叶子,就是这些人像树叶一样活着,像叶子一样像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像野草一样不断的升腾,不断的生长,人就这样一辈一辈传承下来。
这里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寡妇,男人死了,家里剩下三个孩子。这个寡妇为了养活这三个孩子咋办呢,只能找男人,找男人不能找漂亮的,奶油小生,就找一个丑陋的,有苦的,找了一个男人叫王老五。王老五是有力气、能下苦的人。王老五媳妇也死了,剩下两个孩子,他们又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有五个孩子,又生两个孩子,七个孩子。你说七个孩子在那样一个年代咋样去生活,那种生活质量可想而知了,真是铺炕皮盖窑井,溜席子。
王老五曾经有一个故事,大家听一听。他在那个年代进步着了。不让去挖煤他就到路子川去挖煤,挖的一个月挣了四十块钱,那阵的钱非常难挣,一个劳动力一天能挣2分钱,一月能挣两块钱就不得了了。王老五一月挣40块钱。跑到盐池买了100斤面,买了100斤盐,从盐池背到了延安换成了小米,又把100斤盐换成80斤小米。80斤小米也背上走了。白天不敢走,那时候有遣返,白天不敢走晚上走,背着一斗米走回来。你知道,走回来脊背压的稀巴烂,这个绣花秀看见王老五非常心疼,其实王老五的祖父是我家的一个长工,我们一直关系很好,他爷爷的媳妇还是我爷爷给问的,这个王老五为人忠厚、老实,住的房子也是自己铺的,结果他背回来的米就给大队书记发现了。几个坏怂就跟他要了,不给,这要拿命了,他妈的我拿命换来的咋能给你们。王老五把书记骂走了。但这个女人很聪明,把这个小米挖了一脸盆,让王老五送过去,如果不送给,就连一颗都没有了。书记说第二天就办学习班站大会,送给了就不必开会。这米救活了这一家人。所以说,在陕北,在中国,女人是领导,女人是作品。我曾经给人说,你看在陕北大树永远长在河湾和沟湾里,没有长在山峁上,所以男人是山,自许是山,所以他就只能在瓠子啊、野鸟啊、野兔啊在那山峁上圪蹴的叫唤个阵,就像男人一样,气血方刚地叫,但他永远长不成大树。这个家的领导,表面看似温热的女人,是这个家的方向,永远是,我家就也是这样。我爷爷是个知识分子,但我奶奶是方向;父亲虽然狡猾奸诈,但我父母是方向;我家虽然我整天地讲,我媳妇是方向。听女人的准没错,听男人的就完了。
看,这又是另一个故事,就是合葬。弟兄俩个是隔山弟兄,啥叫隔山弟兄大家知道,就是一个母亲两个老子,死后娘埋的不精明,在陕北非常讲究要合并,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埋到一块,但是埋不精明咋办呢。最后弟兄俩个都出来包工,都发了都有钱,都请下说手,我爷爷可吃美了,整天在这些家吃饸饹猪肉,然后我也蹭着饭。原来咋样埋了?就是中间埋了一个娘,两面埋了两个老子,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绝对不能这样埋的,一个草驴咋能占两个叫驴呢,就是这时候一个草驴只能和一个公驴去交配,咋能和两个公驴去交配呢?大家说这会死人,这会冲风水这会咋。最后妥协。一个娘两个老子,最后下来各儿埋各的老子,娘一直中间空着埋着,也没事,也很幸福。大家说没有这个娘是不行的,那你埋了我不埋,我对我的后人不好。传宗接代,这是有史以来中国老百姓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比金钱比什么都重要,你在陕北能看到有人就有一切,有钱不能有一切有权不能有一切,只要我有人,我户子大,我就会掌握这个村子的命运,村子的话语权。中国人出了问题是不会依照法律的,不会依照民主的,不会依靠知识的,是会找家长会找关系的,大家认为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社会最底层的那个结构是中国最稳定的结构。例如抢亲。凡是姓张的,每家出一个人,不出一个就把你家抄了,明天到谁谁谁家去抢亲,这本身是我们的媳妇来了,为甚成他们的了,动屋子去抢,抢不来了就把东西拉回来。真的是这样,我小时候就见证了这样抢亲,抢东西,抢死人,很多很多事,在那块土地上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些非理性的,用理性解决不了的事情。最终做下再说,就是说老百姓有句话说:管球了,做了再说,大不了头砍了算球了。人活一口气,真的,他们身上有这种精神,就是说知识分子身上有妥协性,他们没有,他们敢拿命跟你换,这是他们身上的一种东西,我们这里头不能说赞美,但我觉得有些东西,那种品质还是重要的,它本身这件事是坏事,但它那个做法你不能说它是坏事,它的目的不是为做坏而做的,它的目的是向善的。但它的手段是坏的。
看,这就是我画的那个埋死人的画。画面是6.6米×4.4米。它埋人埋不精明,在前戏打(注:陕北发言,指请来唢呐班子送葬奏乐)的时候耽误了时间。这家人杀了一口猪,过了三日宴席,吃了八九顿饭,这才把人埋下。到埋的时候娘都放臭了。在死亡的问题上,陕北人有一股痴劲。痴情救了老百姓,老百姓就是靠这种痴情和执着活下来的,你看看他们身上的那股劲,你再看看他们闹秧歌打花鼓子(就是打腰鼓)那种劲。他的那种吼声,你能感觉到。
看,这个老汉,执着的老汉,多么执着,尽管儿子死了,煤窑上被压死,眼含热泪,依然拿着 头去山里种地了。他没有被灾难击倒。看,这个母亲,背着一个弱智的儿子,真的,这个儿子是个傻子。小狗在门前照看家园。她依然像宗教一样走向远方,走向了那块希望的田野。这都是06年时候,我在最艰难的时候画下的。他们的希望太小了,他们的希望就是一只羊羔,你说那只羊羔喂得再大能卖多少钱啊,但这就是他们的希望。
这是我画的陕北的风景,这就讲到1992年。92年就进入另一个阶段,我认为中国在90年代以后,人变得不是人,人变得贪婪,变得自私。人变得一切向下。农民变坏,知识分子变坏,所有的人在变坏,走向腐化。老百姓为什么会变坏?还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社会没有给他们心灵留有通道,并不是没有在行为上和行动上给他们通道,是他们心灵的通道被堵死了。比如说82年到92年95年左右,念书是有希望的,能找到工作,92年95年以后念书找不到工作,改变不了命运,鲤鱼跳龙门跳不出去,农民就开始绝望。一定要拯救他们的灵魂,拯救他们的通道,这个是今天的知识分子们的责任,你们有文化就能疏通这种通道,能给社会以理性,只有这个通道通了国家才有希望,民族就会有信心,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对啊,我没有做研究,我都是感性的,都是以艺术家的那种体验来判断这些。
再来说一个事情。一个老光棍找不下媳妇,他会拿女儿给自己换亲,他会拿自己的女儿给自己的哥哥换亲。换亲,非常残忍,就是让你换了就是一种契约,你永远不能反叛。我们村里头有一个叫篮子的,她曾经就换亲换的,我给她了15块钱,她跑了。后来在西安也发了财,她觉得欠着那家人的,又回来拿钱花了12万给那个换的人。这个篮子有良心,回来给她曾经那个丈夫买了个媳妇,她的心理才会平衡,就说传宗接代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是活下去的一个信念。再像这家人:大顺和二顺。父母把他们拉大了,到了他们日子过好的时候,父亲瘫到炕上了,而且性子很烈,他俩不孝敬不侍候不给吃饭,父亲一个人爬,那阵没有轮椅,就爬爬爬到摨崖下摔死,就在摨崖下把自己掼死,掼死以后,活着不给吃,死了以后摆了八碗给全村人吃了好吃的,这就是人性。就两个儿子,日子都过得很好,还你推给我我推给你,因为瘫子么,他拉屎送尿太脏了嫌见不得人。父亲跳摨自杀了,这是农民的那种血性。我一直觉得这里头很残忍,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力量,一直在感染着我,让我的血液时刻在燃烧。
看,还要讲一个故事,就是计划生育的故事。八几年九几年中国的计划生育非常残忍,但是在陕北,生不下儿子是耻辱的。泰哥啊生了6个女儿,门窗全被打完,要逼着结扎。黄宏演过一个计划生育方面的小品,这件事要比那个残得多了。生了6个女儿,最后生了2个儿子。你知道吧?他就是为了在村子正名。这个泰哥做了什么样的举动?生下第一个儿子,他把祖坟上的一棵树——老槐树给刨了,给村里说,这他妈我们的祖坟说冒青烟了从来不冒,我把这个老槐树刨了,给老祖先说我生了一个儿子。他的行为就行为这么极端。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把他祖传的最好的一个锅抬出到当院来,煮了一锅肉,拿个老 头几 头把锅砸碎,告诉村里人,他这是为了2个儿子表决心。都穷成那样了,还要在村里给自己正名:我泰哥终于有儿子了!这种决心,或者说这种愚昧——里头是有力量的。
我们的生活就像这磨道里的驴,我们每个人都想超越自己,实际就像磨磨的驴一样,蒙着眼睛在磨道里头转一天还在磨道里头转着了,转啊转,真是。在有些方面,陕北人真的就像是磨道里的驴,比如说对爱情的那种渴望——信天游里头,比如说——表达爱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我爱上你,咱俩个结婚了,脸挨脸,脸挨脸拉话我还想你。(唱起来)叫妹妹啊,我想你,在山上的水下口的等你。没有底气了,我等一会结束给大家唱一段。
一户人家,弟兄三个,抢回来三个媳妇。都是光棍汉,家里穷。偏僻的地方又问不下媳妇,只好抢。我们村里头前后抢回来8个媳妇,年龄跟我差不多,有两个跑了。这弟兄三个非常穷,抢来三个媳妇,其中一个好像是城里娃,天天挨打,很可怜,但是没有人去告。最后把那个就打死了,埋了。就这样,也没有人报案,这就死了。
再给大家看一幅画吧。这是我画的一个抽象意向的,黄土高原的一个气象,看,这都是画了我们的山,一种印象,不是写实的。这块土地是有力量的,这块土地不仅诞生了人类原始的一种人性,也诞生了共产党,燃起另一种希望。
活着的承受,我画的画就是一种活着的承受。大家看这张画,12米×4米,很大,是一个集体的神像。它画的是霜降,庚寅年画的。庚寅霜降,就是秋收将要结束的时候的一种状态,人的一种状态,虽然在漆黑里头,但它生机勃勃,充满着力量,每个人想法不同,每个人看似没有关系但他们有关系。看,我为啥重复的一个形象是一棵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棵树,是这棵树上的一个枝叶一个根,只有当这棵树长大的时候我们才会长大,所以我们绝不用绝望,我们不管多么艰难都要看到我们的国家在上升在强盛,绝对不是在走下坡路,但我们的人性通道在迷失,需要几十年来完成。
看吧,这幅画!看这个老头还在切土豆,切掉土豆上发出的芽。你知道,你吃的那个炒土豆丝,这就是第一道工序,看着它长着芽子,让城里人说就不能吃了,农村人说这还能吃呀。要把它剜了,去播种,种下了,然后卖土豆。当你看到这个老头和这个人的时候你就看到生活是有希望的,你不能对生活失去信心,何况你们读到博士读到研究生,哪还能没信心呢,你们再苦也不会苦到像他们那样去苦,也不会像我那样去苦。
看,当你看着这幅图,这幅图主宰的时候你就知道生命的延续是多么的可贵,你看看这棵枣树的叶子那么的绿的时候,天那么蓝的时候,尽管那块土地不进步,你还能觉得没希望吗?多么温情,多么善良,多么宽容,多么美啊,陕北!
看,当你看到受苦人赶着牛,在播种的时候的小俩口,这不是在输入希望吗,你击地来我耕种,有一首歌说:天上有些啥羊肚肚呦,地下有啥些里沟着壕,站岗啥石砂啥留下个人,呀呼哎咳个人,那就是咱男人和女人。天上有些疙瘩瘩羊肚肚牛,地下有些里沟沟壕,老天爷留下的男人和女人。意思就是这样的。
看,这个画!活下去就是希望。这是一个春天播种的季节,我画的这张画依然是12米X4米。当你看到惊悚的眼光,当它希望的土地投向恶的土地的时候,它依然会根深叶茂,你不要相信这是绝望,这是绝对的窒息的力量,承载这个世界的力量。人越活到黑暗里头,他对希望越具有渴望,希望和渴望是刻骨铭心的,看着这个山头扭秧歌还能没希望,我给大家唱一首秧歌啊:住在个前里仔细个关啊,我把个妹妹眼睛眨啊,红个纯纯嘴唇刚吃了饭啊,毛个生生的眼睛把我看。
看,锣鼓喧天,这些人能叫喊这么多年,直到今天这个时候这种力量还是没有消失。这就是我们中国,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这就是我们受苦人。看,当你看着这个村子,看着这条路,我小时候冒雨踏着这条路,心想走出这个村子,它就是希望,只要走出去就是希望,只要待下来就是生命的延续,就是繁衍后代的一种仪式,只要有虚无的土地在,只要有人在,就有希望。看,这孔土窑洞,这样繁花似锦的窑洞,这样火红的地毯,你还能觉得生活不美好吗,虽然我画的阴暗,但是生活是美好的,放着这样的电视,这样的比对,你觉得这不是幸福吗,能在这个炕上睡一个女人是多么幸福啊。看,看着羊在这片静谧的蓝天下,这片富有优越感和思绪的大树,你能觉得这幅诗这幅画不美吗,它不是又回到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那种理想主义的状态吗,我们今天还能说羊倌啊,真幸福。
有一首歌,放羊人唱的,我给大家唱一下(站起来,唱):大碗开花,鎏金子的红哦,大姑娘爱上个俊后生,拦羊山枣在背梁上,籽梅啊长在那个干峁峁上;干畔的羊儿光堂堂啊,我把那妹妹叫一声,今下地我要上你的路。
看,看着这群生机的夜景你还会觉得没有希望吗,太有希望了,生活就是这样,幸福不是因为今天有多少,幸福不是因为有多少高级小轿车,有多少房子,幸福是心灵的升华,真的,升华心灵你就会幸福,升华后你的心灵就会很坦然。
本言论纯属个人观点啊!
最后给大家唱一首陕北的民歌,关于爱情的:骑上那个毛驴啊,狗咬腿,半夜里那想起那干妹呀妹;走了那个五里呦又五里,三五走了十五里,哎呀我的那个妹子呦;双翠翠的那个呦,头前罗圈着腿腿,抱住妹妹亲个嘴哦,一二呀呼嘿;冬里那个更大窑啊,化成了芽腿腿(注:陕北方言:意思是一根葱)。
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