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前,大海边
2011-1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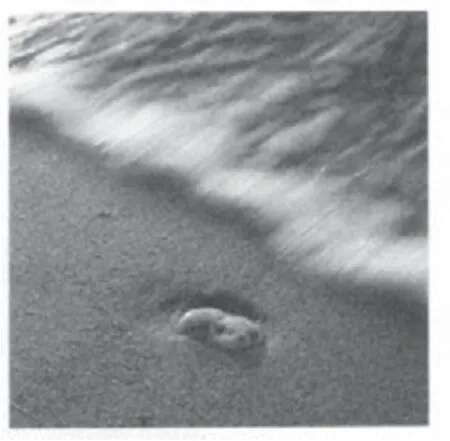
早应了叶舟,为他的小说集写序。但一直没有写。拖着。下笔艰难。
是因为看到了张承志为他写的文章。张承志谈到了“‘T’们”的命运,他们的“某种空洞和一丝轻浮”。
“‘T’们”包括叶舟,我自认也包括我。作为多年挚友,我和叶舟不仅是喝酒吃肉的关系,也有半醉了,默然相对,相会于心的时刻,我们是同类。
我和他,大概都很少郑重地想这个问题——在这个时代,最少被思考、省察的关系或许就是“朋友”,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又是孤魂野鬼,我们不惮于袒露和他人之间世俗的和欲望、实利的关联,但我们羞于正视和他人的精神上的深度联系:可以告诉别人我们谈论了一晚上女人、钱财和八卦,但不能告诉别人,我们谈论了一晚上精神、生命和意义。
那是隐私。是秘密。
“朋友”变成狭邪之事,也只有狭邪着,才能示人。
——我不是在说别人,是说自己,是说我们任由某种力量支配着,张承志说的没错,这就是“轻浮”。
但当要写叶舟的序时,被张承志的序所逼,我不得不思考,作为江湖上、荒野上的两个同类,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为叶舟的序所苦的时间里,我去了耶路撒冷,我到了耶稣受难前被囚禁的“鸡鸣堂”——最后的晚餐散了,耶稣和门徒们向橄榄山走去,耶稣说:
“今夜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
保罗说:
“即便众人都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决不会跌倒。”
耶稣:
“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保罗:
“即便我该同你一起死,我也决不会不认你。”
然后,耶稣被捕了。就在这里,当时的牢狱、现在的“鸡鸣堂”外,保罗在庭院里、在人群中坐着,耶稣正在里面遭受羞辱和拷打,一个使女走过来,指着保罗:
“你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起的。”
保罗躲开众人的眼睛,说: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他退到门廊,又有一个使女指着他对众人说:
“这人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起的。”
保罗发誓道:
“我不认识这个人。”
过了一会儿,人群中有人、也许就是一群人,走过来,指着他:
“的确,你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
保罗赌咒发誓:
“我不认识这个人。”
就在此时,鸡叫了。
保罗一个人,走到外面,远离人群,痛哭。
——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在寂静无人的鸡鸣堂里,我一个人站着,感到这世上所有的人,我,都是保罗。
人的怯懦,人的软弱,耶稣是知道的,耶稣对此并不意外,他把这作为立教的起点。
人在卑下中承担着精神的重量:他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知道什么,但他不说出。
好了,现在,说叶舟。我和叶舟相识于今十几年,十几年前,我就认为,他具有独特、珍稀的性情、力量和才华。
我们那时都年轻,现在,中年了,渐渐老去。
仅就小说而言,我怀念十几年前的叶舟,那个大胆狂徒,那个醉鬼和侠客,那个“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少年。
渐渐地,小说家叶舟成熟了、老练了,他有时似乎知道该写什么该怎么写了。但我还是怀念昔日的他。
但现在的叶舟其实是不“流畅”的——张承志认为他“流畅”,可能是因为他不了解叶舟的底细。一把刀,覆盖油和肉,但我知道,瘦骨和锋刃仍在,我看去,就常觉得不自然、不流畅,感到他勉强了自己。
有的时候,一下子锋芒毕露,写出《羊群入城》那样的小说:他似乎洗去了他操练得溜熟的普通话,他的口音冒出来,质朴、桀骜的口音。
那个少年还在的。我知道。但在这茫茫人海、万丈红尘中,那个少年有足够的聪明,就有足够的老成、犹豫和恐惧、思虑,他知道他的刀、他的口音迎来的只是人群中的寂寞或一两声哂笑——连哄笑都不会有,甚至不会有人有兴趣指出他、认出他。他怕吗?或许他是怕的,他怕他所面对的广大柔软如水的世界,他“见多识广”,知道,刀切不开水。
更重要的是,他和他——“‘T’们”,在他们的血液中天然地包含着怀疑和狐疑的元素,他们怀疑一切专断,他们首先怀疑自己的专断、自己的刀。
他们或许真的是一代寂寞的人,在这种不敢信中,老去。
但是……还有“但是”吗?
这是问题。
——在加利利海边,我看着耶稣和保罗的塑像:耶稣复活后,显现于此,他注视着保罗,说:
“你比他们更爱我吗?”
保罗说: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
“你爱我吗?”
保罗: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
“你爱我吗?”
保罗:
“主啊,一切你都知道,你晓得我爱你。”
那时候,我心中酸楚。
——对于我、对于叶舟,这不是一个宗教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真理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