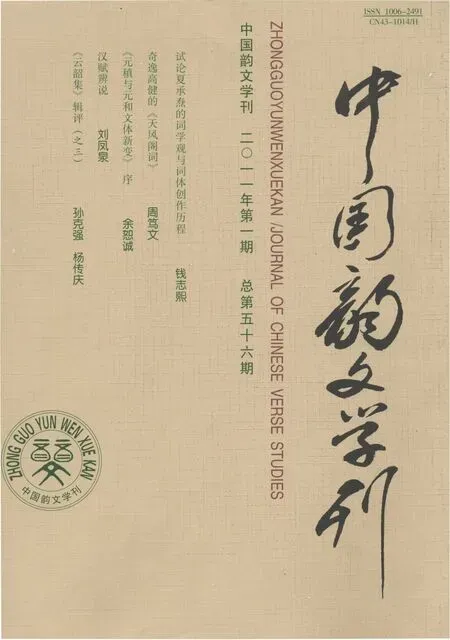近十年汉魏六朝乐府歌辞研究综述
2011-11-19吴大顺
吴大顺
(怀化学院 中文系,湖南 怀化 418008)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
近十年来,乐府歌辞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来,关于汉魏六朝乐府歌辞研究的专著有钱志熙《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大象出版社 2000年版)、赵敏俐等《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孙尚勇《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年版)、王志清《晋宋乐府诗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刘旭青《汉代歌诗研究》(武汉出版社 2008年版)、吴大顺《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版)等 6部;研究论文达 500馀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 40馀篇、博士学位论文 20馀篇。①研究论文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统计资料从 2000年 1月至 2009年6月。研究领域得到极大的拓展,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更加多元,研究观念更加开放自觉。下面将从乐府歌辞音乐性研究、乐府制度与文化研究、乐府歌辞文学性研究、文人拟歌辞研究等方面作简要回顾。
(一)乐府歌辞音乐性研究
从音乐角度研究乐府歌辞兴起于 20世纪三十年代,六七十年代文学主题学研究的兴盛,使这一课题一度受到冷落,近年这一研究视角再次受到学界的重视。主要研究不同音乐类别的表演特点、文化功能及其与歌辞的关系。其研究内容涉及郊庙、燕射、鼓吹、横吹、相和、清商、舞曲、琴曲、杂曲、杂歌谣等十类乐曲歌辞。
第一,郊庙、燕射歌辞研究。在郊庙、燕射歌辞研究方面,主要讨论了如下一些问题:
一是郊庙制度与郊庙歌辞的关系。如王长华、许倩《汉〈郊祀歌〉与汉武帝时期的郊祀礼乐》认为:“汉武帝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下,以新的宗教思想指导郊祀,不仅在词曲创作方面以新声代雅乐,祭祀方式上回归由夏至楚的夜祭旧制,而且其郊祀乐歌中充斥着明显的游仙倾向。”[1]张树国《汉至唐郊祀制度沿革与郊祀歌辞研究》认为:“郊祀祭天是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中心,帝王通过‘绝地天通’,获得沟通神圣世界与世俗国家的独占权,以之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终极来源,郊祀仪式中的巫祭乐舞、游仙乐舞、民间俗乐、胡部新声丰富了郊祀乐歌的表现力和艺术性,郊祀乐章与诗篇是祈祷、祝颂等宗教情感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2]其《诗成何以感鬼神——汉唐乐志中的诗学观念及郊庙祭歌形态研究》则将历代郊庙乐章的创制形态分为自制雅乐、以古入雅、以俗入雅及以胡入雅四种类型。其他如梁海燕《〈武德舞歌诗〉与汉代宗庙祭仪的传承演变》(《许昌学院学报》2006年第 6期)等论文对之也有所涉及。二是郊庙歌辞的主题与文化内涵分析。如张树国认为:“保存在《周颂》、《楚辞》及汉唐《郊庙歌辞》中的太阳祭歌是对太阳崇拜的艺术赋形,是仪式活动中祝祷、祈求诸多情感的表现。”[3]其它论文如曾祥旭《论〈郊祀歌〉的神仙思想》(《南都学坛》2002年第 1期)、罗慧《汉〈郊祀歌〉的天道观阐释》(《社科纵横》2009年第 3期)等也是探析郊庙歌辞的主题与文化内涵的。三是郊庙歌辞的作者与创作时间考证。如龙文玲《汉〈郊祀歌〉十九章作者辨证》(《学术论坛》2005年第 4期)、王福利《汉郊祀歌中“邹子乐”的含义及其相关问题》(《乐府学》第三辑,2008年)、张树国《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立与〈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 2期)等。
关于燕射歌辞的研究比较少见。尚丽新《汉代食举乐考》(《黄钟》2002年第 4期),分析了汉代食举乐的分类和内容、传承中的流变及其在汉代宫廷音乐中的地位等问题。
第二,鼓吹、横吹曲辞研究。近十年有关鼓吹、横吹曲辞的研究成果也很多,其中韩宁的博士论文《鼓吹横吹曲辞研究》(2006年完成,吴相洲《乐府诗集研究》的子课题)是一篇关于鼓吹、横吹曲的专论,论文对鼓吹、横吹曲辞的渊源、在南朝的文人化进程、与唐代边塞诗关系等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此外,鼓吹、横吹曲辞研究还涉及了如下问题:
一是鼓吹、横吹曲的音乐源流及文化功能问题。孙尚勇《黄门鼓吹考》认为:“黄门鼓吹的音乐内容是鼓吹曲,其本原功能是用于乘舆仪仗,四品乐都属于仪式用乐。”[4]其《横吹曲考论》(《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 1期)对横吹曲在汉魏六朝隋唐时期的发展变迁进行了致梳理。曾智安《梁鼓角横吹曲杂考》(《乐府学》第三辑,2008年)认为梁鼓角横吹曲主体为十六国及北朝乐歌,是南北文化交流的独特产物。刘斌《六朝鼓吹乐及其与“五礼”制度的关系研究》(上、下)(《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 1、2期)、洪卫中《魏晋南北朝鼓吹的种类、功用和特征》(《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 1期)等论文主要讨论了鼓吹曲辞的文化功能。二是鼓吹、横吹的生存与传播问题。吴大顺《北狄乐考论》(上、下)(《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 10期、2008年第 7期)讨论了“北狄乐”的内涵、历史变迁以及南传的时间与途径。刘怀荣《汉魏以来北方鼓吹乐横吹乐及其南传考论》(《黄钟》2009年第 1期)、韩宁《乐府横吹曲〈梅花落〉考》(《乐府学》第三辑,2008年)等论文也涉及到鼓吹、横吹曲的生存与流传问题。三是鼓吹、横吹曲辞的文本解读。如姚小鸥《〈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文本类型与解读方法》(《复旦学报》2005年第 1期)、许云和《汉鼓吹镜歌第十八曲〈石留〉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 6期)等。
第三,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研究。相和歌辞和清商曲辞是艺术成就最高、与中国诗歌发展演进关系最密切的歌辞,因此,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关注点。近十年,对这两类乐府研究表现出了继续活跃的势头,主要涉及了如下问题:
一是相和歌概念及与清商三调的关系。吴大顺认为:“‘相和歌’是特指魏晋时期‘丝竹更相和’的‘十三曲’清商曲,其称名到刘宋时期才出现,清商三调是在相和歌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其音乐渊源与相和歌一样,皆出于清商曲。”[5]翟景运认为:“与清商三调歌并无直接关系的‘相和歌十七曲’是‘相和歌’的本义,囊括清商三调歌与相和歌十七曲为一体的‘相和歌’则最早出现在唐代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由吴兢误读前代文献而产生。后者与汉魏六朝时期乐府的实际情形不符,却能够长久流行,产生较大的影响,是因为它在乐府内容的归类方面包含着极有价值的因素。”[6]王传飞认为:“郭茂倩《乐府诗集》编纂相和歌辞的标准与范围正是相和歌概念动态发展的体现。”[7]三人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均认识到“相和歌”不是对汉代民间乐府的泛称,而是特称魏晋时期丝竹更相和的“十三曲”或“十七曲”,纠正了目前学术界对相和歌的认识。二是相和歌表演方式与辞乐关系。崔炼农《相和唱奏方式与辞乐关系》认为:“所有以‘相和’为本质特征的唱奏方式,按构成因素可以分为人声相和、节歌相和、歌吹相和、弦歌相和、丝竹相和五种基本类型,‘相和’唱奏方式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其中包含歌乐不相重叠、歌乐交错、歌乐重奏三种辞乐关系。”[8]王传飞认为:“相和歌作为乐府相和歌表演艺术整体一部分的‘相和歌辞’,是相和歌的歌诗文本,其歌诗演唱的性质与功能,决定了相和歌辞独特的艺术构成,其语言形式与叙事特色也深受相和歌表演艺术的影响,与徒诗不同。”[7]刘怀荣《从演唱方式看清商曲辞艺术特点的形成》认为:“南方民间情歌即兴创作的背景、方式及其交际功能与清商新声的演唱方式,从两个方面共同决定了清商曲辞通俗短小、男女赠答及重抒情、轻叙事等基本的艺术特点。”[9]三是相和、清商曲辞的文献分析。如杨明《〈乐府诗集〉“相和歌辞”题解释读》(《古籍整理学刊》2006年第 3期)对郭茂倩所撰写“相和歌辞”的若干题解加以分析,部分纠正了人们对《古今乐录》辗转引述荀勖、张永、王僧虔等著作而产生的曲解。四是清商三调的乐律学研究。王誉声《相和三调“三种音阶”说》(《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 3期)认为相和三调为三种音阶。徐荣坤《释相和三调及相和五调》(《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 1期)认为相和三调是三种调高,瑟调为宫,清调为商,平调为徵。成军《清商三调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也认为清商三调为三种调高。
第四,舞曲、琴曲歌辞研究。舞曲、琴曲歌辞的研究在近十年也显得比较活跃,主要讨论的问题有:
一是舞曲、琴曲歌辞文献研究。如梁海燕《舞曲歌辞类目成因考》(《乐府学》第 1辑,2006年)对《乐府诗集·舞曲歌辞》作品来源、著录体式、收录标准进行了考察。过元琛《关于“王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及琴曲《怨旷思惟歌》的产生年代——兼考今本〈琴操〉的撰者》(《复旦学报》2009年第 3期)认为《琴操》出于晋代,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是东晋文学自觉风气的产物。元娟莉《乐府琴曲歌辞古题辨析》(《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 3期)认为乐府琴曲歌辞“操”、“引”、“弄”、“畅”等古题在文学特征、音乐风格等方面呈现出类型化特点,此特点与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二是舞曲、琴曲的流变研究。如吴大顺《〈明君曲〉考述》(《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5年第 4期)对《明君曲》的音乐形态及流传情况进行了考述。吴叶《从琴曲〈大胡茄〉〈小胡茄〉试探汉唐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音调》(《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 1期)通过对大、小《胡茄》历史、音乐两方面的考证,探寻我国汉唐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基因。三是舞曲歌辞的文本研究。如姚小鸥《〈巾舞歌辞〉与中国早期戏剧的剧本形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 2期)破译了向来不可晓解的《巾舞歌辞》文本,并从唱词、角色标识字、舞台提示字等方面分析了其舞台表演的特点,认为西汉的《巾舞歌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戏剧角本。田彩仙《六朝“白纻舞歌辞”的发展及审美价值》认为:“白纻舞辞不仅充分展现了女性舞者的轻柔美与忧怨美,而且还通过各种修辞手法完成了舞之意境向诗之意境的转换,充分展现了六朝重‘情’与重‘韵’的精神特质。”[10]曾智安《西曲舞曲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曲辞结构》(《文学评论》2008年第 5期)认为西曲舞曲曲辞通常采用的场景联章叙事体是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曲辞结构的来源。此外,梁海燕《舞曲乐府诗的文体特征探讨》(《延安大学学报》2009年第 1期)专门分析了舞曲歌辞的文本特点。
第五,杂曲歌辞、杂歌谣辞研究。
一是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的专题研究。有人从音乐类别出发,对这些歌辞进行专题研究,讨论其音乐特点、传播方式与艺术风格等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向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首都师范大学 2005年硕士论文,吴相洲《〈乐府诗集〉研究》子课题),论文分上下编,上编对杂曲歌辞的音乐属性、曹植杂曲作品的入乐问题与《行路难》歌辞的入乐问题、杂曲歌辞的文学特点等进行了论述,下编则对歌谣的音乐性质、流传保存与采集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这样集中讨论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的成果尚不多见。二是单个曲调及作家的歌辞研究。如王小盾《〈行路难〉与魏晋南北朝的说唱艺术》(《清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 1期)通过对《行路难》渊源和流变的考察,揭示了魏晋南北朝说唱艺术的表演方式、音乐渊源及其在唐代音乐文学活动中的影响。其它论文如王淑梅《曹植杂曲歌辞的音乐性质考论》(《乐府学》第 3辑,2008年)等。三是歌谣研究。如尚丽新《中古时期的“歌”、“谣”观——以〈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为例》(《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 3期)梳理了从先秦到唐代“歌”、“谣”观念的流变及其内涵,并以《乐府诗集》为例分析了中古时期的“歌”、“谣”观。其它论文如王凯旋《汉代谣谚与世风》(《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 6期)、高贤栋《北朝时政谣谚与民间信仰》(《民俗研究》2004年第 1期)、吴海燕《魏晋南北朝民间谣谚对封建统治的揭露和贬斥》(《平原大学学报》2003年第 2期)等。
(二)乐府制度与歌辞文化研究
第一,乐府制度研究。近十年的乐府制度研究主要涉及到汉乐府机构的源流及职能与乐府职官及职能等问题。
关于乐府机构的成立时间,一直是乐府研究关注的重点,1977年秦乐府钟的出土,推翻了汉武帝始立乐府的观点。陈四海《从秦乐府钟秦封泥的出土谈秦始皇建立乐府的音乐思想》(《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 1期)又从 2000年西安市郊出土的带有“乐府”字样的秦封泥,进一步印证了在秦已有乐府的观点。以此为基础,学界对《汉书》武帝“乃立乐府”解释为“重建、扩充的意思”(赵敏俐《重论汉武帝“立乐府”的文学艺术史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 5期)。龙文玲《汉武帝立乐府时间考》(《学术论坛》2007年第 3期)进一步考证了汉武帝立乐府的具体时间。王福利《汉武帝“始立乐府”的真正含义及其礼乐问题》(《乐府学》第 1辑,2006年)认为武帝“立乐府”的内涵在于使乐府的根本职能及政治、社会地位发生了本质变化。刘彭冰、陈晨《论汉武“乃立乐府”》(《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 2期)也认为武帝只是强化了汉代乐府的职能。赵敏俐《汉代乐府官署兴废考论》认为:“所谓汉武帝‘立乐府’,实则是对汉初乐府官署的规模扩充和职责扩大,其目的是用新声变曲为国家郊祀之礼配乐。汉哀帝罢乐府之后,整个东汉时代并没有重新设立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乐官机构。”[11]比较而言,赵说比较全面合理。许继起《昭、宣至新莽时期乐府述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 1期)从制度史的角度考察了各朝郊祀、宗庙礼仪制度及乐府职官制度的建设。其它如张祝平《西汉乐府职能新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 1期)、李锦旺《西汉乐府的职能演变及其名称的沿用》(《齐鲁学刊》2004年第 5期)、孙尚勇《乐府建置考》(《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 4期)等论文均讨论了汉乐府机构及职能问题。
乐府职官与职能研究方面,有刘怀荣《魏晋乐府官署演变考》(《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 5期)、《南北朝及隋代乐府官署演变考》(《黄钟》2004年第 2期)等论文。吴大顺《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与歌辞研究》(扬州大学博士论文 2005年)上编“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构建史论”也分别对曹魏西晋、东晋、南朝、北朝的宫廷音乐机构建制与职能问题进行了考辨。
第二,乐府歌辞的文化研究。主要涉及到特定文化背景对乐府歌辞的影响、乐府歌辞体现的文化制度与文化内涵等问题。
李山《经学观念与汉乐府、大赋的文学生成》分析了汉代经学与乐府诗的关联,认为:“没有经学的‘王官采诗说’,就没有汉乐府的设立,没人去采诗,那些饥者、劳者的歌唱也就得不到保存,难以进入到后人的历史视野中。”[12]徐无兴《西汉武、宣两朝的国家祀典与乐府的造作》(《文学遗产》2004年第 5期)讨论了汉武帝、宣帝朝国家祭祀制度建设与乐府诗创作的关系。赵明正《汉代养生思潮、经学诗教与汉乐府》(《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 5期)认为汉代养生思潮提倡“固精保气”、反对情感的抒发和儒家诗教主张诗歌“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和观念,造成了汉代文学抒情式微而叙事发达的态势。吴大顺《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的演唱及其文化功能》(《船山学刊》2007年第 3期)分析了郊庙、燕射、鼓吹等仪式歌辞与相和三调、吴歌西曲等娱乐歌辞的表演情况和各自的文化功能。曾祥旭《汉乐府中所见的道家思想和道家审美观念》(《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 5期)分析了汉乐府中所体现的游仙长生、福祸无常、死亡意识与针砭现实的道家思想与以自然为美、以奇调为美、以形写神的道家美学观。张宗原《论北朝民间“婚恋”歌辞》(《复旦学报》2003年第 2期)则从婚恋习俗和婚庆仪式等角度,对北朝民间“婚恋”歌辞进行了论述。阎步克《汉乐府〈陌上桑〉中的官制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 2期)、王莉《汉乐府中“郎官”问题考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 2期)、《论“夸富”类题材汉乐府的官职问题》(《殷都学刊》2006年第 4期)等论文则讨论了乐府歌辞中反映的官制问题。
(三)乐府歌辞文学性研究
主要研究乐府歌辞的生成及传播形态与歌辞文本、乐府歌辞的音乐文化背景与某种诗歌现象的关系,以及乐府歌辞的思想主题与艺术形式等问题。
第一,乐府歌辞生产、传播方式与歌辞文本的关系研究。如赵敏俐《汉代歌诗艺术生产的基本特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 4期)认为汉代在以汉乐府为代表的两汉歌诗艺术生产中,不同程度上发展或完善了自娱式、寄食制和卖艺制这三种古老的艺术生产方式,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征,而其《汉乐府歌诗演唱与语言形式之关系》(《文学评论》2005年第 5期)则对汉乐府表演的戏剧化、程式化与乐府歌辞叙事体裁、歌辞技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廖群《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也认为:“汉乐府厅堂说唱的传播方式,导致了诗歌由抒情言志向娱宾乐主功能转化,汉乐府的叙事再现性、戏剧表演性以及世俗生活化与此有直接关系。”[13]吴大顺《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传播与诗歌史意义》则认为:“歌辞文本传播方式的产生,使歌辞的文化功能出现分化与转移,文人歌辞的诗性特质受到重视,从而在诗歌内容、生存方式、创作观念等方面带来了深刻变革,使中国诗歌发展获得了诸多创新变化的历史机遇。”[14]钱志熙《论魏晋南北朝乐府体五言的文体演变——兼论其与徒诗五言体之间文体上的分合关系》认为:“乐府体五言在脱离音乐之后,一方面在形式上受到徒诗五言藻饰、对仗等修辞技巧的影响,内容上受到徒诗五言主观抒情、哲理化等作风的影响。但作为乐府体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保持其体裁的特点,与汉乐府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15]其它如姚小鸥《汉魏六朝曲唱文本的破译及其在乐府文学研究中的意义》(《文艺研究》2002年第 4期)、刘旭青,李昌集《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与歌诗》(《扬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 2期)、赵敏俐《歌诗与诵诗:汉代诗歌的文体流变及功能分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 6期)、徐明《从〈乐府诗集〉看古代诗的传播与音乐之关系》(《河北学刊》2002年第 5期)、曾晓峰,彭卫鸿《试析汉乐府文事相依的传播特点》(《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 2期)等论文也是从歌辞传播方式对歌辞文本生成的影响角度展开的。
第二,音乐文化及乐府歌辞与某种诗歌现象的关系。如钱志熙《汉代乐府与戏剧》(《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 4期)从“乐”的综合性娱乐艺术性质及“乐府”作为执掌这种综合性艺术的机构入手,发掘存在于汉郊祀乐章及相和歌诗中的戏剧表演及戏剧文学的因素,在娱乐艺术的完整体系中,认识乐府与后世戏剧的关系。其它如胡大雷《宫体诗与南朝乐府》(《文学遗产》2001年第 6期)、傅刚《南朝乐府古辞的改造与艳情诗的写作》(《文学遗产》2004年第 3期)、吴相洲《论永明体的出现与音乐之关系》(《中国诗歌研究》第一辑)、刘怀荣《西晋故事体歌诗与后代说唱文学之关系考论》(《文史哲》2005年第 2期)、吴大顺《梁武帝音乐文化活动与梁代宫体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 3期)等。
第三,乐府歌辞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研究
解放以来,乐府歌辞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研究一直是乐府研究的热点。近十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孔雀东南飞》、《木兰诗》、《西洲曲》等经典名篇的思想与艺术研究。总体上,这方面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不大,大部分论文基本上是对六七十年代观点的重复和补充。谢国先《特定的文学作品与普遍的社会心理》(《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 3期)别有新意,文章把《孔雀东南飞》中的婆媳矛盾置于全球文化背景下进行观照,认为《孔雀东南飞》这一家庭悲剧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性。在老年寡妇和他的儿子、儿媳组成的非完整的扩大家庭中,婆婆和儿媳争夺他们共同关心的男子的情感是这个家庭内的永恒难题,家庭内的情感争夺与社会制度、民族传统并无必然联系。
二是乐府歌辞的妇女形象研究。如胡大雷《从汉代的采风政策与董仲舒的家庭观看汉乐府民歌妇女形象》(《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 2期)认为汉乐府民歌中的妇女形象具有奇行异事化的倾向,并从乐府歌辞文体、汉代采风政策、汉代家庭观等三方面分析其原因。其它论文如廖红《从汉乐府民歌之弃妇诗看封建社会定型期的妇女问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专辑)、辛世芬《汉乐府民歌中的妇女形象分析》(《社科纵横》2005年第 6期)、李杰玲,李寅生《扇子·女子·符号——从汉乐府《怨歌行》看“扇子”的文学符号化》(《唐都学刊》2008年第 5期)等。
三是乐府歌辞的艺术特点分析。如王福利《汉庙祭乐歌辞的语言结构形式及其艺术风格》认为:“汉内外庙祭创造和使用的乐章歌辞语言结构形式,主要是西汉时楚地具有代表性的特殊地域性语言和该类乐章歌辞要求使然,带有很强烈的“原生态”特点,以它们为代表的汉庙祭乐章歌辞,体现出了质朴无华,气象宏大、古穆精奇,典雅宏奥、唱叹吟咏,寓教于乐等艺术风格。”[16]其它如朱大银,张艮《乐府歌辞〈采莲曲〉文学审美意蕴脞说》(《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 3期)、沙云星《试论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专辑)、廖雨《戏剧化的两汉乐府民歌》(《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 5期)、《发调既清修辞亦绣——略谈汉乐府民歌的修辞美》(《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 18期)等。这些论文多从艺术角度分析了乐府歌辞叙事、修辞特点,但大多泛泛而论,创建不多。值得一提的是王福利的论文,该文从艺术风格、语言结构方面对郊庙歌辞进行研究,此前并不多见。
(四)文人拟歌辞研究
文人拟歌辞是近十年乐府研究关注的又一热点。从创作主体看,除原来一直关注的三曹、鲍照外,陆机、沈约、梁武帝萧衍的乐府歌辞创作开始受人关注。
第一,三曹及建安乐府研究。主要讨论三曹、建安乐府歌辞的特点及其对汉乐府的继承与新变问题。孙娟,黄震云《清商曲辞与曹操诗歌的声韵艺术》指出:“曹操诗歌体式、韵律受《诗经》影响比较大,但能自作新声,以情志为创作中心,结合运用胡笳等乐器,因此慷慨苍凉,清刚气长。”[17]其它如唐会霞《曹魏的乐府诗创作对汉乐府的接受》(《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 2期)、李成林《论三曹乐府诗对两汉民间乐府的继承》(《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 4期)、傅正义《论曹丕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发展性贡献》(《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论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6年第 3期)则从创新的角度分析了三曹乐府的文学贡献。赵红玲,王俊洁《三曹以外的建安文士乐府创作低靡之原由新论》(《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 1期)对三曹以外建安文人乐府歌辞创作低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王辉斌《三曹雅好乐府的原因及其情结述论》(《乐府学》第 2辑,2007年)分析了三曹父子雅好乐府的原因。
第二,鲍照乐府诗研究。葛晓音《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通过对鲍照诗集中用“代”字题的乐府诗的辨析发现,“代”字体乐府大都寄托了鲍照个人独特的身世之感,在内容主题上显示出不同于旧题乐府的特点,不加“代”字的乐府则大都是模仿晋宋时期新兴的清商曲辞,没有任何个人寄托。并以此认为:“鲍照的代乐府反映了鲍照对于汉魏乐府体式及其创作特征的深刻体认,为唐代学习汉魏乐府提供了宝贵经验。”[18]
第三,其他文人乐府诗研究。孙明君《咏新曲于故声——改造旧经典、再造新范型的陆机乐府》认为:“陆机不仅用绮靡的风格去改造旧经典,同时,用乐府记录和再现了贵族们的物质生活,从而将文士乐府引入到士族文人乐府的苑囿。”[19]其它如唐会霞,赵红《论沈约对汉乐府的接受》(《求索》2007年第 4期)等。
第四,对某一类别乐府歌辞的拟作研究。很多学者以某一音乐类别的歌辞作为研究视角,分析乐府歌辞的拟作及文人化进程。如韩宁《南北朝时期乐府鼓吹曲辞的文人化进程》(《乐府学》第 1辑, 2006年)对朝廷制作的鼓吹曲辞与文人创作的鼓吹乐府进行了梳理。向回《历朝纪受命功德鼓吹曲的本事分析——兼谈缪袭改制汉鼓吹在乐府发展史上的意义》(《乐府学》第二辑,2007年)认为缪袭改制汉鼓吹,确立了汉鼓吹曲在后世朝廷中以史诗性的组曲来记录、歌颂王朝发展历程的模式,也确定了汉鼓吹铙歌作为组曲在后世的使用与流传。王传飞《曹魏相和歌艺术生产的新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 6期)对曹魏时期相和歌艺术生产及歌辞演唱功能的新变进行了论述,认为曹魏相和歌辞突显了对制词者个体情志的表现性,更加侧重文辞及其意义。
第五,文人乐府歌辞总论。如颜庆余《论乐府古题的传统》(《乐府学》第 2辑,2007年)、吴大顺《南朝文人歌辞用调及其特点》(《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 6期)等。
第六,乐府歌辞的创作范式。如阎福玲《如何幽咽水,并欲断人肠——乐府横吹曲《陇头水》源流及创作范式考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 2期)、《横吹曲辞《关山月》创作范式考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 2期)、《乐府横吹曲辞《出塞》《入塞》创作范式考论》(《河北学刊》2007年第 2期)等论文主要从歌辞的拟作角度讨论了鼓吹、横吹拟乐府歌辞的创作范式。
二 研究特点与进展分析
如上所述,近十年的乐府歌辞研究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这些成果凸显出了两大特点:一是研究领域得到极大的拓展。在乐府歌辞的音乐性研究方面,以往主要集中在相和、清商、鼓吹、横吹、杂曲等五类歌辞的研究上,近十年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歌谣辞等也已经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受到极大的重视。此外,乐府制度、乐府歌辞的音乐文化生态与歌辞文本关系研究也是近十年研究的重点。对文人拟歌辞的研究,已经从三曹、鲍照等主要文人拓展到陆机、萧衍、沈约等多数文人拟歌辞进行研究,而且还从某一乐类的拟作入手,分析歌辞创作的文人化进程。二是研究视野更加宏观、方法更加多元。在研究方法和视野上,开始从原来的单篇经典作品的解读转向对某一时段或某一乐类乐府歌辞的总体性研究;从以往的内容分析与艺术发掘转向对乐府歌辞的整体文化共性的把握;从静态的研究转向乐府歌辞动态的研究,注意乐府歌辞生成、运动、传播等活动过程的考察,其中又特别关注特定的政治运动、文化政策、文化活动对乐府歌辞带来的具体影响。
具体言,近十年在如下三方面研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
一是乐府歌辞的音乐性研究。从音乐类别角度研究乐府歌辞兴起于 20世纪三十年代,徐嘉瑞、萧涤非、王易、朱谦之等学人均十分重视乐府歌辞的音乐系统。建国后,在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指导下,乐府歌辞主题学与艺术学研究开始兴盛,其音乐学研究受到冷遇。近年来,这一研究视角再次受到学界重视。如上所述,对乐府歌辞音乐类别的研究涉及到《乐府诗集》十二类中的十类,研究论文近 150篇。如由首都师范大学吴相洲教授领衔、数名博士生、硕士生参与的《〈乐府诗集〉研究》(2007年完成)就是近年此类研究的重要成果。该成果从文献、音乐、文学三个层面对《乐府诗集》进行分类研究,形成 10卷本的《乐府诗集研究丛书》,分为:《郊庙燕射歌辞研究》、《鼓吹横吹曲辞研究》、《相和歌辞研究》、《清商曲辞研究》、《舞曲歌辞研究》、《琴曲歌辞研究》、《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近代曲辞研究》、《新乐府辞研究》、《〈乐府诗集〉民俗丛考》等。该成果对各类乐府歌辞的音乐属性、发展变迁、艺术风格、诗歌史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讨论,整体上对乐府歌辞研究有较大推进。
二是乐府歌辞的生态研究。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感觉到从歌辞生产、演唱、传播等角度来研究乐府歌辞的重要意义。赵敏俐《关于加强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的几点思考》(《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可以算作诗乐关系研究的宣言。首都师大诗歌研究中心于 2002年、2003年、2007年组织的几次“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学术研讨会”无疑对诗乐关系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研究实践中,围绕乐府歌辞的音乐背景、生成与消费、演唱与传播以及乐府歌辞音乐性质与某种诗歌现象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赵敏俐、李昌集、钱志熙、傅刚、吴相洲、刘怀荣、廖群等一大批学者在这方面均发表了丰富而有见地的研究成果,有力推进了乐府歌辞研究。
三是文人拟歌辞研究。文人拟歌辞也是近十年乐府研究的又一热点问题。在研究对象上,除继续关注三曹、鲍照外,陆机、沈约、萧衍等更多文人的拟乐府受到关注,在研究视角上,开始关注某一乐类的歌辞拟作问题。从研究重点看,主要讨论了文人乐府歌辞的特点、对民间乐府的继承与新变、对诗歌发展史的意义等重要问题。这一研究,使我们对中国诗歌史上雅俗交流与融合、诗歌文人化路径及过程、诗体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更深入具体。
此外,其它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如乐府制度研究、乐府文献整理与研究、乐府主题与艺术特点分析等。但从总体上看,这几方面的研究没有前三方面的研究成绩突出。
三 乐府歌辞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歌辞是在音乐文化的建构中产生的,从属于音乐文化活动的需要,音乐性是其第一属性。但是,在形态上,它又是用语言记录的乐曲唱辞,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歌辞的这种双重性,使其自身具有两种文化意义:即乐文化系统的音乐意义和语言文化系统的文学意义。同时,歌辞在乐文化历史发展的实践形态中又具有多元性:一方面,歌辞在不同的音乐活动空间具有不同的目的,承担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另一方面,歌辞与音乐的具体配合又具有各种复杂性。歌辞的这些特点,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文体说,七言诗、五言诗的发展、成熟与此有关;从题材说,魏晋南北朝拟乐府的兴盛与音乐文化中的辞乐分离、徒诗观的确立也有直接关系;从风格说,魏晋乐府歌辞特殊的风格与当时音乐风格、歌辞“双重性”功能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歌辞文化的双重性与交融性,以及在音乐实践形态中的多元性,使人们研究乐府歌辞面临诸多困难:第一,乐府歌辞的多元性、复杂性,使我们对乐府歌辞具体作品文化功能和文学性质的判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第二,歌辞的原生形态应是与音乐共生的,如果能够结合当时音乐的具体演唱研究歌辞的性质、风格和文化功能,应该比较接近历史实际。但是,中国古代声响资料已经失传,仅存的少量演唱歌辞也是声辞杂写,不可晓解。第三,民间歌辞是乐府歌辞的基础和主要来源。但中国历史传统多偏重于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历史活动与上层主流社会生活的记录,所以在现存历史文献中很少关于民间音乐活动和民间歌辞原始面貌的记载,即便是吉光片羽的记录,也是服务于上层阶级的,有其特定的目的。这些困难,严重影响了乐府歌辞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近十年,虽然在乐府歌辞的音乐背景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对乐府的辞乐关系、歌辞表演等方面的研究还没有成为乐府歌辞研究的主流,其研究成果也还存在诸多推测与想象成分。在研究中还存在内在的分离现象:音乐视阈研究者对“歌辞”在诗歌史上的特殊意义关注较少,文学视阈研究者对“歌辞”文学特性形成的音乐基础和特殊功能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还有不少学者尚停留于乐府歌辞主题学与风格学的研究层面。
针对乐府歌辞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基本特征,选择恰当的路径与可行的方法是推进乐府歌辞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关键。研究的历史实践表明,乐府歌辞研究至少有几个基本的角度是可行的:
第一,从音乐文化视阈出发,研究乐府歌辞赖以生存的音乐基础,从而探讨乐府歌辞的文化功能与文学特性。
第二,在乐府歌辞生成、运动与传播的生态中,探讨乐府歌辞在具体历史演进中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性所引发的乐府歌辞功能的多样性,从而认识乐府歌辞的文学意义、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
第三,从文人拟歌辞的角度探讨乐府主题与形式的嬗变历史,以及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乐府歌辞的雅俗交流与融合、乐府诗体体式形成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文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1]王长华.许倩.汉《郊祀歌》与汉武帝时期的郊祀礼乐[J].文学评论,2007(1).
[2]张树国.汉至唐郊祀制度沿革与郊祀歌辞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1).
[3]张树国.太阳崇拜的历史演变及在郊祀仪式中的文学再现[J].中国文化研究,2008(2).
[4]孙尚勇.黄门鼓吹考[J].黄钟,2002(4).
[5]吴大顺.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与歌辞研究[J].2005,博士论文.
[6]翟景运.再论相和歌及其与清商三调的关系[J].乐府学,2006 (1).
[7]王传飞.相和歌辞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崔炼农.相和唱奏方式与辞乐关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 (1).
[9]刘怀荣.从演唱方式看清商曲辞艺术特点的形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5).
[10]田彩仙.六朝“白纻舞歌辞”的发展及审美价值[J].文艺研究, 2006(8).
[11]赵敏俐.汉代乐府官署兴废考论[J].文献,2009(3).
[12]李山.经学观念与汉乐府、大赋的文学生成[J].河北学刊,2003 (4).
[13]廖群.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J].文史哲,2005(3).
[14]吴大顺.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传播与诗歌史意义[J].山东大学学报,2006(1).
[15]钱志熙.论魏晋南北朝乐府体五言的文体演变——兼论其与徒诗五言体之间文体上的分合关系[J].中山大学学报,2009(3).
[16]王福利.汉庙祭乐歌辞的语言结构形式及其艺术风格[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3).
[17]孙娟,黄震云.清商曲辞与曹操诗歌的声韵艺术[J].文学评论, 2007(6).
[18]葛晓音.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J].上海大学学报,2009(2).
[19]孙明君.咏新曲于故声——改造旧经典、再造新范型的陆机乐府[J].北京大学学报,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