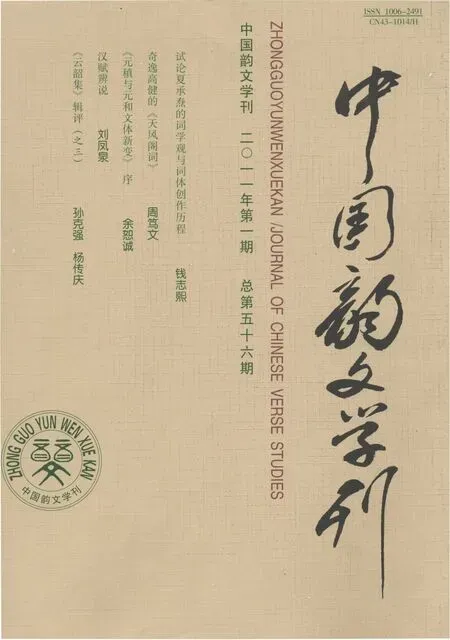《元稹与元和文体新变》序
2011-11-19余恕诚
余恕诚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郭自虎同志的《元稹与元和文体新变》即将出版,这是郭君以多年的辛勤劳动为唐代文学研究献上的一部用功很深的著作。
唐代文学,成就辉煌。自九世纪以来,一代代人们对它的阅读与传播,一直热情不减。多种整理研究著作,即使谓之“汗牛充栋”,亦不足以形容。元稹作为与白居易齐名的中唐大家,研究者也早就“众里寻他千百度”,审视的目光在他身上已打量过无数遍了。郭君有何独到之见奉献给今天的读者呢?作为一位求真务实的人,郭君当然不会因循旧说,把学界早已有过的认识,拿来向我们讲说。对他的论述,我们应有足够的信心,给予新的期待。而事实上,循名责实,即不难发现,这是一本从文体新变角度,深入到元稹所处的时代、元稹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之中,去寻求新知的著作。中唐是文学发生巨变的时代。“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刘禹锡《杨柳枝词》)、“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李商隐《韩碑》),这些名家的诗句,让我们感到,其时文体新变是气势空前的强大潮流。而细察当时文坛活动情况,元稹乃是擎旗劈浪、立于潮头的人物。翻开郭君的著作可见:第一章,对中唐文学大变的背景作整体描述;第二章,指出元稹敏锐的文体意识;第三章,探析元稹对制诰的革新;第四章,论述元稹倡导新乐府之功;第五章,从“次韵”唱酬到包括种种新体新样的“元和体”;第六章,“破拘挛,作长句”的律赋革新;第七章,加入新兴文体传奇的创作队伍;第八章,有关妇女题材的各种新体——八方辐辏,均围绕文体新变的主轴展开。论述了元稹在中唐文学发展中,既敏于辨微发踪,又参与攻坚实战的巨大功绩。
上引诸家诗句中,白居易的一联,无疑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元稹文体创新功绩的高度肯定。两句诗白居易的自注都首提元稹。不过“诗到元和体变新”,仅注“千字律诗”,或如元稹在和诗中所讲的“次韵千言”,还是把它限制在一个狭义的范围内。其实,学术界早已把白居易这一名句用以作为对元和诗变的整体概括了。而如果对白诗作这样理解的话,再联系中唐诗坛的整体变化,元稹的贡献也就会得到更多方面的显现。特别是诗史上受到高度肯定的新乐府,尽管以白居易的创作最为成功,但他毕竟属于在与元稹互相观摩改进中的后来居上,而最先敏感地结合李绅的新题乐府创作,提出改革乐府诗的主张,“取其病时尤甚者列而和之”,大力倡导,形成风气的却是元稹。这种发踪指示、兔起鹘落的快捷反应,是元稹文学活动的一大特点。试看律诗创作和元白唱和中的许多新花样,几乎都是元稹首先发起,即可充分见出元稹在当时该是多么活跃,多么富于才情,勇于创新!
陈寅恪在其名著《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附《读莺莺传》中引录了白居易“制从长庆辞高古”及自注:“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然后加按语云:
今《白氏长庆集》中书制诰有“旧体”“新体”之分别,其所谓“新体”,即微之所主张,而乐天所从同之复古改良公式文字新体也。
又云:
公式文字,六朝以降,本以骈体为正宗。西魏北周之时,曾一度复古,旋即废除。在昌黎平生著作中,《平淮西碑》文乃一篇极意写成之古文体公式文字,诚可谓勇敢之改革,然此文终遭废弃。……惟就改革当时公式文字一端言,则昌黎失败,而微之成功,可无疑也。……然则朝廷公式文体之变革,其难若是。微之于此,信乎卓尔不群矣。
白居易的诗及注,隔了一千多年,才有陈寅恪予以特别重视与回应,但陈寅恪对于元稹制诰“卓尔不群”的具体表现,也未予解释。制诰今天对于我们已经相当陌生,它的艰深高古,让我们感到陈寅恪之推崇元稹制诰,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需要作解的课题。郭君梳理了制诰自先秦至唐的演进过程,指出元稹制诰变空洞罗列为线性叙述,变结构上的平直单一为曲折有致,变浮夸之丽辞为恰当地直接抒写帝王的真实心情与意旨,变排偶句式为散体句式,等等,这些虽未必能将“制从长庆辞高古”的内涵全部说尽,但无疑是对白诗作前此所未曾有过的细致深入的阐释。
《旧唐书》元稹、白居易合传篇末赞云:“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从文体新变角度,以建安、永明时代方驾元和,而代表元和的则是元白。史家之论,无疑足以说明把元稹与元和文体新变放在一起研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郭君在这一课题上付出的劳动是艰辛的,但收获的是硕果。我们欢迎郭君的新著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