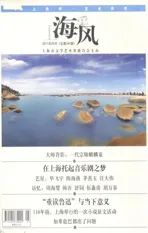上海编辑
2011-11-06田中禾
文/田中禾
上海编辑
文/田中禾

田中禾河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五月》《春日》《秋天》《落叶溪》《匪首》《父亲和她们》等,荣获“上海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
我写小说很晚,当中国文坛群星灿烂的时候我才到县文化馆去做创作员。42岁那年给《上海文学》寄第一篇小说,不久收到一位姓杨的编辑回信,像老朋友似的诚恳、亲切,还寄了一本《写作参考》。投稿时我只在稿纸头上写了一行地址,未免有点简慢,《上海文学》对一个素不相识、毫无名气的投稿者这份热诚,使我成为她的忠实朋友。过了不久,《槐影》在《上海文学》发表,那是我写的第四篇小说。有一天,南阳文联的朋友打电话说,上海来了一位编辑,专程到南阳拜访你。以那时的交通,从上海到南阳可以说是千里迢迢,要坐二十多小时的火车到郑州,再坐十几小时的火车或长途汽车,郑州到南阳每天只有一趟火车,都在夜间运行,几乎每站都停,慢得让人难受,卧铺又很难买。那时的田中禾,总共发了三四个不像样的短篇,劳动一个大刊的编辑不辞辛劳从大上海跑到穷乡僻壤来看望一个文化馆的创作员,感动之情可想而知。和钟佩珍的接触巩固了我对上海编辑的印象,诚挚,朴实,待人实在。此后她一直是我的责任编辑。她既不奉承,也不虚与委蛇。说你写得好,那是真心;说你没写好也绝对是善意。和这种人相处,简单,不累,特别对我脾性。
几年后在三亚参加笔会,又使我领略了《上海文学》哥儿们善以待人的风度,与张重光同住一室,我患了感冒,生怕给人带来不便,他不但毫不介意,还热心为我推拿,每天按时提醒我吃药,给我传授防治鼻炎的方法,一路成为开心密友,如果被外国人看到,或许要以为我们是同性恋者。
《明天的太阳》获第四届上海文学奖,我到上海去参加颁奖会,才得与心仪已久的《上海文学》的朋友们见面。那个颁奖会是我参加过的类似会议中最愉快的一次,除了热情、周到,更有一种融洽、和谐。当时恰好有个中篇在《收获》待发,李国煣和另一位女士陪我吃了一顿饭,在上海作协二楼,店面虽小,环境温馨,感觉《收获》的编辑也一样的实在,不必花费太多应酬辞令。
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早晨,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说他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丁元昌,刚下火车,现在在车站,过会儿到我家来。丁元昌我倒知道,他编了很多河南作家的书,在我们这儿口碑挺好。我因为手里没货一直没和他联系,不知道他是怎样知道我正在写长篇,也不知道他是怎样找到我住的地方。我从县里搬来郑州不久,住在西郊一个杂乱的小街的大杂院的六楼上,即便是老郑州要找到这儿也得费一番周折。丁元昌居然找到了。他坐了一夜车,下了车就奔我家,坐在仅有一个破沙发的“他化自在天”里(按佛教教义,欲界第六重天是“他化自在天”),翻看我刚写了两页的长篇,其实这个长篇还只是个影子。我感到过意不去,想留他玩一天,起码找几个朋友请他吃顿饭,谁知他已经买好了返程车票,下午匆匆登车南返,回程又是通宵夜车。这样辛苦、敬业地干活,丁元昌一下子把我感动了。夏天,我和妻子到杭州作家之家去度假,在上海转车,又着实麻烦他一次。他替我买车票,到站外去接。谁知火车晚点,他饿着肚子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多钟也没接到我。虽然那时已经把他看作朋友,可内心的歉意至今难以忘怀。
那年在美国访问,看到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匪首》,我禁不住与身边的美国朋友谈这本书出版的经过,谈起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如何在书稿只有两页时去约稿,颇有点为我们上海编辑沾沾自喜。
几十年间去上海也有多次,曾在破旧的弄堂住,感受老上海以马桶交响曲开始的上海的早晨;在石库门前长长的人流中排队挤公交车,惊叹上海话骂人如鸟语鸣啭;到南京路逛街,去十六铺赶船,在城隍庙买小吃——从而领教了上海人半两粮票的妙用;眼见得破落的十里洋场变为生机勃勃的国际大都会,上海的风光与故事自然很多,然而,是上海编辑使我与上海建立起深厚感情,想起上海必然会想起他们。虽然上海还有不少朋友,也属君子之交,疏于往还,平时甚至一个问候也没有,心里留下的比文字留下的更多吧。祝福上海的朋友们,祝福上海的文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