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地运用并不完美的手段
——《道连·葛雷的画像》的叙事结构分析
2011-11-02张琪韩丹
张琪韩丹
(重庆科技学院 外语系,重庆 401331)
完美地运用并不完美的手段
——《道连·葛雷的画像》的叙事结构分析
张琪韩丹
(重庆科技学院 外语系,重庆 401331)
考察《道连·葛雷的画像》的叙事策略,研究叙事结构、叙事时序和叙事视角在小说中的组织方式,发现王尔德在《道连·葛雷的画像》的结构上的努力,是其在创作中“完美地运用并不完美的手段”,努力实践以“写得好”为标准的唯美主义的形式观的反映,其实质则是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在作品形式上的表征,是王尔德追求形式和内容统一的结果。
叙事结构;叙事时序;叙事视点;线索
安妮(Anne Varty)在评价王尔德的《道连·葛雷的画像》时说:“不是行动,也不是情节,而是人们对于小说人物对话、心理互动、行为的心理影响、内部心理活动的注意在统治小说的阅读体验。”[1]111在她看来,《道连·葛雷的画像》“既展示了短篇小说在形式上所需要的准确,又有长篇小说允许的散漫”[1]127。的确,《道连·葛雷的画像》有着很深的戏剧的烙印,小说人物的精彩对话随处可见,并充满了王尔德唯美主义说教;此外,道连与画像荒诞的置换、小说情节上随处可见的悬念也深深吸引了读者的注意,使得读者无意识地放弃了对于小说结构的重视。但是据此就认为王尔德轻视故事情节,忽略叙事结构,安妮的评价未免有些失之偏颇。与安妮的判断恰恰相反,秉承“为艺术而艺术”的王尔德在理论上具有强烈的形式意识,在实践上强调对形式的运用。他曾在《作为批评家的艺术家》中论及形式对于作家的重要性,宣称“技巧就是个性”[2]。此外,王尔德关于形式重要性的论调在《道连·葛雷的画像》序言中也充分得到了反映,他说,“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书有写得好的或写得糟的”,“艺术的道德则在于完美地运用并不完美的手段”[3]3。无论是以“写得好”作为评价作品的标准,还是创作中“完美地运用并不完美的手段”,究其实质,都是对于形式的强调,反映了王尔德以“写得好”为文艺形式的文艺观。不仅如此,王尔德甚至提出艺术家都应“从形式中捕获灵感,而且纯粹从形式中捕获”[3]451,公开鼓吹为表达而表达,为艺术而艺术,将表达和形式作为艺术的全部。王尔德并不止步于理论的阐述,而是身体力行,努力在文艺创作上践行自己的文艺思想,他对于形式的重视在《道连·葛雷的画像》有着很深的烙印和体现。
一、螺旋向心式叙事结构
首先考察《道连·葛雷的画像》的叙事结构。小说中,道连面对霍尔沃德为他画好的肖像祈祷道:“如果我能够永葆青春,而让这画像去变老……我愿拿我的灵魂换青春!”道连的祈祷成为整个故事的逻辑起点,小说正是以这个祈祷的应验,安排出负情、堕落、谋杀等一系列后续事件,融离奇与荒诞于一炉,却又自成因果,自圆其说。但是,道连的祈祷是因画像而起,霍尔沃德的画像的存在是道连祈祷的先决条件,没有画像,小说的情节也就无从展开,因此一个简单却不容推翻的结论就是:道连的画像本身也是故事的线索。然而画像和道连的祈祷还不是小说全部的情节基础。在道连祈祷和堕落的过程中与它们共同作用的还存在着一组更为重要的因果关系,那就是亨利勋爵对于道连的教唆和引诱。正是受惑于亨利勋爵的教唆和引诱,道连才会在看见画像的时候失态,伤感终有一日青春不再,由此才引发了道连的祈祷,而后续事件也才得以顺利展开。显而易见,亨利勋爵的教唆和引诱同样是该小说的情节基础,与道连的画像、道连的祈祷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道连·葛雷的画像》的线索。
简单罗列以上三组因果关系,可以得出《道连·葛雷的画像》情节发展的三条基本线索:
线索一:道连的祈祷→后续事件
线索二:霍尔沃德的画像→道连的祈祷→后续事件
线索三:亨利勋爵的教唆和引诱→道连的祈祷→后续事件
在三组因果关系中,存在着一件重复出现的情节构成,那就是线索一亦即“道连的祈祷和后续事件”,包含于线索二和线索三之中。这说明这一组因果关系在小说的情节和结构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是整个故事的先导事件,是小说最为重要的情节和线索。线索二和线索三彼此并不互相包含,也无任何隶属关系,但又一起构成了小说的情节和线索,推动着整个故事的逻辑发展。要说明三组线索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还需要回到文本中寻找答案。首先考察第二条线索即画像的线索。在小说文本中,王尔德设置的画像的线索变化在叙事中这样得以呈现:
(小说起始)“俊美出奇”、“风姿秀逸”→“嘴角露出些微的冷酷”、“冷酷的狞笑”、“它已经变了”→“狰狞可恶、愈来愈老”、“皱纹累累的额上或聚集在淫邪的厚嘴唇周围的丑恶线条”、“体态的变形和逐渐衰弱的四肢”→“一张可憎可怕的脸从画布上向他狞笑”、“开始变得稀疏的头发”、“淫邪的嘴唇”、“尚未完全丧失端雅的曲线美”→“画像上的那个家伙还是那样面目可憎,甚至比以前更加可憎。沾在一只手上的殷红的湿斑似乎更醒目了,更像新鲜的血迹。”→“容光焕发,洋溢着奇妙的青春和罕见的美。”[3]5-240
王尔德在书中清楚地叙述了画像变形同道连作恶和堕落的关系,每一次变化下面都隐藏着道连在道德上的进一步堕落,每一次对于画像的叙述都指向故事的另一条线索或者分线索,彼此纠缠,使得这一单薄的故事变得复杂曲折,引人入胜。即使排除画像变化所指示的隐藏意义,单独考察这一线索,也很容易发现它的起伏和摆动都非常大,出人意料。画像的变化,特别是画像随着人的内心变化而离奇的变化,这一情节毫无疑问来自于王尔德的杜撰或者说是创新。对王尔德而言,创新就意味着以新的形式“准确描述从未发生过的事,这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专职,也是任何有才华和文化的人不可剥夺的特权”[4]。王尔德利用画像的变化巧妙地引出勋爵亨利线索,因为读者在阅读中会下意识地对画像变化的原因进行追问,于是第三条线索浮出水面,即亨利勋爵对于道连的教唆和引诱得以呈现。在文本中,在霍尔沃德的画室前,亨利勋爵极力诱惑道连趁青春年少时要及时行乐,受惑于亨利勋爵的教唆和引诱,道连开始了祈祷,从而开始了小说的第一条线索,它充当着解释的功能,回答了画像与道连互替和道连青春永驻的原因,因此,第一条线索的叙事动力实际上是来自第二条和第三条线索,即画家霍尔沃德的画像的线索和亨利勋爵对道连的教唆和引诱的线索。换言之,王尔德实际上是按照故事的三个主要人物分别设置了一条线索,亦即:画家霍尔沃德线索、模特道连线索和勋爵亨利线索。三条线索彼此纠缠,互为因果,铺陈出曲折多变、新奇无稽的情节结构,大故事套小故事,相互交织,使得情节错综复杂,让读者眼花缭乱。为避免小说自身的逻辑混乱,王尔德精心设置了一个螺旋向心的结构,用于统领小说中枝蔓众多的情节。
尽管三条主线存在着不同的因果逻辑关系,但是所有的逻辑关系都包含了或为因或为果的“道连的祈祷”这一事件,尤其是在后两条线索中,“道连的祈祷”尽管相对于某一事件起着果的作用,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扮演的因的作用,它在实际上推动了整个故事叙述的进程。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道连的祈祷”在小说情节中的作用,我们将上列三条线索的相互关系表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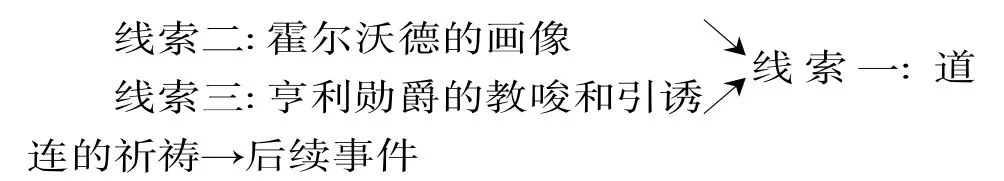
“道连的祈祷”尽管是“霍尔沃德的画像”和“亨利勋爵的教唆和引诱”的一个结果,但在故事情节中,特别是在与后续事件的关系上,它实质是故事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是后续情节展开的源头,尽管小说存在多条线索,但“道连的祈祷→后续事件”这一情节事实上构成了故事的最为基本的主线,“霍尔沃德的画像”和“亨利勋爵的教唆和引诱”成为了这一基本主线的不可或缺的叙事动力,服务于“道连的祈祷→后续事件”这一基本主线,从而在叙述线索上或者说情节上构成了向心式结构。
深入分析三条线索的关系,可以发现画像实质上充当了小说的叙述核心,所有叙事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画像实质上扮演了纽带和节点的作用,将小说线索纵向发展中断续的事件有机地连接成为了一个整体。从小说开篇霍尔渥德在画室里为道连创作画像时开始,画像就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产生联系,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和中心。接着,被亨利勋爵引诱的道连在画像前祈祷,愿意以灵魂为代价换来画像替他变老变丑,而自己能永葆青春。道连的祈祷的应验与否构成了小说情节上的悬念,形成推动情节纵向发展的叙事动力。之后,小说就以这个祈祷的应验发展后续故事情节,画像在叙述中的轴心作用更为凸显。王尔德巧妙地运用了“重复”这一手法,让画像在小说开端、结尾、高潮等处重复出现,整个故事围绕这个中心起伏曲折地展开,形成了“螺旋向心式”叙事结构形态。一方面画像是叙事的核心,所有的阶段性叙事的结果都指向这一中心;另一方面每当阶段叙事的结果指向它时,小说的主题都毫无疑问地得到进一步的凸现和深化。这种单纯有序、高度集中的紧凑叙事方式保持了叙事的螺旋向心运动。情节的集中紧凑与突兀曲折的变化是统一的,它们彼此衬托、融合,丰富了作品对读者心理产生的效应。
二、错综复杂的叙事时序
在创作《道连·葛雷的画像》时,王尔德主要利用倒叙和预叙制造悬念,并在预叙中伴随着一些指点性、评论性内容来实现预叙的功能从而使文章结构更加完整,传达出宿命的悲剧意识,控摄叙事线索,预设情节走向。王尔德采用的倒叙是热奈特称之为“同故事内倒叙”的叙事策略,“与第一叙事有同一个情节线索”,“它的时间场包括在第一叙事的时间场内,显然可能造成累赘和冲突”,用于在“事后填补叙事以前留下的空白的回顾段,该叙事根据不完全受时间流逝束缚的叙述逻辑,通过暂时的遗漏与或迟或早的补救组织起来”[5]。值得注意的事,在同一情节的线索中,王尔德并不单独使用一个倒叙进行叙事,在某一段的线索中,往往一段遗漏还没有得到补救,王尔德又开始了另一处遗漏,然后就是倒叙叙事的补救,整个叙事时序被严重干扰,正常的叙事时序的逻辑被彻底打乱,使得整个叙事时序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
在坎贝尔帮助道连毁尸灭迹的情节中,王尔德不仅运用限知叙事制造悬念的策略,在同一事件中,还使用了错综叙事时序的叙事策略。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这一事件蕴含的故事片段中的逻辑时间关系,以说明其中的逻辑时序的错乱:
蓝皮书中翻查到艾伦·坎贝尔(A1)→道连写了两封信,一封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一封送给坎贝尔(A2)→回忆五年前同坎贝尔的交往和断绝来往的情况(A3)→初识坎贝尔(A4)→坎贝尔来见道连(A5)→道连眼神里露出无限怜悯(A6,B1)→道连提出毁尸请求,坎贝尔拒绝(A7)→道连再次流露出怜悯的神情(A8,B2)→写纸条,默读纸条,递给坎贝尔(A9,B3)→坎贝尔的神情大变(A10,B4)→道连出示信件(A11,B5)→坎贝尔被迫答应销毁尸体(A12)。
王尔德将毁尸事件在短短的篇幅里面不仅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人物,而且借用悬念将这段事件演绎得跌宕起伏,蜿蜒曲折,极尽变化之能事,大有“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味道,让读者读来欲罢不能。观察上述事件的逻辑时间关系会发现,正常的逻辑时序应该是A4→A3→A1→A2→A5→A7→A9→A11→A10→A6→A8→A12,但王尔德并未按照这一时序进行文本叙述,其实际叙述时序呈不规则的倒叙,亦即首先叙述时间段后阶段的事件,给由于缺乏心理预期的读者制造突兀的感觉,在读者的阅读中造成空白,进而形成疑问和悬念,其次才在文本叙述中进行追述和补述,以填补前面形成的空白,进而消释读者的疑问。但是,部分疑问虽然得到解释,更多的还是留给了读者自行解答。此外,在A这一事件中,还套叙了B事件,B事件同样采取了错乱逻辑时间关系以造成悬念的叙事策略,B1和B2实际上是因为B3、B4和B5片断才能引发的结果,逻辑时间上也应该在B3、B4和B5片断之后发生,但是王尔德偏偏就先叙述B1和B2而制造悬念,再用B3、B4和B5片断进行解释和消解悬念。王尔德似乎非常享受使用混淆时间关系而造成悬念的写作技巧,即使在一个本来就是在一个错乱的事件结构中的微小事件也不愿放过。王尔德对于利用错综叙事时序的叙事策略来制造悬念是非常成功的,这大大增加了这本小说的可读性。
为了进一步说明王尔德对于这一技巧的偏爱,姑且再以画像的第一次变化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例。在画像发生第一次变化时,作为全知叙事视角的作者,突然对画像变化的原因避而不谈,有意限制了自己和读者的视角:
可是那幅肖像的变化又该如何解释呢?它掌握着他的生活的秘密,反映出他所作所为。它使道连懂得了如何钟爱自己的美貌。难道它还将教她憎恨自己的灵魂不成?他怎么能再去看自己的像?[3]113
仅仅是因为普通的恋人之间的分手就会导致画像发生丑陋的变化吗?那么,因为心中的美神之死,“他和西碧儿一样应该得到同情”。画像变化的原因没有得到任何真正的解释,限知视角让作者本人和读者对于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当道连决心赎罪同西碧儿结婚,“一起快乐和幸福地生活”时的第二天早上,他收到了亨利勋爵的一封信,但“他犹豫了一下,把它搁在一边”,对于信件的内容,读者的视角依然受到限制。谜团最终在亨利勋爵那里得到揭开:西碧儿自杀了!这正是那封信件的内容,更是画像变化的原因:
它得悉西碧儿·韦恩的死是在他知道此事之前。在他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肖像立刻能感觉到。使轮廓优美的嘴唇边的狞恶的那些微的冷酷,无疑在西碧儿·韦恩仰药自杀的一刹那就出现了。[3]113
悬念至此才真正得以解开,读者的疑团也终于找到释放的原因。一封应拆而未及时拆的亨利关于西碧儿死讯的信,延宕并且丰富了故事的发展。接下来让我们再次从微观叙述层上对这一简短的片断进行时间关系的分析。西碧儿·韦恩仰药一节最主要的事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间系列,分别由不同的事件片段组成,这三个时间片段姑且暂定为A、B和C事件,其叙事时序可以粗略地用以下结构表示:
和西碧儿的决裂(A1)→发现画像变化(B1)→对画像变化原因的探究,道连认为是对西碧儿的伤害(A2,B2)→收到亨利勋爵的信件/西碧儿之死(C1)→同亨利勋爵的会面,被告知西碧儿之死(C2)→信件的内容/西碧儿之死(C3)→西碧儿仰药自杀/画像变化的时间(B3)。
上述系列事件中,A1,A2是属于同一事件的延续,王尔德采取的是预叙的叙事策略。“时间上的预叙”“允许叙述者影射可以说构成他角色一部分的未来,尤其是现时的境况。”在道连对画像变化的原因的追问中,王尔德通过预叙预设了故事情节的走向,发生变化的画像则作为不祥的征兆,暗示了故事情节的悲剧性发展,但这并不是这一故事片断的全部。王尔德在B系列事件中采取了不同的叙事时序。在分析这一叙事时序之前,首先必须要认识到的是,作为A系列事件中的A2片断同时参与了B系列这一延续性事件。分析这一连续性事件的时间关系,很容易发现,按照正常的事件发生的时序B系列事件应该重组为:B3→B2→B1,但是这一本该是连续性的事件的时序被有意颠倒了。同样的叙述策略也被用到了C事件当中,正常的时序C1→C3→C2也被有意错乱了。仔细考察A、B、C三系列事件在整个事件当中的时间关系,有意的时序错乱更为明显,更为复杂。正常的A1→B3→A2/B2→B1→C1→C3→C2时序被彻底颠倒、打乱和重组,构成B事件和C事件的事件片断出现了时间倒错,其结果就是当读者读到B1和C1片断时,由于缺乏全知视角,无从得知情节的走向,因而觉得突兀。特别是当预叙已经显露出不祥的征兆时,读者还在为无从得知具体的事件而焦虑,渴盼知晓“将要发生什么事”或是已经发生什么事,从而创造了阅读紧迫和悬念效果。由此,王尔德的悬念设置得以完成,他的“悬念是情节的本质,惊奇则是其顶点”的文学主张也得以在文本中体现。
三、制造逻辑性与合理性的叙事视角
王尔德为了追求“写得好”这样的终极目标,不仅为《道连·葛雷的画像》设置了向心式的叙事结构,还利用多种叙事手法设置悬念,以期能够充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和调动他们的好奇心。此外,为了避免情节上的不合逻辑,王尔德还利用叙事视角修补情节上的漏洞,以达到自圆其说的目的。
在道连杀死霍尔渥德后的毁尸灭迹事件中,为了让一个大活人的凭空消失合情合理,王尔德在叙事上可谓煞费苦心,对情节的逻辑性进行了精心的推演,一一交待了这一情节前后的所有细节,在叙述上更是小心翼翼以至于近乎琐碎地让小说情节入情入理。考察小说的第12章至第14章中的视角叙事,王尔德的对于逻辑性的“精心”考虑可谓一目了然。需要注意的是,在叙事中,除了小说中的人物视角外,叙述者的视角始终存在,并与小说中的人物视角时而重合,时而分离,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小说的叙事。让我们来逐一分析小说这一情节的叙事视角,以说明它们在情节逻辑上的作用。
首先是道连的视角和霍尔渥德的视角。道连“在十一月九日”他“三十八岁生日的前夕”,“在亨利勋爵家里吃了晚饭,十一点左右从那里步行回家”[3]157,路上巧遇画家霍尔渥德。
迷雾中有一个人打他身旁经过。那人走得非常快,灰色夹大衣的领子竖了起来,手里拿着一只提包。[3]157
道连认出这是画家霍尔渥德,然后被告知“从九点钟起”霍尔渥德就在书斋里等候道连。因为道连的“侍从实在太累”,所以霍尔渥德就叫侍从把自己送走后回去睡觉。霍尔渥德同时告知道连,自己要乘坐“十二点一刻”的火车离开英国去巴黎,因为要离开“半年左右”,特地前来向道连告别。这一情节通过道连的视角得到叙述,其中有这样几组信息需要得到关注:
(1)道连是在十一点左右独自从亨利勋爵家里步行回家,在路上偶遇霍尔渥德。
(2)霍尔渥德从九点钟起在道连的书斋等候道连,因为道连的侍从太累而让画家不忍心,所以告别侍从让其回去睡觉。
(3)霍尔渥德要乘坐十二点一刻的火车离开英国去巴黎。
(4)霍尔渥德要离开英国半年左右。
(5)霍尔渥德穿着灰色夹大衣,拿着一只提包。
进一步分析上述信息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一是道连和霍尔渥德的偶遇无人知晓;二是道连的侍从正在睡觉,为道连的秘密谋杀画家创造了条件;三是霍尔渥德要离开英国半年左右,因此他的失踪不会引人关注。上述结论为小说接下来的情节的开展作了充分的铺垫。
在小说中接下来的情节中,王尔德将叙事视角转换为了全知视角,客观地叙述情节的发展和延伸。小说中,道连不情愿地邀请霍尔渥德到自己家,“用自己的钥匙开门”(侍从已经睡觉了),画家“把帽子和夹大衣脱下来,往他放在角落里的手提包上一扔”[3]159。然后,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霍尔渥德的痛心疾首和道连萌生杀意一一得到客观冷静的呈现。道连邀请画家上楼观看画像,叙事视角再次转换,画家发现:
这间屋子看起来好多年没有人住了。一张褪了色的比利时壁毯、一幅用帷幔遮起来的画、一口意大利大箱柜,一架几乎空空如也的全部陈设。当道连·葛雷把壁炉上架上半支蜡烛点亮的时候,霍尔渥德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在尘封之中,地毯已有不少窟窿。一只耗子在护壁板后面打滚奔跑。屋子里有一股潮湿的霉味。[3]165
这是怎样的一间屋子呢?王尔德早在道连第一次作恶画像发生变化时就有过叙述。画像因为西碧儿之死发生了丑陋的变化,道连决心将它藏起来,因此将画像搬到了住所的最高一楼,这是一个道连自己“已有四年多没有到这里来了”的房间。通过全知视角对道连的心理活动的聚焦,这间房子的来历得以叙述。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间“钥匙由他掌管,谁也进不去”的房间。房间的隐秘性在小说的人物视角里再次得到验证,客观上为道连的谋杀创造了物质条件。
接下来,道连顺利地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谋杀了霍尔渥德。为了让画家的消失顺理成章,全知视角再次聚焦道连的心理活动,告知人们“这位画家素来孤僻成性,几个月之内他的无声无息不会引起任何怀疑”[3]171。这里的叙述同小说开篇提到画家“若干年前他突然不知去向,一度闹得满城风雨,引起许多离奇的猜测”[3]5叙述遥相呼应。道连胁迫坎贝尔帮助自己毁尸灭迹,并销毁了画家的遗物。在后文中,当亨利勋爵同道连讨论画家的失踪时,通过亨利分析,画家的失踪显得十分合乎情理。而艾伦·坎贝尔的自杀又彻底掩盖了事情的真相。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便这样凭空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道连的恶行也得以继续隐藏。
王尔德十分注意刻画细小的细节。道连偶遇霍尔渥德时,他注意到画家穿着灰色夹大衣,拿着一只提包。在进屋后,道连又注意到画家“把帽子和夹大衣脱下来,往他放在角落里的手提包上一扔”的细节。谋杀画家后,道连“看到了角落里有一只手提包和一件夹大衣”[3]170,因此将它们藏起来。在后续情节中,道连彻底烧毁了这些东西。霍尔渥德被谋杀的痕迹完全消失无踪,一切都顺理成章,没有任何不合情理之处。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不仅小说情节的合理性得到了强化,而且在客观上对情节的前后进行了呼应,保证了情节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综上所述,在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王尔德以向心式结构统领丰富而又曲折离奇的多主线的情节,使用错综叙事时序的叙事策略来创造阅读紧迫和悬念效果,再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来实现小说情节的合理性和逻辑性,从而在创作中“完美地运用并不完美的手段”,努力实践其以“写得好”为标准的唯美主义的形式观。
[1]Varty,Anne.A Preface to Oscar Wilde[M].Massachusetts: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98.
[2]奥斯卡·王尔德.王尔德全集(第四卷:评论随笔卷)[Z].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454.
[3]奥斯卡·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Z].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
[4]Ellman,Richard.The Artist as Critic:Critical Writings of Oscar Wilde[C].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351.
[5]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6.
责任编校:朱晓云
The Perfect Use of the Imperfect Medium:A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ZHANG QiHAN Dan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the novel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with focus on the novel’s structure,time strategies,narrative pint-of-view and how they are organized.The effort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novel,in reality,reflects the fact that Wilde fulfills his“well-written”standard set for works of aestheticism by“the perfect use of the imperfect medium”.The application of such strategies is a result of his pursuit of the combination of form and matter as well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aestheticism theories of form of Wilde.
narrative structure;narrative time strategies;narrative pint-of-view;clue
I561.074
A
1674-6414(2011)01-0028-05
2010-12-05
张琪,四川自贡人,重庆科技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20世纪英美文学研究和王尔德研究。
韩丹,湖南长沙人,重庆科技学院人文社科系助教,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