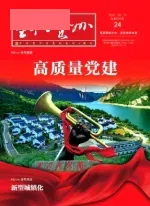创新先锋
2011-10-23
创新先锋
自从智力和资本走到一起,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呈现出了几何级数的增长。公司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的意义超越了以往。究竟怎样才能让公司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
创新,时代的引领者
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瓶阿司匹林,距今已有111年的历史。1899年,它诞生在德国拜耳公司。那是一家经营了30多年的颜料企业,从诞生起就有做实验的传统。
最初,弗里德里希·维斯考特都是自已做实验,比如在自家的厨房里。而系统的、成规模的研发则出现在20年之后,即在19世纪80年代建立起的工业实验室中。
阿司匹林被后人称为“世纪之药”,在拜耳公司的产品销量榜上,多年来一直位列前十。
不断从公司实验室中走出来的新产品,不仅仅意味着源源不断的财富,更是在向世人宣告:公司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主角。
在公司成为研发主体之前,科技发明主要是由少数杰出人士完成,他们在大学、学院或者工作室工作。在发明诞生之后,再努力将这些发明推向市场。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是发明家辈出的年代。一个发明催生一家公司的方式在欧美各国十分普遍。
经济学家诺斯认为,英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中取代荷兰,不仅仅与发明和科学活动的增加有关,也不仅仅与纺织、钢铁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有关,关键还与生产投资及市场新组织方式有关。
诺斯所说的新组织方式,就是指将资金、技术和市场联结在一起的公司。
工业革命最初是由个人创新来引导的,但是为了将其转化为产品、利润和投资,就需要雇佣人员、签订合同等,因此我们就有了公司。
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经指出西方文化的两个特点:一是认为科学是认识和理解宇宙的唯一有效途径;二是认为将科学应用于掠夺性技术从而增加个人财富天经地义。
也许正因为社会这一普遍意识,各国政府很早就开始保护和鼓励人们把发明变成财产。
专利法保护的是个人的发明权,而个人却借助公司平台组织资源,于是,越来越多的专利署上了公司的名字。
当科技创新日益显示出创造利润的能力后,公司对财富的追逐就直接变成了对技术发明的热爱。19世纪中后期,德国大公司率先设立工业实验室,并在化学和电气工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美国则总在不断地把旧大陆的经验放大。1900年,从通用电气开始,美国公司大步加入研发者的行列。
企业的崛起意味着研究与开发第一次开始系统化。公司取代了个人实验室。
经过200多年绵延壮大的杜邦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它从自主研发中得到的回报可谓丰厚。
1928年时,已涉足化工、汽车等多个领域的杜邦公司开始实施一项新计划。
他们决定启动一个只做研究的纯科学的基础研究项目。于是请来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华莱士·卡罗瑟斯博士。
卡罗瑟斯博士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建造新的实验室;二是研究课题不受限制;三是提高工资,年薪从哈佛教授的35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
杜邦公司照单全收。
卡罗瑟斯基本从此开始了他形容为“像煤矿工人那样的工业奴役生活”。虽然辛苦,他却感到很愉快,他说:“没有人过问我如何安排时间,未来的计划是什么,一切都由我自己决定。”最令卡罗瑟斯高兴的是:“研究资金简直没有限制。”
到1936年,他们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分子,一种可以成为尼龙的分子——“尼龙66”。后来它被投入商业开发,并在1939年研制出了商业产品。那是一段令人激动的时期。
这是一个由基础科学产生发明,并诞生新产品的例子。
这个新发明,花了杜邦公司2700万美元和卡罗瑟斯博士7年的工夫,因为它在实质上开启了高分子化学的基础研究。不过,与它随后带来的财富相比,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纽约世博会上,尼龙袜初次露面就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欧美贵妇追捧的时髦产品。作为降落伞的材料,尼龙在随后的二战中更是名声大噪。

在纽约世博会上,尼龙袜初次露面就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欧美贵妇追捧的时髦产品。作为降落伞的材料,尼龙在随后的二战中更是名声大噪。
如何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这个让很多国家苦恼的问题,但在市场机制下早已有了答案。一连串的经典案例不断表明:公司能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成本,把试管和柜台连接起来。
科技,经济的发动机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这样的产业链:贝尔实验室负责研发,交由西方电气生产,产品由贝尔系统运营商销售。并按一定比例付给贝尔实验室专利使用费,以保证研发经费的充足。
如此循环下,公司的业务迅猛扩张。
贝尔实验室先后有11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它曾拥有14位美国科学院院士、29位美国工程院院士。
从1934年开始,贝尔实验室的文件中频繁出现一个新名词——R&D(研究与开发)。在这里,大约10%的人从事基础研究,90%的人进行技术开发。
因为,总裁尤厄特认为:电信业不同于传统工业,只有基础研究的突破才能带来真正的创新。1947年,晶体管的诞生证明了这一点。
自由,是科学研究中最需要被尊重的品质,也是创新者不可或缺的环境。给思想自由的天空,才可能培育出飞翔的能力。
万尼瓦尔·布什在1945年发表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被认为是美国国家科技政策的经典之作。报告要求国家制定政策支持科学事业,同时又强调了在科学研究中保障自由精神的必要性。
让政府意志和科学自由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给创新提供了空间。
一方面,美国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大学从事技术研究,不但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持,而且不干预大学的科学研究,让科学家有更大的自由。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又通过减免税收,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开发,使企业在技术开发当中具有更大的动力。
二战后,世界科技正处在一个革新不断的时期,DNA的发现掀起了生物学革命,高分子化学带来了材料革命,原子能技术和空间技术也突飞猛进。20世纪50年代,半导体成为美企业的主导技术产品。
随着世界逐渐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在科技竞赛的疆场上,公司再一次成为决战的先锋。
正当贝尔实验室将晶体管视为公司绝密时,远东的日本人很快嗅到了它的味道。一些敏锐的小公司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刚成立不久的索尼就是其中之一。
盛田昭夫一直梦想着做出便携式收音机,但只有使用晶体管才能把收音机做得那么小。
种种努力加上机缘,1953年10月,盛田和夫飞往纽约,前去签署技术引进的协议。
1955年1月,索尼生产出了晶体管收音机的雏形,研究中有着出色表现的江崎玲於奈还因此成为日本第一位公司出身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但是美国公司却在一个月前,将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投放到了市场。
二战后,日本从美国买回了技术、买回了专利,但它不是简单地复制或是简单地重复。一美元的专利,它可以投入三美元或者更多的创新经费,使技术进一步地深化,再做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产品。这种二次创新精神在日本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一时期,很多美国公司靠美苏争霸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军方订单,过着舒服的日子,而日本公司已经打起了民用电子产品的主意。
欧洲人曾嘲笑日本是一个“由晶体管销售人员组成的国家”。但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有人这样形容道:“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被佳能复制,被尼康拍摄,被松下录影,被精工计时,被夏普的斑斓色彩魅惑。”
日本的企业在制造产品方面,是非常具有冒险精神的。在开发集成电路方面,政府得到了企业的积极协助,走向了新的方向。
1975年,日本宣布:将五家最大的电子工业公司联合起来,实施开发最高集成电路的五年计划。这是不满足于技术引进的日本发出的自主创新宣言。
1979年,日本公司在美国一举占领了40%的存储芯片的市场。惠普公司检验了日本芯片,发现故障率仅为美国产品的五分之一。
这如同一个晴天霹雳,美国公司开始猛醒。而这场从公司到国家的科技战,才刚刚开始。(本文选编自中央电视台十集大型纪录片《公司的力量》
编辑/李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