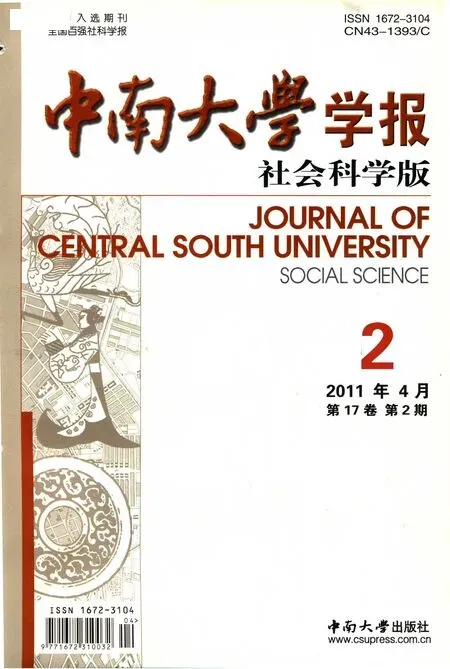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2011-10-18李斌陈超凡万大艳
李斌,陈超凡,万大艳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长沙,410079)
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李斌,陈超凡,万大艳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长沙,410079)
回顾了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和其产业结构演变的现状,并从理论上分析了承接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通过建立四个时序计量模型,检验理论分析变量与湖南省产业结构优化的联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正向影响,产业集群对结构优化效应并不显著,而就业规模则与湖南产业升级成负相关。最后对FDI与产业结构进行Granger检验,发现FDI与湖南省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联。
产业承接;产业结构优化;产业转移效应;时间序列模型;Granger检验
一、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的理论及文献回顾
在世界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的演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因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二者之间又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1]。从实质意义上说,产业转移是一国(或地区)为实现自身产业进步,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与行业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2]。历史上形成的产业转移理论主要有赤松要(Akamatsu,1935)的“雁行模式理论”、弗农(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小岛清(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论”、 普雷维什(Prebisch,1981)的“中心一外围论”、刘易斯(Arthur Lewis,1984)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论”等。我国学者对区域产业转移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兴起:夏禹农、冯文浚(1982)将生命周期理论引入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创立了区域经济梯度推移转移理论。周江洪、陈翥认为促进产业跨区域转移的总体思路是增大产业转出地的推力、增强承接地的拉力以及缩减制约产业转移的阻力[3]。
产业结构是指一国(或地区)各产业部门、行业之间的质的内在联系及量的比例关系。威廉·配第最早指出农业——工业——商业渐次提高的收益必然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西蒙·库兹涅茨从统计学的角度,研究了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钱纳利等人发现当国民平均收入增加时,生产结构转换表现为农业向工业生产转移的特征。区域产业结构是指区域内各产业的组成状态和发展水平,以及产业间的生产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4]。在我国,对区域产业结构问题研究做出较大贡献的有刘再兴、陈栋生、魏后凯等学者。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原毅军(2008)认为,产业结构优化是产业间协调发展,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并不断升级的过程。纵观现有文献,产业转移对区域产业结构演化影响的研究侧重于理论层面,产业转移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的定量分析不足。本文结合最新的时政热点,在继承产业转移及产业结构的有关理论基础上,对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做出理论和实证方面的一些创新性研究。
二、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及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从“十五”到“十一五”期间,湖南省产业承接效果日益显著,利用境内外资金能力极大增强,积极吸纳产业转移使得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有关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湖南省2000~2009年GDP增速、实际利用外资额及增速
从表中可以看出,近年来,湖南省GDP呈高速平稳发展态势,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不断增长,尤其是“十五”至“十一五”的过渡期间,利用外资增速创历史新高,2006~2009年增速虽有回落,但仍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这与近几年湖南不断以积极的姿态吸纳境内外产业转移密切相关。当然,地处产业低梯度区的湖南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尚存在着一些制约性因素,如现代物流体系不健全、产业配套设施不足、集群效果不强、行政运行效率较低等。
2006~2009年,湖南省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4.7%、17.4%和13.5%。三次产业增速的差异导致了产业结构的明显变化——打破了持续六年的“三二一”排序,调整为“二三一”排序。第二产业日益成为拉动湖南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详见表2)。根据霍夫曼定理:资本品工业规模越发展,相应的消费品工业比重越小,工业结构乃至整个产业结构高度越高。2009年,湖南省产业中轻重工业之比为32.8:67.2,重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大于轻工业和服务业。因此我们认为,湖南当前工业化水平大致处于由重工业化向高加工度化逐步推进的时期,即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
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说明湖南省产业结构趋向“理性回归”。1995~2005年第三产业比重虚高,直接原因是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二产业比重过低,优势不突出;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十一五”以来湖南产业结构的变化与湖南经济发展阶段相符,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主要得益于现代农业发展加快,工业发展向高科技、低能耗转变,现代服务业比重上升。与此同时,湖南的产业发展仍存在农业比重偏大、工业化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内部实力不均衡等问题。有关湖南产业结构与全国指标比较如表3所示。

表2 湖南省GDP中各产业构成的百分比

表3 2005~2009年湖南与全国三次产业构成比例
三、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多项研究表明地区GDP(或人均GDP)与地区FDI(或引进内资量)有显著正相关性,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以下我们就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效应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做出理论初探。
(一) 产业集聚效应
地区的产业集群状况是吸引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产业转移给转入地带来的显著效应。产业转移易形成与企业配套的上下游行业和相关服务业的集群,而产业集群又会产生外部规模效应,实现生产要素在集群范围内高效流动及配置。以新兴产业园区带动新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是实现工业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及与其他产业比例变化的重要途径。培育有规模有特色的产业集群,提高社会经济有限资源的综合效益,是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因素[5]。
(二) 资本注入与技术创新效应
资本流动是产业转移的内在机制,产业转移也必然将相关产业的资金、技术带入转移地。产业转移能够为承接地注入比当地企业更为雄厚的资金,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由于产业集群的发展,园区企业在技术合作和资本共享的平台上能够推动技术创新,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可以强化第二产业的发展亦或推动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崛起。
(三) 人力资本优化效应
转入企业拥有较强的人力资本优势,其对承接地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影响颇深。同时,由于转入企业的集聚,人力资本在聚集区内实现优化配置,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管理精英和各种专业性技术人才。人力资本是制约一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因素,直接引起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化[6]。一般而言,劳动力素质较低,第一、第二产业比重较大,而高素质劳动力对推动资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举足轻重。
(四) 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
产业转移的优化效应综合在一起,实现了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物流系统的全面升级、基建设施的互利共享、人力资本的合作交流、信息平台的自由透明等。这些无疑对转入企业及当地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集结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人力资源就会向高科技产业及第三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带动地区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五) 增加就业效应
转入企业能为承接地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的转移,充分缓解了承接地的就业压力。而劳动力的流向也导致了不同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态势不同,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
(六) 内外资规模拓展效应
产业转移表现在国与国之间是FDI,表现在一国区域间就是引进内资数。而内外资大量涌入某一区域弥补了当地的资金缺口,为产业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不同类型的内外资对产业结构影响不同,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入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入就对当地不同产业的发展产生不同影响,从而改变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引起产业结构变化。
(七) 政策洼地效应
政策和优惠是吸引产业转移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产业转移给当地带来的福利。由于当地对转入企业都有着较高的期望,因此政策的倾斜也是促进这些移入企业在当地生根发芽的保障。对相关企业的政策优惠引起了以该企业为代表的整个产业的发展,政策的导向促进了重点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产业结构。
总言之,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其能以较低的成本引进对其自身来说相对先进的产业与技术,以“后发优势”来提升产业整体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甚至产生“逆梯度转移”效应,最终使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格局。
四、实证研究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与量化
科林·克拉克印证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从第一向第二进而向第三产业移动,说明了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效益的密切联系[6]。我们以人均GDP来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实际反映。同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越高,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越强已在发达国家中达成普遍共识。因此,我们将以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定量指标,并作为实证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产业集群、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就业规模、科技创新、内外资规模、政策因素等方面。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关联图如图1所示。

图1 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关联体系
统计数据来自《湖南省统计年鉴》(1999~2009)、商务部及湖南统计网站有关资料。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统一性,将解释变量的量化指标选择如表4所示。
五、实证模型的设定、估计与计量结果的分析
基于以上指标量化,我们最终将可量化的因素纳入模型的解释变量(暂不考虑政策因素)。本文选择的研究时期是1990~2009年,在湖南省相关数据基础上建立时间序列回归模型研究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联效应。为了更好反映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绝对量和相对量,我们又在时序模型基础上分别建立一般线性模型及双对数模型进行比较。以下是分别以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建立的四个时序模型:

其中,方程(1)和方程(2)是一般线性模型,方程(3)和方程(4)是双对数模型,由C-D生产函数等号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Y1、Y2分别表示人均GDP及第三产业占GDP之比;LN(Y3)、LN(Y4)分别表示相应的对数值。C变量反映的是随机误差因素及未纳入模型中变量的影响。α、β、λ、κ分别表示不同方程的系数项,下标T、I、P、J分别表示不同方程中时间序列项即1990~2009年的时间跨度。借助EVIEWS计量软件,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
由于实证分析中涉及到的变量较多、时间跨度不长、数据资料有限等客观原因,模型中易产生共线性、序列相关等问题,为了最大程度保证模型估计的效果,我们对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进行适当的删减,并将估计效果最优的一个线性模型结果和双对数模型结果展示如表5。
以下我们将从湖南省的实际出发来解释回归结果。模型(1)是以人均GDP为因变量,R2值、F值较高,说明模型较好地解释了有关变量之间的关系,但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反映了当前湖南面临的实际即产业集中程度仍然较低,产业集聚对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具体表现在带动作用强的大企业较少和行业集中度较低。同时,产业转移带来的人力资本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1%条件下是正向统计显著的,说明其对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全员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元/人),人均GDP就提高0.45元,产业结构就进一步优化0.45个单位。

表4 解释变量量化指标选择

表5 模型(1)和(4)的回归结果
两个负向的指标分别是科研投入、就业规模。在1%水平下统计显著,也就意味着科研投入、就业规模和湖南产业结构优化呈负相关。目前湖南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科研投入增加的比重缓慢,科研投入用于新型工业化建设份额较少。这使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对湖南省产业结构起到优化作用,因此当前湖南省科技投入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呈现负相关。我们知道,湖南产业承接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行业。大量的社会人员涌入这些行业却充当初级劳动力,因此,产业转移带来了高就业而这种高就业却不能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再看模型(4),其反映的是相对量的变化,在理想状态下与模型(1)在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显著上达到高度一致:如人力资本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果能提高0.45个百分点。此外,模型(4)解释了之前未解释的FDI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是显著负相关的。因为当前外商向内陆的投资主要是一些夕阳产业,而夕阳产业对中部崛起下以壮大新兴第二产业和发展第三产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六、实证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
在此前的时序模型中,我们分析了产业承接带来的影响效应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联变量,为了检验产业转移是否在整体上与湖南省产业结构优化有因果联系,我们对模型中的FDI、产业结构优化这两个变量进行Granger检验。
Granger检验的主要思想是:要检验X和Y之间的因果性,先估计Y被其自身滞后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引入X的滞后值之后对Y的解释程度,如果提高了对Y的解释程度就称X是Y的Granger原因。具体如下:
设Un是到t期为止的所有信息集合,Xn是到t期为止X的所有信息集合,Un−Xn为除了X之外的所有信息。F(Yt+1|Un)表示Yt+1的条件分布函数。如果有:

则可以认为变量X是变量Y的Granger原因。信息集Un包括所有的相关信息。在信息集Un内X的信息可以改善对Y的预测,则称相对于信息集Un,X是Y的Granger原因。
根据以上定义,假设信息集Un仅由序列Xt、Yt构成,设Xt、Yt是零均值平稳变量。Granger检验的具体做法是对(5)式或(6)式首先进行约束回归和无约束回归后,然后用得到的两个残差平方和计算F统计量,进行检验。

假设检验X是不是Y的Granger原因,对(5)式模型检验的零假设是:

若零假设成立则有:


其中RSS1是式(5)回归的残差平方和,RSS2是式(7)回归的残差平方和,m是X滞后期数,T是观测值的个数,K是无约束回归中待估计的参数的个数,其中K=2 m。
在置信度α下,如果F>F(m, T−k), 则拒绝零假设,即式(5)中至少存在一个X的滞后量的系数显著不为0,也就是说X是Y的Granger原因。接受零假设,则X不是Y的Granger原因。同理根据式(6)可以分析Y是否是X的Granger原因。
本文要检验产业转移是否是产业结构优化的Granger原因,首先要检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的时间序列与FDI的时间序列是否平稳。经过ADF单位根检验和PP检验后,发现FDI序列是非平稳的,故对FDI取对数,得到的LN(FDI)仍然具有经济意义,LN(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用Y表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对Y和LN(FDI)分别进行ADF、PP单位根检验,其中滞后期的选取依据AIC准则。结果如表6、表7所示。
经过ADF、PP单位根检验证明了Y与LN(FDI)均为平稳序列。故可以直接运用Granger检验Y与LN(FDI)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如表8所示。
经过检验,在显著性水平为1%、5%、10%的情况下,由于F值很小,P值较大,我们接受上述两个原假设。得出在湖南省,FDI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并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反馈性联系。现实中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及影响机制都是非常复杂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所得结论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系,并不能完全反映现实情况。同时,由于湖南省FDI统计数据的有限性,所作出的Granger检验也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偏离。当前,FDI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对我国产业结构的深层次优化作用不明显[7]。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就目前而言,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项目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上,这对于其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并不显著。而人力资本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可能更多来自省内的产业政策和产业自身变动的作用机制。湖南应当放眼未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之路,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形成有规模的产业集聚群,从而从根本上优化产业结构。

表6 ADF检验结果

表7 PP检验结果

表8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注释:
① 用支出法核算工业增加值除以工业总产值得出结果。规模以上工业指主营业务5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
② 基于引进内资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省内,且引进省外资金大多评价标准不一,数据不可比性较强。故这里专门以实际利用外资数作为引资规模的量化指标。
[1] 王全春. 产业转移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8.
[2] 戴宏伟, 王云平. 产业转移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分析[J]. 当代财经, 2008, (2): 93.
[3] 周江洪, 陈翥. 论区际产业转移力构成要素与形成机理[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9, (2): 66−67.
[4] 陈国生. 关于湖南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思考[J]. 经济师,2003, (2): 229−230.
[5] 冒艳玲.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研究[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1(1): 78.
[6] 陈静, 叶文振. 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度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3, (1): 44−45.
[7] 杨伟文, 余丽娟.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效应分析[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10(6): 763.
Abstract:Reviewing the Hunan Provincial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achievements, and its current status of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on the effect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established four sequential measurement models to test theory analysis of variabl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Hu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human capital and labour productivity in industry structur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dustry cluster effects which those on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is not significant, and employment scale and Hunan industrial upgrade into a negative correlation. Finally,with FDI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for inspection, the authors found that FDI Granger and Hunan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re no direct causal associations.
Key Words:?Hunan industry to undertak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oretical analysis; empirical study; granger inspection
Hunan Provincial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heory and an empirical research
LI Bin, CHEN Chaofan, WAN Day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 China)
F062.9
A
1672-3104(2011)02−0118−06
2010−11−20;
2011−01−06
国家重大软科学项目(2008GXS1B022)
李斌(1968−),女,湖南湘乡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产业经济;陈超凡(1989−),男,福建福州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学生,主要研究方向:计量经济;万大艳(1989−),女,重庆巫山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编辑:汪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