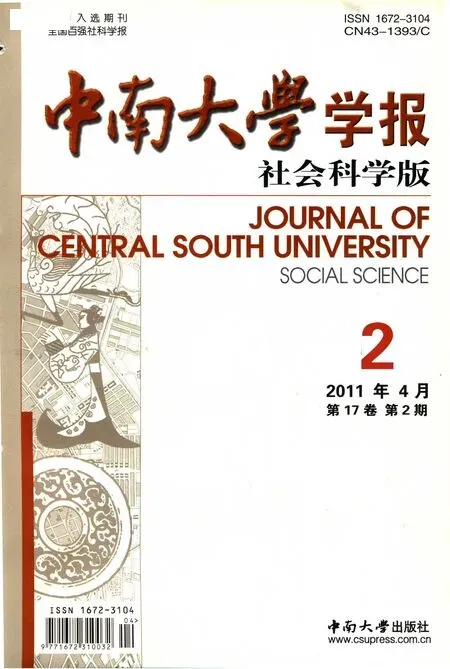《判断力批判》中判断与愉悦感的先后
2011-10-18宋桔
宋桔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判断力批判》中判断与愉悦感的先后
宋桔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判断力批判》两处提到了判断与愉悦感的先后关系,出现了看似“矛盾”的表述。以此“矛盾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对“判断”“愉悦感”的重新界定,构建了《判断力批判》中内在的审美图式,论证了“判断与愉悦感的先后关系”何以能成为“解读审美判断”的钥匙。
康德美学;判断在先;《判断力批判》;柏拉图;判断;愉悦感
柏拉图告诉我们“美是难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讲述了这种“难”的美学与“难”的审美——审美不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是包含着先验前提的、可以细分讨论的逻辑过程。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第一节区分鉴赏判断和认识判断时指出“为了分辨某物是否美,我们不是把表象通过知性联系着客体来认识,而是通过形象力(也许是与知性结合着的)与主体及其是否愉快的情感相联系。”[1](37)即愉快与否的情感是做出审美判断的前提。康德为“在鉴赏判断中是愉快感先于对象之评判还是后于前者”这个问题专列的一节中,指出“解决这个问题是理解鉴赏判断的钥匙”,“假如在被给予的对象上的愉快是先行的,而在对该对象的表象作鉴赏判断时又只应当承认其普遍可传达性,那么这样一种处理办法就会陷入自相矛盾”[1](52),这论断看似斩钉截铁地作出了回答:判断在先,愉快感在后。
有学者认为这一组看似矛盾的论述是“康德始终没有做出比较成功解释”[2](99)的败笔;近年来也有学者在论述康德美学与现象学关系、审美判断先验性与经验性时也涉及到了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3,4]本文将立足于《判断力批判》文本本身,通过对文本中内在的关系梳理来论证其所谓“矛盾”的真实含义,运用这一解读的“钥匙”解开审美过程中判断与愉悦感孰先孰后的问题,并借此构建出《判断力批判》的审美判断图式。
一、“矛盾”的前提——论证“先后关系”的含义
首先,康德对“判断”与“愉悦感”的先后关系的界定是非经验性的。日常生活中的“前后”是时间关系。在康德这里,这个“先”绝不是“时间在先”——现实经验中个人所体验到的情感或状态的“先后顺序”,而是一种“逻辑在先”。据此,笔者认为上述矛盾命题应当释为“判断是产生愉悦的前提”与“愉悦感是做出判断的基础”,两者间的“对立”或“联系”则应以康德美学中的“判断”“愉悦感”等概念的界定为基础。
康德在文中述及了多个判断形式:如把表象通过知性联系客体的逻辑判断;具有客观量和主观量并符合认识的客观目的的认识判断;与“利害”相关并借助于理性以单纯概念、令人喜欢且具有主观量的善的判断;参与了“利害”并完全构建在感观愉悦基础之上,且不具有主观普遍性的快适判断以及美的判断。通过对以上若干判断形式的比较,康德推演出“美的判断”:鉴赏判断即审美反思判断,“指向内心世界,为了通过对象表象(即直观)在主观中引起的诸认识能力的自由协调活动而产生的感情”。[5](69)
“康德赋予‘判断力’一词的意义是从来没有第二个人用过的,它不是知解力所用的逻辑判断。”[6](348)换言之,“判断力”不是康德所说的“定性判断”,而是“反思判断”。作为“反思判断”,就必然遵循从特殊到一般的顺序。同时,它与利害的观念无关,故是不具功利的实践性;它与逻辑无关,故不是认识活动;它与客观目的无关,故不是道德活动。“判断力”是主体的想象力与知性和谐自由运动后,与对象形式相契合而产生的快感。因为“审美判断”具有心意状态的可传达性,所以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
先验意义上的“审美判断”需要与现实经验中的“判断”分开来。我们在判定某物美前总是会在心里先掂量一下,但这绝不是康德所说的“判断”。比如有人说“A比B美”,那么这种“判断”就不是鉴赏判断而是认识判断,鉴赏判断所要展示的是这个“掂量”的行为在先验意义上是何以成立的。
其次需要明确的是“愉悦感”——审美判断中的情感因素——的真实含义。《判断力批判》是通过分类比较方式逐步深入对“愉悦感”的分析的。
在第三小节,康德通过分析“感觉”这一词的可能的“双重含义”,区分了“感觉”与“情感”。康德认为在没有区分两者之前,“一切愉悦本身就是感觉”。在这里,“草地的绿色”是对一个客观对象的表述,表现了表象与客体的关系。而情感是指在“只停留在主观中,并绝不可能构成任何对象表象的东西”[1](41)。故对这草地的快意只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与主体无关。一方面,这种感受不用于任何知识;另一方面,这种感受并不尝试借用主体来认识自己。
接着,康德又进一步区分了“快适”“善”和“美”三种不同的特征的“愉悦”。“快适”是对某个人来说使他愉快的东西,作用于无理性的动物,所产生的愉悦是“爱好”即“快乐(agreeable)”;善是“被尊敬的,被赞成的东西”,作用于有理性、无动物性的精灵,所产生的愉悦是“敬重(esteem)”;“美”既没有感观利害,也没有理性的利害对赞许的“强迫”,它所产生的愉悦——“喜爱(liking)”,它与对象的实存无关,只是和“愉悦的对象做游戏,而并不拘泥于某个对象”,所以是“唯一自由的愉悦”,它适用于既具理性,又具动物性的人本身。
第三层次,康德对“审美判断”中的“愉悦”做了细分。将“审美判断”中那个“愉快不愉快的情感”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与诸认识能力和谐的愉快”,一种是“对对象(表象)的愉悦(情感愉悦)”。前者指的是想象力与知性之间的自由游戏关系,后者指由这种关系导致的主观感受。(自由游戏关系)情感状态是鉴赏判断具有普遍性的基础,正是这种情感状态引发了“审美判断”,同时审美判断的行为本身又引发了愉快的情感体验。
将上述界定应用到康德的两个方面的观点中。第一方面的意见所指的“为了分辨某物是美,还是不美”是“鉴赏判断”。通过对比“认识判断”与“审美判断”突出了后者的特质,即“审美判断通过形象力(也许是与知性结合着的)而与主体及其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联系”[1](37)。在这里强调的是:主体及其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是审美判断的前提——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在先,判断在后。
而在另一方面的意见中,使用的是“愉悦感(The feeling of pleasure)” 这个词,不是“审美判断”中的“喜爱(liking)”,也不是“快适的判断”中的“快乐(agreeable)”。那么这种愉快感究竟是哪一种愉悦?或哪几种愉悦的混合?
还是回到原文来看,康德在指出了“愉快感在先”与审美判断所要求的普遍可转达性“自相矛盾”之后,接着向我们指出当判断中愉快感先行时,“这一类愉快将不是别的,而只是感官感觉中的快意(快适)”[1](55),当愉快感为“快乐(agreeable)”时,愉快感先于对象之评判的形成,是只具有私人有效性的快适的判断。
那么鉴赏判断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判断在先”?从上述“情感”因素的细分中我们发现,康德第一方面意见中的“愉快不愉快的情感”仍然是一个可分项,因为想象力与知性之间自由游戏的关系所引发的内心的“情感状态”,对这种“内心状态”的估计与判定才是审美判断中快感的来源。这里的“判断”是对审美判断中那种协调一致的“内心状态”的心理事实的判定,即感受到了内心理性与知性和谐一致的自由游戏状态。所以已具多重定义的“审美判断”被归化为了一种心理暗合的过程。而“情感体验”是做出以上判断后,主体体验到的心理状况,所以“判断在先,愉悦感在后”中的“愉悦感”,应当被定义为愉快不愉快的审美情感中“判断”之后感应到的“愉悦”。
所以“愉悦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体。首先它指的是“鉴赏判断”中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在康德的论述中它又被细分为由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关系构成的情感关系,以及由这种判定“内心状态”产生的愉悦的情感体验两种。康德在文中并没有一一点明“The feeling of pleasure”中蕴含的多重的“愉悦”类型,需要读者从其文意中梳理出来。
由此我们可以在“先后关系”上得到两层含义:一是“鉴赏判断”中情感关系在先,鉴赏判断在后,而后产生情感体验;二是“鉴赏判断”中鉴赏判断在先,感官快适在后。对于后者,康德强调的是感观快适不能成为鉴赏判断的基础,它必须在“后”而不能在“先”;对于前者,康德更换了一个论述角度,鉴赏判断中因内心认识能力的自由游戏而引发的情感关系必须在审美反思判断之前,否则反思判断就失去了“美的依据”。
二、矛盾的产生——图式“判断在先”的鉴赏判断
从先验哲学的角度看,鉴赏判断中“判断在先”在康德那里是在先验层面上被推出的,或它本身就是先在的。那么从文本的解读中就不可能得到有关“为什么鉴赏判断中‘判断在先’”的结论,而顺着康德的思路来看,分析的关键应是“鉴赏判断中‘判断在先’何以可能”。为此我们构建了图1来展示《判断力批判》中快适判断与审美反思判断,多重愉悦感之间的关系。

图1 由表象至愉悦感的过程图示
如图1所示,在第一个阶段,个人通过感官的直观能力及相关的表象方式获得某外界事物的表象。而内在的表象能力——“想象力与知性”一方面参与了第一步中某物表象的形成——“一个使对象借以被给出并一般地由此形成知识的表象”,[1](52)其中“想象力把直观的‘杂多(manifold)’复合起来;知性把结合诸表象的概念统一起来”[1](52)。在这一获得表象的阶段,认识判断与审美判断获得的表象是同一的,即获得表象的行为本身并不存在认识与审美的区别。
另一方面在获得自由的“审美表象”的过程中,想象力是将表象与情感联系起来的中介,它不是再现性的,“而是被看作生产性的和自身主动性作为可能的直观的随意形式的”[1](77)。在这里,人是自由的,审美表象是自由的,人与审美表象的关系是游戏性的。由这种生产性的想象力再生出来的表象——“审美表象”与客体本身存在(实存)无关,不受概念的限制且是变动不居、飘摇不定的,是想象力的创造物。知性也进一步参与到“审美表象”的形成过程中,当它意识到所接触的只是一个表象时,认识能力解除了限制,进入放松的状态。这就是“知性为想象力而不是想象力为知性服务”[1](79)的状态,即知性中的抽象能力与抽象概念分离了,抽象能力用于联系表象与主体;抽象概念退出判断过程,保证了鉴赏判断不涉及概念(利益的一方面)而成为纯粹的鉴赏判断,以确保其纯形式性。
分析至这一层面,可知在康德看来,鉴赏判断与认识判断的唯一差别即知性与概念是否分离。在审美判断中建立的是一种自由和谐、互相应和、彼此不即不离的关系。康德把这称为“诸表象能力的和谐”[1](72),这就是审美过程中的“内心状态”。这种状态产生的内在“动机”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1](54),即人们出于天然的认识事物的需要,通过“附加”的方式把一个实际上不具有明确目的的事物看作是形式上合于目的的。
在图示的第二阶段,在这种自由、谐和的“内心状态”中,主体因自由感或称为情调(协调感)之体验(即“判断”)而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愉悦。如朱光潜先生所言:“康德把这种同一感觉的可共享性叫做主观的普遍可传达性。就是对这种普遍可传达性的估计或判定才是审美判断中快感的来源。美感之所以有别于一般快感的正在于它富有,而一般快感没有这种对心境的普遍可传达性的估计。”[6](355)
对内心状态的“判断”逻辑上应先于对对象的“愉快”,这就是鉴赏判断中的“判断在先”。这种“内心感觉”在我们之前的论述中被认为是在愉快与不愉快的情感中再次细分出的“情感状态”,在图示中表示为“愉悦感A”。康德称这种普遍可传达的“内心状态”为“共同感”,以此保证了审美判断的普遍可传达性。“判断在先”就是审美判断中必须产生想象力与知性的和谐一致,并实现的“知性的分离”。而后产生由这种审美反思判断而导致的“情感体验”,在图示中表示为“愉悦感B”——愉快与不愉快的情感为第三个阶段。
康德所论述的“审美反思判断”实现了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中两种“愉快与不愉快的情感”转化,那么在这个论述的意义下,鉴赏判断的“判断在先”与最初提到的两条看似矛盾的命题就可以统一在了一个审美判断的模式之下。总而言之,在审美过程中,对象的直观形式是具有主观合目的性的,引发主体心意能力(想象力和知性)的协调一致而产生的审美的“心意状态”逻辑上应先于由此“心意状态”带来的情感上的愉悦。
三、打开钥匙——出现“矛盾”论述的内在逻辑需求
为什么《判断力批判》中会出现这两段看似矛盾的论述,是否是康德的有意为之?
康德所要论述的是鉴赏判断是与“快适”或“善”等带利害的愉悦不同的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又是与通过知性来连接客体的认识判断不同的对一个对象的表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判别的能力。
当需要论证鉴赏判断与认识判断、与善的判断及快适的判断的在“质”的方面的差异时,问题集中于鉴赏判断中所涉及的表象是否带有利害,以及表象是与客体联接还是与愉快与不愉快的情感联接的问题上,这两点在图示的第一阶段的审美表象形成就可以推论出,快适的判断只是以感官经验为基础的,善的判断在表象中参与了概念的利害,两者快感的形成都与实存相关。而认识判断中的表象是由感性和想象力按一定规律构造出来的,再现对象的存在与性质的表象,是运用抽象能力的概念的判断,因此不具有审美表象的“自由”性。所以在集中讨论这个关系问题时,康德将图示的第二阶段暂时隐藏了起来。
当需论证审美判断无概念且具主观普遍性时,康德关注到“愉快先行”与“具有主观普遍性”是相矛盾的,即“主观普遍性”是论证的“最直接依据”。因为“鉴赏判断的主观普遍性”是先在的,“鉴赏判断中判断先行”可用以论述“鉴赏判断主观普遍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这之前,康德只能用反证法来论证鉴赏判断具普遍性:因为鉴赏判断所依据的是“情感”,而快适的判断所依据的是“感觉”,且“感觉”的形成是不具有普遍性的。另一方面,康德认为审美能力是人所共有的,即“若你做出的审美判断的根据不是个人性的,则是普遍性的”[1](69),因此鉴赏判断只能依据“情感”而非“感觉”获得普遍性。而在提出了“判断在先”之后,康德就可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协和一致的内心状态”与“反思判断”的动因来阐释“鉴赏判断主观普遍性”的问题。所以在这一论证阶段中,康德必须将第一次论述时暂时“隐形”的第二阶段还原,回归到完整的审美图示中。
所以,正是这种随论证内容的需要而发生的审美图示或局部或整体的变化,造成了本文开头提到的“判断与快感孰先孰后”的矛盾论述。
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为什么“在鉴赏判断中是愉快感先于对象之评判还是后于前者,是区分感官快适与鉴赏快感的关键”[1](52)。“快适”是单纯的经验性愉悦,属于感官鉴赏;而审美快感是既略带认识的性质,又略带意志的性质的“复杂的情感”[6](237),它是一种内感觉,不是靠单一器官产生的,属于反思判断。在形成表象时,快适判断的依据是感官体验,所以感官能力单独参与就可以产生快适的体验;而鉴赏判断的情感体验是由感官直观能力(负责给予表象)及相关的表象能力——知性与想象力,经过两个不能完全分割的小步骤而产生的“自由的审美表象”。
图1所示的具有普遍性的“鉴赏快感”是第二阶段产生的愉悦感A,快适的形成过程直接跳过了第二阶段——“愉悦感A”被“省略”了,“愉悦B”转变为“感官快感”。所以快适判断中表象的性质并不能引发“无目的的合目的”机制而产生想象力与感性的自由游戏状态,使“感官快适直接成为了判断的基础”[1](53),“感官感觉中的快意”先于的只能是仅具私人有效性的“快适判断”。
[1] 康德. 判断力批判[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2] 叶知秋. 无美之学——西方美的本质学说的批判[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3] 余慧元. 康德向现象学的逼近——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判断力批判>[J]. 江苏社会科学, 2003, (3): 35−39.
[4] 杨金刚. 纯粹审美判断的演绎: 先验的还是经验性的——试论康德<判断力批判>中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J]. 甘肃理论学刊, 2009, (3): 89−92.
[5] 邓晓芒. 论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先验人类学结构[A]// 德国哲学论文集第十五辑. 北京: 大学出版社, 1996.
[6] 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7] 柯佑祥. 适度盈利与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65.
Abstract:The precedence of the judgment or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has been mentioned twice in Critique of Judgment,which forms a contradictory. Focused on this problem, the author makes a redefinition and the core esthetic scheme from a close reading of the whole text, and demonstrates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udgment and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could be the key of understanding the esthetic judgment.
Key Words:the Kants’ Aesthetics; antecedent judgment; critique of judgment; Plato; judgment; feeling of pleasure
On the precedence of the judgment or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in Critique of Judgment
SONG J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I01
A
1672-3104(2011)02−0052−04
2010−05−18;
2010−09−19
宋桔(1983−),女,浙江杭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语史与语言哲学.
[编辑: 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