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打工诗歌对借居城市的苦难表现
2011-10-09姜超黑龙江绥化学院黑龙江绥化152061
⊙姜超[黑龙江绥化学院,黑龙江绥化152061]
论打工诗歌对借居城市的苦难表现
⊙姜超[黑龙江绥化学院,黑龙江绥化152061]
打工诗人艰难的生存使他们在城市留下了慌张的表情,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身”与“心”的背离与游荡使他们最终成为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双重“他者”,这些苦难也造就了打工诗歌,使其具有很高的文学贡献。
城市打工诗歌苦难表现
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成为城市无法忽视的真实存在,也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宝贵的发展契机。他们被城市“土著”称为外来者,是城市的寻梦者,憧憬着淘金梦。干最累最苦的活计,拿很低的报酬,地位低下,艰难的生存使他们留下了慌张的表情,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身”与“心”的背离与游荡使他们最终成为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双重“他者”。
庞大的城市闯入群体,背离乡村的热土,走向繁华的都市,扑入汹涌的商潮,开始漂泊的打工生活。“打工的”、“劳务人员”、“城市建设者”、“盲流”等都是他们的临时称谓,在都市追寻着他们的黄金梦想的过程中,城市的幸福之门时常傲慢地将他们排拒在外,他们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族群,见证了急于发展的大时代留下的苍凉阴影。打工诗人早已摆脱了藏在深闺的未名状态,开始频繁亮相于诗坛,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成为诗坛不可小觑的新锐族群。他们像被埋藏着的原子弹,迟早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诗人赵亚东说:“诗歌于我是奢侈的,但我希望诗歌是一条绳索,她把我从人世的深渊拉上来。”
打工诗人对城市有着感同身受的真切性,他们不需由代言人发声,而是内心“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的原始冲动变成了诗歌。他们不是为了诗而找到苦难,而是苦难玉成了诗。
好亮好亮的黑夜啊
很守时间的,扭亮
长街短巷的灯
如同睡眠不足
被人拍醒,睁开的
朦朦胧胧的眼睛
但不是叫人看路
而是叫路看人
好黑好黑的光亮啊
——雁翼:《路灯》
雁翼诗笔下的深圳肯定与它的宣传片搭不上调,而是城市闯入者艰辛的日常写照。一群睡眠不足的打工者眼里的路灯成了有罪之物,它是开工死命劳作的象征,是驱赶人忙碌工作的替代物,甚至比半夜鸡叫还让人心惊肉跳。“好亮好亮的黑夜啊”与“好黑好黑的光亮啊”实为互文,闯入者竟然在国际大都市产生了眩晕感,这无疑是晚近城市诗歌书写的一个重要斩获,而它根植的土壤绝对是中国化的。工业区,这个词汇在政府官员眼里是政绩报告、GDP数据的象征,遮蔽了打工群体灰头土脸的真实生存状况。工业区是许多打工者首先要面对的现代化宿营地,是他们初入城市的生存空间,成为打工诗人反复言说的对象之一。
谢湘南的《一只钟的生产流程》铺陈了一只钟的生产流程,它需要三十个打工者在流水线忙碌,有人付出了宝贵的青春,有人销蚀了灵魂。工厂主唯利是图,不惜践踏女工的人权,以至于“看不见内裤里的血”。这样的诗篇压抑着摧枯拉朽的力量,揭示了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没有建立对工厂主的有效监督机制,保护打工者利益的工会组织尚未形成,打工者没有能力改变被奴役的现实,也只好“怒向刀丛觅小诗”,独自“写下工业时代的绝句或者乐府”。张守刚的《加班加点的夜》描述了流水线前的打工妹夜夜加班加点,以至于呵欠不断,夜晚在她们的眼里无限漫长。
现代科技文明借助冷冰冰的“机器”,向闯入者发威。郑小琼的《流水线》描绘了在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惊恐、灰暗的生活画卷,文字的内里喷发着身在城市的“疼痛”。在同名散文《流水线》中写道:“作为个体的我们在流水线样的现实中是多么柔软而脆弱,这种敏感是我们痛觉的原点,它们一点一点地扩散,充满了我的内心,在内心深处叫喊着,反抗着,我内心因流水线的奴役感到耻辱,但是我却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剩下的是一种个人尊严的损伤,在长期的损伤中麻木下去,在麻木中我们渐渐习惯了,在习惯中我渐渐放弃曾经有过的叫喊与反抗,我渐渐成为了流水线的一部分。”单纯地对“流水线”本身的控诉,就像汹涌的拳头击在棉花团上,不久就令出拳者丧失继续战斗的信心和耐力。
郑小琼们写作的大量“流水线”、“机器”等题材的诗作,其认识与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的表述接近,“这些机器在其形式上越来越没有人情味,越来越禁欲、神秘、深不可测。它们用一些微妙的力、流和张力所织成的无限网络笼盖着大地。”①这样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刻性,的确以机器为核心的后现代文明造成了城市的“单面人”的出现,但对机器的仇恨、咒骂是浅表的思考,与奴隶通过破坏生产工具来实现反抗何其相似,这样的认识还是在思考现象本身,而应深入生成现象的体制内部叩问。“机器。铁。工厂的耳膜已麻木于它们的叫喊/但春天,还是要细心,分辨出它们异样的音调”②。在敲打机器的同时,更应该去“敲打”时代的灵魂,打工诗歌才能更见精进和锐度。郑小琼在《生活》等诗作中,将“人”在机械和不由自主的运动中比喻成“哑语的铁”、“生锈的铁”、“战栗的铁”,无意间揭露了工业文明下人的异化命运,传达了难能可贵的个体精神追问和反思。“沉默如一块铸铁”,这样的沉默压缩着想要表达的千言万语。
黎旭的诗歌《老板请客》惟妙惟肖地记录了工厂老板暴力克扣的同时,偶尔也对流水线的小头目“怀柔”一下。张绍民的诗歌《成为老板的人》则更进一步,深入追踪了打工仔成为老板后的精神畸变、道德沦丧,“他过去是打工仔/成为老板/一举一动都像老板/不再像打工的人/他以老板的眼光看人了/像过去老板的目光/看他一样/也希望手下打工的人/像一台机器/不知疲倦/像一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厉彦林笔下的“暴发户”有着丑恶的嘴脸,“抿抿嘴眉角挂着诡意/训老爹如同训儿子/见了大老板腰弯三尺/不敢大声喘气”,他的眼里、心里全塞满了钱,“金币滋生一种虫子/短短几年的光景/就把脑袋啃空了/剩下一位/金钱塞满肚子的乞丐”。打工诗歌的重要意义之一是看到事实,然后发现真相。在特殊的转型时期,打工诗人敏感觉察到“阶级退场了,阶层出现了”,他们客观陈述了这一事实,为曾经的历史做了及时的真实镜像。“螺丝钉”曾经是人与人团结一心、和谐奋进的大背景下,劳动者以主人翁姿态热情投入工作的象征,而现今蜕变成为工厂主辛勤“奉献”、超负荷工作的打工者的譬喻。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体人民共同致富”,这个伟大战略构想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前瞻性,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有不和谐的因素和局面。胡续冬的诗歌《毕业证、身份证、发票、刻章……》很具有争议性,“张三砸锅,李四卖血/王二麻子的艾滋病老婆/还在陪客人过夜。只有俺/过得排场,戴黑镜、穿皮鞋/尿尿都尿在中关村大街。”原诗里充斥着一个假证件贩卖者的“一腔废话”,很多人读出了闯入者在城市的道德下滑、堕落和犯罪,认定贩卖者的“一腔废话”没有必要如斯铺排。这首诗却是一幅闯入者的“众生相”,在大时代的小阴影下,社会给他们提供生存的空间、条件实在可怜,他们是面目可憎、行为可恶的“恶人”吗?闯入者持有的致富资源实在有限,他们经历了时代变革带来的屈辱,背井离乡的苦痛,被压榨的心理失衡,他们的诗歌注定不会吟风弄月、粉饰太平,而是下意识地书写艰难,客观呈现繁荣景象覆盖下的心酸遭遇。生之艰难,活之不易,闯入者的艰辛生活流入诗歌。打工诗人郑小琼主张“没了疼痛感,诗歌便没了灵魂”,代表了打工诗人共同的心性追求。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不管打工诗歌揭露的伤疤怎样的令一些人不舒服,但一个铁的事实是城市在使他们蒙羞、受屈。在现代文学史上,夏衍描写的“包身工”如同生活在地狱一般。而打工群体拥有人身自由,他们有选择继续留在城市或者回返乡土的权利,有选择做什么工作的自由,他们闯入城市是为了追逐更好的生活。然而,他们在夹缝和边缘中求生存,生存条件低劣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的吃穿住行比城市失业工人更为悲惨。打工诗人有置身其间的真切感受,胸中藏着悲愤的河流,苦难的浪潮径直扑向诗歌,无暇计较溅起的浪花是否美丽。宋晓贤在诗歌《乘闷罐车回家》描摹了民工乘坐运过牛的闷罐车的场景,“像牛群一样闷声不语/连哭也哭得没有声响”,而不觉得特别的屈辱,他们对苦难的隐忍不亚于自甘受难的“圣徒”。打工诗人客观呈现了苦难,让存在自身直接说话,对许多城市居民发出了物伤其类的呼告:
胡贯六站在工棚门口
看着大楼被一节一节地拔起
看着一车一车的水泥和钢筋
被挤压成一块一块坚牢的骨肉
胡贯六晃荡着一只空空的衣袖
在工地上走来走去
谨慎地守着工料和工友们替洗的毛巾
好像他才是这幢大楼的主人
胡贯六已经不能再干活了
身体少了关键的部件
一年前胡贯六喂进了自己的一条胳膊
在往搅拌机里喂砂子的时候
——江非:《胡贯六》
离结婚仅剩下九天
他把跟随他二十多年的一只手
在一秒钟丢进机器里
让另一只手为今后的日子
突然尴尬起来
我问及事发的现场
讲起的情景煞是恐怖
他用自己健康的右手
握住自己模糊的左手
一个劲地喊
我的老婆没有了
——一回:《工伤》
如《工伤》、《胡贯六》等诗作,深入到时代噬心的悲剧主题,一切有良知的人都不会视而不见。这些诗句饱蘸着底层的血泪和愤怒,拥有刀劈斧砍般的力量,这是良知靠近诗歌的体现。“我仍不断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珠江三角洲有四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③谢湘南的《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田禾的《一个农民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彭易亮的《第九位兄弟的断指之后》、罗德远的《刘晃祺,我苦难的打工兄弟》等作品都传达着诗歌的悲悯和关怀,更充满了对缺乏人性关照的事实的质问,把个我之痛升华为生存的叩问——“我们的生命不是草芥,我们的身体不应受到没有意义的侵害。”
据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全国每年因工伤致残人员近70万人,其中农民工占绝大多数。他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环境差、危险性高的劳动岗位,工作在旧机器、噪音、粉尘、有毒气体严重超标的环境,职业病和工伤事故频有发生。?没有永远的异乡人与闯入客,城市在大踏步前进的同时,应当尊重并保护所有参与建设的人。
花枪的《黑工厂》结构简约,语言轻松,节奏自然流淌,调子略带诙谐,然而读后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多数的打工诗歌自苦难撞响灵魂的时刻产生,从城市的阴影里喊出生命的痛。“是的,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他们的诗歌以一种赤裸裸的触目惊心的原生态风格呈现在我们面前,字里行间涌动着对底层民众的悲悯气质和人文关怀,尽管这种关怀是有限度的,但是他们已经进行生存经验的灵魂书写了。”④异化的城市给予了闯入者太多的伤痕,打工诗人通过诗歌敞开自身的汩汩伤口,揭露资本异化的残忍和冷酷,目的不是为了博得同情,而是如鲁迅所说那样——揭示肌体的痈疽,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
①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03页。
②刘建化等主编:《1999中国诗歌选》,台湾诗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③黄河:《疼痛着飞翔》,《社会广角》,2007年,第11期。
④龚奎林:《“打工诗歌”:底层述写的缘由与意义》,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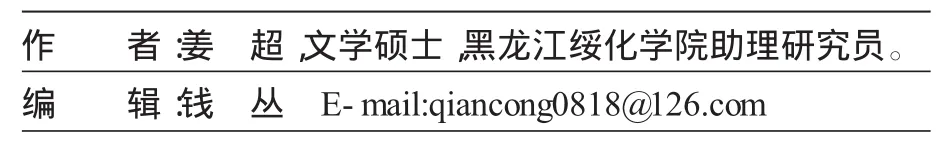
作者:姜超,文学硕士,黑龙江绥化学院助理研究员。编辑:钱丛E-mail:qiancong0818@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