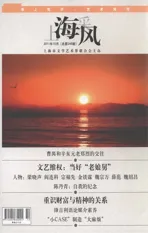锋言利语论媒介素养
2011-09-07采编黄舍得
采编/黄舍得

李 蕾

梁文道

姬十三
电视上常听主持人说“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这是假话,我都不知道谁在看我的节目,我都不认识这些观众,怎么就成了他们的朋友,怎么就成了“亲爱的”?我跟我妈才是亲爱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是假话
李蕾(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风言锋语》主持人):中学时上代数课,我把《今古传奇》《射雕英雄传》用代数的书皮包着,假装听课,其实是在看小说,当时我正看梅超风和郭靖对决,代数老师走到桌旁,咚咚咚地敲我的桌子,敲得很响。同桌一个理着小平头的男生说,如果我能见到金庸,死了都值得。那时候我们都十几岁,十几岁的人都是不怕死的。今天之所以说起这件事,是因为金庸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很多年以后我真的在华山见到金庸,那一年他80岁,可是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人家说他80岁,别人问他多大年纪,他说70多岁,如果问70几了,他就脸色很难看,说,79了。我们在华山顶,说爱情,说侠客,说英雄,说江湖。我们能活到今天,似乎都活得不错,还能相遇聊天。他们(指梁文道、姬十三)都特别大公无私,当年梁文道力战香江,和很多人辩论,也泡过很多女朋友,后来有一天忽然成为一个有知识有信仰的人,一个电视人,这么专业这么复杂的一个人,因为种种职业原因我们能够见面,通过几次聊天,他让我发现很多我不明白的东西,为我推开另外一扇门,我觉得我这个便宜占大了。有好多好东西在我们身边,还有好多人值得我们去了解。
梁文道(香港著名文化人、传媒人):我这些年做电视节目,到处演讲,通过工作认识一些不错的朋友,大家可能以为我很喜欢这种状态,但是,就像我在这套书的序里写的,我特别不能以自在的状态做电视。我虽然到处演讲,能够在舞台上自在地说话,但我不明白大家和我是什么关系。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要对我拍照,为什么要在微博上看见我,这有意义吗?这有什么意义!有人对我说他是我的粉丝,我完全不懂,这到底怎么回事。电视上常听主持人说“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这是假话,我都不知道谁在看我的节目,我都不认识这些观众,怎么就成了他们的朋友,怎么就成了“亲爱的”?我跟我妈才是亲爱的。我讨厌在电视上看到自己,从来不看我自己做的访问,如果正好看到电视上有我的节目,我一瞄就转台,没法忍受。我写完的文章也从来不看,写完发出去我就不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出现在电视、报纸、杂志、书上的我都不太能适应。但我比较享受的是,在演播厅里一个人对着麦克风发表观点,观众喜欢我还是讨厌我,我跟这种情绪是隔开的。我既不因为人家讨厌我而生气,也不因为人家喜欢我而高兴。
姬十三(果壳网CEO、科学松鼠会创始人):我一直不太喜欢上电视,一方面觉得自己嘴笨,另外,每次上电视,我妈都会打电话给我,说你怎么那么胖。但是我还是愿意上李蕾的节目,因为李蕾是一个不错的主持人,她特别会谈话,会带动场上的嘉宾放松,并尽可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当下各种访谈节目非常多,对话也特别多,但是真正好的主持人却非常少。李蕾是其中的异类,不是那类仅靠巴掌脸来撑场面的主持人。
李蕾:大家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我的好话。我其实很多次想问自己,我这样长相的人也可以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况且我还不是播音主持专业毕业。因此,常常有专业人士问我,你是怎么能够做到电视主持人的?我不擅长讲话,但大家表扬我讲得不错,我觉得很诡异,不知道为什么会博得大家的认同。但是有好奇心,彼此之间有好奇心是一定的。
梁文道:我也是,我做节目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很多人也问我,你长成这样怎么能做电视?我回答说这个问题你不要问我,你去问电视台。我赞同姬十三的观点,李蕾是少数我遇到的有想法的主持人之一。很多人干这行,不太会想这件事情和我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想要做什么。尤其做电视节目,他总是会认为他天生就是做这行的,从来不去反省为什么要去做,而李蕾会去思考。如果一个人带着思考去做节目,在过程中会出现一种奇怪的格格不入,我辨别一个同行是不是有想法,就看他在做节目前后和做节目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一点格格不入。
做电视这一行,其实很容易清楚观众及上头的喜好,知道如何去迎合大众,这种态度的节目很容易倾向油滑。在这样的前提下,没有陷入一个油滑的流水线,这就是一个电视节目、电视人的态度。
媒体的态度就是用心说真话
梁文道:对我来讲,教书、写作、演讲、做电视节目,都是同一回事,都是以此为媒介在传播观念,我做节目和我写文章状态差不多,尤其当我一个人对镜头说话时的状态还算自在,但是在这种状态当中我又有一点不适应,包括我写作。不适应来自什么?在这种环境,这种行当里面有着各种潜在的关系。我在写作的时候就在想,我的东西写给谁看,读者是谁,我制造的观点是什么,而做节目时背后的假设关系是虚伪的,比如“亲爱的观众朋友”。做完节目后,主持人要假装收拾文件,两个人假装聊一聊,如此种种让我发出疑问,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这样做,这些状态令我非常不舒服。
今天在中国大陆,我们做电视其实是很困难的,尤其是《风言锋语》这样的谈话节目。我们总在假装我们无所顾忌,其实我们很多说话的方法是被动式的。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试图用别的方法或者途径将你的看法传达出来,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在我看来,这种态度的谈话节目是不屈不挠的,仍然试图去触碰一些看不见的条件和限制,而不是一味乖顺或顺从。做电视这一行,其实很容易清楚观众及上头的喜好,知道如何去迎合大众,这种态度的节目很容易倾向油滑。在这样的前提下,没有陷入一个油滑的流水线,这就是一个电视节目、电视人的态度。
李蕾:态度这两个字,在我看来,都是用心在说真话,用心在做事,如果不能用心说真话,那就避免说假话,这是我想要的态度,但是很难,不是每次都能做得到,也不是每次我都能说我真正想说的话。
我想起二战时诗人策兰写的诗:妈妈,我在用敌人的语言写诗。有时候我们没有母语,我们不知道怎么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思想。我得承认我经常会面对一些诱惑,比如有一次我录节目时突然会闪出一个念头,如果这个时候我骂一骂周立波,节目的收视率一下子就能上去了。因为不管你多爱周立波或者多讨厌周立波,只要有人讨论他,收视率就会高。但是我不能这么做,我的不可以是因为我自己的选择,是因为媒体的特征,这是职业道德,但是我会常常面临这样的诱惑,当我这么说我会得到某种补偿,当我那么说我就是坏人,要写检查。打击、失望、挫折是常常发生的,我们必须接受,但是也要坚持希望,不管现在这个时代是最坏的时代还是最好的时代,我们都要有所保留。
有一个现象是,张悟本倒了以后绿豆就成为坏蛋了,方舟子只要打假说这个人不好,那么他永远都不能翻身站起来。我完全不认为方舟子就等于真理,所有争议讨论都是有价值的。
相信观众都有判断力
李蕾: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很多嘉宾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有时候他们是一些小人物,但我不认为他们“小”,他们让我看到了我不了解的世界。比如赵作海,当年因杀人罪被判死刑,但多少年后“被他杀”的人活过来了,他由此获得国家赔偿。我非常心酸,当年如果我的父亲没上大学,那么我不会有我的现在,赵作海的命运有可能是我的命运,有可能是每个人的命运,一个个体面对很大的时代或者制度时是非常脆弱的。凡是能够有这种想法的人都是令人尊敬的好嘉宾。
《风言锋语》请了马悦凌做嘉宾,有观众提出质疑,让如此有争议人上电视是危险的,并对我提出建议,作为《风言锋语》的制片人,以后选择嘉宾时慎重一点,要把好关。我承认这个栏目发生的所有问题应该是由我来负责。马悦凌上节目的确有这回事,当时我们录了一个健康系列的节目,其中有一期是关于肠道减肥,马悦凌和上海一位专家上了节目,如果看了节目,会发现他们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对于生吃泥鳅这个观点我们的节目持否定态度。有一个现象是,张悟本倒了以后绿豆就成为坏蛋了,方舟子打假只要说这个人不好,那么他永远都不能翻身站起来。我完全不认为方舟子就等于真理,所有争议讨论都是有价值的,但不能说,因为马悦凌在某一个领域,在某些问题上不严谨,从此以后,马悦凌说的任何话,譬如人渴了要喝水这样的常识话语,从她嘴里说出来也成为骗人的话。如果马悦凌说冬天感觉寒冷了,用红枣当归桂圆煮汤来补补身体,这不是她的发明,是我们古人的发明,从她嘴里说出来也是骗人的吗?有些东西不是单纯用“科学”这个词就能涵盖的。譬如发烧,我39度时还能干活、还能说话、走路和看书,但过了39度2就不行了,而有些人37度2就要倒下。我认为个体之间存有差异,有些方法对他有用,对你不一定有用,而这也不是科学就能给它定义的。
姬十三:我纠正一点,个体差异化本来就是生命科学应该诠释的东西。不能用科学不科学来定义。
李蕾:如果方舟子认为他38度才发烧的话,有人可能会比他更高或者更低。把东西都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从来不低估观众的智商,我认为大家是有判断力的。
梁文道:我没看到那期节目,但是我常常也会遇到这类观众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要谈这件事,这会对大家有坏影响”。我常常被人要求去正视我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责任,因为大家常认为我们身为媒体人一不小心就会有坏影响。比方说,有人指责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有时候有港台腔,他们会认为这样对观众有坏影响。请来一个观众认为错误的人上来做节目,一直到你的发音的问题,他都会认为这些会给社会带来坏影响。每次听这些话,我都会想,我们这个社会太纯洁,我们都像孩子一样,我们都是处男处女,我们很天真,我们很容易被“坏影响”所影响。但是更为有趣的是,有时候我请一个人上来,或者我介绍某本书,我发现很多观众的想法是甚至不应该让这个人物或者这本书出现,比如说,李蕾做节目,安排一个观点让嘉宾进行辩论,这个我以前也参与做过,请一个有争议的人上台,另外一个嘉宾和他辩论或者没有人和他辩论但我们的节目自己发出疑问,观众会觉得有问题的,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不能存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有问题就要上电视,要让大家看得更清楚,通过负责任的媒体人的讨论、辩论,我们才能更了解它,从而让观众进行判断。而不是我们做媒体的人下的判断。我相信我们的读者、观众是有判断力的,这个权利属于他,而不是媒体。我不相信一个观众听了我的普通话,第二天他的口音就变了。我们没有权力告知人们什么东西可以看见,什么东西不可以看见。我们只能够把所有东西呈现出来,然后让人们去判断,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该如何对待它,它和我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凭什么在给观众、读者看之前就决定他们不能看什么能看什么,凭什么把所有人当成小孩子,我们都不是小孩子。
姬十三: 媒体最难的一件事是它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受众是什么,它没办法去选择它的受众。你真的不知道哪些观众会对你的哪些观点发生质疑,而且,媒体应有这样一个态度,让尽可能多的事情发生,让尽可能多的观点进行碰撞。但是依然会有观众产生误解,产生这样那样的质疑。尤其在当下“快阅读”时代,人们很容易轻易下判断。比如在微博上,大家会对一些问题展开讨论,但人们往往在看完140字的微博而不是它后面所附的更长的文章之后就在一两秒内轻易下判断,从而在网上引起某种情绪,而其实他引起的某种情绪和长文章中的内容完全背道而驰。在这样的年代,我们媒体人要做到的就是既不能低估读者、观众智商,也不高估读者、观众智商。
李蕾:非常难。我们做电视面对两边的声音,一边来自上面,一边来自民间,两边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我希望媒体展现出的内容是丰富的,频道丰富,最起码打开电视,如果50台都是超女,这个就是单调,50台超女它还是超女,总要有个不一样的声音吧。如果50台都是50种不同类别的节目,那么这就是丰富,就像调色板一样。媒体需要提供更多的声音和观察角度,大家从中可以选择。只有判断力是自己的,谁都拿不走。新闻联播的准则就是三个十分钟,我的节目只提供我们的功能,尽可能让自己的技术好一点,让自己的立场更加坚定一点,把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呈现给大家看,这是我所期望做到的。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有问题就要上电视,要让大家看得更清楚,通过负责任的媒体人的讨论、辩论,我们才能更了解它,从而让观众进行判断。而不是我们做媒体的人下的判断。
梁文道:刚才姬十三讲得很对,我们不能太高估受众的智商也不能太低估他们的智商。但是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很多读者书都没看过,就开始评价这本书,或者一篇长文章也许只看了一两段就动笔写感想臭骂作者一顿,而事实完全在冤枉作者,这种情况太常见。在“快阅读”年代,我们都不愿花时间去看去理解,我们在理解前,甚至在完整的阅读、观看之前就先下判断,结果离事情本身越来越远,这不能构成“什么应出现什么不应出现”的理由。这方面就牵涉到“媒体教养”(媒介素养)这个学术概念,英文即media literacy。媒体也需要足够的教养,谁不会看电视,谁不会看报纸,谁不会看电影听收音机,都会,但是需要视觉能力,辨识能力或者说媒体教养。媒体教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它包括人们对各种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现在拥有的听、说、读、写诸能力之外,还应具有批判性地接收和解码影视、广播、网络、报刊和广告等媒介信息的能力。
我们的确有一些朋友,天天看电视,但他不去思考为什么节目要这样结构……这里面都有媒体自己的话语存在,对于媒体呈现的观点受众能不能耐心判断和解读,这都涉及到教养,这个教养是今天全世界都欠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具备足够的媒体教养或说媒体辨识能力,在中国,受众没有机会去发展这些能力,永远都是温室里的宝宝。因此我们从来没有对媒体下判断。有没有人在岸上看游泳指南学会游泳的?没有。在陆地的环境中,你一辈子都学不会游泳。受众能力需要培养,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这和我们的教育有关,但我们的教育恰恰是什么东西可以看,什么东西不能看,什么东西有好影响,什么东西有坏影响。我们这样的教育观其实是“喂奶观”,而不是教你学懂如何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