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幕的黄金时代—— 安德烈·希夫林的职业生涯
2011-08-31◎叶青
◎ 叶 青
“它不受广告的影响,也不必针对大众。它可以逆潮流而动,可以宣扬新的观念,可以向现状发起挑战。它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它的读者就会出现。它就是——出版业。”这是安德烈·希夫林在自己薄薄的自传——《出版业》的扉页上所写下的话。
安德烈·希夫林1962年加入兰登书屋旗下的潘塞恩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格拉斯在4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将米歇尔·福柯的《疯狂史》介绍给了美国人;他认识令人生畏的英国文学评论家利维斯教授;他向文化研究的创始人雷蒙德·威廉斯约稿;他让萨特和波伏瓦晚年的作品和玛格利特·杜拉斯的《情人》广为人知。他见证了美国出版业大并购时代的开始直至分散的家族式独立出版机构成为垄断集中的全球性传媒集团,他经历了那个永不复返的既能出好书又能赚到钱的黄金时代,却绝不妥协于如今媒体工业化之下唯利是图的市场原则。对于一个子承父业的出版人,没有谁比他更了解出版业;对于一个绝不向资本利益低头的出版人,没有谁比他更坚信书籍的价值。对于出版界而言,他是一个始终保有热情与执著的精神战士。
一、黄金时代与媒体垄断
安德烈·希夫林1935年出生在法国,他的父亲是俄裔犹太人,一战后移民到法国创立七星出版社,是一位非常出名的出版商。当初以平装本普及名著是老希夫林的初衷,尽管时至今日已经归到伽利玛名下的《七星丛书》仍然是众多文学名著丛书中的一个著名品牌,却只做豪华珍藏版了。二战爆发后,老希夫林逃难到纽约,加入潘塞恩图书出版公司。潘塞恩图书出版公司作为独立的出版社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以出版卡夫卡的作品闻名。老希夫林仍然致力于出版名著,比如《忒修斯》《维吉尔之死》《局外人》等,通过潘塞恩走进美国民众视野的欧洲作家名单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成为了重要的欧美文化交流的桥梁。20世纪50年代,潘塞恩出版了中国《易经》的完整英文译本,日后对美国知识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出版的《日瓦戈医生》畅销600多万册。父亲的行为深深地影响着小希夫林,他一直以潘塞恩所出图书的学术品味和思想价值而深感自豪。
然而好景不长,1961年,兰登书屋只用了100万美元就收购了潘塞恩,一举成为美国出版的巨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潘塞恩并没有太大的利润压力并且深得兰登决策者的信任,所以,希夫林得以实现各种各样的出版计划。1980年,几经转手之后,兰登公司被媒体大亨塞缪尔·欧文·纽豪斯以6,000万美元买进。在这十年中,潘塞恩公司的编辑开始为了实现高额利润预算而东奔西走,传统出版业的生态环境逐渐改变。在过往没有电视甚至无线广播的时代,占尽优势的出版业还依赖于禁酒制度保留下来的销售体系分销书和杂志。酒贩子坚持到月底就把没卖掉的书和杂志一起退回出版社,这个运转良好的分销渠道和时间节点分明的运营规则逼迫出版社多出书、出好书。这个看似良性互动的反馈机制催生出美国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各种制度变得越来越“科学”,每本书都要填写盈亏表,每个编辑每年都必须获得一定的盈利,书店里的每立方米空间也都有考核的指标。“一本书待在书店的时间比鲜奶长,但比酸奶短。”图书的退货率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的20%翻了一番,超过了40%。这一转变直接带来的负面效应则是编辑的决定权让位给了财务报表,出版社的利润越来越依赖于畅销书。全球化趋势下的重商主义倾向和根据每本图书是否能马上赚钱来决定是否出版的“市场审查制度”对出版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纽豪斯为了政治利益干涉图书的具体出版,甚至不惜支付巨额的稿费讨好政要。不止于此,资本对于利润的追逐愈发疯狂:过去出版业被看作是会给出版人带来荣誉和乐趣的行业,它的税后利润率大都在3%~4%。而之后当纽豪斯以10亿美元将兰登书屋卖给贝塔斯曼大赚一笔时,兰登书屋的利润率下滑到了惊人的0.1%。新的媒体集团要求图书部门要向旗下的报纸、电视、电影看齐,15%的利润率成为出版业的新目标。
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力,使得希夫林感到举步维艰理想破灭,“看看那些畅销书,除了享受生活,就是名人轶事,以前的知识性和艺术性几乎荡然无存,这体现的完全就是娱乐业的标准。”①在20世纪90年代身为发行人的他成为从兰登书屋集体辞职的人之一。最大的原因也许是他所坚持的出版业传统价值观与纽豪斯寻求迅速改变以求利润的作风完全背道而驰。对于纽豪斯而言,变就是变,它不是慢慢变。②而对于希夫林来说, 图书能否获得读者的认可,完全取决于它的内在价值,而不是它对账本的贡献。
二、媒体集团与独立出版
20世纪上半叶,出版人坚信让读者接触到真正的好书是出版的使命,20世纪下半叶,出版业在盈利的驱使下沦为第二个娱乐业。当潘塞恩公司从独立到归属兰登,再到兰登被贝塔斯曼收购,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出版业走向了集中甚至垄断。 正如希夫林在接受艾米·古德曼采访时说:“在漫长的过程中,商业书籍、大型媒体集团已经开始购买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并拥有了电台、电视、有线电视、杂志、报纸等。目前在美国向广大读者出版发行的书籍中有80%被五大集团控制。”③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通讯法案》通过之后,美国出版业在10年中经历的变化是激烈的。到了上世纪末,五大集团(AOL-时代华纳、迪斯尼、维亚康姆、贝塔斯曼-兰登书屋和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已经控制了美国图书销售市场的80%,最大的20家出版社已经占领了93%的市场,其中最大的10家则又占去了全部收入的75%,美国出版版图已经被完全改写。时代华纳集团的年销售额超过了30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图书市场的总销售额230亿美元,它甚至可以购买美国整个出版业。图书出版业务几乎要被大型媒体集团吞没了。④“如此说来,在今天的出版界,唯一会因为放弃原则而看不起自己的就只剩下作者了。出版商在乎的,只是怎样迎合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出版历程,但希夫林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自己信念的坚持。
亲历了广播、报纸杂志、电影和电视对出版业步步紧逼的挤占和蚕食,希夫林习惯了以作品本身的价值作为决定出版与否的标准,习惯了只有一部分书才能赚到大钱、相当一部分的书必定要亏钱的行业特点。“所以出版是一个你必须要冒险的行业,因为你得知道它并不是一定能在短期内获得巨大报酬。” 1990年,希夫林成立了自己的 “新新出版社”(The New Press),一个替代大型商业出版社的非营利性的出版社。它致力于出版在教育、文化和社会价值方面有创新意义的书籍。出版社的编辑程序有三个标准:拓宽读者对于严肃的哲学作品的了解;引进传统却不易被理解的思想;解决社会问题并尝试在更广泛领域内的创新。⑤十多年来,希夫林出版了为数众多的有争议性的政治类图书、外国文学作品、非小说类作品和艰深的法律著作。到1998年为止的8年间,这家小出版社的书单上已经有了300多种图书。尽管新新出版社获得了书商、教育家、批评家、读者广泛赞扬和数不清的奖项,年过半百的希夫林仍不得不承认,他的努力在被大公司收购四起的出版业中简直微不足道,所有独立出版社的销售额加起来也占不到图书市场1%的份额。“金钱的重要性已经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那些原本被视为抵抗力量的价值观正在迅速消失。无论我们的财产,还是我们的工作,甚至我们自己,都已经成为商品,被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同样的变化也曾在其他历史时期出现过,可现在世界的全球化和媒体的工业化让它的影响力更加惊人。”⑥
好在希夫林在出版业多年的经验使得这个非营利出版社可以继续很好地运转下去。在他看来,独立的、非营利基金会的报纸和图书出版社是保护政治和文化自治的最好途径。而传媒集团控制则会对媒体的发展产生危险。⑦因为对于一个媒体世界,又要坚持自身道德又要注重政府底线,这就使得出版或者广播的内容很难保证巨大的销量和利润。在阿富汗战争时,商业出版社为了获利借机出版批评言论的书籍,一度登上销售排行榜。总之,资本完全渗透到出版行业之中,以利润为中心成为出版业不可逆转的潮流,出版短时间内没有多大销量的思想类、学术类、社科类图书的出版社或被其所属集团关闭,或者转而疲于奔命地经营畅销书,这使大众出版的图书品种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单一化。而这正是希夫林忧虑之所在:生活在一个没有新观念的社会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⑧
我们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它能统治一切,相信它能让世上所有的价值观为之臣服。我们还把它看作是消费者民主的一种体现。所有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了出版业。然而当理想遭遇现实的滑铁卢,只有真正的勇士敢于前行。安德烈·希夫林,作为历经几十年风雨的出版界精神战士,他让我们看到,成为商品的图书仍然表现出与其他媚俗性大众媒介的本质不同:图书可以逆潮流而动,可以宣扬新的观念,可以向现状发起挑战,它是民主社会核心的沟通渠道,它是人类社会得以前行的光热和希望。
注释:
①杨红卫.产品创新:文化创造商业价值[J].出版发行研究,2008.6.
②[美]汤玛斯·麦尔著,徐绍铭译.媒体帝王[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6.6.
③⑤ [美]艾米·古德曼. 从媒体垄断到非盈利独立出版——安德烈·希夫林在出版界的五十年[DB/OL]. http://www.democracynow.org/2007/3/28/andre_schiffrin_on_50_years_in
④ 陈晓梅.出版业的启示[J].中国图书评论,2005.9.
⑥ [美]安德烈·希夫林著,白希峰译. 出版业[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59.
⑦[美]安德烈·希夫林.如何经营非盈利出版[DB/OL].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7-11-07-schiffrin-en.html
⑧方卫平.责任与精神如何被消费[DB/OL].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0/2010-07-09/87445.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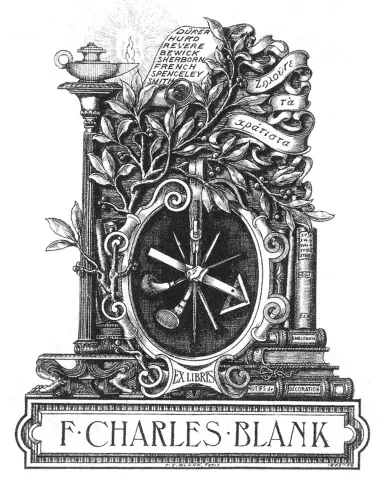
F.Charles Blank 美国 C2 8.1X10.2cm选自《藏书票风景·收藏卷》 河南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