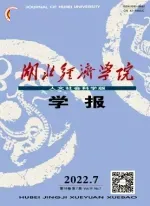得“意”不忘“形”
——试论文学方言的汉译方法
2011-08-15李源园
李源园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1)
得“意”不忘“形”
——试论文学方言的汉译方法
李源园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1)
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大量方言一直是译者需要面对的一大难题。对此译界长期以来讨论和争议较多的是方言对译法和口语体译法。本文通过选取具体语段,旨在分析比较这两种译法的得失,初步探讨文学方言汉译的方法,为翻译策略的选择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文学方言汉译;方言对译;口语体译;方法
方言一词最早见于希腊语,是指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主要用在口语上或口头上的地区性或区域性的语言变体,可以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在文学作品中所使用的方言,对于塑造人物形象、折射地域特色、传达艺术效果和增强作品感染力等方面都能发挥显著的作用。然而,如何处理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对于译者来说,却是棘手的难题。奈达说过,“如果一个文本是以非标准的方言写成的,译者就要面对在目标语中寻找合适的对等物的困难”。因此,如何让浩如烟海的一部部优秀的国外文学作品穿越时空,为尽可能多的中国读者欣赏学习,便要求译者要正确处理好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转换,既忠实于原文,又能将文化风格传递到位,同时不对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有任何的增减而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或偏差。基于这一议题,译界讨论得最多的就是以张谷若先生为代表的方言对译法和韩子满先生主张的口语体译法。所谓方言对译法,就是用译入语中一种方言的成分来翻译原文中方言成分的方法。而口语体译法,则是用比较通俗、口语化的汉语来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这两种译法各有千秋,而要获得成功的译文,首先,要吃透原文,深刻把握人物与方言的内在联系,注重人物所操语言在塑造作品风格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即必须得“意”;其次,不可忽视方言本身的功能性,让译语尽量贴合原语,即不能忘“形”。在汉译时不妨结合方言对译和口语体译两类译法,对具体语段作具体处理,随机应变,融会贯通。两者双管齐下,从而做到“意”“形”结合,相得益彰。下面通过一些实例,做进一步的比较、分析和说明。
一、以“意”为本 还原风格
文学作品是通过语言创作的艺术,而语言所彰显的风格则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对于译者来说,如何最大程度地还原原著的风格是需要在翻译过程中不断追求的目标。翻译是对意义的翻译,更是对风格的再现。因此,翻译文学作品不仅要忠实于原著的内容,而且要忠实于原著的风格,这样才能把原著的真实面貌传达给读者。
美国文学巨匠马克·吐温及其代表作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全书由主人公哈克这样一个十三、四岁的流浪儿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叙述故事。该书主要特点便是方言、土语及黑人英语的大量使用,形成了原著浓厚的本土风格。对此,张万里先生的译本是其中的佳品。他采用通俗简洁的汉语口语体形式,将原著的这一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请看下例:
原文:We slept all day,and started out at night,a little ways behind a monstrous long raft that was as long going by as a procession,she had four long sweeps at each end,so we judged she carried as many as thirty men,likely,she had five big wigwams aboard,wide apart,and an open campfire in the middle,and a tall flag-pole at each end.There was a power of style about her.It amounted to something being a raftsman on such a craft as that.
译文:我们几乎睡了一整天,到了夜里才动身走,有一排很长很长的木筏,好像一大队游行的人马似的,在我们的前面漂着。它每一头有四根长浆。我们猜想那上面恐怕至少载着三十个人。筏子上搭着五个大窝棚,彼此离得很远,木筏当中还生着一个露天的大火堆,每一头还有一根大旗杆。它的气派实在是大极了。在这样的筏子上当个伙计,那才够神气的哪。
原文句子短小精悍,浅白通俗,孩子气十足。再看译文,同样简洁明了,稚气未脱,一个单纯淳朴、想象力丰富的小男孩形象便跃然纸上。
在用词上,原文除个别词汇如 monstrous,procession,wigwams等之外,其余都是常用的单音节或双音节词,long,tall,wide,big等形容词频频出现,其中long甚至重复了三次。这十分符合哈克的年龄身份与个性特征,译者在处理这些词汇时也用了“很长很长的”、“大窝棚”、“大火堆”、“大旗杆”这样的浅白字眼使得译文的风格与原文环环相扣,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人物的形象和特色。
这样一段孩童式天真浪漫的叙述段落如果用某一特定区域的方言来译,会显得生硬刻意,不如口语体来得平实自然;而如果用标准语来处理,那效果更将大打折扣,风格也将与原文相去甚远,甚至会让读者觉得难以接受。
二、以“形”补形 语随其人
方言土语能映衬人物的个性特征,身份地位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是一种立竿见影的艺术手段。因此,作者往往会花费很大功夫去模仿人物现实生活中的说话口吻和方式,使每一个人的语言都富有自己的典型特色。这对译者来说是一项挑战。奈达曾提出“译文在译语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应等同于原文在原文读者中产生的效果”。虽然完全的等同是无法实现的,但是译者至少能够尽可能增大这种等同的程度。
张谷若先生在这一方面开创性地融合山东方言和北京市井土语翻译了托马斯哈代的著名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威塞克斯乡村方言,即采用了方言对译法,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意义和形式上的双重对等。郭著章认为张先生的译法“不失为传译原文中乡土气息的成功做法”。(郭著章,1994:746)下面我们来看其中的片段:
原文:“Had it anything to do with father’s making such a moment of himself in thick carriage this afternoon?Why did’er!I felt inclined to sink into the ground with shame!”(Tess P. 58)
译文:“今儿过晌儿,俺看见俺爹坐在马车里,出那样的洋相,他那是怎么啦?是不是叫这档子事折腾的?那阵儿把俺臊的,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进去!”(张译,35)
苔丝是一个生活在英格兰西南部偏僻落后农村,远离繁华都市的女孩,译文以北方方言为桥梁展现了其特定的身份背景以及身上浓厚的乡土气息,地域属性模糊,社会标志清晰。这是因为北方方言使用范围广,已被绝大多数人接受,对于非北方的读者也不会构成理解上的困难。例如,在苔丝的这段话当中,译文采用的是北方方言的人称代词“俺”,许多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都使用“俺”来显示方言与标准语的区别。类似的还有“爹”这一称谓。另外,像是“今儿”、“过晌儿”、“这档子事”、“折腾”等,均是北方方言中十分常见的口语,特别是最后一句“那阵儿把俺臊的,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进去!”这是苔丝当下尴尬心情的自然流露,与原文的风格十分贴近,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这样一个乡村女孩的形象特征,真正做到了“语随其人”。而如果放弃方言对译法,而改用口语体译法来诠释这段对话,那么人物的神情口气便不会那么逼真,她的社会标志也不会那么明显,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不如前者那样深刻。这便是方言的优势所在。
三、“意”“形”结合 如影随形
翻译是创作的艺术。在达意的基础之上,找到最佳的措辞来对应。郑振铎指出,“译书自以能存真为第一要义……最好一面极力求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林语堂也说过,“译者不但要求达意,并且要以传神为目的,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之字神句气与言外之意”。可见,翻译不仅要神似,还要形似。就犹如临画一般,神形兼备的才是一幅好画,意形结合的才是一篇好译文。在翻译文学方言的过程中,如果能将方言对译法和口语体译法灵活运用,融会变通,效果会比单独使用其中一种贯穿到底要来得好。请看傅东华先生对于美国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米歇尔的成名作《飘》的处理:
原文:She could not endure the suspense another moment.
译文:这个闷葫芦她再也熬忍不下去了。
原文:They(the Tarleton brothers)…mettlesome and dangerous but,sweet-tempered to those who know how to handle them.
译文:他哥儿俩……不但顽皮而且恶作剧,可是谁要摸着他们的顺毛,他们却又脾气好得很。
原文:Although born to the ease of plantation life,waited on hand and foot since infancy,the faces of the three on the porch were neither slack nor soft.
译文:这两位哥儿和一位小姐,都生长在殷富舒适的大户人家,打出娘胎就有人从头到脚地服侍着,可是他们的面孔都不像娇生惯养。
从这几段译文不难看出,译者根据实际情况,对具体的语段采用了不同的译法。有像前两段译文中用方言对译法译出“闷葫芦”、“摸着顺毛”的传神,也有如最后一段采用口语体一译到底的做法,将读者带入原著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使得整篇译作读来有一种能屈能伸,摇曳多姿的感觉。
无论是方言对译法还是口语体译法,在使用时都应该有个度,也就是读者的接受限度和理解程度,以此为翻译标准,过犹不及。较理想的做法就是将不同的译法结合,为我所用,既得“意”,也不忘“形”,让译文与原文有一样的味道和意境,达到翻译的目的要求,传达原作神韵,传播异域文化,译出更符合中国读者的译文。
[1]Nida,Eugen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3.112.
[2]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郭著章.语域与翻译[A].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739-750.
[4]韩子满.试论方言对译的局限性——以张谷若先生译《德伯家的苔丝》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
[5]笪玉霞.《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原作与译作语言特色的比较[J].济南大学学报,2002.
[6]谷婷婷.语言变体与翻译——由《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看语言变体的汉译[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7]徐泉,王婷.析傅东华译《飘》中的归化翻译[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