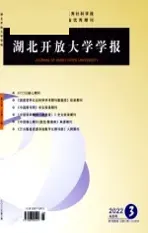从词体发展看况周颐的词体意识
2011-08-15朱兴艳
朱兴艳
(河源广播电视大学,广东 河源 517000)
从词体发展看况周颐的词体意识
朱兴艳
(河源广播电视大学,广东 河源 517000)
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况周颐在其的词学论著《蕙风词话》中阐述了自己的词体意识,充分体现了况周颐的对常州词派词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从词体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况周颐的词体意识。
况周颐;《蕙风词话》;词体意识
词这种文体历来是不被重视的,在唐五代宋初,它的作用只是“用助娇娆之态”,“聊佐清欢”“娱宾遣兴”。唐五代时,文人词开始逐渐流为“侧艳之词”,其地位与诗文不可同日而语。北宋钱惟演甚至说:“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所谓“诗庄词媚”。作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深受“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的长期薰染,被赋予了较强的社会性和写实性,侧重于表现作者的生活理想、政治态度、人格精神等方面内容,呈显出一种庄重而严肃的品格,即“诗言志”。随着燕乐的发展而兴起的词,在表现功能上与诗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它侧重于描写属于个人私情方面的内容,男女间的情爱为其最主要的表现对象。词体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已更多地融入了词人的主体精神,题材上的咏物、写景之作有了长足发展,但仍以抒写恋爱艳情为主。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词的性质、作用都起了不小的变化。苏轼以诗为词,客观上提高了词的地位,后人认为:“词体之尊,自东坡始。”[1]苏轼认为词是诗的发展,他在《祭张子野文》中赞扬张先词:“微词婉转,盖诗之裔。”他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李清照从词的体性入手,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二者提高了词这种诗歌体裁的地位。前者否定“小道”之说,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词体的文体特殊性。苏轼与李清照的尊体说,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划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不断在后世得到回应。不仅南宋的辛派词人和格律派词人大致沿此道路,即便是清代词学复兴,也是在这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上展开的。[2]
自元代中期至明代末年,词的创作更加衰敝。“论词至明代,可谓中衰时期。”[3]词学亦是中衰时期,词话数量大大减少,词学研究无大的进展,明代的词学论著在理论方面较为浅薄,考证亦多舛误。词仍然摆脱不了被视为“小道”、“小技”,如明代王世贞所言:“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4]明代俞彦《爰园词话》云:“词于不朽之业,最为小乘。”陈子龙《幽兰草·题辞》云:“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惭宋辙。”
清人对词体的态度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一方面是鄙视词体,如纪昀,其《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小序云:“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倚语相高耳”,又云“惟歌词体卑而艺贱”,清代朱彝尊《红盐词序》云:“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周济《味隽斋词自序》云:“词之为技,小矣。”沈曾植《彊村校词图序》云:“宋人以词为小道,名之曰诗余。”但清人对词之创作亦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焦循《雕孤楼词话》云:“谈者多谓词不可学,以其妨诗、古文,尤非说经尚古者所宜。余谓非也。人察阴阳之气以生,性情中所寓之柔气,有时感发,每不可遏。有词曲一途分泄之,则使清纯之气,长流行于诗、古文。且经学须深思默会,或至抑塞沉困,机不可转。诗词是以移其情而豁其趣,则有益于经学者正不浅。古人一室潜修,不废啸歌,其旨深微,非得阴阳之理,未足与知也。朱晦翁、真西山俱不废词,词何不可学之有。”从人的心理需求、创作心理上立论,分析情与理的互动关系,认为词作并不妨碍经史,反而有益,对学词妨碍经史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李佳也以陈澄为例,批评了鄙视词赋的儒士:“以经学称,诗词亦超隽。……视彼一孔半瓶,沾沽自命为儒士,转鄙词赋为雕虫而不屑观之,能勿汗颜。”[5]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在《今词选序》中很明确地说:“词非小道”。在《词选序》中又进一步提出:“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乎。”陈维崧不但把词和历来备受尊崇的儒家经典著作和史书相提并论,而且认为词就是经,就是史。沈曾植则认为词在文体价值上并无高下雅俗之分,是诗歌的有益互补,“词家之业,与诗家方轨并驰,而诗之所不能达者,或转借词以达之”[6],清人对于词体的宽容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词创作的繁荣。
清人复兴词学,提高了词这一文体的地位。清代词人和词论家从儒家正统思想出发,认识词的政治伦理教化作用,肯定词合乎儒家诗教,应当和诗一样受到尊重。浙西词派的汪森、王叔和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周济等人都极力推尊词体,为清词的复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到嘉庆、道光时期,常州词派兴起,张惠言、周济等常州派词人以力挽颓衰词风为己任,打破对词体的传统偏见,提高词的文学地位,此即所谓“推尊词体”。其创始人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说: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不徒雕琢受辞而已。”[7]由于张惠言是吴派汉学新秀,是治《易》的著名学者,因而其“推尊词体”的词学观念具有浓厚的儒家诗教色彩和鲜明的重古倾向。张惠言以词通于诗的“比兴变风之义”,即诗词同源,来作为自己立论的起点,他强调词是有“意”的,是和《诗经》、《楚辞》一样用比兴寄托的手法来表达“意”的。同时,该序还指出:“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几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他在此明确提出应将词“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即认为词与诗赋一样,同跻于儒家传统所认可的传统文学行列。其目的也是尊崇词体。推尊词体,也是周济论词的基本出发点,如其《宋四家词筏序》云:“文虽小,吾能尊其体,慎重而后出之,驰骋而变化之,前无古人不难矣!” 他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提出著名的“词史”说,这是对张惠言推尊词体理论的发展。
晚清的况周颐在前人,特别是常州派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尊词体。他在《蕙风词话》卷一第一条中,便开宗明义地说:“词之为道,智者之事。酌剂乎阴阳,陶写乎性情。自有元音,上通雅乐。别黑白而定一宗,亘古今而不敝矣。唐宋以还,大雅鸿达,笃好而专精之,谓之词学。独造之诣,非有所附丽,若为骈枝也。曲士以诗余名词,岂通论哉?”在他看来,词的作用并非“助娇娆之态”,也不是“聊佐清欢”、“娱宾遣兴”,而是酌剂阴阳、陶写性情。前人大多从儒家诗教出发,以诗词同源立论,以达到诗与词同样值得重视的效果,但往往难脱“诗余”之见。谭献甚至说:“词为诗之余,非徒诗之余,而乐府之余也。”[8]况周颐则不然:“诗馀之‘馀’,作‘赢馀’之‘馀’解。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往往声希节促,则加入和声。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遂成为词。词之情文节奏,井皆有馀于诗,故曰‘诗馀’。世俗之说,若以词为诗之胜义,则误解此‘馀’,字矣。”(《蕙风词话》卷一)从而把词的作用、地位提得很高。
况周颐论述词的文学地位,提出词“自有元音,上通雅乐”,以说明词的本体内涵,高度肯定词的文学地位和社会价值。如“填词家自度曲,率意为长短句而后协之以律,此前一法也;前人本有此调,后人按腔填词,此后一法也;沿流溯源,与休文之说相应。歌曲之作,若枝叶始敷;乃至于词,则芳华益茂。”在此,他为填词的两种方式,即或“率意为长短句而后协之以律”,或“前人本有词调,后人按腔填词”(《蕙风词话》卷一),找到根据。这发展了张惠言《词选序》中提出应将词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同跻于儒家传统所认可的正统文学行列。
虽然,况周颐尊崇词体,但他并没有把词和诗完全等同起来,他在《蕙风词话》卷二中说:“《吹剑录》云:‘古今诗人间出,极有佳句。无人收拾,尽成遗珠。陈秋塘诗 ‘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按此二句乃稼轩鹧鸪天歇拍。稼轩倚声大家,行辈在秋塘稍前,何至取材秋塘诗句。秋塘平昔以才气自豪,亦岂肯沿袭近人所作。或者俞文蔚氏误记辛词为陈诗耶?此二句入词则佳,入诗便稍觉未合。词与诗体格不同处,其消息即此可参。”在《蕙风词话》卷三中又说:“赵愚轩《行香子》云:‘绿阴何处,旋旋移床。’昔人诗句:‘月移花影上阑干’,此言移床就绿阴,意趣尤生动可喜。即此是词与诗不同处,可悟用笔之法。”他认为词自有其特点,它与诗的体格有不同之处,因此,与诗的用笔也不一样。
在况周颐看来,词“与诗判为两途矣”(《蕙风词话续编》卷二),“词曲之为体,诚迥乎不同”(《蕙风词话》卷三)。然而“词之所以别于诗者,不仅在外形之句调韵律,而尤在内质之情味意境”[9]况氏用心之处在词的内质之情味意境。他继承了中国传统词论从词的音律、辞章两方面相结合的角度论词的传统。他说:“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余于诗,故曰诗余”。词亦文之一体,况氏借“情文”,指词的文学性。词源于曲子词,所以保留有音乐的节奏;词也是语言的艺术,所以含有语言的节奏。况氏借“节奏”表示词的音乐性。“情文”、“节奏”是构成诗、词等艺术的组成部分。但与诗相比,况氏认为词的“情文节奏”比诗“赢余”。词之为体,宜于表现幽深细腻之情,有宛曲缠绵的节奏之美。
词的创作由于体性等方面的原因,易出现艳冶淫靡、空疏尘俗的弊端。况周颐认为可用加强学养的方式予以矫正,“昔贤朴厚之作醇至之作,由性情学养中出,何至蹈直率之失”。他强调词人的学问与修养,“平昔求词词外,于性情得所养,于书卷观其通”[10]况周颐认为,深厚的理论修养不会凭空而来,它需要根植于深邃博大的学养之中。况周颐本身就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与创新意识,对词史有宏观把握与透辟理解。他对词之流弊的得鲜活的见解,并以一己的创作实践印证理论,如其重拙大、境界说等的提出,实质上,也是推尊词体的一个方面。而这种注重学力的倾向,与清代重朴学,提倡通经致用,反对空疏的学风以及其他文体对学问的强调是一致的。
况周颐对词体的推尊,还表现在对词人地位的突出和强调,如“词之为道,智者之事”,“夫词者,君子为己之学也”(《蕙风词话续编》卷一)等。他改变了“词为小道末技,诗人(君子、智者)不为”的看法,由抬高词人的地位来抬高词体。在况周颐看来,词人和诗人一样,是“智者”、是“君子”同样有着高尚的人格形象的解读,而他所提出的诸如“襟抱”、“性情”等才是对词人内在修养的规定。如他说:“填词第一要襟抱。”(《蕙风词话》卷二)在况周颐看来,作者的胸襟和修养对填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填词也和作诗一样,实现和完善自身的人格力量。况周颐便说:“斯旨可以语大,所谓尽其在我而已。”(《蕙风词话》卷一)这实际上是对儒家思想的直接反映(《论语•颜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况周颐又说:“襟抱与性情,非外铄我,我固有之”(《蕙风词话》卷一),这几乎是《孟子•告子》“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也。”的转述,由此可见,况周颐他在为人原则的理解上,在涵养词人的“襟抱与性情”的看法上,继承了儒家传统,认为词人仍然要以儒家的圣人、君子为榜样,继承其中的入世情怀,完成“兼济天下”的使命。如他曾说南宋词人王沂孙与吴庄敏“二公襟抱政复相同”(《蕙风词话》卷二),前者是“平生志不在温饱”,后者是“断是平生不肯寒”,两人皆借助“梅”的意象来展现自己所具有的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胸襟。况周颐认为:“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他自己也积极创作,用创作来实践自己的理论主张。
况周颐继承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理论主张,但其立论又与张、周不同。他对传统“诗馀”说正本清源,赋予其以“赢馀”的新内涵——“情文节奏皆有徐于诗”,即充分肯定词摹写精神世界和表达心境意趣之所长,驳斥鄙视词体的世俗偏见,给予根深蒂固的“诗馀”观念以彻底否定,使词体地位得以提高。况周颐推尊词体,对于词这一文体充实了新的内容,坚持了词不同于诗,不同于政治教化的独立品格,具有着艺术审美的价值与意义,为词的复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陈询. 海绡说词[J]. 词话丛编(第五册).
[2] 张宏生. 推尊词体与开视门径——周济〈宋四家词选〉札记》,《第二届国际宋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C].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3] 吴梅. 词学通论[M]. 商务印书馆,1933.
[4][5][7][8][10] 唐圭璋. 词话丛编[M]. 中华书局,1986.
[6] 沈曾植. 彊村校词图序[A]. 朱祖谋. 彊村丛书[C].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 缪越. 诗词散论[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I206
A
1008-7427(2011)02-0074-02
2010-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