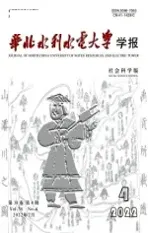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民参与
2011-08-15张红梅
张红梅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0)
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民参与
张红梅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0)
公民参与乃是形塑健全公民社会的根本力量。网络个人表达是个人利用互联网向外界进行的关于自身思想、感情或生存状态等个人信息的传播行为,它是一种社会参与。我们应当关注生长中的公民社会遭遇的这一新元素,研究促使网络个人表达助推公民参与的评判标准以及公共权力控制网络个人表达的价值取向及其限度。
网络;个人表达;公民参与
正如学者胡泳所说:“一些重要的东西被忽视了,就像大象在卧室活动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人们根本无视它的存在;或者,对一些重要的东西人们得不出完整的看法,有如‘盲人摸象’的寓言所显示的那样。”就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民参与而言,发现这只大象,正是文章所意图站立的位置。
一、网络:公民社会的新元素
按照现代学者的看法,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国家不是由每个个体组成,而是由无数家庭组成的。进入近代社会,随着“救亡压倒启蒙”,在用政治革命解决所有问题的认识与实践逻辑演进过程中,急风暴雨的暴力斗争消灭了士绅主导的民间社会,使社会生活的一切都统制在全能国家之下。国家权力成为组织社会的唯一形式,从此,由城市的单位到乡村的公社,包揽了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社会日益萎缩,终至为国家权力所吞噬,也即哈贝马斯所说的第三领域大幅度的国家化。“由于中间领域的消失,每一个个体都不得不直接面对国家,在国家面前,没有任何个人的可言。”[1]
物极必反。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不断加深的市场化进程而来的还有去“政治化”的政治时代,国家化中止,中国社会重新开始了胡适所说的“三百年来社会化的倾向”(指近代以来民间社会的发展)。国家权力不再垄断所有领域,农民脱离了人民公社的束缚,职工与单位的关系减弱,而新的民间社会却尚未建立起来(比如,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以取代一去不返的家族、乡族纽带。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又恰逢世界信息化和知识化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挑战。在未来,中国社会现代化需要完成两次社会转型。
具体而言,第一次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活产生更多的相互依赖关系。例如工业已愈益专门化,以致一个工厂的产品或一个工人的劳动如果不与别的产品或劳动结合是无用的。一个人愈来愈依靠其他人,但从各个人来看,一个人就像另一个人一样。这种分化和相互交换性的结合是以往从未见过的,各类循环也日益增多。“这将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人们是专门化的但却可以是互变的;一个游牧人的社会,既是紧密的又是有距离的,既是同质的又是多样化的,既是有组织的又是自律的。在某种程度上将回到以往的但却是不同的社会。”[3](p334)
第二次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城市社会向城乡动态平衡社会的转型。与此相适应,全国人民的空间结构(人口分布结构)、生活方式、劳动结构(就业和职业结构),都将发生重大转变。回顾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史,在第一个十年的发展中,中国跟随着世界最先进的网络技术脚步,如今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互联网用户群与无线互联网用户数量。伴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是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极大改变,这一改变已经渗入到政治领域并引起政治环境的革命性变革。公与私的含义和边界都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游移。网络已经和人类行为密不可分,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已经成为民意的重要窗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网络行为主体不仅利用网络传递信息,也同时利用网络表达其态度、价值观、意识行为和对行为的偏好,其也成为组织社会行动的工具和表达,因此网络与开会、征求群众意见一样,无疑是个人表达和公益诉求的重要途径,是社会群体参与的公共空间,成为各种力量对话和博弈的主要场所。
二、从个人表达到公民参与
网络是一个开放的、也是相对自由的舆论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交流的匿名性似乎是其与生俱来的特性。曾几何时,彼得·斯坦纳绘制的一幅漫画在网民中几乎无人不晓,这幅1993年登于《纽约客》杂志的漫画所取的那个诙谐的标题“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3],被网民们当作不言自明之公理加以信奉[5]。相较于现实,网络的这种更彻底的匿名性,使得个体可以更真实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互联网一个最大的特点和优势。相较于传统媒体,网络在表达民意方面更具便利性和交互性。美国前大法官卡多佐曾说过,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通过研究网络民意表达并分析网络民意的内容指向可以发现,网络民意“传播权利”的实质,就是现代社会赋予公民的各种权利在网络环境下的实现,互联网使“传播权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得到真正的普及”[4]。因个人网络表达所引发的网络传播,进而导致的公民参与,对推动当代中国政治、法制、民主的进步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价值。比如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正是由于网络的传播与网民的参与讨论使得舆论迅速扩大,为最终的收容遣送制度的改革发挥了积极影响。
网络在极大地促进了公民参与的同时,也向人类提出了诸多的挑战。网络的低门槛和低成本使广泛的参与和使用媒体成为可能,“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数字化生存以虚拟的方式突破了现实生存的局限和制约,极大地张扬了人类的表现空间,激活了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并为人类社会普遍尊崇的人文操守向数字化的虚拟世界延伸及发展提供了基础与可能。网络本身的技术特点使其迅速与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消费主义融合。但是,在倡导和传播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同时,网络媒介也完成了自身的消费主义文化变异——网络成为欲望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媒介和手段。“充斥着许多非人性、非人道的思想意识的数字化生存,它的负面效应也引发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并带来一定的精神文化危机,从而导致人的生命意识的颓萎。”[5]正如阿伦特所攻击的两个目标:消费主义和极权主义。看上去虽然有所不同,却都在抹杀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前者是公共领域吞噬了私人领域,后者则相反。结果都是对正方兴未艾的网络公共领域毁灭性破坏。因此我们既要肯定互联网对于当下“生长中的公民社会”的价值,又要警惕对于网络的过分溢美。
不言自明,公民参与乃是形塑健全公民社会的根本力量。然而,公民社会是存在着差异或者差别的多元社会。因为历史、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群众划分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谁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再具有以前均质统一的性质,谁都想表达自己的利益。因此多元社会首要关注个体的自治,但共同体的正义又须臾不能离开集体行动,因为一定要在一起共同行动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或决定未来重大的问题。“理性分歧的永恒存在和要一起行动的信念这两个因素构成了政治环境。”[6]永恒分歧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人类朝着更安全、更文明、更正义的社会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分歧的背景下进行的。著名哲学家罗尔斯以其敏锐的目光洞察到现代社会由于个人自由和公共自由、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及失衡所造成的种种政治合法性危机,通过其前期无知之幕之后所隐含的公民设计以及后期明确表达的公共理性的公民资格观念,表达了以公共的正义规范制衡私利,调节自由市场的自发后果,抑制市民社会个人私利泛滥、促进积极自由和公共利益“在个人和国家、个人和社会之间保持一种适度平衡”[7],从而保持多元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正义性的建构离不开个人表达汇聚而成的民意基础,而民意具有多重价值尺度。但它首先是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出现的,其首要价值应该体现在社会的政治生活追求中,其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基于对“群体的善”的追求,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正义”。[8]网络使得人们表达的空间越来越大,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这是一种社会参与。但是如果这种参与只强调个人的权利却并没有带动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以及对公众社会的负责,那么就不会形成社会文明程度和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标识的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和政府公共政策过程不可或缺的部分。“公民参与不仅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赋予公民表达自己利益的机会,保证公民获得影响其自身生活质量的权利,而且它更维系了公民与政府之间持续沟通与信任的关系,保持了政府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9]公民参与形成“善治”。
因此,从民主的意义即众人之事众人定的视角来看,个人表达对于公民参与有不可或缺的方法论意义;从自由视角来看,个人表达涉及到主体难能可贵的思想自由,“但真理的相对性及其方法的多元性与法律之下自由的理念又必然决定个人表达的限度”[10]。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较多地倾向于自我主义,它涉及的问题是让每一个人诉说(包括倾听他人后的诉说)各自对正义、善或邪恶的思考或意见,但共同体正义要求的公民参与须以个人表达的相对自律性为前提,它要求追问个人表达在道德上的是非对错,它要求认真对待权利,尊重他人意见,理性的表达意见而不是个体的私欲,唯有此才能确保个体的生命品质。
三、珍视和认真对待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
美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认为:“政府应当给予其治下的所有公民以平等的关切。”[11]无表达便无参与,无参与便无民主。多元化的社会一定要有多元化的表达。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矛盾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容纳冲突并能够用制度化方式解决冲突的社会,也是一个通过解决冲突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加快以及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个人表达和民意日渐成为媒体和政府关注的中心。给个人表达更为广阔的表达空间,对个人表达汇聚而成的民意做出积极的回应,创建政府与民意表达交流的绿色通道,形成真正有效的公民参与,是政府公共决策的必然选择。当冲突压过融合,偏激对真理追求的意义必将大为削弱。虽然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是一个自由的状态,但并不是一个随便的状态。个人叙事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不存在孤立的个人表达。在一种对实际过程的控制转变为一种比较“虚的”原则性控制以及控制手段的规范化,使任意性逐步走向规范,不再趋向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极端化的前提下,公共权力应对网络个人表达进行规制。或者说,对这种最具参与性的传播媒介的限制,应该明显低于对传统媒体的限制。唯有如此,网络上的嘈嘈小音才能化为稀声大音,借助网络的个人表达才能助益公民参与,网络民主才能走向社会民主!
[1]景凯旋.对家族的想像[J].随笔,2009,(6).
[2]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胡泳.人人都知道你是一条狗[J].读书,2006,(6).
[4]张淑华.网络民意表达的实质[J].青年记者,2008,(2).
[5]黄健,王东莉.数字化生存与人文操守[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0).
[6]徐斌.公民尊严:立法vs.司法[J].读书,2009,(11).
[7]宋建丽.公共理性的公民资格与多元社会的正义秩序[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9]孙柏瑛.公民参与形式的类型及其适用性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5).
[10]张昌辉,何荣华.偏激表达与思想自由[J].温州大学学报,2006,(4).
[11]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和众声喧哗与公共讨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Individual Voice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on the Cyber world
ZHANG Hong-me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Citizen particip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forces to shape and strengthen civil society.Individual voice on the cyber world is kind of action to transmit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individual's thought,emotion and survival condition to the outside world through the internet,which is sort of social participation.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new growing factor which civil society is faced with about the people's livelihood.The research will promote individual's voice to help standardize the judgement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value and its limit of citizen rights to control individual's vo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twork.
Cyber world,Individual voice,Citizen participation
D035
A
1008—4444(2011)02—0044—03
2010-12-25
张红梅(1976—),女,河南郸城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董红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