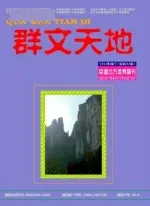西方当代翻译思想和流派述略
2011-08-15刘红
■刘红
西方当代翻译思想和流派述略
■刘红
二十世纪最后25至30年,西方译论有了显著的发展。它虽然没有完全突破固有的理论阵地,但确实从五个大的维度——结构与意义、意义与交流、意义与文化、意义与认知、翻译与社会政治——“热热闹闹”地拓展了翻译思想,深化了理论认知。具体来说,就是在对待意义、结构、形式、功能等四个基本层面的问题上有了更符合翻译实际和时代诉求的翻译基本原则和基本的理论主张。西方当代的翻译理论按其基本的理论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流派和一些值得注意的发展或动向:语言学派(Linguistics-based approach)、功能学派(Function-based approach)、释义学派(Hermeneutic approach)、文化翻译学派(Culture-based approach)、后现代主义(此处主要指文论)与翻译理论、心理-认知心理学派(Translation and cognitive sciences)、新直译论(Neoliteralism)。
一、语言学派(Linguistics-based approach)
西方语言学派的前身叫做“修辞—语法学派”,它的基本主张是Sense-for-Sense(意义对意义),反对Word-for-Word(词对词),这个古老的主张传承自西塞罗和昆体良,经过文艺复兴,直到二十世纪初索绪尔的语言学说问世和布拉格学派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开拓性研究。其时的翻译思想则集中于直译以及如何保持古风(archaism)问题,译论完全是学究式的论述(R.Copeland,1991)。
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思想随近百年来语言学的发展演进而发展变化。十九世纪下半期以前的欧洲语言学即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主要关注罗曼语与拉丁语之间的语音变化,尤其是西班牙语、法语与意大利语之间的语音发展渊源。二十世纪初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问世(1916),随后的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韩礼德(M.A.K.Halliday,1925-)的功能语法学说、美国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都是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派重要的理论思想源头,尤其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说。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语言学派翻译理论衍生出了语段语言学派。语段语言学派关注的中心是“text”,他们的基本对策是re-textualising(语段重组),就是说,他们对结构的关注焦点已经从“词”推进到了“语段”,将语言陈述单位由“句子”推进到了“超句子”。传统语言学派译论的代表是 Catford(1965);Nida(1964);Koller(1979);Newmark(1989)等人。语段语言学译论的代表有Neubert (1983,1992,1993);Hatim and Mason(1990,1997);Gopferich(1995);Stolze(1999)等人。
二、功能学派(Function-based approach)
功能学派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语言交流(或传播communication)和使用(use,运用、应用),而交流与使用的目的和效果息息相关;语言学中的功能观则集中于语用学(pragmatics),焦点有三:目的、效果与运用。因此功能学派的哲学理据和源头,始自后期的维根斯坦哲学以及哲学上的实用主义以及皮尔士的pragmaticism。语言学中功能主义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也是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之“源”。西方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 Vermeer(1978,1989,1996),Reiss(1984,1991),Nord(1991,1993,1997,1988),Neubert(1992,1993),HonigandKussmaul(1982,1995,1997),Holz-Manttari (1984,1993),Rhodes(2000),Munday(2001)等人;其中有些学者也被称为“翻译行为学派”(translatorial actionist)。
三、释义学派(Hermeneutic approach)
释义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摒除误解、对意义进行解释并达致理解,其基本的理论思想是理解是释义的中心任务,也是翻译的核心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释义学派认为“翻译就是理解”;理解必须依仗语言,而语言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理解不应与任何一个组成语言整体的部分脱节,“释义思考”的“整体性是理解的保证”;除语言的整体性外,理解的整体性还包括: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认识与应用的统一、理解的当下性与历史性的统一等等;在整体性的前提下,释义学派提出的翻译“基本策略”,可以表述为“信任”、“侵占”、“吸纳”和“补偿”;释义学派认同译作对原作的超越,因此译者应该是一个进取的、积极的、被赋予了应对能力的个体。释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 H.Meschonnic(1973);Steiner(1975);Berman(1984);Sperb 和 Wilson(1988)等人。
四、文化翻译学派(Culture-based approach)
目前西方并没有形成着眼于全方位文化的、有系统的文化翻译理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西方当代翻译理论整个来说还比较“浅”,不足以解决深层的问题。实际上所谓“文化翻译学派”目前并未形成,眼下译论关注的大都集中于文学翻译中的文化意义诠释问题,因此只能说是文化翻译的文学“剖面”或“维度”。西方当代文化翻译思想的基本特征是翻译运作向译语文化“极度倾斜”、向“市井趣味”及商业价值极度倾斜。由此而造成“翻译行为”及品类的“本体性分化”,“折射”难免变形,一部文学作品的“折射性改写”将难以被视为翻译。“文化不可译”只是说出了文化独特性的一面,文化还有很重要的另一面;人的文化经验的普遍性、广泛的同一性和“可描述性”以及语言极强的功能补偿性、读者接受的可塑性,等等——因此,必然还有可译的一面。本杰明的这个观点也不能不看到。
五、后现代主义(此处主要指文论)与翻译理论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思潮,具有明显的反思、反叛、反逆倾向,针对的是二十世纪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文化以及西方传统。既然是“反思”,就必然具有批判性甚至叛逆性,也必然会有是有非、有正有误。这些是非正误必然影响到当代译论,因此,对我们来说应冷静、客观地对之加以审视。“后现代文论”指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批评理论,一般具有强烈的叛逆特征。当代西方译论中具有这一倾向者不乏其人,但主要有两派:一是解构派;二是所谓“翻译与政治派”。也有人将他们合称为“新功能主义”。“解构论”的观点十分芜杂,其代表人物正是思想芜杂的J.德里达。“翻译与政治”流派的基本思想是:翻译必不可免地与社会群体的政治倾向与诉求挂钩,原语与译语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超政治的,“译出”与“译入”从来就是“权利(霸权)”与“反权利(霸权)”(或者相反)的表现形式。
六、心理-认知心理学派(Translation and cognitive sciences)
西方当代译论认知心理学派是二十世纪80年代西方认知科学发展的产物。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学派。它的基本理论思想是:翻译过程是一个认知心理过程;对传统心理学论者波因克尔于1913年提出的程式论四段式进行甄别性论证,波氏四段式是 preparation(准备);incubation(孵化);illumination(领悟);evaluation(评估)(Ulmann,1968;Landau,1969;Taylor,1975;Preiser,1976);翻译不仅是创造性行为,而且是再创造行为;引进心理学家吉尔福德氏的divergent production(趋异生成)论,来论证文本分析的多样性和创造性翻译的心理机制,目的在于说明这一流派的主要观点之一:译语文本样式的产生与其说取决于原语文本,勿宁说取决于译者认知心理分析机制的运作,因为原语文本只不过是一个符号集,关键在译者如何分析、解析这个符号集,而这一心理机制的运作,人各有异,译文文本因而呈现多种多样。
七、新直译论(Neoliteralism)
“新直译论”是美国当代译论家罗斯(M.G.Rose)于1993年提出来的一种对欧美翻译发展趋势的评估。他认为70年代前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所倡导的直译论正在趋向于形成一种新直译论,即在直译原则下关注品位或公认的修辞准则。罗斯认为,新直译论认同文努蒂(L.Venuti)提出的“看得见译者”的翻译,它的对立面则是“看不见译者”。新直译论一直是当代西方翻译的一种倾向或思潮,并没有形成什么稳定的有群体意识的“流派”,但他们讨论的“外域化VS本土化”、“异化VS归化”以及所谓“流利论”等等问题却常常触及西方译论的“核心价值”,因而往往壁垒分明。
综上所述,可以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思想归纳为以下要点:第一,当代西方的翻译思想主流是:侧重交流目的、交流形式、交流效果;侧重译者的功能发挥,抑制原作的意蕴;侧重译文倾向并抑制原作反映的外域文化,要让外域文化和价值观适应本国文化。第二,西方翻译理论的一个核心价值观:翻译是为目的语文化服务,而且只为目的语文化(通常则是英美文化)(Anglo-Ameriean culture,Venuti,1995)服务,可以说,西方当代译论的几个主要流派,充分反映了西方的功利观,不少英美理论(或论断、主张)更显示了英美文化的话语霸权。总之,当代西方翻译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西方(尤其是英美文化)的功利考量。第三,西方译论对待传统的态度可以给我们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启示:不应该墨守传统,应该让传统“reshape”;出自叛逆的传统改造未必是一种科学的归宿。我们也可以看到翻译思想实际上是翻译流派对某种理论理念的基本共识,而所谓“理论理念”则无不源于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的长期的、执著的体验、体认和领悟,源于他们对自身和同业者的经验观察和审视,因此这里的经验既包括直接经验也包括间接经验。翻译思想是无数同业者对实践的体验、体认和体悟的结晶;而流派则是同业者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某一翻译思想的认同为纽带而形成某种“神聚形散”的专业阵线或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松散的群体。有翻译思想不一定能形成流派,有流派的存在则必然有某种该流派赖以维系其“神聚”的翻译思想。此外,世纪之交总是新论踵出、思潮涌现。今天,由于与翻译有关的种种学科的发展,翻译思想已愈趋复杂,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可以“浓缩”为一、两句箴言。当代各流派翻译思想往往涵盖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而且同一流派中的成员的翻译思想也不尽统一。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切忌简单化,一定要掌握针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学会尽可能全面、深刻地看问题。
[1]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5.
刘 红(1981.12-),女,汉族,湖北天门人,武汉东湖学院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