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 妹
2011-07-18黄冰↓
黄 冰↓
小姑娘和金娃娃是两姊妹。我们都管她们的爸爸叫彭伯伯,却从没想过小姑娘和金娃娃叫彭什么,好像她们的名字就叫小姑娘和金娃娃似的,虽说有点怪,倒也不难听,起码比我的名字好听。不知道母亲为什么给我取名黄红兵,院里的伙伴都叫我红兵,省了个黄字也没变得好听。
小姑娘比我们大几岁,所以从来不屑跟我们玩。金娃娃却是我们玩伴中的一员。
小姑娘长得瘦筋筋的,眼睛便出奇的大,跟我们玩的弹珠似的,又圆又黑,看人时有点凶巴巴的。她的上门牙往外凸,说话时两颗门牙总是轻轻咬住下嘴唇,把酒窝恰到好处地露出来,每次见了小姑娘两颗好看的门牙,我都感叹自己干吗长不出这样好看的牙来,还有那头自然卷曲得像我的玩具娃娃头发,似乎所有的好看都特别亲睐她。小姑娘在我的眼里是完美的,她就是不跟我们说话,不跟我们做游戏,表情严肃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也忍不住要好好打量她浑身上下的好看。她特别突出的表现是,任何东西在她身上都会显出不一样来,就说她肩上挎的那个洗得发白的军书包吧,一般学生都斜挎着背,她却偏偏把背带收得短短的,背在单肩上,既显成熟,又带了几分时髦;她身上那件普通得没什么款式的白色的确良衬衫,也随时都像刚换上的那样干净整洁,并被她穿出了一种轻盈和飘逸;金娃娃曾偷偷告诉过我们,她姐姐裤子上的两道精神线是睡觉时放在枕头下压出来的……
小姑娘的每次出现都会吸引我的目光,激发我的想象。我常常羡慕地看着小姑娘从跟前直挺挺地走过,直到看不见了,才回过头来继续手中的游戏。那时,我甚至把她视作我的理想和目标,心想自己长大了要像她那样好看该多好。我曾偷偷对着镜子,有意把自己的上门牙微微咬住下唇,试图使牙齿往外凸,以为这样就能像小姑娘那样好看了。母亲说,好好的你咬嘴唇干什么?我说牙齿应该这样才好看。母亲说,爆牙齿有什么好看的?
每一次,当我们站在彭伯伯家窗口叫金娃娃出来玩的时候,我总想趁机看看小姑娘在做什么。但他们家实在太暗了,我只好故意大声叫金娃娃,事实上是想把小姑娘引出来。但多数时候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是一连串干瘪的咳嗽声,是我们难得见到的金娃娃的爷爷。每次我们听见彭爷爷的咳嗽声都要猜猜他究竟有多老,我们一致认为,声音听上去肯定有一百多岁了。问金娃娃,她便学她爷爷弯腰驼背走路的模样,还把一只手放在后背,边走边捶,说,就这么老。
有时遇上小姑娘背着书包轻手轻脚地掩上门,从我们身边直挺挺地走过,也不告诉我们金娃娃在不在家,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好像我们是一群不惹眼的蚂蚁似的。
小姑娘不但不跟我们说话,连对我们笑笑都很吝啬。她倒也不是从不跟人笑,比如在大院里遇上大人时,她就会翘起嘴角,抿着嘴淡淡地笑笑,嘴唇嗫嚅几下,声音比蚊子还小,根本听不清她说些什么。我们都说,可能是小姑娘饭没有吃饱吧?

卢西安·弗罗依德作品-55
在小姑娘眼里,我们一定是脏兮兮的,成天只跟泥沙打交道,玩疯的时候,鼻涕都往袖口那儿抹,所以她对我们的态度才那么不屑吧。后来我们就给了小姑娘一个冷冰冰的外号,冷美人。看她走路的样子……我们跟在她背后,把背也挺得直直地,像贴住一块门板似地学她走路,并且嘻嘻哈哈地故意笑得很夸张,小姑娘一定是听到我们的笑声的,但她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只是步伐加快了,头上扎得趾高气扬的马尾辫也随着左右摇摆……虽然我们这样的表现是想打击小姑娘在我们面前的骄傲,但说实话,我心里却一直幻想小姑娘有一天能加入到我们里面来。
医院药房的窗口是我们每天必去的地方,我们挤在窗前,踮起双脚,伸长脖子,七嘴八舌地对着窗口喊,彭伯伯,有没有空纸盒。彭伯伯像早就准备好了的,放下手中的活,顺手便从窗口里扔出大大小小的空纸盒。我们闻着纸盒散发出熟悉的各种药味,开始盘算它的用途。大的厚纸盒可以坐进一个人,并且还能拖着走,相当于人力车,只是没轮子,得全靠人力,也不结实,但坐在里面的人却很舒服,直到纸盒磨破了底。
金娃娃每次都当车夫,一是因为她长得胖乎乎的,力大无比,另一方面也是没有谁能拖得动她。
金娃娃不仅人长得胖,胆子也最大,像是她可以依靠她的肥胖来状胆似的。医院澡堂子那儿最能考验一个人的胆量,因为澡堂子紧挨着的就是停尸间。停尸间与澡堂仅一墙之隔,我们要去澡堂必须先经过停尸间。每次去澡堂我们都紧紧挤在一起相互壮胆,有时候还故意大声说话唱歌,但谁都怕走在靠近停尸间那侧,总觉得走在那侧就会碰上鬼。走过那段路时我眼睛都不敢完全睁开,但又不敢完全闭上。所以每次都虚掩着双眼快快跟着伙伴走过。金娃娃每次都自告奋勇地走在靠近停尸间的那侧。有一次,她甚至在一个伙伴的怂恿下走到停尸间去数里面摆放的柜子有几层。
我们几乎所有的零食跟玩具都源于医院的药房和库房;药房里源源不断的甘草就曾被我们当作零食吃个不停,记得我在一个下午吃下数不清的甘草,以至长大后一想到甘草味就头晕想吐;但记忆中的酸梅却比现在街上卖的包装精美的话杨梅还好吃。有一些不能当零食吃的药就成了玩具;好看的相思豆,在我们眼里像珠宝那么宝贝和稀罕,因为不能随便拿,每次去中药房玩都趁大人不备,拿几粒放在兜里,回家装在一个小药瓶子里保存起来,平时也舍不得玩,晚上临睡觉时才拿出来欣赏一番。
药瓶子的瓶盖可以用来做秤盘,在瓶盖上钻三个眼,将线从孔眼穿过,再拿一根竹筷子当秤杆,刻上尺度,找一把小锁用线套上当秤砣,摘下大大小小的树叶,草坪上拔来一些草,分门别类摆在地上,一部分人扮小贩不停吆喝,另一部分人便模仿自己母亲的模样,扮讨价还价的家庭妇女。金娃娃每次都抢着扮小贩,她嗓门特别大,像是真的怕菜卖不出去似的,特别卖力,有时还会为那“几分钱”吵得面红耳赤。
等那些药瓶药盒玩腻了,我们就捏黄沙球,我最喜爱的游戏。我甚至从来没把它当作游戏,觉得更是一项严谨的工作。我的这种认真的态度曾被母亲挖苦说,我对玩有种全力以赴的热情,不知道以后上学会不会有这个劲头,因为每次只要父亲提出要教我学习拼音时我就开始犯困。但是母亲的话根本不起作用,我仍痴迷于各种游戏。
那时,医院的每个角落都能找到细黄沙。住院部楼前、中药房门口、加工房的四周……细黄沙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无处不在,家属区大院那儿就有个名字叫沙上坡,便是因为长期堆放黄沙而得名。
捏沙球的工序很复杂,先用一小块水泥做核,和上很少的水,用半干的黄沙再一层层裹起来,捏得越紧越好,然后用干黄沙打磨,直到磨得像个钢球般锃亮才算完成。一次,金娃娃神秘地说,要给我们看一样好东西。我们问了半天她不肯说,只说跟着她去。于是,她带我们一口气跑到医院洗衣房附近,那儿满墙的大字报,不过跟大院周围的大字报不同,这里的大字报全是写在彩色纸上的,红的绿的黄的蓝的……金娃娃冲到一排大字报跟前,双手在上面一阵乱抹,然后像投降的人那样举起双手让我们看。于是我们看到那些粉末一样的颜色沾满了她的两个掌心。这个发现让我们兴奋不已,从此,那些大字报便隔三差五被我们撕得支离破碎。而从此我们的黄沙球就变成了一个个好看的彩色球。
蓝的最好看。金娃娃说着小心地把黄沙球用纸包好,独自跑到离我们几米远的那棵桂花树下,挖出一个不大的坑,把黄沙球埋进去,然后跑回来对我说,这样下次出来时还能玩。我舍不得放在无人看管的院子里,我说我要拿回家。我紧紧地拿着手上红色的黄沙球。同时又怕母亲发现后会把它当垃圾扔掉,所以每次偷偷带回家都藏在饭桌下靠墙的地方,既不会被发现,也防止被踢坏。
这样的游戏一直要玩到彭妈妈下班回来,叫走金娃娃,金娃娃每次都很听话很顺从的样子。不撒娇也不撒野,这是她跟别的女孩不同的地方,也是我们喜欢跟她一起玩的缘故。
我们也无可奈何地“扁担开花各自回家”,百无聊赖地盼着吃饭。到了吃饭时间,我们又兴奋起来。那时候都住平房,每家每户紧挨着,家家房门都开得大大的,吃饭时间一到,各家饭菜的香味全都混淆在空气里,做好饭菜,大人小孩都用一个大碗盛满,带上小板凳,聚在沙上坡那儿吃。大人们边吃边聊天,小孩以玩为主,吃饭成了幌子。我端着饭菜对母亲说,我要到沙上坡去吃。母亲不让。吃饭就得规规矩矩地坐在家里吃,她说,又不是叫花子。我觉得我家的规矩比哪家都多,吃饭不许发出声响、不许摇晃凳子、不许用筷子敲碗、不许把手肘撑在桌上……但母亲每次都在金娃娃和几个伙伴的叫喊中妥协。他们围在我家门口大呼小叫地喊我的名字,还把碗敲得当当响,母亲只好把饭盛到大碗里,配上菜递到我面前。
小姑娘却从来不把饭菜端出来吃,也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时候吃完饭的,当我们还在沙上坡那儿打闹时,小姑娘家的窗户那儿已经亮起了灯。
一次,我问金娃娃,你姐在家里跟不跟你玩?
对小姑娘的好奇总是令我一刻不停想要知道得更多。我有时甚至羡慕金娃娃,设想如果我不能成为小姑娘,是金娃娃也好。

卢西安·弗罗依德作品-56
不跟。金娃娃答得很干脆。
那你们吵不吵架?
不吵。
你爸和你妈喜欢你还是喜欢你姐?
有时候都喜欢,有时候都不喜欢。
你爸妈打不打你们?
怎么不打?我就不信你没被你妈打过?
那你姐被打的时候哭不哭?
金娃娃摇头说,从来不哭。我妈说她勇敢得很。
她不怕痛吗?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妈打我的时候我就使劲哭。金娃娃说完露出一丝狡猾的表情。
我妈打我,那是真的打,真的痛呵。我觉得找到了知己,恨不得我心里的委屈统统都跟金娃娃好好的倾诉一番。金娃娃一面听我说,一面顺手把我的洋娃娃拿来抱在怀里。
我很想好好对金娃娃说说我妈是怎么打我的。好多细节都立即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了,但她好像一点好奇心也没有,只是不停抚着那个洋娃娃。但我不想就此打住这个话题,因为那时我突然觉得,没有一个人来和我分担这种痛苦是件很难受的事情。那你妈用什么打你们呢?我又问。
用衣架。金娃娃头都不抬一下。继续摆弄我的洋娃娃。有一次衣架都打断了……
是打你还是打你姐打断的。
打我姐。
是为什么打断的呢?
好像是我姐要买什么新衣服,我妈不同意,我姐就不吃饭,一天都不吃,整整两天都不和我妈说一句话,我妈就打她了。
那她还是没哭吗?
没有。反正我没听到她哭。
我站在凳子上从穿衣柜的顶上拿下一根两尺来长的竹片子给金娃娃看,我妈就用这个打我。
我的行为还是没能引起金娃娃更多的同情和共鸣,她说我们来“扮姨妈”好不好?
我有点泄气,但“扮姨妈”是我一向喜欢的游戏,所以立即就同意了。于是按惯例找来一块枕巾把洋娃娃严实地包裹起来。金娃娃把洋娃娃抱在怀里说,我当妈妈呵。说着她便将洋娃娃拥在怀里,很快进到角色中去,看布娃娃的眼神瞬间就变得慈爱起来。
我自然成了医生。学着母亲的样子,拿出听诊器给金娃娃怀里的洋娃娃听诊拿脉,一边听,一边摇头,还伸手去摸洋娃娃的额头,好热,发高烧了。金娃娃很着急的样子,那怎么办呀?医生!
我一脸严肃地说,一定要打针,否则好不了。我取出母亲从病房带回来的报废注射器,用棉签蘸上红药水紫药水,照着洋娃娃的屁股那儿一阵乱抹。
金娃娃一面轻轻地拍着她怀里的洋娃娃,一面说医生你轻点呵。
彭伯伯时常会在晚饭后到我家里来找父亲聊天,并心甘情愿地为父亲做模特儿,我们家墙上有好几张彭伯伯不同角度的素描画像,有时候彭伯伯也会把父亲画好的素描如获至宝地用一张废报纸卷起来带回家。在我的记忆里,彭伯伯似乎永远都穿着那件浅灰色的中山装,头发花白,清癯的脸上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说话慢吞吞的,平时里也不太与人交往,在医院,彭伯伯好像就只跟我们家有往来。听母亲说,彭伯伯年轻时喜欢拉二胡,爱好文学,还偷偷写过些小文章发在市内的各种小报上。不过彭伯伯最喜爱的还是剪影。他让我母亲紧靠墙那儿坐着,用灯光把侧影投在墙上,再用一张纸蒙在上面,用铅笔把侧影勾勒下来,包括眼睫毛也画得惟妙惟肖,最后就依着描好的图像剪下来。
彭伯伯和彭妈妈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曾听母亲跟父亲议论说,彭伯伯结婚之后性情大变,不拉二胡,不写文章,连书都难得再看,只是规规矩矩上下班。彭妈妈是棉纺厂的工人,早出晚归,所以虽说同住一个大院却很少见到。大院里的大人们议论说,彭伯伯与彭妈妈感情向来不好,吵架从来不避左邻右舍。有时两人吵得激烈时,就互骂对方是没有性别的阴阳人、公母人。
大人们说,如果没有彭家两姊妹的话,俩人可能早就散了。母亲跟父亲说起彭伯伯一家时,很是同情彭伯伯。母亲说,老彭这辈子最不幸的就是他的婚姻,虽说有两个女儿,不过谁也说不清将来是福是祸。
我也曾问过母亲彭伯伯跟彭妈妈为什么总吵架。母亲说小孩子别打听大人的事。于是我只好继续用手中的注射器给洋娃娃打针。我通常是脱下布娃娃的裙子,在它的屁股上一针接一针地打进许多自来水。布娃娃常常被我折磨得面目全非,有一次,布娃娃的头不知怎么地就剩了一根线勉强跟身体连着,全身上下的紫药水红药水把它的模样变得越来越狰狞,我终于被洋娃娃的模样吓坏了,扔下它,逃难似的跑出门去,逃到沙上坡人最多的那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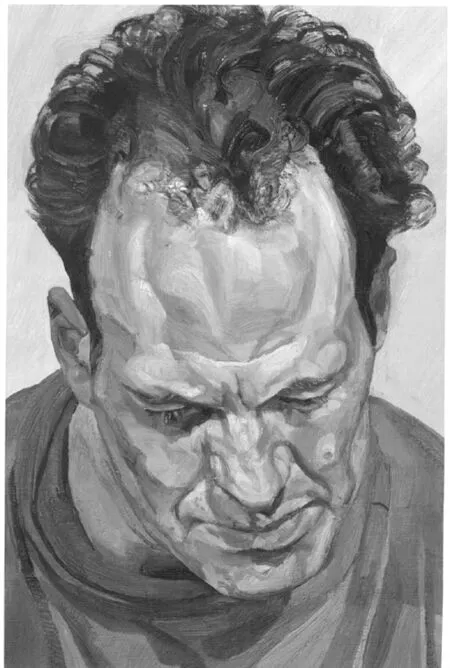
卢西安·弗罗依德作品-57
黄昏的沙上坡是最热闹的时候,那时没有电视,晚上便显得冗长而闲散,于是沙上坡就成了人们饭后的聚散地,人比开会到得还齐。大人们一边织毛衣一边聊天,我们则寻找各种角落捉迷藏。有时也围在大人旁边,听大人说些我们似懂非懂的事情。
有一次我们听见大人们说,罗小红的妈妈生老三了,还是个女孩,那口气里带着替罗小红妈妈感到的遗憾和不满,但跟罗小红和她妹都不像,罗小红和她妹都像她妈,而这个老三却长得跟她爸一模一样。我们好奇地拉住罗小红问,小孩是怎么生出来的?罗小红得意地卖关子说这不是随便可以说的。我们更加好奇。罗小红死活不说,我们就决定孤立她,威胁说,如果她不说的话,我们就不跟她玩了。罗小红没有办法,只好对着我们小声说,跟拉屎一样。答案像炸弹一样在我们中间立即炸开了,我们大呼小叫,都觉得这个答案实在太离谱了。我们夸张的笑声使罗小红很委屈,她几乎带着哭腔说,真的,真的像拉屎嘛。后来我们又问,你们家老三明明是你妈生的,为什么会像你爸呢?罗小红这次被问住了,她只好老实地说她也不知道。金娃娃若有所思地想了想说,是不是老三在你妈肚子里的时候,你妈天天看你爸,所以你家老三才长得像你爸的。我说那罗小红跟她妈长得像,是不是她在她妈肚子里时,她妈天天照镜子呢?罗小红认真地想了想说,那……金娃娃跟她爸妈都不像,是她在她妈肚子里的时候,她妈不看她爸也不照镜子!罗小红的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是呀,金娃娃不但跟她爸妈长得不像,跟小姑娘也一点不像,金娃娃长得跟皮球一样圆滚滚的,眼睛小得像两条缝,简直就是小姑娘的反义词,我们一同看着金娃娃,像是要在她的脸上找到答案。金娃娃也很困惑的样子,认真地想了想说,这个问题我倒没想过。
回家问母亲,母亲每次对类似的问题都只有一句话,你思想复杂。
一天,大家在沙上坡那儿玩得都有些心不在焉,这也不好玩了,那也没意思了,金娃娃出主意说,我们不如到后门那儿去吧。
医院后门外是一片很开阔的菜地。事实上是菜地包围了半个医院。医院大门临街,一般过往的人都从大门出入,大门两侧各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桂花树,面对着医院办公楼,办公楼后面是住院部,再往后便是医院职工宿舍楼,宿舍楼与菜地只一墙之隔。宿舍旁边有一扇小门便是通往那片广阔的菜地的。
平日里,医院的孩子是不许迈出医院大门和后门一步的,母亲就曾严厉地告诫过我,如果哪天我犯戒的话,就让我吃“笋子炒肉”,意思是要让我饱尝皮肉之苦。不过那天大家都玩疯了,互相怂恿,再说要受惩罚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大家都有风险。当时大家就拉钩上吊地发誓,绝对严守秘密。
开始时大家在菜地里你追我赶,还不时拔起一些未长好的南瓜苗当手雷,包谷已经长得老高,正好为躲避对方当掩护。金娃娃跑起来像皮球滚起来一般快,每次都机灵地逃脱追赶。包谷林被我们弄得唰唰响,一些未成熟的包谷也被我们摇落在地。菜地不但比医院里宽畅,还比医院自在,又能避开大人的监视,所以那天我们差不多快发狂了,金娃娃和另外几个女孩甚至放肆地骂起了粗话,把平时里学到的记住的甚至不明意思的脏话统统骂尽,骂完还不忘叮嘱伙伴,别告状哦。别的伙伴就把这当作把柄,处处威胁……

卢西安·弗罗依德作品-58
我们是被农民的骂声赶出菜地的。跑出菜地后,便有一块相对高些的土坡,上面光秃秃的,翻过土坡,有一个看不出有多深、散发出难闻气味的大坑,有人捂住鼻子说,是粪坑。我们一听都大叫起来,兴奋得捡起石子往下扔,石头落进坑里像扔在棉花上,声音很闷。大家七嘴八舌猜测,这坑有多深?金娃娃干脆捡起一节长长的包谷杆,沿着边上往下插,但最终也没触到底。她挑起一些杂草说,谁要!谁要!便宜卖。大家尖叫着你推我搡地躲闪,害怕金娃娃手中的恶臭溅到身上。见我们四处躲闪,金娃娃一下兴奋起来,挑着杂草对准我们晃来晃去,金娃娃很快成了我们集体对抗的目标;不知是被谁推搡,还是她自己不小心,在我们大呼小叫的当儿,金娃娃突然滑落到坑边,一只脚立即陷到坑里,她的手本能地抓住了来不及躲闪的我,她的尖叫声使伙伴们惊惶失措,好在别的伙伴没有丢下我,我的另一只手被许多手拉扯着,我就像连着金娃娃与伙伴们的一根绳索,越拉越紧,拉得我五脏六腑都仿佛被打上了一个个死结。
我们也不知是怎么把金娃娃弄上来的。我后来在回忆整个过程时一片混沌,只恍惚觉得金娃娃好重,浑身湿漉漉的,沾满了刺鼻难闻的杂草……
回来后,大家都闭口不谈这天的事情,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早早回到家,比哪天都听话,甚至像约好似的,连吃饭也不到沙上坡去了。但到了彭妈妈下班的时间,大家还是听到了金娃娃的哭声,那哭声大得像恶梦。我第一个被叫出来,彭妈妈对我母亲说起事情的经过,她说,多亏你们家的红兵救了金娃娃。母亲一边安慰彭妈妈,一边把目光转向我。那天母亲对我的处罚在我的记忆里是最重的一次,先是竹片被打断,然后在洗衣板上一直跪到天黑,连吃饭都没让起来过。
从此我们中间少了金娃娃,也没有谁再敢去叫她出来玩,金娃娃的母亲威胁说,谁再把金娃娃叫出去,她就要用剪刀剪谁的手指头。我想象着彭妈妈布满皱纹的双手和锈迹斑斑又黑又尖的长剪刀,不寒而栗……
金娃娃被她母亲成天锁在家里,我们只能从窗户那儿看见她那张模糊不清的面孔。
那之后的一个黄昏,在沙上坡那儿,我听见大人们议论起了金娃娃和小姑娘。
金娃娃的命够大的。要不然也活不到今天。
毕竟不是自己的,打得那么狠,不是自己生的也是自己养的,好歹还是个孩子呢。
没生过娃娃的女人心狠着呢。捡来的娃娃当球踢。我看这话一点没错。
捡来的娃娃都乖巧得很,会看脸色,也会讨大人喜欢,像天生知道她的命似的,小姑娘虽说话不多,倒也逗人喜欢,漂亮、懂事,又勤快。没见过哪家娃娃像小姑娘那样爱干净的,家里的桌椅板凳她都用肥皂刷洗得一白二净,哪像这些娃娃,只知道疯玩。金娃娃也可爱,有礼貌……
老彭不愿承认是他老婆不会生,老彭还替他老婆藏着掖着的,说是她身体不好,不敢要,实际上是他老婆卵巢有问题……

卢西安·弗罗依德作品-59
小姑娘跟金娃娃是彭家捡回来的?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被吓呆了。
回去问母亲,母亲只说小孩子别乱打听。
那卵巢是什么意思?我还是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你从哪儿听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小小年纪问这些干什么?母亲严厉地打断我的问题。
但我还是在沙上坡那儿继继续续地听到了一些有关小姑娘和金娃娃的事情。
据说,小姑娘是彭伯伯在医院大门那儿提回来的,裹着一块蓝花的枕巾,装在一个黑乎乎的大布袋里。而金娃娃在垃圾堆边被彭伯伯发现时,身上连根纱都没有。向东的母亲说,还不足月呢,又是冬天,全身上下冻得青里透紫,连哭声都没有,大家都说这娃娃怕活不过那个星期天……
那段时间,我们都在不停搜集有关小姑娘和金娃娃的信息,每个人回家都会从父母那儿打探,在一起玩耍时就互相把对方假想成金娃娃或者小姑娘,直到对方用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来澄清自己的身世才罢休。在游戏过程中,我对自己的身世也产生了怀疑,心里忐忑不安地对母亲寻根问底,问一些我小时候的事情,包括我生在哪所医院,会不会抱错了?母亲说你连脚指头都长得跟你爸一模一样。加上我从小到大都不断听到大人们说过,我吸收了父母亲身上的所有优点,也就是说我身上的每个部分都能从我父母的身上找到依据,我这才最终踏实下来。
我们又有了许多新的游戏,跳皮筋、踢键子;伴着童谣,边唱边跳,但我们不再邀请金娃娃跟我们一起玩了,就好像谁跟她接触,谁就会变成捡来的似的。当然我们也没跟她翻脸,只是对她抱着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自顾自玩我们的,金娃娃显然对我们的态度有所觉察,但她一定弄不懂为什么,所以她总是站在一旁,跟我们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既不妨碍我们游戏,又似乎身处我们中间,而脸上则始终保持着一种勉强的笑。有时候她会装得若无其事地主动要为我们拉皮筋,而我们中间的一个就自然而然地抢在她的前面拾起皮筋头。终于有一天,金娃娃脸上那种勉强的笑容不见了,只是咬着右手的食指默默地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就转身走开了。
看着金娃娃胖乎乎的,慢慢跑远的背影,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跳皮筋失去了兴趣,我记得那天我们又硬着头皮玩了一轮,接着就散了。
那之后我们几乎就再没玩过跳皮筋,甚至根本就不怎么在一起玩了,什么原因似乎也说不清,只是觉得心里老不踏实。有时候我也特别想叫上金娃娃,叫上院里所有的玩伴,重新开始我们的游戏,但那天金娃娃一个人慢慢走远的背影让我明白,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无忧无虑地游戏了。
也就是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后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听到了小姑娘出走的消息。
许多年来我一直在猜测小姑娘出走的原因,试图揭示其中的真相成了多年后平淡生活中富于刺激的一种游戏,而且随着阅历的增长,我的结论变得越来越离奇或者说越来越惨烈。但实际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心里都很清楚,小姑娘出走的原因只可能是一个,那就是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这一点其实很容易理解,那段时间无论我们这般大的小孩,还是那些老于世故的成年人,不约而同地都在谈论小姑娘和金娃娃的身世。原本成人们从不谈及此事,可能是出于对彭伯伯两老和小姑娘两姐妹的同情,但金娃娃挨打时让人心惊胆战的嚎哭声解除了人们的禁忌。
那段时间人们对小姑娘的出走议论纷纷,是谁不小心还是有意把小姑娘的身世透露给了她?她又到哪里去了?人们相互回忆最后一次见到小姑娘时的时间、地点和印象。她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啊?人们说,五点半放学,然后坐在书桌前做作业……
她不是在做作业,彭妈妈憋了一会说,这么多年来大家都以为她在做作业,但我敢肯定她一直在写一封信,一封很长的信……
什么信,写给谁的?人们问。
彭妈妈气鼓鼓地说她不知道,但她肯定那是一封信。
那天彭妈妈似乎什么都愿意说出来。小姑娘一直都是这样,她说,什么事情都装在心里,从来不跟我们说,她想什么我们也从来不知道,就是挨骂,也从没当着我们的面哭过。我们没少给她吃穿,但跟我们就不如金娃娃亲。关于她们俩的身世我们从来没有告诉过她们,总想等她们长大后再说。
不知道是哪个缺德鬼干的。彭妈妈最后狠狠地骂了句。
那段时间我成天沉浸在一种既亢奋又恐惧的心情里,总以为事情就像一出戏那样会愈演越烈,但事情发展让我倍感失望,原因是一周之后小姑娘突然回来了。她被彭伯伯领着,像刚上了一趟街似的,有说有笑地回来了。她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又出现在我们的大院里。对于小姑娘的神秘失踪又突然出现,大人们都在猜测,小姑娘是不是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不是没有下落;或者是找到了,但亲生父母根本不认她,她又才被彭伯伯领了回来……但所有的猜测最终也没有得到证实……
事情过后,一切仿佛归于平静,我们也重新开始了那些游戏。在大院里见到金娃娃时,她不再跟我们接近,看上去,金娃娃仿佛突然长大了,她的神情中甚至有了某种跟小姑娘极为相似的东西,我印象里的金娃娃的笑容像被这种东西给收了回去。包括脸色都变得跟小姑娘一样的苍白如雪,那两团腮红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姑娘仍然那么趾高气扬,不过我不再希望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小姑娘了,我觉得她变得一点都不好看了。当小姑娘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我们就把牙齿故意往外咬住下嘴唇,学着小姑娘的样子互相看。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伙伴们,我妈说这叫“爆牙齿”,是生理缺陷。大家听了都幸灾乐祸地大笑,像抓住了小姑娘的什么把柄似的。我们就用“爆”字来组词,比如“爆米花”、“爆竹”、“爆炸”、还有“爆……”,最后就是“爆牙齿”。只要遇到小姑娘,我们就把牙齿使劲地咬住下嘴唇,咬得一个比一个更难看。但小姑娘对我们的表现从来不作出任何反应。最终让我们的兴奋落了空。
有时看见金娃娃,我们就故意夸张笑声,但金娃娃已经不再对我们的游戏有一丝的好奇了,她甚至学会了用跟小姑娘一样的眼神打量我们,然后骄傲地从我们身边走过。
更让我们大惑不解的是,小姑娘和金娃娃开始变得形影不离了。小姑娘和金娃娃走在一起的样子,没有人会怀疑她们不是两姊妹,并且是一对感情甚笃的两姐妹。小姑娘总是用手搂着金娃娃胖乎乎的肩膀,搂得很紧,两个人走路的姿式和步调显得那么和谐一致。金娃娃也变得跟小姑娘一样干净了,她身上的衣服都是我们曾在小姑娘身上看见过的,洗得发白的干净。
九月,我上了小学。母亲在给我报名时,也觉得我的名字实在不像女孩子的名字,加上时代的烙印太重,先是去掉兵字,剩下两种颜色觉得不妥,留下兵字更像男孩,母亲便把兵换成了冰,母亲说我是年底生的,正好是冬天,从此我改名黄冰。上学的第一天,我突然想小姑娘的学名会叫什么呢?金娃娃会不会就用现在这个名字去报名上学,不知道别人会不会猜到她们是捡来的?
小姑娘高中毕业后顶替她父亲的工作,在医院洗衣房当了工人,但她的表现一点不像个洗衣工,什么时候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那些经小姑娘洗过的白床单,挂在洗衣房前的十几根绳索上,兜着风翩翩起舞。床单上除了白净,一丝病痛与死亡的痕迹都找不到。
我从来没有跟小姑娘说过一句话,我们像是从来都不认识,但我们又是认识的,我们一同在一个大院里长大,一同经历着时间给我们带来的变迁。
念书,长大,恋爱,结婚……后来的许多事情终于使我们那群成天在一起玩耍的孩子们分道扬镳。偶尔回母亲家时,我总不免会想起他们。有时遇到也没有了往日的那份亲密。彭伯伯和彭妈妈再没有见到过,就是见到了,我想,恐怕也认不出来了。特别是后来那排平房拆除后,所有人都搬进了医院新建的职工宿舍单元楼,各家各户的防盗门,一模一样的铝合金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早已不相往来。凹凸不平的沙上坡变成了水泥地,修了一个很大的圆形水泥花坛,种上许多好看的花,成了医院病人看花散心的好去处。听母亲说,彭伯伯已经快八十岁的人了,几次遇见,叫他到家里来玩,他都说楼太高,爬不动了。
金娃娃结婚的消息是偶尔得知的,嫁了她的一个大学同学。毕业后,两人去了西藏。回来过几次,但我从没遇到过。只听说金娃娃变得跟非洲人似的,黑得都有点让人认不出了。
小姑娘一直在医院,但已从洗衣房调到供应室去搓医用棉签。直到前不久才听母亲说小姑娘偷偷地从医院开杜冷丁,拿到外面高价出售,因为杜冷丁是限额的,每次不得多开,她便用各种令人同情的理由托别的医生出面开出,时间长了自然便被人识破,不久被医院除了名……
后来,又听说小姑娘去了深圳,一去就没有再回来过,开始时还有几封书信,再后来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但有着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直延续着,一种说法是,她在那里成了家,嫁了一个港商,生有两个孩子,过得挺好,穿金戴银的。一种说法是,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本城,因为染了毒瘾,她便开始贩毒,以毒养毒。
有的传说她已经死了,有的又说在某个夜总会看见她,很瘦,但仍很漂亮。
关于小姑娘和金娃娃的消息后来越来越少,但我总觉得小姑娘跟金娃娃的故事还没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