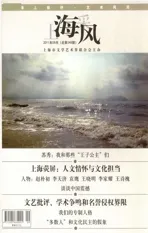袁鹰:70年的文学情缘
2011-07-11
文/特约记者 程 也

袁鹰
原名田复春、田钟洛。当代散文家、诗人、儿童文学家、编辑。1924年10月出生于江苏淮安。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和业余创作。担任过《人民文学》《儿童文学》编委、《散文世界》主编、《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名誉理事。
“我们楼前正在造房子,路很难走,你坐什么车来呀,我附近有地铁,有……”电话里,袁鹰老师朗朗地说着,听不出这是一个耄耋老人的声音,只有长辈对小辈特有的事无巨细式的关心。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电话约访,我终于在人民日报社的一座居民楼中,见到了著名作家、资深报人袁鹰。一头银发,胖胖的身材,眼睛里满是谦和、慈祥的袁老热情地招呼我到书房落座。书房里除了一张办公桌和两张旧式的沙发,书橱里、桌子上、地板上到处都是书,就连从大门走向书房的过道里也放了两书架的书。我们的话题就从书与文章开始了。
回首第一篇习作
拜访袁鹰之前,文汇报笔会主编刘绪源给了我一本袁鹰的书,我惊喜地发现里面居然收录了袁鹰在1940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稿。70余年过去了,今天仍然笔耕不辍的袁鹰是如何看待自己处女作的呢?
回首当年,袁鹰的眼光变得有些悠远:“写作的爱好最早是从对阅读的喜爱开始的。我从小爱看书。幼时在家乡,祖父有一间书房堆满了线装古书。” 十岁进小学后,老师鼓励大家读白话文课外书。袁鹰至今还记得当年读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冰心的《寄小读者》,后来又读了朱自清的《背影》等,第一次感到白话文的优美动人。
十四岁时,他跟随父母从杭州搬到上海,当时正是“孤岛”时期,因为家里比较拮据,他读的书全靠借阅和在书店里白看,“我是福州路文化街上的常客”。书店里有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和进步书籍,买不起书的人可以站在那里看,店员决不会撵人或者给白眼。每天下课后在开明书店的店堂里站着读书,成为少年袁鹰的一大乐趣。成年后回想起来,袁鹰认为,阅读的兴趣和习惯可以慢慢对一个人的思想、生活发挥作用。在阅读的当时当地,读者并不一定能完全消化,阅读的成果在当时也不一定看得出来,“但它会像种子一样落于心田,哪一天就发芽、开花、结果了”。
书读多了,自然而然也手下痒痒,萌发起写作的兴趣。“当时家里订有《申报》,我就尝试着投了一篇稿子。其实那时自己才16岁,也没有多少生活阅历,看见什么写什么,好玩而已。”袁鹰说,他在短文里写了一位热衷于搓麻将的办弄堂小学的校长,题为《师母》,用笔名“裴苓”寄到《申报》的“自由谈”副刊。暑假之后的9月5日他居然在报纸上看见自己的文章发表了,“那真是大喜过望,写作热情高涨。”袁鹰展开一脸皱纹,笑得一如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稿费领来,相当于当时一个月的学生月票钱。那是不少啦,我就约同学一起出去吃面,大家都很高兴。”
在发表的刺激下,他和几个喜爱文艺的同学开始热切地寻找写作指导书看,至今他还记得茅盾的《创作的准备》给他启发很大。现在再看这篇习作,袁鹰觉得虽然有些幼稚,但从身边的人和事开始写作倒是写对了方向,没有走弯路:“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自己的生活,不要胡编。”
文学之路是艰辛的,袁鹰用初生牛犊的胆量去接触小说、散文、新诗、活报剧、书评等等各种形式。在对文字的求索过程中,他与文学再也难舍难分。

袁鹰和冰心探讨文学
跨界飞翔的鹰
袁鹰原名田复春,又名田钟洛,袁鹰是笔名。我很好奇,周围的人都叫他什么,他呵呵地笑道:“《人民日报》的老同事都叫我‘老田’,也有人叫我‘钟洛同志’,不过读者好像更熟悉‘袁鹰’这个名字。”因为喜欢写作,袁鹰用过许多笔名,其中用得最多的是“袁鹰”,他说,他取笔名时想学习鲁迅用母亲姓氏,于是有了“袁”,当时因为处于“孤岛”的上海,希望在黑暗中飞向光明的远方,苍鹰一飞千里,于是有了“鹰”。“袁鹰”开始在文坛上翱翔。
作为著名的散文家和儿童文学家。袁鹰的名字在少年儿童中声望很高。他的《井冈翠竹》曾经入选教科书,还有《白杨》——“白杨是高大挺秀、生命力顽强、坚强不屈的树”——有些年纪的人一定还记得自己当年朗朗诵读的情景。此外,《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小红军长征记》等都有很大影响,广为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
其中必须要提的是《丁丁游历北京城》。当年无数少年儿童对它爱不释手,他们正是跟着这本书游历了我们的首都——人心所向的地方。说起此书的诞生,袁鹰笑着说那是无心插柳顺便为之。因为工作关系,当年袁鹰从上海出差去北京一周。当年难得跑长途,又是到首都去,他趁便到天安门、故宫、颐和园等处看了看,到街上走了走,见闻颇丰。或许知道他一定会把所见所闻付诸文字,正在《新少年报》当编辑的夫人就向他约了稿。没想到,以故事形式向小读者介绍北京风物的文字获得了孩子们的喜爱,不仅他们爱读,老师们也爱把这些文字当作教材。于是干脆结集出版,主角少先队员“丁丁”一下子成为大江南北孩子们共同的朋友。现在北京变化可大了,袁老是否考虑过写一个《新丁丁游历北京城》?“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你可以写。写丁丁长大了,带着小丁丁看今天的北京。”袁鹰老师慈祥地看着我。
除了业余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外,袁鹰的工作是记者编辑,写过不少有火药味的文章,他经历了革命年代,接触了许多老一代的革命者、文艺界的先行者,他写的传记文学《长夜行人——于伶传》等,在海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大家把他叫做“两栖人”。对于这个称谓,他说:“半个世纪的两栖生涯,一面为他人缝制嫁衣,一面为自己裁剪衫裤,忙忙碌碌,风风雨雨,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我至今不悔,还常常引以为荣,引以为乐。它是生活给我的厚爱,使我的人生道路虽然平坦却不单调,而且还算充实。”

丁聪给袁鹰画的像
难舍上海情结
听说我也是上海人到北京,袁鹰非常高兴,立马来了一句纯正的上海话:“侬是上海人?”上海是袁鹰魂系梦绕的地方。
圆明园路,那是上海的一条靠近外滩的小马路——“地处外滩的群楼背后,北起苏州路,南到滇池路,大约三四百米左右……它镌刻下了《文汇报》从‘孤岛’上创刊第一天起的青春岁月,留下了几代读者的思念深情,包括我这个70年前的老读者或许也可以忝为老朋友的人。”
思南路,上海市中心一条闹中取静的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总是深情地伸展双臂,枝叶交叉,成为一道绿色长廊,为过往行人送去一片浓荫,一缕恬适。四五十年前,当思南路还叫马斯南路的年代,它在上海人心目中,就已是一条绿荫覆盖的马路。人们谈起茂密的林荫道,就会赞叹地说:‘像马斯南路那样’。”
虽然袁鹰在上海只生活了15年,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辈子,但他仍然关心着上海的方方面面,仍然在用他深情的笔书写着记忆中的上海。在上海曾经住过的一条条弄堂、一个个石库门都被他用手中的笔描绘出来,那些曾经的人和事被他一再说起。他说,上海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进入了他的生命,影响了他的一生。
在袁鹰看来,上海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在那里涌现出许多文化名人、革命先辈。“上海接受新事物非常快,对先进的、好的东西就马上吸收,我到过南北几个地方,感觉这个特点在上海最为突出。”袁鹰说,“这就是海派,在文学上也出现了很特殊的‘海派文学’,我觉得以上海为代表的这种新的文风有益于文明程度的提升。”
基于对上海的感情,他晚年的很多文章选择在上海发表,比如《上海文学》就连载着他撰写的专栏,颇获佳评。
袁鹰还提到了许多当年引领他前行的老同志,很多人默默无闻地为文艺事业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上海的繁荣与这些人的贡献分不开。“结缘上海、结缘这些前辈是我能够走上文学道路的幸运。”上海是袁鹰文学创作起步的地方,是提供了他文学素材的地方,是他走南闯北一生难以忘怀的地方。

袁鹰同家人游苏州(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