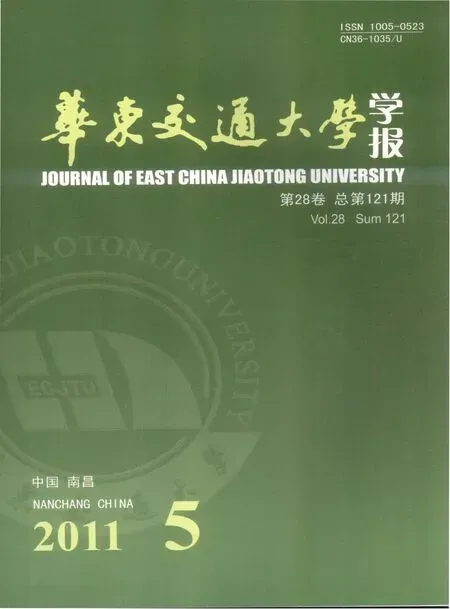批判性话语分析再思考
2011-07-05郑颖超
郑颖超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代表人物有Roger Fowler,Norman Fairclough,Teun Van Dijk以及Ruth Wodak,其发展可以追溯到Aristotle的修辞学,当代哲学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及Habermas和Foucault的社会学理论[1]3。CDA结合了社会理论和语言学理论,描述和阐释话语是怎样建构世界同时又被世界建构,探讨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其目的在于揭示语言作为国家软实力如何被当权者和强势群体使用,实施政治、经济、文化控制,以及蕴含在话语内的意识形态,从而唤醒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意识。Widdowson[2]ⅷ-ⅸ曾经对CDA抱以肯定态度,认为CDA不仅扩大了话语分析的范围,而且明确了应用语言学的目的,即要与现实世界相结合,理论要联系实际。但是经过对CDA的审视,他又改变了最初的看法,并且持有怀疑批判的态度,而且对CDA的批判直指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简称SFG)。对此,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CDA进行再思考。
1 CDA与SFG的结合问题
CDA自开始发展就与SFG结合,如今已有30年的历史。Young&Harrison[3]1指出CDA与SFG有3个共同点:1两者都把语言看做社会建构的一个要素,寻求语言对社会的主动建构性;2两者都认为语言具有辨证性,即话语活动影响语境,同时也受语境影响;3两者都强调语言的文化和历史意义。这3点与Halliday[4,5]对语言的理解相符,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语言的多功能性可以干预介入社会过程,他支持Sapir-Whorf的观点,即语言对现实世界的主动建构性,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反应和表达世界,人们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在选择语法时是有倾向性的,并不是持有客观中立的态度,因而Halliday将语言解释成社会符号。Halliday的语言观对CDA影响颇大,CDA的中心思想是语义服务于权力,话语服务于意识形态。可以看出CDA从SFG中汲取了不少养分,甚至其分析者(Fowler[6],Fairclough[7],Wodak[8])声称SFG是CDA的理论基石,Halliday的语言多功能观是恰当理解CDA与充分论述社会问题的必须。
然而,Halliday的SFG基于社会学,其目的是系统地研究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语言特征,语境既决定语言实用又受其建构,也就是说Halliday考虑社会语境是为了研究语言系统。显然,Halliday通过由外向内研究语言,但是CDA分析者是从语言出发来研究社会问题。因而CDA分析者有选择性地不仅运用了SFG理论中的几个概念,如及物性、情态、语法隐喻等,还借用了其他语言学理论,如言语行为理论、Grice的合作原则、关联理论、图式理论、原型理论等。可见CDA分析者从语言学理论中挑选相关概念,将其视为分析工具,从而达到有利于实现分析社会问题的目的,即揭示社会意识形态和权力。Kress[9](引自Young&Harrison[3]2)指出,CDA的目的是将语言学移到了社会政治领域,Fowler[6](引自Widdowson[2]97)声称,SFG过于细节化,太复杂,以至难以应用。语言学理论是抽象的,无倾向性的,通常研究普遍常规的语言现象,至于语言的民族性与非常规性却很少涉及,SFG亦同,然而CDA是从语言的民族性出发,解释产生意义背后的社会政治动机。进一步说只靠语言学理论,如SFG,要解读出蕴涵于话语中的深层社会意义是不够的,不完善的。实际上CDA不仅借用语言学理论,在研究社会问题时还运用了社会学理论,比如van Dijk[10](引自 Luke[11]101)借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交际民族志(EOC),Fairclough[12]运用Gramsci的权力理论等,因此,只能说SFG是CDA的理论指导之一,CDA也没有系统地运用某一个特定的语言学理论作指导。
除此之外,Halliday的语言系统是功能性的,它反映了语言的必要社会功能,即语言三大元功能,而CDA需要的语言功能是具体的语言实用中语义潜势的语用实现。Halliday的三大元功能过于抽象,解决不了语言交际的实际问题。换言之,三大元功能是被抽象语义化了,被编码到语言系统里,是高度概括了语言的功能。显然Halliday把语义和语用融合了,并没有区分语义和语用,这点与他的“体现观”相符。也就是说,语义被语言形式体现出来和被编码出来是一回事,因为他没有区分以下概念,即在语言实用(use)时,意义由语言形式(语音,词汇,语法)所体现,而在语言使用(usage)时,意义可以被编码,因此他将语用纳入语义的范畴。据此,CDA是要考虑语言的语用功能,如果把Halliday的SFG作为主要理论势必会出问题。
另一方面,CDA的话语分析方法上也深受Halliday思想的影响。Halliday[13]提出话语分析分为两个层面:“理解”和“评估”。在理解层,主要通过分析语法特征,理解语篇的意义,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语义模糊现象,即多义或歧义,而在评估层,语篇分析要与语境相联系,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读语篇,在哪些方面,话语有效地表达了目的,哪些方面失败了,评估层可以确定语义,消除在理解层出现的语义模糊现象。换言之,Halliday认为,话语分析是从下到上,从部分到整体,从内到外的,这一点他[5]278自己也承认,话语分析“从上到下”不能取代“从下到上”的分析。CDA分析者Fairclough[14]75提出的话语分析框架也与Halliday的话语分析思想相符,即先进行语篇内部分析,再考虑语篇外部因素,把语篇与语境相结合。Halliday的话语分析与Fairclough的话语分析框架存在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语篇先进行语义分析,然后结合语境进行语用推理,从而解读语篇意义。如果这样,读者或分析者只需按照一定的分析步骤,便可得到语篇意义,揭示意识形态,权力关系。换言之,Halliday与Fairclough对语篇进行语义分析时,已经预设语篇本身就蕴含意义,意义已经存在于语篇中,也就是在这一层,语篇可以脱离语境被独立成为语言分析的对象,而直到分析进入第二个层面或者语篇内部分析结束以后,语篇才与语境结合起来解读出语篇意义。实际上,意义不是现成就存在的,而是被读者或分析者想出来的,他们在理解语篇时是从主体本身这个视角出发,根据自己的认知和此时此地的语境,直接做出语用推理,进而得到语篇意义。由此,话语分析“从上到下”可以取代“从下到上”的分析,没有必要先进行理解,可以直接进入评估层,其实人们在理解语篇的同时也在评估语篇,二者同时发生。
2 Fairclough话语功能与Halliday语言功能的对应问题
Fairclough[14]64指出,话语具有建构性、辨证性,表现出3大功能:身份功能(identity function),即建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确立“我是谁”;关系功能(relational function),即建构社会人际关系;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即建构知识价值体系。正是这3大功能使话语表达出不同层面的意义,从而建构世界。同时Fairclough(ibid)声称,这3大话语功能分别与Halliday的语言3大元功能对应,在任何话语中它们相互并存且相互作用。然而,Fairclough又承认,身份功能和关系功能实际上同属于Halliday提出的人际功能,并不是完全对应关系。对此Widdowson[2]批判Fairclough自相矛盾,并且用第一人称——“我”,第二人称——“你”和第三人称——“他/它”来表示Fairclough和Halliday两者功能的对应关系,如图1,2(图中1,2,3点分别代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

图1 Fairclough话语功能之间的关系[2]90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rclough's discourse fuctions

图2 Halliday概念功能与人际功能之间的关系[2]27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lliday's ideational function and iterpersonal function
如图1,2所示,人际功能是第一人称“我”与第二人称“你”之间的关系,概念功能是“我”与第三人称“他/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话者从“我”这个主体角度出发,与“你”建立人际关系,与“他/它”外界事物建立联系,换言之,语言让人们先确立“我”这个概念,然后以“我”作为起点,认识“我”以外的“你”和外部世界“他/它”并建立联系。由于Hallliday的篇章功能具有实现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作用,与人际关系“你”和外界事物“他/它”不发生任何联系,因此该功能没有被表示出来。显然Widdowson用图式批判Fairclough的话语功能并没有与Halliday的语言功能对应起来。对于Halliday的篇章功能,Faiclough[14]65说到此功能对分析语篇很有利,但是他却没有说明篇章功能与其它话语功能的联系,将篇章功能列为附属品,根本算不上话语功能,所以在他给出的语篇分析框架中,将“衔接”这项只当做分析的步骤之一,除此之外,对篇章功能没有过多地涉及与阐释。
从基本话语(primary discourse)和功能性话语(meta-discourse)的角度出发,话语就具有两个功能:表征功能和交际功能。根据成晓光[15]的定义,基本话语是言语活动的基本内容,它是由指示意义和命题意义构成,传达命题信息,而功能性话语是由言语者的命题态度、语篇意义和人际意义组成传达言语者根据交际的需要来组织和监控言语活动的生成和发展的程序信息。语言让人们认识世界,解构世界,即语言的表征功能。而Halliday[5]276认为的语言把经验识解成意义,外部和内心世界的经验都在身体和意识中呈现,其实这也就是人脑的表征活动,所以语言具有表征功能。另一方面,语言的交际功能就是把人脑中的表征传达给别人,是外化的表征,期间便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根据上述分析,基本话语就具有表征意义,而功能性话语则具有交际意义。基本话语解构命题意义,让人们有命题思想,为交际做准备,在进行交际时,就要运用功能性话语,采取交际手段,与受话者沟通过程中通过信息推进建立起局部语境,从而达到人际互动与有效传达命题意义。因此,将概念功能列为表征功能,把人际功能(包括Fairclough的身份功能和关系功能)与语篇功能合并成交际功能。那么Fairclough的话语功能和Halliday的语言元功能表面上是不对应的,但他们的深层内涵是一致的,都说明了语言的两个基本功能,即表征功能和交际功能。
需要强调一点,Widdowson[2]99指出Halliday的三个系统都具有表征功能,不仅仅针对的是及物系统,为此还用主动转被动的例子说明,两个句子用不同的表达就是在表征建构不同的现实世界。首先我们认可Widdowson这样的理解,但是此理解未免有些片面化,只考虑到语言一个方面的功能,即内化外部信息,在人脑中呈现,加工以及符号化,而没有考虑到输出表达信息,即外化表征内容。根据Halliday多功能语言观,把语言看做一种社会行为,那么他势必要注重人际互动交流,语言不能只“进”不“出”,所以Widdowson曲解了Halliday的初衷。
3 结语
本文从两个角度对批判性话语分析进行了再思考,即CDA与SFG结合问题,Fairclough与Halliday的功能对应问题。讨论了CDA作为一门学科,以SFG作为理论基础和采用其话语分析方法存在的一些弊端,对CDA有了更清醒地认识。当然任何一门学科、原理和理论都有局限性,CDA亦然。我们不能抓住它的旁枝末节,而全面否定了CDA的意义。可以说,CDA价值在于将语言作为出发点结合社会理论研究社会问题,进一步揭示深层的意识形态及权力关系,从而使人们更加理性地认识到,通过语言的使用或滥用当权者建构的生活方式。
[1]HART C.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gnitive science:new perspective on immigration discourse[M].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0:3.
[2]WIDDOWSON H G.Text,context,pretext:critical issues in discourse analysis[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
[3] YOUNG L,HARRISON C.Introduction to the collection[C]//L Yong&C Harrison(eds).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studies in social change.London/New York:Continuum,2004:1-11.
[4]HALLIDAY M A K.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second edition.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3:13.
[5] HALLIDAY M A K.Is the grammar neutral? Is the grammarian neutral?[C]//Jonathan J Webster(ed).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271-294.
[6] FOWLER R.On critical linguistics[C]//Caldas-Coulthard and M.Coulthard(eds).Texts and practices: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routledge,1996:3-14.
[7] FAIRCLOUGH N.Linguistics and intertextual analysis within discourse analysis[C]//A Jaworski&N Coupland(eds).The Discourse Reader,fifth edition.London:Routledge,2002:183-212.
[8] WODAK R.What CDA is about—a summary of its history,import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opments[C]//R Wodak and M Meyer(eds).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fourth edition,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5:1-13.
[9] KRESS G.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language:history and structures of domination[C]//P H Fries and M.Gregory(eds).discourse in society: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s,norwood,NJ:Ablex,1995:115-140.
[10]VAN DIJK TA.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C].London:Sage,1997.
[11] LUKE A.Beyond science and ideology critique:development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02,22:96-110.
[12]FAIRCLOUGH N.Analysing discourse: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M].London:Routledge,2003:45.
[13]HALLIDAY M A 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third edition.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8.
[14]FAIRCLOUGH N.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eleventh edi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06.
[15]成晓光.语言哲学视域中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建构[J].外语学刊,2009,146(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