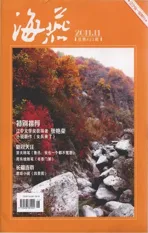书香门第(四则)
2011-06-23周东坡
文_周东坡
秋天的书房
一场疾病夺走了我的春天,更没想到的是连夏天也一并剥夺了,将我一个趔趄推进秋天。
我对时令是马虎的,这么多年寒来暑往,日子俗常得让人五感迟钝,今天是昨天的堆砌,明天也不过是今天的复述,有多少微妙的变化在进行当中呢?
也许是有的,但我感觉不到。
四季轮回本是一种正常逻辑,有微妙的过渡,有适时的更迭,然而我却被一场疾病无端搅乱了生活节奏,以至于面对这个秋日仿佛怀揣了心事,发出四处漏风的细微声响,却说不清所以然。
我已经很久没有进书房了。
空置的书房不叫书房,叫摆设——样子货,给人看的、抚摩的、把玩的,与阅读无关。
而书房从来不是私密的,它只是一个相对密闭的场所,属于一个人,以及散布在空气中的那些绵长的书香、悠远的阅读。
我已经做好准备,重新回到熟悉的阅读状态。
这样一个秋日午后,暖暖的阳光在窗外徘徊,它们一定有所期待,在我拉开窗帘的刹那一拥而入,将我瞬间淹没,通身照亮。
明亮的还有书房。
书房依旧是春天时的模样,我诧异地看到,书桌上不知哪天摊开的书籍还在原位,只是已经覆上薄薄一层灰尘,把字里行间都填实了。
离开书房的那天,我一定匆忙到来不及整理案头,任由这一册书籍空耗了整整一个春天,以及接下来的整整一个夏天。
那是一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已经被我翻毛了边。我不记得这是与大师的第几次对视,我喜欢这种方式,平易、亲切,不远不近的距离,让我的呼吸时时能够跟上他们的频率。
在我患病的日子里,生活在继续着,时光在不紧不慢流逝着,但这一册书籍却把书房当时的场景,乃至每一个细节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于是,我今天的接续虽然有所停顿,却没有丝毫陌生感。
秋日阳光是绵软的,从窗口斜射进来,由于玻璃窗的阻挡而稍稍改变了行进路线,游移、漂浮,给人一种虚幻感。
空座椅会让人产生很多联想,可我想象不出自己当时是怎样一种阅读姿势,慵懒的?端正的?好在那个姿势的余温还在,它们散布在书房的角角落落,我一伸手就可触及。
宁静、致远,友人赠予的书法作品静静悬挂在北墙,颜体,极见精神,与书房陈设相得益彰。但这不是我的心境,而是书房的。
说到书房,自然要提到客厅。不过,书房与客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客厅是家常的,而书房相对家这个概念来说就是一个附属物,有就有了,并不值得炫耀,当然,如果没有也不必沮丧。现实是,我的书房常常高朋满座,客厅则往来稀疏。恰正是这场疾病,让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长久以来被我忽略的问题:我的生活是不是缺少了点什么?
我的内心疑问是,病菌终于在我身体的某个部位找到了出口,而我也需要某种出口吗?
我的书房与外面的世界只隔着一扇窗,互为照应,却无法融会贯通。
也许,我应该时常把书房的窗户打开,让外面的空气无遮拦地闯进来,与书房里的空气中和一下。
那么,就从今天开始吧。
我把窗户完全打开,把自己安放在书房与外界交汇的那个点上。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发现自己的视野变了,不再局限于10平米的书房,而是拥有了更大的疆域。
我的另一个发现是,这栋大楼下面居然还完整保留着一排低矮的平房,是上个世纪末常见的那种红砖石棉瓦结构。我曾经以为它早已退出了都市舞台,成为一种只与年龄有关的记忆,殊不知它依然在为需要的人们提供着庇护——我视而不见,一定是因为我常常忘记了对生活俯一下身子。如今,这样的场景是难得一见了,却远比书本更亲切、真实,其中一家的屋檐下还悬挂着一串干辣椒,细长的辣椒簇拥在一起,密密匝匝,红得耀眼、热烈,将我们司空见惯的秋日生活无限放大开去。
向我靠近。
向书房靠近。
曾经,书房安置着我每一个俗常的日子,让我习以为常,甚或自以为是地认为生活本就应该是这样的,然而,一场不在计划内的疾病证明我还有更多需要。
不是吗?
把书桌安置在哪里
每天,我都会在大致的时间段坐到书桌前,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与一次疾病最终演变成顽症稍有仿佛,偶有偷懒,脚步都会不由分说把我拖进书房。
在书房里,我坦然打发着一天中难得的轻松、自由时光。
书房略显拥挤,有一架墙的书柜,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最占地方的是一张单人沙发床——平时折叠着,需要用时才摊开。我不能改变书房格局,只能说书桌大了点,占用了过多空间,却是我一见钟情的,在卖场见到它的时候,我直觉它出现在这里是为了专门等我。我欣赏它暗里透红的色调,就是微微发散的干燥木材气息也是我喜欢的——有这两条理由还不够吗?
布置书房曾让我很费了一番踌躇。书房西南朝向,门开在南边,窗户开在西边,要在这方寸之地把所有物件都安排稳妥显然是有难度的,我先在纸上推演,又拿着卷尺实地丈量,总算得出一个还算满意的方案:南边大半边墙全部交给书柜;书桌则摆放在书房中间,面南背北,显出主角的地位——这是它所处的最佳位置;剩下一点余地都归沙发床,平时靠着东墙,面向书桌,摊开时书桌要先向西腾挪点地方出来,沙发床顺势转向,靠住北墙,面向书房门——这样布置虽然不够严谨,但把书房门关上也自成一统了。
每当坐到书桌前,我的心态都是平和的,即使偶有起伏,也会很快平静下来,就想,这应该是书房所营造的气场施予我的影响吧。
钢筋混凝土构造的书房里有满室书香,却与嗅觉无关,我能闻到的,是空气中散布的丝丝缕缕的木香。这种香应该很让肺部脏器受用,它畅通无阻地进来,走的时候又顺便把一些沉积物、附着物带走,让人变得身轻眼明。
有一段时间,家里来了客人,书房兼具了卧室的作用,终于让我发现自己当初的布置有多么不切实际——如果说三天挪动一次书桌是运动,两天挪动一次书桌是兴趣,那么每天挪动一次书桌肯定是无奈之举了——不胜其烦之下,我索性将书桌搬到西边的窗户下,背向而坐。这种微小改变的效率是显而易见的,书房一下子就不再显得局促,只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习惯,究其原因,竟然是由此生出了一种不安全感。
书桌安置在哪里一定是有讲究的。
唐人王维在《竹里馆》诗里这样描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他把古琴搬到了空旷之地,一轮明月下,青衣书生在竹林中静静地弹奏,轻挑慢捻间,竹风催动竹叶,音色明澈,音质相和,人与古琴,与竹林,与自然,尽显某种相通之处,忽然想,这是一件多么写意的事啊?
那么,要是把书桌搬到森林中又会怎样呢?
这个大胆想法一度让我激动不已,当木制书桌重新回到森林,回到生长的地方,仿佛失散多年之后再次见到亲人,一定可以唤醒被家具厂切割、刨磨、安装、油漆过的记忆,并且渐次从平整的桌面萌发出鹅黄的嫩芽。
而我会成为身旁那一棵最弱小的树木,与整个森林融为一体吗?
这仅仅出于我的想象,最终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而作罢,现实最大的可能是,将一棵树简化为一张书桌,安置在我的书房;但这也只是我的幸事,对于一棵树而言,它离一张书桌始终隔着漫漫行程,以至于最终能不能演变为一张书桌尚在未知之数。
由此,我基本认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离书桌最近的,不是我,而是森林。那些挥之不去的木制气息,是从终止了生长的年轮缝隙中泄漏出来的,它始于记忆,最后还将终于记忆。一如将一棵树与一张书桌并列,生长在哪里、安置在哪里,通通不重要。
值得庆幸的是,每当我开始阅读的时候,这张书桌都会适时为我打开一座森林。
低烧的椅子
有一段时间总感觉浑身乏力,明明什么地方不对劲,却又说不出,量一下体温,只有37度8,才发现自己一直发着低烧。
我怎么会发低烧呢?
想不明白其中缘由,也就没往心里去。可是,接下来的日子,体温始终在零点几度上下纠缠,原有的一丝担心渐渐弥漫,并且被放大了数倍,终于不得不借助于药物。不过,药物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用,低烧状况拖拖沓沓从仲春延续到了孟夏,直到再也拖不下去,才决定去见医生。
很多年没有进过医院,不曾想医院也快赶上了菜市场,闹哄哄、乱糟糟的,好像所有的病人都扎堆聚到了这里。医生门外拥挤着一张张蜡黄、焦黄、黯黑的面孔,我不知道属于自己的是哪一张,但应该与他们有所不同。因为医生看到我这张脸的时候明显露出了不以为然——这也是我希望的。可是当他用尽望闻问切一切手段依然无从确诊,终于变得焦虑了,喃喃自语:“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这样是哪样?医生的神情无端加深了我的恐惧。
“你先去验个血,再拍几张片子吧。”我听出了医生言语中的不自信。
忐忑不安中,我在医院里折腾了一天,最终的检查结果却是重要指标一切正常,这表明我的身体基本处于健康状态,可是持续了一个多月的低烧该怎么解释呢?
医生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也算是一种解释吧。
我给自己放了长假,理由很充分,我得了不治之症。
那段时间,我的心情极其低落,每天无所事事,也想不起要做什么事,常常不自觉地抬手摸摸额头,低烧,还是低烧,该死的低烧。
一场雷雨过后,天空重新放晴,潮湿气息冉冉上升,与明澈的阳光绞在一起,匆匆拍打着我的窗棂。我起身把关得严严实实的卧室窗户、书房窗户、客厅窗户通通打开,将室内污浊不堪的空气交换出去。
坐在凉台上,晒着太阳,我与这个夏日保持了相同的体温。
然后,伸手取出书报篮里昨天的报纸,展开来阅读,却始终心思不宁,忽然想到,以前在家里阅读的时候我从来不坐藤椅,藤椅展现给人的是一种闭目养神或小酌品茗的闲适姿态,而不是阅读姿态。
走回书房,我把书房椅子搬到凉台上,擦去灰尘,放端正,一套程序过后,才坐上去。
阅读的时候,我只坐这把椅子。
只是一把椅子。
椅子在哪里都是椅子,供人坐的,这是它存在的普遍意义。至于怎么坐,因人而异,有的懒散,有的严谨,总之要自己舒服。
而一旦把椅子搬进书房,就有了许多讲究,比如与书房气场相不相配、用材是否一致、舒适程度等等,丝毫不能马虎,否则就有暴发户之嫌了。
我的书房家具是配套定制的,这就省去了许多心思,只需关注椅子款式以及由此带给我的舒适度即可。我不是一个挑剔的人,椅子款式千变万化也只是做给人看的,不在实用之列;而把自己的肉身置于板材之上,同时还要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乃至忽视椅子的衬托作用,实在考量匠人的工艺手段。
我找到了一把适合自己的椅子。
这把椅子与我以前坐过的椅子不尽相同,座位部分有略微凹陷,呈现一个臀部形状,看着就有些特别,试坐一下发现恰好把臀部安置妥帖——只是一处小小的改动,却见了大技巧,不禁让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它。
我想说的是,阅读首先需要有一把好椅子。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椅子在书房里,对应的是书桌、书柜,三角关系,最节省的稳定支点,由此构成了书房基本的物质格局。
在那段时间里,我通读了一直想读而迟迟下不了决心的《二十四史》,这大致相当于我一年的阅读量。
而那把椅子的座位部分,也被磨出了暗红的光芒,照耀着我的疾病,一天天好转起来。
把书柜打开
书柜之于我的意义,远远小于书籍之于书柜的关系。
搬进新居之前,我曾一度寄宿在一间只有15平米大小的单身宿舍里。那间宿舍原来有两张老式木板床,看着挺结实,我留下了其中一张,床板上铺上塑料布用以安置锅碗瓢盆各种杂物;然后把席梦思床、写字桌椅、衣柜搬进去,尽管我已经把个人物品精简到极致,然而空间依然捉襟见肘,几大捆书籍中只有一小部分摞在案头,其他的只好随意堆放在犄角旮旯。
睡前我有读几页书的习惯,平时读的书就搁在枕头边,读时拿起来,放下就睡觉,很随意;案头也极少归整,因而显得房间里到处都是书,东一册、西一堆,杂乱不堪。可即便如此,只要是想读的书,我都能很快的从一堆堆书籍中把它翻找出来,毫无障碍——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只是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而已。
有时,我也会觉得委屈了这些书籍,它们给过我那么多美好时光,而我却不能给它们提供一处安身之地,由此及彼想一想,真是汗颜啊。
我对自己说:面包会有的。
我对书籍说:一切都会有的。
度过那一段生涩时光之后,我的生活步入了正轨,新居不仅让我拥有了独立的书房,而且还拥有了一架四开门书柜。书柜上半部分是玻璃开门,把书籍分门别类填放进去,露出书脊,书名、作者名就一目了然;下半部分是木开门,正好收容平时不常阅读的闲书——我用了两天时间才整理完毕,看着多年来积攒的书籍终于各有所归、各就各位,我心里那块内疚的石头才落了地。
一切都变得条理清晰了。
包括我的生活。
可是,我却在忽然间丧失了阅读的欲望,完全是无来由的,说不清,道不明。
我时常在书房里枯坐,发呆的样子,眼睛虽然没有闲着,来来回回扫过书柜,但却没有一本书能够投下倒影。
我这是怎么了?
随后一段日子,我有意疏离书房,把阅读和写作搬到了凉台上,那个相对密闭的空间让我恍若回到了杂乱无序的以前——我想时间会慢慢帮我弄明白到底什么地方出现了偏差。
我把书房当做了图书馆,把书柜当做了陈列架,可是查找资料的时候常常出现麻烦,因为我总是忘记书柜是有门的,手指直通通戳到玻璃上,戳得生疼,然后心思就打了岔,或忘记自己来干什么,或想不起要找的那本书放在了哪里。
一道门,将我与书籍远远隔开。
几次三番之后,我想是应该做些改变了。我找来小号起子,把玻璃门卸了下来(当然,木门还保留着),让书柜呈现出开放格局。此外,我的心态也随之做了调整,书房只是自己的一隅私人空间,干吗一定要摆出供人参观的架势?至于放置书籍最好的位置,一定是离心思最近、取用最方便的地方。
那天,当阅读告一段落,抬起头,我忽然发现自己竟然坐在了书房里。对于这一点,我没有表现出丝毫惊讶,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这一天就终会来的,不是昨天,不是今天,也会是明天。
我把那段丧失阅读欲望的日子归因于我以及书籍在身处新环境下的生疏感、陌生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感,毫无疑问,那段心路历程我们都需要经历并且适应。
至于我会不会再把玻璃门安上,那是以后的事。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呢?
第二天,我在书房门上贴了一张便签,上面写着:个人工作室,不欢迎参观,不提倡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