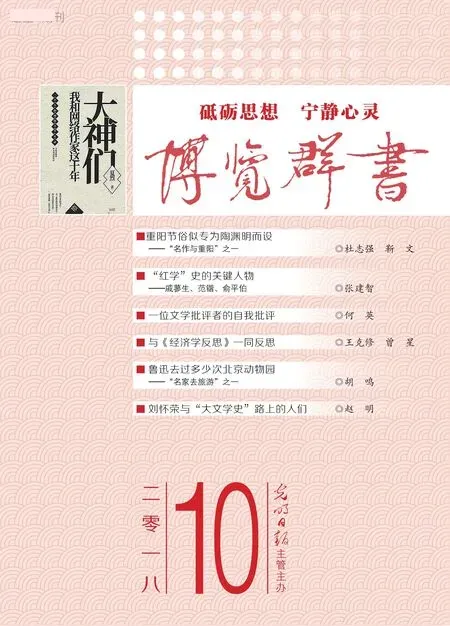给予农民政治上的尊重
2011-06-05倪雪君
○倪雪君

《农民的政治》,赵树凯著,商务印书馆2011年3月版,26.00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维持清代社会运转的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政府”。较之同时代西欧诸国,清代各级政府的财政规模都不算大,中央不太干涉地方政务,而是委任州县官全权负责维持秩序,另由士绅分担济贫救荒的责任。县级政府则立足于教化,既无具体管理农村的需求,也无主动改造农民的兴趣。套用西方的术语,或可以说中国农民在政治上虽无“民主”,但有“自由”。
这一“无为而治”的格局随着近代西方的入侵而骤然改变。“永不加赋”本是朝野共识,但自从清政府被迫将“富强”立为国策,其对税收的需求即开始增加。其后虽经政权更迭与意识形态变迁,政府对农村的汲取始终未减,对基层的管制也逐渐繁密。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在生产上才取得相对自主的地位,扭转了越管越严的趋势。以2006年废除农业税为标志,延续一个世纪的劫农济工基本收官,政府开始反哺农业。但财政流出的趋势刚获扭转,身份属性、土地产权等深层困局即浮出水面。20年来农村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又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新一轮改革已是破局在即。《农民的政治》(赵树凯著,商务印书馆2011年3月版)一书,可说是应时切题之作。
这本书集中呈现了赵树凯先生自80年代以来的经历与思考。1982年,作者进入被称为“九号院”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办公室工作。这个往日的清代礼王府,当时正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风云际会之所,作者在此工作近十年。作为农村改革的亲历者和观察者,作者曾到“弱”村禁牧,在“穷”村修桥,于“乱”村修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书中展现了不少鲜活的案例,并基此展开深入的思考。在《九号院之“老”》等文章中,作者回忆了“九号院”的运转模式和决策流程,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其思想渊源及思考脉络,对理解中国30年农村改革史也多有裨益。与其稍早出版的《纵横城乡》(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和《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相比,书中少有统计数字,行文也非学院风格,但说服力并未稍减。
这种说服力来源于扎实的调查基础之上。通过整理上访信件及实地接访,作者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勾勒出30年以来农民诉求的变迁概貌。改革初期,农村纷争多为“民与民争”,往往由因历史遗留问题或土地农机承包不合理而起。从80年代末开始,农民负担急剧增长,农民与基层政府间的摩擦日增。到本世纪初,征地问题又远超税费负担,成为社会冲突的主因。转折点出现于2003年,从那一年开始,国家渐次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全面取消农业税,将公共财政逐步覆盖到农村,使得上访事件明显减少,对抗程度减弱,形成了许多农民和基层干部心目中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但作者在2007年即已敏锐地意识到体制深处的巨大隐忧,这隐忧表现为农民对中央的信任显著提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反而越来越低。这一担心不久即应验。2007年至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因征地引发的诸多矛盾迅速蔓延。县市级政府在打破农村生计网络的同时,并未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以至数量庞大的“新楼民”有沦为“新笼民”的危险,从而引发了大量矛盾甚至对峙。
不过,民生疾苦仅是这本书的话由,探讨农民在政治中的角色与地位才是作者的用意所在。一如书名所示,“农民”作为“政治”的定语,应有体现其主体性的政治属性与参与方式。书中以相当篇幅来破除关于中国农民“该管”的误解。世界范围内的农民形象都离不开守旧涣散的影子,亨廷顿对农民“恒久保守”的概括,马克思对农民“一袋土豆”的比喻都曾为人津津乐道。农民政策的设计者也往往强调农民虽有“自发”意识,但很难形成“自觉”的利益判断,必须通过政策和制度安排加以引导。但就实际而言,农民在过去30年里恰是最具进取精神的群体。乡镇干部眼里农民难管的现状,也从反面说明农民的组织和博弈能力都有了极大提高。在作者看来,30年来的历史证明,不论多么聪明的学者,多么有能力的政治家,都没有能力去规划设计农村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观察和追随农民的脚步,因为农民的考量要远比设计者们更加理性。这一论断看似平和,却可能是解决当下困局的唯一出路。
目下农村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形势,与80年代已大不相同。80年代的第一轮改革是以“吃饱饭”为诉求的增量改革。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生产方式与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新型生产主体,之前因“解放生产力”而受肯定,之后因粮食总产徘徊不前而受质疑,褒贬之间的衡量指标始终是经济增长,显示了某种框架性的局限。而目下所面临的困局,较80年代更为复杂,因其不仅涉及经济因素,更需直面极为敏感的体制身份的革新。
赵树凯先生提出,“中国农民的政治属性之所以值得重视,根本原因在于,此农民不是彼农民”。当下,“农民工”、“农民企业家”等群体的存在,表明“农民”早已不再单纯指向一种职业,更多成为一种身份制度下的群体划分。他们的权利要求有相当部分与职业活动无关,甚至与土地、与农业生产无关,而是将矛头指向因体制身份而带来的医疗、教育等问题。而在关键性的产权分配层面,诸多土地冲突也超出了经济的范畴。作者用一段对话说明了这一困局:
当谈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时候,一些地方官员常常说,给农民的补偿已经相当高,甚至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比原来已经高很多,政府的安置也很好,可是农民还在“闹”,这是不应该的。但是上访农民的理由也是充足的。那是他们的地,不论卖多少钱,这是他们的事情,政府强行卖他们的地已经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而通过卖他们的地来赚大钱更加不合情理。
类似对话显示出双方的立场分歧已不能在经济框架内解决,而涉及根本的法权制度。
从大局来看,农村改革已到了关键之处。废除农业税带来的制度红利还未消失,以征地为焦点的农村冲突也未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新一轮的改革可谓恰逢其时,呼之欲出。有鉴于此,作者提出,应让农民成为改革棋局中强有力的博弈力量,通过张扬农民的权力来推进政策执行和改善乡村治理。“现代的中国农民,最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尊重。或许,唯有追随农民的脚步,才能让我们准确把握政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