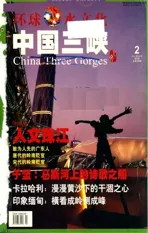敢为人先的广东人
2011-05-18何以端成有子编辑
文/何以端 成有子 编辑/陈 陆

广州,在西塔顶上远眺东南方的城市天际线,广州新电视塔、琶洲广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珠江啤酒厂等尽收眼底。摄影/吴吕明/CFP
古代边地之岭南
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流域之中,唯有珠江流域的中下游,因受南岭山脉的重重阻隔,进入内地艰难而遥远。梅岭古道和珠玑巷分别是不少先民入粤的孔道和重要栖息地。
广东古为百越之地。至今广东人的血液中仍含有古越族的成分,粤语中古百越底层核心词汇依然保持着约15%。百越散处江南广阔地区,很早便形成稻作文化。岭南越人长居亚热带,善渔猎习水性,喜食鱼贝类,尤嗜蛇、虫、鼠;断发文身,住干栏式住宅,笃信巫鬼,在商周之交过着比中原远为蛮朴的生活。越人的一些习性嗜好,与中原风土迥异,至今在广东人身上依然可寻踪迹。
秦汉之际,岭南人被称为“南蛮”。历史上中原曾多次大规模移民到岭南,极大促进了岭南的社会发展。最早是秦始皇发50万大军攻岭南并留守,再发罪徙等中原居民50万。秦二世之乱,赵佗建南越国与越人打成一片,大臣多是越族。经过他的长期努力,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完成了第一次大融合。东晋五胡乱华,又导致北方汉人大批南迁。此后的唐、北宋、南宋,每次重大政治变故或危机,均有大规模入粤的移民潮。

广州珠江新城广场。摄影/陈瑞光/CFP
这些不同朝代的移民多半有共同之点:不是被贬窜,受打击,便是忧亡国、避战乱。他们不少曾是中原社会上层,不乏满腹经纶之士。但故土失意,容身不得,长途辗转,才最终得以在远离权力中心、争斗尚少的岭南安身立命。此种经历处境,感悟会比得意时更深,自然在其意识中打上烙印。看看岭南各书院、各祠宇所奉祀的先贤,最普遍的是苏轼、韩愈、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有学者名之曰“遗民教化”,可见对于岭南民风的影响。
这样,无意中形成了岭南文化的一大特色:既奉诗礼传家,尊华夏正朔,又并不对权力中心亦步亦趋。北方普遍存在的重大社会弊端,例如对权位的阿附追逐乃至合污、对名教的盲目僵化尊奉、浓厚陈腐的官场习气等等,在广东向来是相对淡薄的。相反,甘居野朴自食其力的人生观、唯实不唯名的价值观、以结果而不以概念判定的是非观、散淡闲适我行我素的品味观等等,却一直存在。
以此观之,从六祖慧能南来驻锡韶关开启一代南宗,到始终秉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学术”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的离京谢绝台、港,甘以羊城终老,恐怕都不是偶然的。
广东人“讷于言而敏于行”,从容淡定,不太在乎别人的评论,低调而不热衷于争“名次”,加上无意中透着一股“我是南蛮我怕谁”的气概,便构成较明显的特立独行意识。
岭南民系可分为三大块:客家民系、潮汕民系和广府民系。客家民系已见前述。广府民系指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的广东人,广义的还包括整个西江、北江流域讲白话(又名粤语)的广东人。广府人通常被看作典型的广东人,具有性格开放大气、乐于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识重,务实精明、敢闯敢干等特点,很早就在岭南的经济文化中大展拳脚。
潮汕民系是指粤东一翼,包括今日潮州、汕头、揭阳诸地,潮汕话属闽南方言。其民多自福建移来,故又名“福佬”,向以刻苦耐劳、精耕细作、老乡认同感极强著称。近代潮汕人的商贸才能大大激发,极富创业精神,华侨众多。他们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只要有一点点土壤便能生根,开枝散叶乃至成林。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便是其杰出代表。
广东语言现象复杂。全国七大汉语方言,广东即占其三:粤、客、闽;而且粤、客两大方言的代表都在广东。
由于地理及社会生态的相对独立,这三大方言仍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大量古汉语的词、音、义诸元素。例如粤、客语之“粥”、闽南语之“糜”均系古词,普通话相应的“稀饭”已毫无古意。这类例子甚多。事实上用粤语朗读唐诗宋词,无论押韵还是平仄,均远较普通话为顺溜、为铿锵,更能体现原作神韵。

广东开平:正月十三泮村舞灯会。摄影/吴吕明/CFP

岭南大地。 摄影/Wu Lvming/CFP
含有多达九种声调及多种尾音的粤语,外人难以掌握,被戏称为“鸟语”。但粤语其实源于先秦到两汉的标准语言“雅言”,即宋以后的“官话”;在现代各种方言中,粤语保存雅言元素最多,规律依然清晰,是我国古代普通话的活化石。之所以能如此,全拜长期相对的封闭生境所赐。
相比之下,北方由于凡沧桑必尽历,受阿尔泰语系诸游牧民族语言的多次冲击,普通话相对于古汉语,早已“乱了”。
后发的蓝色文化
岭南文化虽然别具一格,清新可人,也出了像陈白沙、陈子壮、黄遵宪、屈大均等具真知灼见的名士,及岭南画派始祖居廉、居巢这样的大师,但它毕竟只是华夏文化的一个支流,长期为正朔主流所忽视甚至歧视。
事实上,远离华夏文明中心的广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但学术上总体比较落后,而且相关农耕文明的其他一切,也几乎无不落后。作为历朝流徙贬谪的瘴疠之地,广东长期为中原人所不齿,是毋庸讳言的。直到不久之前,一些北方朋友提到广东,依然会有“文化沙漠”的印象。
广东跃然而起,在全国占据一个显眼甚至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进入近代史的事。究其根本,是因为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使中国面临“千年不遇之大变局”,耕读至上的“黄土文化”已碰上致命的海外克星,海洋文化即“蓝色文化”优势突显。
广东历来先行一步的,便是其独特的海洋文化。
广东位于五岭之南,南海之北,域内大都山峦起伏,江河纵横,平原盆地相对较小,农耕优势不强;相反因海岸线长、江河出口众多、江海一体、海洋性特强而成为优势。粤民世与水居,天热喜泅,舟楫娴熟,不惮漂洋过海,尤以沿江沿海世代浮家泛宅的船民“疍家人”最为突出。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广东已形成通畅的古海道,秦汉就形成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港口之一。唐代广州取代了交趾成为南海交通之总枢纽,广东人率先成批到海外去做生意。到明代广州已有出口商品交易会了。
广州同时成为我国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从三国时期起,佛教、伊斯兰教先后传入广州。明清时又传来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以及近代一系列科学知识。岭南成为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最早设立学校、医院、报纸、杂志的地区。
明代中后期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衰落时期。但岭南却率先形成一些资本主义的工商企业,经济不降反升,明显领先于内地。
1757年以后,清政府闭关锁国,只保留著名的“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更使广州拥有了无可比拟的经济优势,在18、19世纪时其对外贸易达到了历史的辉煌高度,产生了富可敌国的潘、卢、伍、叶诸巨头,其中的伍秉鉴更被整个西方称为“世界首富”。鸦片战争前后,岭南已不仅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而且率先开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晋徽苏浙粤五大商帮中,粤商的海洋文化色彩最为强烈。
在老大封建帝国农耕文明屡受列强打击的日薄西山中,广东终于以先进生产力及先进思维的闪亮形象,脱颖而出。
最先奔向世界的群体
在广东禁鸦片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史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然而若以群体而论,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人群,无疑是广东人。
在林则徐之前,广东世代与洋人打交道者成千上万,上至办卖通译,下至贩夫水手,无不比内地的士大夫阶级对外部世界有更多的认识。这自然深刻影响到民风。以林则徐之睿智,抵粤后很快便从中觉察端倪,而从体制内一片“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中猛醒。
进入近代,岭南文化史无前例地居于领先地位,对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广东具有推动历史伟大意义的文化名人璀璨如星,具有领先全国意义的新思想一浪高于一浪。无论是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康梁戊戌变法,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领导辛亥革命,还是国共两党合作及北伐战争,都是以岭南为起点的。这些运动,对推进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均具决定性意义。
广东民风通达,坐言起行,在抵御外侮、除旧布新的血战中可以慷慨赴死。从黑旗军刘永福到致远舰邓世昌,从三元里抗英到广州起义均是如此。近代广东军素称“烂打”(敢打硬仗),如北伐时的“铁军”粤军第一军、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和滇缅血战的新一军,辉煌壮丽的恶战背后,凝聚了多少机灵勇猛的广东子弟的碧血。
广东华侨及港澳同胞众多。其血肉相连的巨大影响与无私援助,成为广东近代一个突出优势。所有重大历史贡献和思想创新中,几乎都有爱国华侨的身影。
晚清民初的广东,无论是物质建筑还是精神建设,都创造了一连串的全国第一。仅以人才而论:《资政新篇》的洪仁玕、《盛世危言》的郑观应、首倡节育优生和乡村建设的张竞生、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者容闳、“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飞机之父”冯如、“五四”时期“北陈(独秀)南杨”的杨匏安等,一众煌煌大家,都是广东人。首批赴美留学120名勇敢聪慧的幼童中,广东孩子便占了三分之二,他们回国后为中国的海军、工业、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开天辟地的贡献。此外,各艺术领域的不少鼻祖巨匠,如洗星海、马思聪、黄药眠、黎民伟、郑正秋、蔡楚生……也都是广东人。
成批叱咤风云人物的集中涌现,自必有民气根基。广东无疑是藏风聚气、人才辈出之地。

2009年8月20日,广东东莞石排镇塘尾古村落的“康王宝诞”民俗活动由来已久,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在每年农历七月举行。活动的七天里,有康王巡游、千人宴和福灯竞拍等活动。摄影/陈帆/CFP
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革命大潮过去,20世纪的中间几十年,广东渐渐归于庸常,人们重新过自己的小日子。
历史常常是惊人相似。在共和国的前30年,中国事实上已走向重新闭关自守;而广州却由于每年两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而又一次成为相当程度上的一口通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持续高压的万马齐喑之中,广州由于毗邻港澳的“南大门”地位而仍然维持了一丝惨淡的、珍稀的亮色。
但是历史的重大机缘再次降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公,将睿智的目光投向广东。
春天再一次降临南粤大地,广东人再一次“生猛”起来。他们迅速创造了一大批新的全国第一,从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到第一台移动电话,从改版的生活杂志《家庭》到鲜明的政经杂志《南风窗》,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到春节报纸“恭喜发财”。每个“第一”都引来普遍关注和轰动,也引来不少的猜忌与非议。途中尽管有曲折有压力、有人中箭下马,但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在广东诞生,终于尘埃落定。
广东人不负所托,30年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社会发展成绩单,无愧于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称号。
历史说明当初这颗棋子,下得真准。
为什么如此重大的历史机遇能落在广东?因为她毗邻港澳吗?因为她华侨众多吗?因为她临海方便吗?
或许这些因素都有。但广东民风之务实灵活、开放创新,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浓厚海洋文化气息,无疑更是决定性因素之一。邓公的“猫论”、“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等观点,在长期极左禁锢下,属石破天惊之论。在不但敢吃螃蟹还敢吃蛇、猫、龙虱,早就向往港澳人凭本事挣钱的广东人看来,最对脾胃;执行起来顾忌最小,而且常有发挥。在禁令如林、乍暖还寒的改革开放初期,“遇到红灯绕着走”便是勇敢的创新之一。
广东人自然也有一些局限,例如理论性不强,常被嘲为“只懂生孩子,不懂取名”。一些粤谚如“执输行头,惨过败家(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好机会)”,潮谚如“识字的捉不到虾(虾塘边写着严禁偷捞呢)”,又常折射出他们浓厚的草莽本色。
只是他们不会停步。广东,更有好戏在后头。
文化的传统与创新
广东人这30年也变多了。一是在发展的实践中提高,更多原地踏步的人落伍了;二是新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粤人子弟已崭露头角。尤其第三,是多年来“孔雀东南飞”的“新客家人”成了广东重要社会成分,广义地还包括大量来粤投资、贸易及工作的港澳、海外人士。这些外省外籍“新客家人”,能量甚高而且融入了这片热土,与原居民互补性极强,成为三大原住民系以外非同小可的第四家。
广东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巨变。珠三角都市圈已成全球最大都市圈之一,昔日的“桑基鱼塘”、“雨打芭蕉”已成稀罕之物。广东迅速国际化,人财物流天天潮涌,那种化外岭南的清幽早已不知所踪。污染堵车快节奏,成了珠三角的另一张名片,广东人还能洒脱淡定得起来吗?
传统岭南文化正呈现一种大开大合的格局。一面是粤菜、粤语歌、广东凉茶史无前例地全国开花;一面又是“食在广州”正受满街外省外国餐馆的挑战,不少老字号消失,“西关大屋”与老街坊日益减少,粤剧等地方剧种年轻观众甚少,广东音乐惨淡经营,广彩、广绣、广雕已经式微……老传统正受现代冲击而被边缘化,危机是毋庸讳言的。人们大声疾呼要保留传统,正是对过度“开发”的一种理性而微弱的抵制。
另一方面,这又是新的机遇。一场现代浪潮冲击过后,传统文化的价值常常更加突显。岭南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包容性、开创性、务实性是它的根本。这三性决定了它的强大活力。岭南的古代文化,原本就是融会了中原、百越与海洋诸文化的结果;而近现代岭南文化,更是贯通中西文明于一体的产物。
兼收而能并蓄,参差所以百态。今天,岭南文化完全可以融入新的元素,以一种无拘无束、宽广厚重、创造力旺盛的新姿态,开出更灿烂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