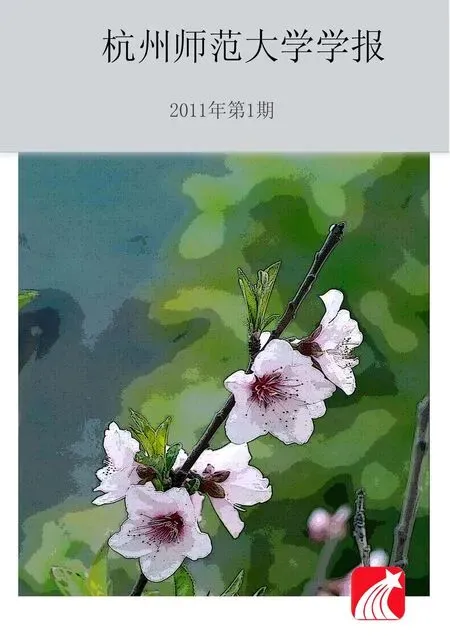空有圆融之境
——弘一大师佛教艺术的美学解析
2011-04-13徐承
徐 承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
弘一大师研究
空有圆融之境
——弘一大师佛教艺术的美学解析
徐 承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
弘一大师的佛教艺术,虽广泛涉及书法、绘画、诗词、音乐等多种体类,但其美学品格却是统一的,即在华严学圆融思想的指导下,融通西洋与东方、人文与佛道、净土与般若、空性与实相,从而在圆成妙有的艺术形式中寄寓缘起性空的佛家义理。在此,西洋美学观念的融入并未改变弘一大师佛教艺术的中国品格,反而化归于后者,并愈加张显出后者的特色。
弘一大师;佛教艺术;圆融
学界对弘一大师的研究,很长时间内都存有一些偏颇,仅仅把出家以前的李叔同看成是中国近现代艺术文化的启蒙者,非常重视其在俗时对西方艺术各门类的倡导、传播之功,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皈依佛门后所达到的新的艺术高度。其间的原因,主要是文献材料不足,误以为弘一大师出家后除书法外不再进行其他艺术活动,从而无法对其宏阔的佛教艺术创制予以整体的美学考量。所幸,随着本世纪初弘一大师佛像画被公诸于世,学界的实证研究亦迅速跟进,修正了所谓弘一大师出家后“诸艺皆废,惟书法不辍”的旧观点,提出了“诸艺未废,随缘耳!”的新说。①参见陈星《弘一大师绘画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文本条件和实证材料的具足,使得对弘一大师之佛教艺术展开综合研究成为可能,同时也更显出其必要性。本文结合弘一大师的佛学思想背景,对其佛教题材艺术作品展开分类解析,从中抽绎出统一的美学品格,从而尝试为此佛教艺术的经典个案作一美学史定位。
一 因缘际会的写经艺术
弘一大师身前好友范古农曾这样评价其佛教文艺活动:
师又尝以文艺为佛法导俗之具,若诗歌,若书画,(辄命弟子作之,)迄今或影印或刊板,流通于学界者,亦复不少,彼爱而宝之者即于佛法生爱敬心,古德有未出家前作谤法论者,乃出家则大弘佛法以忏悔之,师之以文艺作佛法之宣导,亦犹是也。[1]
范古农指出,弘一大师的佛教文艺创作包括诗、书、画等多个种类,且已通过现代传播手段广泛流通于学界。他还提出,弘一大师的佛教艺术能使“爱而宝之者即于佛法生爱敬心”,因而其艺术创制的目的是“以文艺作佛法之宣导”。所以说,只要某种艺术手段有利于佛法宣导,弘一大师便尽管以圆融的态度取用之。这是他在出家以后作有大量佛教题材绘画、书法、诗词、歌曲的原因。除了数量可观的艺术创制以外,弘一大师还积极推动佛教艺术传播,曾经计划在他所参与编辑的《佛学丛刊》中,专门编一个佛教艺术专辑。他在写给蔡丏因的信中透露:
如第一辑所选者,以短、易解、切要、有兴味、有销路为标准……。第二辑拟专收音所辑编者三十种。(或旧编者如《寒笳集》等……)第三辑拟专收佛教艺术。(旧辑《华联集联》可编入……)[2](《致蔡丐因》,P.168)
可见在弘一大师心目中,佛教艺术与那些“短、易解、切要、有兴味、有销路 ”的“佛书 ”,譬如他自己编撰书写的蕅益警句辑录《寒笳集》,是有相同弘法功效的。另外,弘一大师准备把他手书的《华严集联》编入《佛学丛刊》的佛教艺术专辑,说明他自己也信心满满地认为,这件以《华严经》为全部题材的书法作品,在佛教艺术史上实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事实上,这一部深广博大、为弘一大师所推崇备至的《华严经》,不仅是其佛教哲学的主要思想来源,同时也是他笔下瑰丽的佛教艺术世界的灵感泉源。论者指出:
今天我们看到弘一大师遗留在世间的书法,其中除经本、佛号、少数格言、古德诗句之外,几全是《华严》偈颂。[3]
(按:弘一大师)出家以后,渐渐脱去模拟形迹,也不写别的文字,只写佛经、佛号、法语,晚年把《华严经》的偈句,集成楹联三百,有人请他写字,总是写着这些联语和偈句的……[4]
书法是弘一大师佛教艺术创作的重要方面。在大量的经本、佛号书写之中,又数《华严》写经为其用功最勤。顺理成章地,在艺术质量上,《华严经》的书写也代表了弘一大师书艺的最高成就:
据他 (按:指弘一大师)自己说,生平写经写得最精工的,要算十六年在庐山牯岭青莲寺所写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含宏敦厚,饶有道气,比之黄庭。太虚法师也推为近数十年来僧人写经之冠。法师寄来时也极珍重……后来《华严经集联三百》印成,来信又说:
……昔为仁者所书《华严初回向章》,应是此生最精工之作,其后无能为矣。[4]
弘一大师手书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完全用工楷写成,体势庄严工整、字形方正宽腴、笔画丰满圆润,颇能显示华严学“广大圆融”的世界观。与弘一大师晚年的《华严》写经比较,这一幅尚属壮年之作的《十回向章初回向品》,并不那么清瘦、内敛,而是端正饱满、平稳凝重,很有一种愿令佛法常住人间的决心与气度。
曾领受过弘一大师晚年风范的陈祥耀,对其书体风格之演进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
法师 (按:指弘一大师)近来所创书体之演进,吾从其作品上观察,似有三阶段在:其初由碑学脱化而来,体势较矮,肉较多;其后肉渐减,气渐收,力渐凝,变成较方较楷的一派;数年来结构乃由方楷而变为修长,骨肉由饱满而变为瘦硬,气韵由沉雄而变为清拔,冶成其戛戛独造、整个人格的表现、归真返朴超尘入妙的书境。其不可及处:乃在笔笔气舒,笔笔锋藏,笔笔神敛。[5]
根据陈祥耀三阶段的说法,弘一大师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显然仍属于第一、第二阶段的创作。到了晚年,弘一大师的个人风格越来越张显,逐渐由其早期字体中抽脱出来,形成一种清拔、疏朗、消尽火气的新字体。此种书体主要有两个显著的形式特征:其一,字形清瘦。这是弘一大师晚年独有的风格特点,个中原因且容稍后再予论述。其二,用笔敛神藏锋。这一特点在弘一大师早、中期书法中——如《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即已现出端倪,到了晚期则日益显著,终至笔力尽收、蓄而不发的圆融境界。后一种美学特征显然是受华严学圆融思想的影响所致。
至于字形清瘦的问题,需结合弘一大师的书法美学观再作进一步探索:
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贴之派,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画观之斯可矣。[2](《致马冬涵》,P.252)
摒除传统书法碑帖流派之影响,全以西洋画的图案原则配置调和字体形状,这样的书法美学观,即使不是后无来者,至少也能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了。李叔同早年留学日本,受到系统的西画教育,归国后成为最早将西洋美术引入中国的艺术家之一。因此,他的西画技术和西方美学观念都是相当成熟的。其以西洋画的构图法配置书法字体形状的做法,一方面说明他正以西方思维重新处理传统书法的表现功能,使之朝审美优先的方向靠拢;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到他对传统书法之美学典式进行革新的努力。书法在中国是典型的文人艺术,经过数千年发展,逐渐形成以草书为代表书体,以“意”和“气势”为基本审美典式的传统。唐代张怀瓘《书断》曰:“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6]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种讲求“气势”的动态美学,其背后的本体论基础,是比儒道两家学说更为古老的“元气论”哲学。弘一大师的书法作品以楷书和行楷为主,间有篆体,唯独很少写草书。他以图案原则重新配置字体形状,带来的最显要的变化,就是打破了传统书法以“意”和“气势”为圭臬的审美典式,而使书法审美经验的重心向着静态的空间布局转移。所以弘一大师说,他“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贴之派,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揣摩”,其深层次的意图,正是要抛开传统以元气论为哲学基础的“气势”美学,而依西洋美术法则重建一种新的“形象”美学。
但是,西洋美术法则只是从技术上提供了开创新书法风格的可能,推动弘一写经朝着字形清瘦、疏朗之具体方向发展的,必定是彼时主导着他进行写经活动的思想观念。毫无疑问,这一思想观念只能是佛法。弘一大师晚年所写佛经,除《华严》以外,尚有律宗、净土宗和般若系的经典,这几派思想对其书法美学产生过影响应该是可以想象的。相比之下,律宗和净土宗的影响较易理解,前者重日常行为的恭谨严正,后者重发起慈悲之愿心,这一里外交合,正能产生一种谦恭而修长、祥和而清远的意识品格,这就部分解释了“清瘦”风格的由来。而般若系经典,如弘一大师晚年所写《金刚经》《心经》,主要讲缘起缘灭之性空,其所描绘的万法没有自性,只有偶然联系的片断式世界图景,其实正与这种以静态空间布局为主的书法美学相契合——笔画与笔画之间没有笔意或气韵的连接,每一笔都各居其位,凭借相互拼合而不是勾连,组成一幅疏松、朗逸的图案。不过,尽管这一静态图案刻意摒除了连绵的笔意,使各笔之间看似偶合,但在整体布局上,却有一个和谐匀称的结构——这固然可以用西洋美术讲求比例协调的构图原则来加以解释,但从哲学上看,却又完全合乎华严学一理交彻于万法之中,而使一切万法“事事无碍”的法界观。
弘一大师在一次关于写字方法的演讲中说:“我觉得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在于从学佛法中得来。要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才能达到最上乘的地步。”[7]弘一大师晚期书艺的美学特征,正是由西洋美术理念与其身上所具备的各派佛学思想因缘际会、互相调和融通而成。其历史意义,在于用佛教观法代替元气论哲学作为书法的本体论基础,从而开启了一条新的书法美学道路。
二 圆融无碍的佛像画艺术
如果说,书法的构图相比之下还不够形象,还不足于从直观上尽情表现《华严经》所载莲华藏庄严世界海之纷繁富丽、妙趣横生的话,那么,弘一大师的佛像画,尤其是他晚年纯以朱砂勾勒而成的罗汉画、观音画,则以无与伦比的生动笔触、惊为天人的高妙意趣,为世人展现出了几乎不可想象的佛国世界的宝相庄严。
弘一大师的俗家朋友许霏,曾在大师示寂后撰写了一篇《我忆法师》,其中有一处提到其精美绝伦的佛像画:
(按:弘一大师)晚年以其写字的笔法绘佛像,清新劲练,天趣盎然,每一线条,如生铁铸成,笔笔不苟,间有设色,也很雅淡可爱。[8]
诚如斯言,弘一大师的佛像画,多以线条勾勒,少有敷彩设色之作,与其早年所作西洋画截然两样。令人称奇的是,就是这些全靠毛笔勾线而画成的人物画,居然一扫中国传统人物画人体比例不调的弊病,将人物造型构造得非常精当——这不得不说是得益于李叔同早年留日时所打下的扎实的西洋画构图基础。
线描是弘一佛像画的核心技术。有论者指出,弘一大师所画佛像,许多都是有临本的。[9]此论主要着眼于佛像造型与整体构图。而弘一大师佛像画之不同于前人的地方,从技术上看,除了人物造型更为准确以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其线描无比流畅圆润、挥洒自如。中国传统人物画曾在长期实践与摸索当中,总结出系统的线描方法——“十八描”。晚清至民国时代的佛像画名家黄泽,一度运用 20种线描方法,画得佛像与古禅师像 160余幅。弘一大师的佛像画与黄泽的古佛画在人物形态上非常接近,从时间上看,前者大约作于 1929至 1933年间,后者则在 1924年结集出版、流布于世。弘一的佛画完全有可能受到过黄泽的影响。但蹊跷的是,弘一大师佛像画的线条却很难被归为“十八描”或“二十描”中的某一种,至多与其中的某些描法如兰叶描 (即钉头鼠尾描,弘一化用此种描法最多)、柳叶描、竹叶描、游丝描、琴弦描等比较接近,若细加比较,则能发现弘一的线条要丰满、流畅、圆润得多,且在起笔、收笔时率性而为,此起彼收,不局限于任何单一的描法。如此用笔,若欲穷究其哲学观念之来源,则还是要用华严学事事圆融、了无滞碍的观世界法方能解释得通。
落实到画面内容,弘一所绘佛像的神情举止,无论是庄严肃穆的佛陀,或是高贵仁慈的观音,又或是生趣盎然的罗汉,尽皆惟妙惟肖、亦真亦幻,几乎将那遥不可及的华藏世界佛国图景,在这一笔一画之间完美再现出来。
罗汉画是弘一佛像画中神态最为丰富有趣的一种。这些尚未顿入佛道,仍带有强烈人间气息的阿罗汉们,或慈眉善目,或凶怒暴戾,或愁容满面,或欢喜天真,总之,一个个都带着颇为夸张的表情,做着只有普通人才做的事情:挖耳朵、修指甲、拔脚刺、照镜子、打哈欠、缝衣服,甚至拿了放大镜看书,等等等等。恐怕在历史上,很少会有哪个画家或雕塑家敢让作为佛弟子的罗汉们做出这样的动作。但又不得不说,这些尚未修到菩萨果位的阿罗汉,从理论上讲确实应该于人间百态应有尽有才对。如果这样看,弘一大师的罗汉画还真的是合情又合理的。
相比之下,弘一笔下观音的神情举止就没有那么夸张,毕竟,那是正在修菩萨行,马上要获证佛果的一位。但弘一大师对观音的处理仍然是惊世骇俗的。诸多观音画里,有几幅专门表现她在紫竹林里独处的画面,或睡眼惺忪,或温婉娇柔,或孤苦可怜,活脱脱一个闲居空闺的人间女子。这一表现手法,与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一段观音描写颇有异曲同工之处。性急的美猴王为求见观音大士,不等诸护法大神通报,急步抢入紫竹林,看到了一位在私底下闲居的生活态的菩萨:她未及梳妆,头发散落,璎珞、素袍、披肩、绣带都不曾穿戴,只缚了一件贴身小袄与齐腰锦裙,两臂与双足都裸露在外,正坐在残破的箬席上悠闲地削着竹皮。这样一位菩萨,没有了高坐莲台、接受膜拜时的高贵与庄严,却让人觉得贴近人情、可亲可近。弘一大师的观音像亦是如此,既然尚未成就佛果,那就不必严肃得全无表情,尽可流露出人性的美丽的一面——这与民间传说中观世音菩萨以 32种身相示现人间、救苦救难的亲和形象,在理念上有着互通的地方。
当然弘一大师的观音画里,也并非没有表现其雍容华贵、高洁庄严之菩萨相的画作。这一部分作品,尺幅宽大,因而绘画技巧也趋于复杂,出现了苍劲有力的线描手法,以及山石的皴法、竹木花叶的点法,等等。这一批画作的整体视觉效果更为强烈,细节处也更为精丽,显然弘一大师在创作时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三 即空即有的诗词艺术
诗词偈语是弘一大师用于表诠佛教空观的重要载体。不过,弘一大师的诗作并非一味讲“空”,而是常用华严学“事理不二”之法融会“空”“有”二观,以期获证据称真实不妄的净土佛境。弘一大师后期的诗词偈语,便经常流露出这种即空即有、性相圆融的佛学品格。请看《竹园居士幼年书法题偈》:“文字之相,本不可得。以分别心,云何测度。若风画空,无有能所。如是了知,乃为智者。”[2](P.26)
偈中表达了极高明的空观义理。真理实相本来是离于文字的,但为了诠显实相,又不得不假借文字。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不起分别心,把文字诠显实相的过程看做是风在空中舞动,不执着于孰为风动之主体,孰为风动之客体,或者说不深究能诠之文字与所诠之实相的分别,而仅仅是观相,如此才能了知“色”“空”一体的真理实相。弘一大师此说其实是把禅宗空观与华严学的圆融无碍之法贯通起来了,一方面,如禅宗所说,文字乃是名相,不必执着于斯,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辨能所,实际上是援引了华严学的“理事无碍 ”说 ,认为“事 ”即“理 ”,“理 ”即“事 ”,等无差别,当一体观之。
弘一大师对这首佛偈一定非常喜欢,曾在三次不同的题词中应用这一偈语,其中一次甚至只改动了一个虚字。而另一首《题郑翘松卧云楼诗存》,则在化用之外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一言一字,莫非实相。周遍法界,光明无量。似镜现像,若风画空。如斯妙喻,乃契诗宗。”[2](P.26)
在这一首偈语里面,弘一索性不以文字为名相,而直接把它看作是周遍法界的实相。这其实运用了华严学一多相即、交彻融通的“周遍含容观 ”,在此观法之下 ,“空 ”与“有 ”,或曰“理 ”与“事”之间的关系,就如明镜现像、长风画空一般,相即相入,平等不二。
《马冬涵居士三异图题偈》在表意上更为抽象:“非三而说三,了三即是一。亦未可云同,那复分别异。”[2](P.26)此偈直接明言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差别之相本来等无差别的华严义理,并在末后的题记中以“亡言”二字,表达了欲纯粹观图画之名相而洞悉其所含融的空性实相的愿望。
弘一大师晚年著名的《清凉歌集》中,《山色》《世梦》两首是用以表诠般若空观的。这两首歌词,主题内容都是讲“空”,不同的是,前一首从“我”的角度出发,讲万法作为“我”所观之色,于眼根之中呈现出各种幻相,没有稳定如一的实体性;后一首从“法”的角度出发,讲人生一切诸事,永远变化循环、无止无息,便如一场梦一般无需迷执。两首都强调了佛法中“空”的一面,至于“有”的一面,则在《观心》当中体现出来。
这是颇令人踌躇犯难的一首词。弘一大师不是笃信净土,很少讲心性论的吗,何以在此将佛学义理的线索归结为心性一念,且并不将此心性看作客观外在的佛性,而是看作可以令人顿悟的“自性真常”?显然,如果认为弘一大师在这首词中短暂地投向了禅宗心学的一边,是不符合他的整体佛学思想的。那么如何理解此处“心性”的概念呢?回到文本。弘一在歌词中对“心性”的真义作了自问自答。首先发问:“现前一念,心性应寻觅。试观心性:在内欤,在外欤,在中间欤?过去欤,现在欤,或未来欤?长短、方圆欤,赤白、青黄欤?”言下之意,在纷繁变化、一切皆空的现象界中,何处才能觅见永恒不变的心性?回答是:“觅心了不可得,便悟自性真常。是应直下信入,未可错下承当。试观心性:内外、中间,过去、现在、未来 ,长短、方圆 ,赤白、青黄。”他说 ,就在四处寻觅毫无所得的时候,突然悟得自性真常,便是那纷繁变化、一切皆空的现象界本身。在这刹那之间,无常的现象竟与心性本体相即了。这是如何做到的?关键一句在于“是应直下信入,未可错下承当”。原来,获得顿悟的前提,还是那毫不犹豫的净土信仰啊!这正应了弘一大师那番取自蕅益智旭的谆谆教导:“但专持净戒,求生净土,功深力到,现前当来,必悟无己之体。悟无己,即见佛,即成佛矣。……倘不能真心信入,亦不必别起疑情。更不必错了承当。只深信持戒念佛 ,自然蓦地信去。”[2](《致邓寒香》,P.181)“真心信入”“不必错了承当”,这些承蕅益大师而来箴言,均被弘一大师化入《观心》的歌词。一言以蔽之,只需真心信入,获佛力加被,自然也就能从自心上悟得“无我”的真如体性 (亦即空性),从而实现空幻的现相与真实的体性之交彻融通——这便是《观心》一词的要旨所在。所以说,在弘一大师这里 ,“事 ”与“理 ”、“有 ”与“空 ”、净土与心识、现相与体性,始终都是相即相入、相辅相成,须臾不曾分离的。这样一种主客合一的自由境界,才称得上是“清凉,清凉,无上究竟真常”。[10]
1942年旧历九月初四午后八时,弘一大师于福建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圆寂。弥留之际,除留下数纸遗嘱和“悲欣交集”绝笔以外,还给夏丏尊、刘质平留有一首遗偈,表达了自己入灭以前最后的心迹:“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对于佛偈所表露的思想内容,弘一大师的弟子大空和尚已有一番详尽的阐释,颇觉与弘一的原意十分贴近,且予摘录如下:
大师遗偈云:“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此偈即谓大师自证念佛三昧,决定往生唯心本具之极乐净土也。昔彻悟大师《念佛百偈》有云:“一句弥陀,妙真如性,春满华枝,像含古镜。”“一句弥陀,大般涅槃,一轮明月,万里空寒。”一公之一偈,即此二偈之本义也。彻祖之二偈,本谓阿弥陀佛法界净土,极乐世界之万德庄严,即是当人妙真如性本源心性所本有之性具功德,空有同时,寂照不二,譬如朗月之有光辉,又若明镜之影含万像,阳春之遍妍百华也。盖镜含影像,则非离含像之镜别有明镜,此喻性具极乐净土,则非离本具极乐净土之真性以外另有妙真如性也。春满华枝,若舍华枝则何以见阳春景象,此喻心造极乐净土,若舍极乐净土则何以证大菩提心佛果常乐。天心月圆,而流辉耀彩,光明照于十方,此喻涅槃真空,而佛土佛身,庄严遍于法界。以是三喻,则可显知无上佛果,本源心性,本自具足万德庄严也。[11]
大空的阐释与笔者的论证虽视角不一,但得出的客观结论却是一致的:弘一大师深信净土念佛法门,其心性论观念,受到了净土信念的化导,最终在华严学圆融方法论的助力下,得出了“唯心本具之极乐净土”的不二结论。如此看来,若以“空有相即”“性相圆融”概括弘一大师佛教诗词的思想境界,应该不致与历史事实有太大的出入吧。
[1]范寄东.述怀[G]//夏丏尊.弘一大师永怀录.台北:龙树菩萨赠经会,1991.149.
[2]《弘一大师全集》编辑委员会.弘一大师全集:第八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3]陈慧剑.弘一大师论 [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141.
[4]蔡冠洛.廓尔亡言的弘一大师 [G]//夏丏尊.弘一大师永怀录.台北:龙树菩萨赠经会,1991.182.
[5]陈祥耀.弘一法师在闽南 [G]//夏丏尊.弘一大师永怀录.台北:龙树菩萨赠经会,1991.54.
[6]张怀瓘.书断[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66.
[7]弘一.弘一大师最后一言——谈写字的方法[M]//萧枫.弘一大师文集·讲演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129.
[8]许霏.我忆法师[G]//夏丏尊.弘一大师永怀录.台北:龙树菩萨赠经会,1991.227.
[9]陈星.弘一大师绘画研究[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77-102.
[10]弘一.清凉[M]//余涉.李叔同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180.
[11]大空.痛念弘一大师之慈悲[G]//夏丏尊.弘一大师永怀录.台北:龙树菩萨赠经会,1991.279-280.
A Complete Harmony of Emptiness and Existence——An Aesthetic Analysis ofMaster Hongyi's BuddhistArt
XU Cheng
(College of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China)
M aster Hongyi's Buddhist art includes several areas,such as calligraphy,brushw ork,poetry and m usic.A ll these have a coherent aesthetic character,nam ely,to harm onize the W est and the East,hum anism and Buddhism,pure land and prajna,vanity and realit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vatam saka's complete harm ony thought,and to place the Buddhist principle of vacant essentiality on the round and great art form.W estern aesthetic conception did not alter the Chinese style inM aster Hongyi's Buddhist art,but blended in and displayed it.
M aster Hongyi;Buddhist art;complete harm ony
J205
A
1674-2338(2011)01-0116-06
2010-06-12
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艺术教育)科研项目《弘一大师佛教艺术的美学解析》(YSJYJDHL10001)的研究成果。
徐 承(1980-),男,浙江长兴人,文艺学博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在站博士后,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美学史与思想史研究。
朱晓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