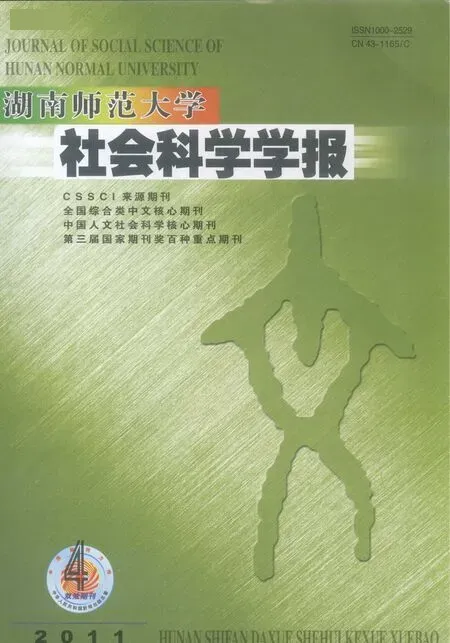解构主义时代的宏大叙事
2011-04-13谌林,刘鹏
谌 林,刘 鹏
(三亚学院 社科部,海南 三亚 572022)
解构主义时代的宏大叙事
谌 林1,刘 鹏2
(三亚学院 社科部,海南 三亚 572022)
解构主义是意识形态的集中表达,它把以历史意识完整性为旨归的宏大叙事作为叙述主线。在解构主义思潮对宏大叙事造成极大冲击和瓦解的当下,辩护宏大叙事的现实合理性与学术合法性,是走出当前思政课教学困境、维护该课程学术尊严的内在思路。
解构主义;宏大叙事;思政课;意识形态
就事实判断而言,意识形态的宣讲确实是古今中外一种普遍的行为。当下中国高校开设的四种思政课,正是宣讲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阵地。本文的核心关怀是证明宏大叙事的合法性,以及为何这种合法性是甚嚣尘上的解构主义所不能摧毁的;而本文所称宏大叙事主要指征思政课,因此为宏大叙事开显合法性也就是为思政课开显合法性。
本文简要的哲学分析表明,思政课教学遭遇的全部困境,包括部分学生的逃课厌学,社会普遍存在的对思政课意义和学理性的怀疑与轻视(认为这门课既缺乏现实合理性又缺乏学术合法性,并且与就业技能和职业发展无关等等),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处在一个解构主义思潮大肆蔓延的时代,而解构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又是技术时代权力分散和下移的必然结果。瓦解以历史意识完整性为旨归的宏大叙事是解构主义的本质,而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政课教学之本性又必然只能是宏大叙事的。一线教学人员要想自觉地坚守宏大叙事,创造性地守护意识形态,就必须从学理上认清时代特质,达到对思政课现实合理性和学术合法性的自觉证明。比方,解构主义为何能在上世纪末期应运而生并迅速获得广泛的同情?它如何极大地冲击了主流和传统价值观念,以至在一些人眼中思政课所宣示的内容,那些曾经被崇奉的伟大情操和高远理想,竟然一夕之间变成了虚伪可笑的东西?但是,尽管如此,解构主义真的具有彻底摧毁宏大叙事的学理潜能吗?
一、解构主义时代
把当下社会称为“解构主义时代”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这高估了解构主义——解构主义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尤其不可能成为意识形态。国家和政党及一切现实政治组织,就其本性而言决不可能是解构主义的而只能是宏大叙事的。因为政治组织必须具有意义和目的的确定性、统一性并表达某种超越现实的理想,这些品质和解构主义无法相容,奉行解构主义必然意味着政治组织的自行瓦解。但本文所称的解构主义已经远远不只是某种学术思潮(本文所称解构主义是德里达“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利奥塔“不相信宏大叙事”的结合体,指征个体性、反权威、意义消解等),而是一种足以左右行为模式的价值标准。中国社会自上个世纪解构主义来势日渐汹涌,影响及于社会心理和行为的方方面面,造成了对于传统价值与主流价值的极大压迫,宏大叙事遭遇普遍嘲弄与质疑,这是坚守宏大叙事的思政课教学必须面对并因应的重要背景。
本文没有选择使用“后现代思潮”一词,因为“后现代”这个词容易让人联想到某种生产技术水平,而本文关心的则是社会心理和价值标准的变迁,以及在此背景下思政课合法性的哲学根由。中国社会就其生产技术水平而言还谈不上“后现代”,但后现代哲学散播的思潮即本文所称的解构主义,则已广泛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这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并且重要的是,解构主义一词已经很好地表达了个体化、碎片化和多样性这些属于后现代思潮的核心观念,足以表征当今社会年轻一代在价值和心理方面的新型变化,而这些颇具解构精神的年轻人正是思政课教学的主体受众。
上世纪60年代,德里达、利奥塔等人倡导解构主义的初衷,是要反对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这一传统认为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万物虽然变动不居,但总有一个东西是恒定不变的,它最终指向世界的目的,这个东西就是“逻各斯”(logos)。“逻各斯”一词的内涵之广未免令人头晕目眩,其与中国哲学中“道”的意义之复杂性不相伯仲,且大有相通之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不变,道亦不变”,可见道的原初性和终极性。“逻各斯”既然无处不在和恒久不变,万物遵循“逻各斯”而运转,那么可以推演的是:其一,世界有一个终极法则,真理只有一个;其二,世界有一个终极目的,万物生灭演化,皆为此终极目的而生而灭而演化;其三,世界是理性的,理性终归是最后的胜利者。总之,“逻各斯”昭示着世界有一个“总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开头,有演变,有结尾,它在总体上是线性演进的,并必将最终达致完满的结局。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既是目的论和本质论,又是中心论和进步论,它似乎具有一种反对多元化和个体性、崇尚权威和整体的内在逻辑。在德里达等人看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基督文化传统,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到宣讲“总体性”的卢卡奇,无一例外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者,都是必须被“解构”的。何谓“解构”?“拆解完美结构”是也。把那些看起来庄严神圣的东西一一拆解,使其零乱不堪而不复庄严神圣。不仅不复庄严神圣,甚至显得丑陋和虚伪,而且永无恢复原状之望,此之谓解构。
解构主义的根本旨趣是反中心,反权威,反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抗思维路向,那么它提倡的必定就是非中心的、多元的、个体的、破碎和零乱的后现代价值观念。归结到政治哲学上,其本质诉求在于反对整体性而张扬个体性。整体和个体的关系是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它不仅直接与民主和自由问题相关,与政治和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和放任主义相关,而且透过对历史性质的不同回答而与历史哲学相勾连,这种勾连最终又必然关涉到本体论层面的根本立场。社会由个体组成,无数个体汇聚而成国家和民族这些整体。任何整体为了其目标和利益的实现,必然或多或少限制和牺牲个体的权益[1](P125),否则整体即不复成为整体,从而个体的权益也终将化为乌有。整体是实施个体限制的,但同时也是实施个体保护的;个体渴望自由和解放,但为了更大的自由和解放,他又必须接受整体的限制。这是一个永恒的二律背反。没有完全不考量个体权益的整体,因为个体权益是整体合法性的源泉,失去合法性的整体必将消亡;也没有可以完全脱离整体的个体,即使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例如老子(同时也是极端的反智主义者),其实也承诺了合作的必然性,不然他的权谋之术和“无为而治”就从根本上没有了着落。那么,解构主义是在何种背境下提出个体性诉求的?这种诉求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具有合法性?它具备颠覆宏大叙事的真理品质吗?
解构主义或任何理论都不会凭空产生。按照唯物史观的逻辑,一切言说方式都必定后在于社会生产方式,都只能以现存社会生产方式为土壤并受制于这种生产方式,都只能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总结与升华。诚如马克思所说:“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P83)个体要求摆脱整体统治与压迫的呼声古已有之,但在漫长的前技术农耕时代,无论中国或欧洲,这种呼声都显得太过微弱,以至难以获得宏大的回应。中国六朝时期也许是一个特例,那时“解构”成为时尚,个体性得到极度张扬,儒家的宏大叙事受到极度嘲弄,传统价值几乎坍塌。不过,这种情形基本上限于知识贵族的口头清谈,对社会大众和现实政治影响甚微。而且,除了艺术和“解构主义”本身,六朝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成就的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战乱频生,生灵涂炭,可见不合时宜的、早产的解构主义成了社会倒退在文化上的某种标识。农耕时代对整体性的绝对强调和对个体性的极度压制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必须把它称为整体主义才是恰当的。整体主义意味着对个体的过度化约,它要求个体必须完全服从整体,把自己当作整体的一个符号和工具,从而彻底丧失个体性。而个体性总是和自主性并肩而行的,于是整体主义也就彻底剥夺了自主性。整体主义当然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在世俗生活上它要求皇权至上,在精神信仰上它要求一神教,在意识形态上它要求绝对一元化,那么,在这种处境下,个体就被完全消解了。对整体优先性这种过度强调的整体主义,是东西方社会在前技术时代的普遍特征,它的合法性的根基在于农业生产方式,即产品剩余的有限性、交换的偶然性和生产生活的地域封闭性,一言以蔽之,在于生产效率的低下。当此之时也,整体主义的霸道与专断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似乎也是合理的和有利的,它至少可以维持起码的生产效率和社会公正。贡斯当在论及古希腊城邦民主时写道:“个人以某种方式被国家所吞没,公民被城邦所吞没。”[3](P28)素以民主著称的古希腊尚且如是,遑论其他地区的传统社会了。
以蒸汽机出现为标志的技术时代宣告了整体主义的终结,尽管在实际上这必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要求确立个体性,把个人从整体主义的铁血统治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价值的多元性和信仰的自由,没有言论和迁徙的自由,生产和交换的自由就无从产生,从而资本主义也就无法确立,就像中国宋明清时期的状况那样。在欧洲,从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到解构主义宣称“碎片化就是后现代”,整整间隔了一个世纪。为何尼采早已对传统价值施予了极大破坏,因而被奉为解构主义的鼻祖,但解构主义要直到上世纪晚近才臻于成熟并产生广泛影响呢?也许尼采那种虚无与唯美的、狂躁而杂乱的思想在未经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细致缜密的阐发之前难以获得学术尊崇性?也许上世纪前半叶“任务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还不存在或者不成熟?事实是,尼采思想只有在实际经过了尼—海一系之后,才终于达到了这一谱系的末端解构主义,到上个世纪中叶时,工业文明遭遇进步瓶颈,理性(实际上是工具理性)的神话早已不再被人毫无反思地迷恋了,因为物质的极大丰富并未造就期待中的美好生活,相反,心灵的枯竭、精神生活的贫乏、一系列传统德性的丢失,尤其是物欲的统治和压迫,使人变成了马尔库塞所称的“单向度的人”,即人的生命只剩下物质生活一个维度了。人们对“理性万能”和“社会必然进步”的怀疑,引发了对存在本身、对一切理想和彼岸的怀疑,并最终呼唤出了本文所称的解构主义。
就技术时代的客观要求而言,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破除英雄崇拜并警惕现代性的种种陷阱,这些观念的张扬实属必需。西方社会乃至当代中国的民主进步和制度改善,解构主义与有荣焉。不过,打碎整体主义虽然必需,打碎整体性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法的。解构本无罪,问题在于解构主义在“破障”的道路上未免走得太远,它要求彻底的个人生活,鄙视和反对所有宏大叙事,如此只能撕裂社会整体,使之成为无数碎片,这和整体主义当初造成的个体性丧失同样贻害无穷。今天的宏大叙事并不要求整体主义,它坚守的只是整体性,并且这种坚守建立在对“整体为个体而存在”[4](P67)的当代民主信念的承诺之上。这种宏大叙事不仅对解构主义充满“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而且也理应理直气壮地进行自我辩护,这正是思政课教学的职责所在。遥想魏晋六朝,玄学走向极端之时,引发的“口谈虚浮,不遵礼法,时俗放荡,风教陵迟”[5](P202)的行为,比照今日一些年轻人看不起先贤英烈的事功业绩,把愤世嫉俗看作旷达,把怨天尤人看作深刻,把德行高洁看作愚昧,把不负责任看作潇洒,种种情状,足令我人对此解构思潮无限蔓延之危害,深予警醒。解构止于整体主义之崩溃足矣,若危及整体性,则超越了它的合法边界规定。解构主义在民间的“行为艺术”即所谓“恶搞”,“恶搞”虽然强化了平等精神和娱乐性,但同时也撕裂了精英意识,埋葬了批判性,把社会生活降格为一种齐一化的、肤浅而麻木的娱乐版本,从而丧失了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将理想、献身与责任等高尚价值置于被嘲笑的地位。以当下社会价值观念的紊乱思之,解构主义难辞其咎。可以认为,德里达开启解构主义,正如郭象、王弼开启魏晋玄学,民智未必为开,魔鬼却尾随而来,知识精英的书斋臆语一旦赢得大众接受,其可怕如此。
二、坚守宏大叙事
利奥塔成功地将“宏大叙事”塑造成了某种贬义词,以至很多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都羞于承认自己是宏大叙事者,仿佛这个词不仅指征着政治化的独断,还指征着去学术化的肤浅,这是很不正常的。总结起来,利奥塔等人对宏大叙事的指控无非有以下几点:其一,与意识形态联系紧密,政治功能强大,从而总是有“将某种意志强加于人”的嫌疑;其二,与总体性、普遍性和共识具有同质内涵,从而构成了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对立面,威胁和排斥“个人叙事”及“日常生活叙事”;其三,“由于将一切人类历史视为一部历史,在连贯意义上将过去和将来统一起来,宏大叙事必然是一种神话的结构”[6](P51)。罗斯这里是说,宏大叙事总是意味着历史决定论,宣称未经证实、但或将证伪的人类历史的规律性。限于篇幅和本文性质,以下仅对上述指控分别给予简短辩护。
首先,关于宏大叙事的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化,本文认为不是要辩论“是与否”的问题,而是要辩明“是否应该或必要”,或者说“是否可能完全去除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宏大叙事当然具有政治功能,并且总是自觉地力图使之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如此,基督教如此,儒学和尼—海也如此。政治功能无非是指某种影响社会群体之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作用和能力,具有这种作用和能力的不只是某种思想体系(无论宏大叙事的还是解构主义的),还包括习俗和传统,也包括物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信徒就有指责“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传统,马尔库塞甚至批评广告商对商品不遗余力地宣传也属政治行为,因为他们利用大众传媒技术煽动公众的“虚假需求”,使之耽于物欲,从而遗忘和消解了批判精神。政治化是人的本质属性,不只宏大叙事具有政治功能,一切公共言说和行为都不可能没有这种功能。解构主义或后现代理论竟然是与“政治”无关的吗?它们批判整体的叙事不是为了破除一种“政治”并确立另一种“政治”吗?它们难道不是为了游说公众并希翼产生广泛的群体影响吗?在此破除、确立和游说中,它们不也是意欲“将某种意志强加于人”的吗?它们或许确实没有运用国家机器而只是运用逻辑去强加于人,那只是因为它们还不是现实的意识形态、还没有掌握国家机器而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都是说人们总是必然互相影响的,除了纯粹的生理活动,人们总是不得不与社会连接的,即人总是必须政治化的,区别只在于主流政治和边缘政治而已。反对一种政治化只不过意谓另一种政治化,而绝对不可能纯粹去政治化。如果一种叙事打算真的去除政治功能,唯一可行的就是根本不叙事。但是,难道一种异乎寻常的沉默就不具有政治功能吗?
其次,宏大叙事确实强调总体性、普遍性和共识,但并不必然反对差异性和多元性,也并不必然淹没“个人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理论家总是乐于创造过多的术语,其实这里所有的对立都可以归结为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对立。解构主义总是对整体性忧心忡忡,其实它应该忧心的本来只是整体主义,因为整体性是无法消除的,整体性是个体性的必然归宿。用海德格尔独有的悲呛语气来说,整体性是人的天命(海德格尔的原话是“技术是人的天命”)。传统时代的宏大叙事确实演变成了整体主义,但这并不意谓它只能是整体主义的。“国家”也曾经只是“君王”,但国家并不必然只能是君王,它也可以并已经演变成现代民主组织。而且,问题是,难道我们可以离开总体性和普遍性而存在吗?难道差异和多元不是建立在统一的背景下,而是反而可以脱离并清除统一吗?难道“个人叙事”可以完全替代宏大叙事,难道个体居然可能没有共识,而只有亿万互不同质的、互相不可通约的“个人叙事”?一言以蔽之,如果人类不想回到丛林时代从而失去人的类特性,难道个体性可以遮蔽整体性并且还是合乎法则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体性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也可以是美好的。如果“整体为个体而存在”成为普遍性和共识,那么个体的权益空间将日渐扩展,千万个不同的声音终将汇合成一个总的宏大旋律,这种充分包容个体性的整体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P273),谁能说这样的整体性会反对差异和多元性,会排斥或打压“个人叙事”呢?相反,这样的整体性正是差异性和多元性的统帅,建基于这种整体性的宏大叙事正是“个人叙事”或“日常生活叙事”的灵魂。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无非有两个含义,其一,它相信社会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8](P247),就是说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一样是有规律的,而不是纯粹被偶然性决定的;其二,可以科学地认识这种规律并预测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的由低级向高级、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就是说,人类历史是总体进步的。这种历史决定论并不排斥偶然性的巨大作用,不否定历史进程的曲折性,也不认为对历史发展的预测可以像数学计算那样精准,但是,只要人的活动总体上还是有目的的意向性活动,只要理性依然是人的根本属性,那么,“从现实的人出发,即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为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出发”,“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互作用的产物”[9](P8),认识和把握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预测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就决非神秘难解之事。唯物史观的宏大叙事确实反对孤立地看待社会历史现象,确实主张“将一切人类历史视为一部历史”,但它决不是什么空洞无物的“神话结构”,它只是一种视野开阔宏大的辩证结构而已。就学术真理而言,我们没有读到过一部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可以真的否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就历史实践而言,我们确实看到了一条历史进步的宏大轨迹,看到了人类自由王国的地盘越来越大,而古今中外形形色色关于世界末日和人类灭亡的悲观主义预言,却都如梦呓般一次次落空了。
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非决定论者对历史决定论的高度敌视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中间包括一些素负盛名的作家,例如哈耶克和波普尔。这些敌视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其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背境,就是前苏联专制主义和经济失败带给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强烈震撼。但是我们认为,前苏联模式并不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没有必然导向专制主义的内在逻辑——解构主义及一切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思想真正忧虑的东西,就是宏大叙事逻辑必然地导向专制主义——但论证这个思想显然不是本文的任务了。其实波普尔穷尽毕生之力,也并未否证历史规律的存在,相反,他常常是含糊和矛盾的。例如他为反对历史决定论而提倡的“技术的社会科学”,就容易让人疑心他又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他反对的立场上。他说:“这种方法论将导致对社会生活普遍规律的研究,以便发现一切必要的事实,作为谋求改革社会建构的人的工作依据。”[10](P36)无论波普尔怎样辩护,从这里都很难发现他的“技术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决定论有何本质区别。
观察和思考问题有两个角度,首先是整体角度。整体角度所以是必需的和合理的,只是因为人是社会的和不断衍续的,即马克思所说的人只能是“类存在物”。人的类特性决定了个体必须建构整体感和历史感。如果没有整体感,如果离开其他个体及其本质力量,任何个体连一天都无法存在;如果离开历史感,任何个体都将失去意义。何谓意义?意义只是超越。用理想超越现实,用无限超越有限。理想是什么?理想是一个绝对的善的物理世界以及由此决定的绝对的善的人文世界,那就是无限;何谓无限?无限就是也许可以在时空之中但绝不接受时空羁绊的主体的存在,对那样的主体而言,物理世界与人文世界都是绝对的善。因此理想就是无限,无限就是理想。这样的超越没有任何个体可以完成,因此一切意义都源于整体和类。“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这是具有整体感和历史感的人类特有的情怀。整体角度给我们带来了历史进步论和乐观主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纵我死也,有子存焉。子又有孙,孙又有子,子子孙孙,不可尽也”;这是何等豪迈而宏大的意义!但由于整体角度强调个体对整体的责任和牺牲,它确实有可能带来整体主义,从而否定民主与个人自由,因此我们还需要另一个角度,即个体角度。
离开个体就没有整体。意义在整体中产生,但最终必须由个体承载和分有。个体是重要的,因为个体是有限的。个体的有限存在时刻警醒着整体不应忘记其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不应忘记对个体的关怀和服务,否则整体就将成为空壳,或蜕化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名不符实的整体。个体角度张扬了生命的价值,唤醒了民主与自由,甚至也唤醒了终极关怀,但个体角度也造成了悲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甚至还造成了反对任何公共责任和义务的无政府主义。“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这种个体角度与其说是潇洒的,不如说是悲怆和孤独的。过度个体化必将最终消解个体,这也许是解构主义未及周详考量的。
用整体遮蔽个体生命是专制的,但渴望摆脱一切整体的一切约束,也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宏大叙事不拒绝对它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因为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本就是宏大叙事应有的题中之义。但毫无疑问,解构主义更需要批判,因为仅有解构是不够的,解构之后终将建构。理想被解构不会造成更好的现实,现实被解构必定破灭理想,因此,坚守宏大叙事,合理解释现实,在现实和理想、实然与应然之间建构良好的平衡,正是思政课教学应有的品格与操守。没有一种实然是完美的,但迷失实然的应然则永远不能成为应然。明乎此理,那么要求彻底个人生活、反对一切宏大叙事的解构主义可以休也。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2.
[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Dorothy Ross,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转引自程群.宏大叙事的缺失与复归[J].史学理论研究,2005,(1):51-60.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易杰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0]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Grand Narrative in the Deconstruction Times
EHEN Lin,LIU Peng
(Sanya College,Sanya,Hainan 572022,China)
The political course i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ideology.It can only be taught with Grand Narrative with the integrity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Given the case of Grand Narrative under extreme impact and the threat of disintegration exerted by Deconstruction,its intrinsic solution which can help the current political course get out of the predicament in teaching and safeguard its academic integrity is to defend the practical rationality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legitimacy of Grand Narrative.
deconstruction;grand narrative;ideology;political course
B08
A
1000-2529(2011)04-0037-05
2011-01-20
谌 林(1962-),男,湖南安乡人,三亚学院社科部教师,哲学博士;刘 鹏(1983-),男,陕西扶风人,三亚学院社科部教师。
(责任编校:文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