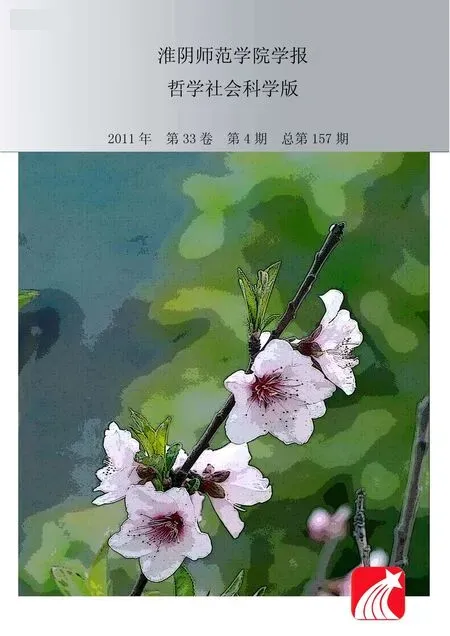萧一山对清代民生与民俗的研究及意义
2011-04-13田园
田 园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萧一山对清代民生与民俗的研究及意义
田 园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20世纪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十分重视对清代社会人民生计与民族风俗的研究,他在“新史学”思想的指导下,关注普通人民大众的生活史,其史著首次对清代各民族生计与习俗作了生动、丰富的记载与论述,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无论是他对于清代民生状况总的认识,还是对清代贫富分化社会状况的揭露,以及他对清代满、蒙、藏、回、苗等各族人民生计与习俗的全面阐述,都深刻反映出萧氏对清史研究领域的大力开拓,贯彻了其客观而全面撰述清史的思想,同时也是其“经世致用”史学精神的体现。
萧一山;《清代通史》;民生与民俗;史学精神
萧一山(1902—1978),是20世纪著名的清史专家。在其巨著《清代通史》中,他对清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十分深刻、全面。他认为:“一国之财政,与其社会之经济,人民之生活,有密切的联系,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者,即其例也。”[1]265“自来言郅治者,以民生与国计并提。”[1]387在财政经济与人民生活习俗密切联系、互相影响这一思想指导下,《清代通史》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展开对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其一是国家财政与社会经济;其二则是人民生计与社会风尚。前者包括了清代财政收支状况以及“以农为本”经济条件下的土地、人口、赋税等大的内容;后者则关注清代民生状况与风俗变迁,以小见大反映社会经济的全貌。本文即旨在探讨萧氏从民生与民俗的角度研究清代经济史的深刻意义。
一、关注清代人民的生计状况与发展趋势
(一)勾勒清代民生状况发展演变大势。
萧一山为清代人民生计发展变化的趋势勾勒了一条清晰的曲线,指出:“在乾隆中叶以前者,则可谓之‘安定时期’。在末叶以后者,可谓之‘衰敝时期’。过此以后,则时处于恐慌困顿之境,无复有太平景象矣!”
萧氏认为清初由于刚经历过明末的衰败与丧乱,“闾阎凋敝,城邑荒凉,然而户口骤减,谋生反易”。当时战乱减少、百废待兴的社会状况,使农民得以安心开垦土地,生计状况有所缓解,于是出现了顺治年间物价低廉、财货充斥的承平景象。这种良好的经济局面继续发展,“康熙六十余年,深仁厚泽,轸恤民生,蠲免之诏屡下,亦所以藏富于民,故物阜财丰,号称盛世”。至雍正年间,由于注重整顿吏治,“不特财政充裕,国计民生,亦较优焉”。到乾隆年间,社会经济繁荣,“民物丰阜,小民生活之安乐,盖以斯时为极盛也”。然而,此种繁盛景象没能持续多久。乾隆晚年,吏治腐败,财政靡费,逐渐出现“民穷财匮之景象”。至嘉庆时期“社会之现象,愈觉不安,盖人民连年困苦于刀兵之下,不能从事耕殖,而生产之力大减”。此种衰敝之趋势,顺“道咸同”年间继续下去,社会矛盾重重,黎民之疾苦尤难解决。自鸦片战争后,满清朝廷苦于内外战乱,而西方列强输入鸦片,给中国的民生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人民之所以颠连无告者,又不仅属于国内问题,洋货之输入,鸦片之供给,皆足敲骨吸髓”[1]389,于是清代晚期人民生计更加困窘,不堪其苦。
萧一山详细论证了清代人民生计的大体情形与发展的趋势,总结为:“当以乾嘉之际为鸿沟。”指明乾隆末年嘉庆初年是清代国家财政经济以及民生状况转折的枢机与关键。此后,人口迅速增加,物价大幅上涨,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使得人民生活状况迅速恶化,直至晚清出现了“民穷财匮”的困境。
(二)对清代富人与穷人生活状况悬殊的深刻揭露。
综观《清代通史》,萧一山虽然由于时代局限而没有明确的阶级观念,但却能从贫、富对比的角度阐述清代的民生状况,实属难得。
首先,萧一山指出清代富人过着十分奢华的生活。“富者日用百金,极其豪奢,锦绣裹体,高楼奠居,食前方丈,侍女数十”,如清代笔记《觚剩》文中所指江南季氏、山西亢氏等,以豪富闻名天下,“其居绕墙数里……月粮以外,每月犒高邮酒十瓮,烧肉三十盘……曝裘于庭,张而击之,紫貂、青狐、银鼠、金豹、猞猁狲之属,脱毛积地,厚三寸许……珠冠象笏,绣袍锦靴,一妓之饰,千金具焉”。并据《啸亭杂录》所记载,某内阁大臣奢侈异常,“舆夫皆着毛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云”。而身处清代盛世的曹雪芹撰写的《红楼梦》对于封建贵族大家庭奢侈生活的描述,十分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贫富不均的弊端,如文中刘姥姥说:“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正是富人奢华生活的写照。
由于富豪多半为朝廷官吏,萧一山对于清代吏治腐败、中饱私囊的现象十分痛心,指出:“民谚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殆为实录”,“富人豪奢之状况,大抵如此,其与贫人较,一饭之值,可抵中产数年之费,此种人大半属于官吏,因官吏皆聚敛峻削,中饱自肥者也”[1]400。的确就是当时的社会实际状况。“富绅大贾土豪的奢侈情形,要是和权奸朝贵来比,仍属小巫大巫……河员盐政的积弊之深,用费之汰,更是人所习知。”[2]96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配不均,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和明显的阶级对立。清中后期,贫苦农民不堪生活之苦,屡屡揭竿而起,即是当时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
对于清代贫穷人民的生计状况,萧氏也十分关注。他认为当时的穷人生活是困顿不堪的,“普通人之生活,每饭不过一二十文,虽由物价之低廉,亦生活程度之简陋矣”。在《儒林外史》中曾有记载,范进的丈人胡屠户说:“老人家每日小饭菜,想也难过……这几十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还有如描写“身上衣服,甚是破烂”等,说明当时穷苦百姓的生活状况是衣衫褴褛,三餐仅吃白饭、小菜、豆腐之类,住的往往是草屋茅棚而已,更有甚者,“若特别疾苦,掘草而食,或失业困于草野,至一钱而不名者,则并此而不如矣”![1]402可见清代穷人生活的窘态。
对于满洲贵族逐渐陷入困顿的原因,萧氏有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最要者,不过安富尊荣,虚糜无度而已,犹之依赖他人,不事生产,坐吃山空,终必荡败。”而朝廷给予的赏赐越多,惰性也就越深厚,这种安于现状的惰性,实为满族旗人生计日渐艰难的原因。虽然满清朝廷对此种状况也予以过重视,甚至采取了“赈济”、“偿借”、“给地”等多种措施予以改善,其结果仍然不见乐观,而只足以救济一时。并且始终无法改变“八旗治生苟且,糜费极多,官兵所给之米,辄行变卖,而银两耗去,米价又增,于是后悔无及”[3]的恶性循环,而逐步落入困顿之境的结局。可见,萧一山对于清代社会问题的分析和认识是全面而具体的。
从萧氏的论述可见,清代的阶级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但美中不足的是他未能提及阶级斗争。实际上,清代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导致了反抗地主等各种形式的抗清斗争,乾隆、嘉庆朝的王伦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白莲教、天地会等结社和起义的斗争都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这些反抗活动,较之抗租抗粮、索赈抢米更有组织、更加持久,对封建政权更具有威胁性。”[4]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来看,萧氏对于经济与政治之间密切联系的考察略显不够。
二、对清代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与民间风俗的研究
萧一山作为一位卓越的史家,在考察国家财政、社会经济与人民生计这些烦琐而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十分关注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等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与风尚,实可谓撰述全面而精博的清史著作。萧一山同时对不同的民族生计状况作专门论述,十分明确地反映了其重视中华民族整体的“大民族”观念和各民族团结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进步性。
考究萧氏撰写民风、民俗的原因在于,虽其不同于经济、政治问题那样直接作用于社会,但其作为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氛围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社会风俗的形成明显受到经济与政治状况等多方面的影响,而形成以后,又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对于社会经济和国家政治产生一定的作用。至于同一民族内部,由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等,直接生成同样的风俗习惯,而不同的民族之间则习俗各异、特点分明。
(一)重视对清代汉族人民生活习俗的记述。
虽然汉族内部具有十分悬殊的贫富分化,生活的状态各不相同,但是汉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有鲜明的特征,对此萧一山逐一缕述。
关于社会风俗,萧一山认为:“人生四事:衣、食、住、行而已。”故大体从这四个方面加以论述。在他看来,不论是衣着服饰、饮食方式、住宅建造、交通出行,都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紧密联系。比如他认为“自清人入关,挟其政治之力,以改变社会,汉人之最受影响者,厥惟服饰”。
其一是对于清代服饰体现社会等级的论述。
服饰之中,首先是“冠”,即帽子。萧氏指出帽子分为官帽与便帽两种,官帽为官吏所佩戴,而便帽是普通民众所使用的,可见清代社会等级鲜明。官帽又分为冬帽与夏帽两种,或称为暖帽与凉帽。官员所用暖帽“其形圆,其缘用紫貂,或海龙之大毛……高等官吏,用薰貂之冠,非一般人所能假借也”。反映了统治阶层的豪奢。至于一般百姓所使用的便帽,“六瓣合缝,缀以檐,如筒,取六合一统之意,初创于明太祖,俗名瓜皮小帽”,这是至今还在流传的清代传统服饰。而“毡帽、斗笠、草帽,则需费甚廉,下级之人,多服用之”,从这些穿戴也可看出社会等级的差异。
帽上的“顶子”也有明显的等级差别,萧氏指出:“要视戴帽人之阶级身份而不同。清制:一品官用红色之宝石,二品用花红色之珊瑚,三品用亮蓝色之宝石,四品用暗蓝色之宝石……七品八品九品皆用金,然亦有等差……民人所用之顶,多用绢丝编结为之,时亦有用假石模造者”,“又大臣中有于冠后垂孔雀翎者……六品以上者戴花翎,普通皆一眼,公冠双眼,贝子则戴三眼花翎,康熙时,特赐施琅,遂开酬庸之例”[1]403。这些严格的帽饰规定充分体现出清代官吏的上下等级之别,其制繁复而森严,可见封建等级制度是无处不在的。
至于衣服之类,萧一山指出可以分为袍、褂、裤、袄、裾五种,袍和褂为四季之长衣,官员的袍和褂上有丰富的颜色与图案,“有官衔者,用青色之贡缎,前后腹背,着有大花纹之黼黻,其纹文官绣鸟,武官绣兽,又各以等级而不同”,并列表详细加以说明。由此可知,从服饰着装之不同,亦可判断其官职、品级的差异,且颇为明确。对于清代十分有名的黄马褂,萧氏指其“初为领侍卫内大臣等巡幸扈从銮舆,以壮观瞻”,而后,凡大臣“有功绩者,朝廷特赐之,以示宠异”,因而成为清代帝王笼络群臣之一种方式。
还有一类为“履”,分为鞋和靴两种,也因为贫富不同而穿着不一。普通靴“其质则绸缎绒布等类,底则毡、毛、披、布层叠而成”,穷人则不同于此,“又有麻鞋、草鞋,穷人所用”。至于妇女则缠足,鞋尖,而“旗女天足,鞋底作u形,似马蹄”。记载可谓细致入微。
萧氏详述清代服饰之沿革,并指出:“虽有百年不变之礼,断无十年不易之俗、尤以服饰随心意时尚之所好者,其沿革尤难究诘。”[1]405事实上点明风俗、习惯虽然有一贯性,但是与封建礼教相比较而言,是更容易发生改变的。
其二是关于汉族人民饮食生活的阐述。
关于清代汉族人民的饮食民俗,萧一山也论述详尽。他首先指出,“食之品类,大别之,有饭、粥、面、饼、馒头、汤、菜等类”,并列表详细分类。还提到点心类有:“饽饽、火烧、烧饼、油条、芝麻糖、馄饨,粽子、饺子,糖糕、枣糕、散子、包子等及作坊所制之各种茶食。”[1]407这些难得的材料让我们十分清楚地了解到清代人民的饮食生活状况,也反映了中华传统美食的丰富多样、蔚为大观。
萧一山对清代人民的日常饮食习俗也颇有研究。他指出:“茶为一班之饮料,普通视之如饭食等,盖初仅视为消遣之品,渐而至于日用必须。昔人言品茗,今人言喝茶,即可知其事之殊异矣。”对于清代贵族生活以品茗为风尚,萧氏提到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多有描绘,如对妙玉请宝、黛品茶的描述,极其细致地反映了当时的品茶习俗,甚至连茶水都要细分为“旧年的雨水”、“梅花上的雪水”等,所用茶具也从瓷器到形制不同的玉杯,十分讲究[5]。萧一山指出当时的“贵族士人阶级,知以品茗消遣为事”,不仅煮茶有法,还讲求水质好坏。至于茶之品类有“如武夷山的花香、小种、名种、奇种四等,品茶有格,如清、香、甘、活四类”。恰好反映了当时封建士大夫和贵族们的附庸风雅的生活风尚,颇有追求生活品质和格调的意味。实际当时的“下级社会之民,或竟不得饮茶”,正所谓不同的阶级地位具有不同的生活状态,清代社会阶级的各种矛盾也就蕴涵于其中。
饮酒的习俗由来已久。清代酒之种类繁多,以米酿造的有“绍兴酒、女儿红、大曲酒、茅台酒”等类;以高粱酿造的有“太白酒、汾酒、兰陵酒、麻姑酒、高粱酒、高粱烧、莲花白”等。萧氏指出酒的用途多为应酬、成礼,而清代不少饮酒的学人雅士也常以“但愿长醉不愿醒”的风范自命。
其三是深入揭示清代民居建筑形式的内涵。
萧一山认为清代百姓所居住“房屋之构造,随贫富而异同:有瓦屋、有草屋、有土屋”,其中草屋与土屋甚为简陋,此外南方还有穴居、舟居者,虽然是“上古之遗风,亦生计穷苦之所致也”,可想见贫苦百姓住宅之简陋、生活之艰辛。房屋的建筑风格不同,南方与北方差异也很大。普通之房屋“客屋多在外院,寝室率居内庭,士人则有书房,农家则有仓屋,皆以各人之情境,自为配置……门常南向,取向阳之意,门前有影壁,所以防窥伺,壮观瞻也”[1]408。然而实际上,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也深刻影响着住宅的建造风格和式样,如“有官阶者,则石狮巍蹲门侧,旗杆高插云表,若普通之家,则并影壁而无矣”,并且“房屋建造,平常人不得用兽头,无官职者,用兽头亦不得用开嘴兽,开嘴兽惟官家用之。正房与大门,不得成一直线,须稍偏斜,影壁不得成八字形(官四品以上者始得如此),此一般人之禁例也”[1]408-409。可见房屋建造形制讲究颇多,内容甚为复杂。
因此,萧一山深刻认识到“盖阶级之制未除,衣住形式之事,皆不得不受官府之干涉,所以别等差辨贵贱者”。可见他承认封建统治的内容最终会决定封建统治的形式,并且政治地位的高低不同决定了衣食住行的方式和差别。
其四是传统的出行方式。
萧一山认为:“中国在衣食住行四事上,惟行路最难,交通不便,则文化之沟通与进步,皆受阻碍。”清代社会的出行方式的确如此,交通工具可称得“十分简陋,数千年甚少进步”,其中行车、坐轿、乘船,品级各有不同。南北地域略有差异,“南人行船、北人使马”,各有特色。至于轮船的发展始于曾国藩编练水师,铁路交通也是西方引进的交通方式,可见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旧的经济形态中难以孕育出崭新的交通方式,而生产力的进步也最终推动了清代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解体。
其五是对于南北风俗差异的鲜明对比。
在中国地大物博的地理环境之下,南北生活习俗也有较大的差异。大体看来,在服饰习惯上,“南人尚华,北人尚朴”;以饮食习俗而论,“南人食米,北人食麦”;以住宅结构来看,“南多用瓦,北多土砖”;而以出行方式论,则“南人行船,北人使马”[1]409-410。
萧一山认为风俗之形成除了气候、地理、民族等因素外,经济的因素也不可忽视。萧氏指出:“我国古代,精华在西北,自唐宋以来,移于东南,故清代东南文物之盛,甲于全国焉。”政治中心的南迁,是导致江南土地开垦、经济发展、文化繁盛的重要因素。并且“江南气候温和,土地肥美,物产丰饶,居民资生较易,因是浮靡之习,亦较他省为著。清初,盐商富豪,竟为奢侈,声伎服饰,园林池馆,斗富矜奇,一时风尚所被”,这也着实是“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暴殄日甚而不知返”[6]。反映了江南生活状况不同于北方之处。
时至今日,社会进步、交通便利,南北方生活方式的差异普遍存在,更可证萧一山撰述清代南方与北方人民生活风俗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
(二)撰写各具特色的满、蒙、回、藏、苗等族人民生计与民族风俗。
清代,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意识大大加强了。清代帝王重视民族的治理和民族关系的处理。康熙帝平定准噶尔部落噶尔丹的叛乱,稳定了蒙古与回疆民族的各个部落,促进了清代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同时也推动了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雍正、乾隆时期,在青海和新疆用兵,平定了西部边疆的叛乱,改变了蒙、藏、回各部落之间“连年战争,各部乏食,彼此争夺牲口粮食……而自相残杀,秩序大乱”[7]的混乱局面,保证了西部边境的安宁与进步。
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居于全国统治民族的地位,萧一山首先论述“满族人民之生计渐穷”的状况。他指出:“自清人入关,满族在中国社会,有特殊之权力,无论政治上、法律上皆占优越之地位。”然而历数朝以后,满洲八旗之生计日渐窘迫,对此,萧一山作了一番分析,他认为“顾经济之情形,甚或每况愈下,日困一日,斯虽限制生产,养尊处优之所致,抑亦人口增加,风气不良之结果矣”[1]411。关于满洲八旗人口之增加,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也曾指出:“合妇女老幼,当在百五十万口内外,比之国初,殆增七八倍无疑。”[8]与萧氏旗人生计日渐困顿乃由人口迅速增加所致的论断一致。萧氏还认为满族人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仍住关外,从事耕牧者;然而内地旗人,住房由官府拨给,与汉人分别而居,有地不能耕,一味仰赖口粮,极意挥霍。由于满族主政,八旗尤其受到诸多的优待,但是他们生活豪奢,喜好鲜衣美食,酒肉烟草,耗费巨大。“曾有赌博,赴园馆,斗鸡,斗鹌鹑,斗蟋蟀,雇人当差,放印子银两,典钱粮米石……以玩好为所务也。”[1]418雍正曾有上谕指出:“近来满洲等不善谋生,惟恃钱粮度日,不知节俭,妄事奢靡……但兵丁等相染成风,仍未改其糜费之习”,即是指出满洲八旗这些问题之所在。
萧一山充分重视清代蒙古族人民的游牧生活。萧氏论述蒙古人民的生计有“太古遗风,以射猎牧畜为职业也。大漠南北,地广人稀,民无奢望,衣食概称足裕”。而作为以游牧生活和畜牧业为主的民族,每当“春夏秋日,或则游牧,或则狩猎,逐日游走于山林原隰之间,一届冬寒,则闭包门,闲居叙天伦乐事”[1]421。这种简单而质朴的生活方式也颇有悠闲的乐趣。蒙古民族擅长骑射,性喜狩猎,广阔的草原沃野千里,便于发展畜牧业,主要牲畜有牛、羊、马、驼四种。其中马的优良品种以“内蒙乌珠穆沁为多,优美强健,发育匀称,素有梁骥之誉”。蒙古人以游牧为主,而后“亦稍稍知有土地之观念矣”,逐渐也开始发展农业、手工业等多种生产方式。
萧氏认为清代蒙古民族的服饰习俗,与所居漠北之生活环境有关,“大概王公着官服,补挂袍套,完全清制。一般人服用棉布,领袖宽大,腰束条带……冬着老羊皮袄,不制面,暑天多赤足”,蒙古妇女的服饰特点为“服宽袖阔,裙辄拖地”,“处女编发,嫁而束髻,好装饰”。论及其饮食以“兽肉和乳类为大宗,有奶茶、奶酒、酸奶子等以供饮料;奶油、奶豆腐、奶果子等以供食品,此在富贵家为然,若中苦之家,则专以羊肉充饥,羊汁解渴而已”[1]423。由此可见贫富分化在各个民族内部都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蒙古社会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牧民各阶层的划分,都是清朝维护蒙古牧奴制的一种手段。”[9]286除了少数王公贵族有府第以外,大多数蒙古民族的平常百姓居住在毡房帐幕中,俗称为“蒙古包”,这种居住方式是十分宜于游牧和畜牧生活的,因为他们多逐水草迁徙而无定所。萧氏指出:“内外蒙古自清初先后归降,历世列于藩卫,惟额鲁特则常为敌国。自世宗定青海,高宗荡准部,而毡裘重酪之族,始完全归中国之制矣。”也可得知蒙古各部与清朝之间的密切交往及前后的复杂关系。
萧一山关注清代回民、藏民、苗民的生计与习俗。按照同样的宗教信仰,将回族人民分为南疆回人、缠回、哈萨克、布鲁特等部族,他认为这些部族之生活“逸为异位而一体,风俗习惯,大略相同”。
萧氏认为“新疆之回,安土乐业,家多小康”,其生产的农产品十分丰富,著名的“哈密瓜为缠民特产,形似蚕茧,皮绿色外缠白丝纹为蛛网,味甘而脆”。服饰上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男女的帽饰衣着都十分华丽,饮食特色是忌食猪肉最严,生活居住之处“多平房,粉垣四周,上出天窗,以纳日影。富贵之家,彩梁画栋”[1]429。萧氏指出回族各部族人民与中原百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哈、布两族,在清为藩属国,其处于近边者,贸易相通,声气相应”。民族习俗虽有不同,相互交往仍为密切。萧氏处于20世纪前期,即能重视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正反映出其进步的史学思想。
萧氏撰写清代藏民生活也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藏民笃信喇嘛教”,“由于藏传佛教的影响,使藏族的文化、艺术大部分带有宗教的色彩……能从中看到藏族人民的聪明才智”[9]311。其生产方式“有耕稼者,然大半为游牧之生活”,手工业发达,“陶器、造像、土工、石工,皆极精巧”,并且织物种类繁多,“毛织物有氆氇、蚕丝、栽绒、细毯、球子、细花布等,其中,以羊毛制成之种类尤多”。其所用香料是“有以诸种香木制成之绵香,名曰‘藏香’,多输入于内地”。藏民以青稞酿酒,男子喜配刀,女子挂佛珠,这些生活习俗既有地域特色又与其宗教信仰颇为相关。其民“富者戴珍珠帽……外镶以金,绿松石为顶,周围密缀珍珠,有价值千金者”。反映了当时的藏民内部贫富分化已经很明显。关于藏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萧一山也有明确论述,指出:“拉萨有自克什米尔移住之回民,专从事于布帛及银之贸易。有自不丹、尼泊尔等处移住之人民,专业金银、铜锡玉石及妇女首饰等细工。”这些内容不仅反映了藏族与回族等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而且反映其与西南相邻国度之间的贸易与文化往来也十分频繁。
萧氏指出苗族地处中国西南地区,种类复杂,“散处六省,虽部族各异,而习俗大概相同”[1]435。其生产方式为“男耕女织,妇能蚕桑”,服饰上喜着短裙,“胸前方绣以银线饰之”,而布艺精细,品种繁多。萧氏指出:“其装饰之美,织工之巧,可以想见矣。”苗族内部也有明显的贫富等级分化,萧氏认为“其聚而为村者为峒,推其长曰峒官,峒官之家,豪侈相胜”。可以推知其族内长官生活应该是富足且奢侈的。
三、萧一山对清代民生与民俗研究的史学意义
萧一山对清代的民生与民俗倾注了大量的笔墨,对汉、满、蒙、回、藏、苗等各民族的衣、食、住、行逐一进行考察,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民族的生活情景、衣饰打扮,他都能细致入微地加以描述,使民族生活的场景生动鲜活而有趣,栩栩如生,可谓精心独到。萧氏还十分强调民族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及其生产与贸易状况,尤其重视表彰各个民族为清代社会生产发展所共同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这一点,体现出其作为良史的进步思想。
无论是关注清代之民生,还是勾勒清代各族人民习俗与部落形态,萧一山都能客观而生动地再现清代社会的多个层面,真正做到了撰写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既关注财政政策和政治制度,也关心人民大众的生活与疾苦,及其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演变,并从中总结经验与教训。而以往许多史家,很少关注经济、民生和风俗问题,即使偶尔涉及,也往往只记载朝廷财政及其制度之施行,人民生活状况如何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却常常被忽视而无论述。萧一山的见识卓越之处,就是既重视财政制度,又重视人民生计和贫富状况,将这二者紧密联系起来,并通过考察民众的生计来验证朝廷的政策、制度施行之结果,从中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对后世更有借鉴意义。
首先,体现了萧一山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萧氏继承并发展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对于客观的史事作详细的考察,并重视专门史的研究。清代的经济史在萧氏所处的时代,尚未有比较专门的研究,而他对于清代的财政经济,尤其是对清代的民生与民俗能加以重视,实属不易。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提倡写“普通人民大众的历史”[10],主张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对萧一山的清史研究有重大影响和明确的指导作用,这也是萧氏撰写的清代史具有丰富的人民性与民族性内涵的直接原因。
再者,相比较同时代的孟森等清史大家,萧氏的清史研究更具有全面性与整体性的特点。孟森等学者的清史著作更加着重于考证某些具体的史实、史事,而没有对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作全面的考察和论述。孟森在《清史讲义》中虽然也有关于“八旗制度考实”、“绥服蒙古”、“定西藏”等篇章,但是有关民族生计与风俗的内容却少有论述,如“内蒙四十九旗,早服清。漠北三汗,犹以前代帝族自居……”[11]等内容只是十分简略地讲到清代蒙古部落的一些情况,而不能让人了解蒙古民族的整体情况。萧一山撰写清史,不仅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的方面着笔,同时能深刻地关注清代各族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日常生活的民族特色,及其所反映出的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历史发展的眼光。
在《清史大纲》中,萧一山对于清代社会的民生状况有如下论述:“我国自然的富力和人口的密度以及社会组织能力……都是世界上大有可为的优秀民族……官吏贪黩的风气,逼得人民靠天吃饭,一般的生活真是穷苦不堪。”[2]93可见其关注清代人民的生计与社会风俗、民族习惯是与其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密不可分的。其注重民生和民俗的思想充分体现了萧一山史学经世与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
[1]萧一山.清代通史(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萧一山.清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中仁.康熙御批[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4]戴逸.简明清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23.
[5][清]曹雪芹.红楼梦(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0:488-491.
[6][清]龚炜.巢林笔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1:141.
[7]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15.
[8][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09.
[9]白寿彝,周远廉,孙文良.中国通史:第十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10:136.
[11]孟森.清史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0:141.
K092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007-8444(2011)04-0477-06
2011-06-06
田园(1975-),女,湖北武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
责任编辑:仇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