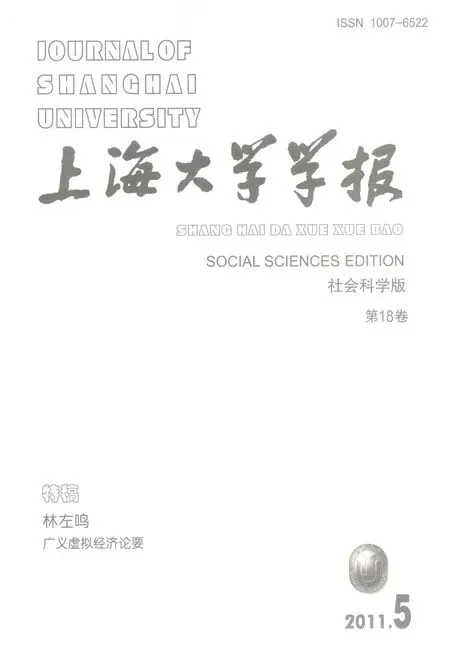善恶观:可欲为善、公意为善
2011-04-12祁志祥
祁志祥
(上海政法学院 新闻传播与中文系,上海 201701)
善恶是人类通行的基本价值范畴。扬善去恶,是待人接物、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如何辨别“善恶”?这个看似司空见惯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
一、善恶不是事物的客观品质
一种很容易产生的误解认为,“善恶”是人类生活中的客观品质。哪些品质是“善”、哪些品质是“恶”呢?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人的理性是善,本能欲望是恶。中国古代有“性善”、“性恶”论。两者所说的人性之“性”其内涵却不同。孟子所说的“性善”指人与生俱来的理性,荀子所说的“性恶”指人与生俱来的欲望。秉承先秦儒家的人性观,汉儒宣扬“性善情恶”,“性”即天赋理性,“情”泛指情欲。在孟子、汉儒那里,“善”的理性不是泛泛而谈的纯粹理性,而是“仁义礼智”的道德理性,这诚然与“善”保持着极大的一致性。到了三国时期魏国的刘劭①劭或作邵,今依《三国志·魏书》本传。那里,“善”就变成了纯粹的理性认知能力。刘劭《人物志·八观》认为,“智”是“德之帅”:“夫智出于明,明之于人,犹昼之待白日,夜之待烛火。其明益盛者,所见及远。”“故以明将仁,则无不怀,以明将义,则无不胜。”“圣之为称,明智之极明也。”人的理性智慧具有认识、辨别仁义之善的独照之明,是善的道德意识的统帅和根本。王弼认为,理性的“神明”能够控制情欲,使之趋善。这些都属于理性为善的主张。道家主张“无情”,佛家明确指出“情恶”,这些都可归入情欲为恶的阵营。在西方,类似的观点也不少见。柏拉图认为,人的欲望和感情是低级的、罪恶的,人的理性能够认识善的理念、控制情欲,是高级的和善的。基督教道德把情欲与罪恶等同起来,控制情欲的理性具有善性成为不争之理。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这种思想虽然受到巨大冲击,但并未绝迹。17世纪上叶荷兰法学家格劳修斯强调人的理性能力能够鉴别利害关系,作出正义的举动,为自然立法;符合理性的行为就是道义的行为,反之就是罪恶的行为。17世纪后期德国伦理学家莱布尼茨指出:什么是善的德性呢?就是用理智控制情欲的习性,即按理性行事的习性。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事实上经不起仔细推敲。
理性固然可以正确地辨别善恶,并能够控制自然情欲趋善离恶,从而具有一种善性,但理性也可能自以为是地误判善恶,当将这种错误理念付诸实施的时候,会造成可怕的灾难。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理性曾经剥夺了人之为人的最起码的生物权利。宋明理学盛行时期,曾产生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以理杀人”的事实。美国学者郑麒来根据《明史》和《古今图书集成》,统计出明代有619名女子割肉为丈夫或长辈疗伤,割肉的部位有大腿、上背、肝脏、手指、耳朵、乳房、肋骨、腰、膝、腹等,堪称人类理性异化的极端案例。所以清代启蒙思想家戴震在《与某书》中批判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在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左的政治理念造成的死伤更是难以数计。姑且不说斯大林的大清洗在苏联造成了多少无辜的冤魂,[1]也不说疯狂的“文革”在中国大地上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即以红色高棉的极端理性为例。20世纪70年代后期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执政的四年间推行的极左理念,直接造成了200万左右、约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死亡。1975年,在波尔布特的指挥下,红色高棉一举推翻朗诺政权,在4月17日这一天宣布“全国解放”,1976年1月柬埔寨颁布“新宪法”,定国名为“民主柬埔寨”。作为柬埔寨共产党领袖、政府总理的波尔布特年轻时的理想,是建设一个纯而又纯的、“公平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他看来,像中国“大跃进”时期那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太慢了,他要坐火箭一下子蹿入共产主义。怀着美好的理想,他一上台,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他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于是他推行的第一个壮举,就是一夜之间将首都金边的二百多万居民统统赶到农村去,不让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城市里萌芽。占领金边后,波尔布特马上宣布要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在他的领导下,柬埔寨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无正规学校、无邮政电信、无公共交通、无医院、无宗教、无法律法规、无广播电视、无出版物、无私有财产,甚至没有家庭。人们的生活都被规定好了,何时可以吃饭,何时必须劳动,何时允许性交,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实行“平均分配”的原则,在全国建立“农村合作社”,农民和下乡的“新生者”除了保留睡觉的铺盖外,其他私有财物全部充公;每个村成立一社,30至40家编为一个大组,每组成立一个公共食堂,每十人一桌吃大锅饭;已婚的夫妇则被分开编组,一两个星期才允许“团聚”一次;合作社天天吹哨出工和下工,田间地头插着红旗,一片片黑衣人围着汗巾在挖土挑担;全国老百姓和军人只发统一样式的黑色“革命服”,禁绝其他服装,姑娘穿花衣服就被定为“资产阶级思想”。在他为首的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旧政府的官员、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商人和僧侣被认为对“新社会”有毒害被消灭,旧知识分子也通通被清洗,全国只剩3个旧知识分子、1个旧技术人员得到正式录用。1976年年底,波尔布特认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于是开展了对一大批中央高层领导的血腥清洗。在金边附近的一个集中营,亦称“S-21监狱”,就有近2万名“有问题”的人被关押,仅有六七人生还。波尔布特在不到4年的执政时间里,组织领导了4次大肃反,在革命军总参谋部中,除了总参谋长宋成一人外,所有人员统统被捕杀。其时宋成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只因他在前线指挥而一时幸免于难,直到1997年6月才被波尔布特派卫兵给杀了,不仅宋成夫妻两命归天,连他们的9个子女也一同被杀光。当美国记者纳特—赛耶采访临死前被红色高棉软禁的波尔布特时,波尔布特还毫愧色地说:“我只是要斗争,不是要杀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的确,波尔布特的私德似乎没大问题,他平时称得上“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在20世纪70年代来访北京时,还在驻地同种树养花的工人一同干活,体现“劳动人民本色”。在他死时,身上穿着件皱巴巴的短袖衬衫,身边只有一把蒲扇。他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不过是一个“政治妄想狂”将极其荒谬的理念付诸实施的恶果。这充分说明,理性并不绝对是善。同理,人的生存欲望及其活动如果符合法律道德,也决不是恶,而是人类生存和延续的必要基础。
另一种观点认为,利人即善,自私即恶。汉代刘向《说苑·杂言》指出:“出于利人即善矣,出于害人即不善也。”16世纪后期英国的培根说:“利人的品德我认为就是善。在性格中具有这种天然倾向的人就是‘仁者’。这是人类的一切精神和道德品格中最伟大的一种。”[2]弗洛姆指出:“人本主义伦理学中,‘善’和对人有好处是同义语,‘恶’和对人有坏处是同义语。”[3]宋儒宣扬“大公无私”,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宣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都是利人即善、利己即恶思想的体现。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事实上也不可一概而论。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无疑是出于为孩子前途着想的利他动机,但对于处于青春期和成年期的子女来说恰恰受不了,也无助于他们的独立和成长,肯定不是一种善举,因此必须加以调整。爱上一个人,极尽殷勤之能事,但如果对方拒绝接受,继续示爱就绝不能算是善行,甚至会导致恶果。善良仁慈本来无可厚非,但对恶不抵抗,姑息养奸,纵恶成患,恰恰会贻害无穷。乐善好施堪称义举,但毫无顾忌的施舍恰恰会助长不劳而获的奸恶。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指出:“确有许多形式的‘善行’产生出恶,还有许多‘善’意无边的人却并没有使一个人因此得利,倒使每个置于他影响下的人都腐化掉了。不明智的仁慈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所以,决不能仅仅从这些欲望倾向于利他就推断它们是善的,更不能把它们说成是唯一的善。”“而且,即使牺牲个人利益在事实上推进了他人利益的时候,是否就能够承认这种牺牲始终是有功的和值得赞扬的,甚至是一个义务呢?我想不能这样。我是否应当忽视我自己最重要的和根本的利益而去给别人一些微小的快乐呢?我是否应当牺牲我的财产、健康以至生命去满足一个病人的一个无关大雅的念头,以减轻他的负担呢?……我应把推进我的家庭的利益看作自私的吗?我应当拒绝我的兄弟、我的孩子那种对他们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却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别人的愿望吗?公正的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相反,对我来说,我的家人和亲属比陌生人更为亲近,忽视他们的利益以满足他人的愿望不是一个义务,而是对义务的违反。因此,我们可以说:牺牲个人愿望和利益本身并不是善的,而只是在他人的根本利益要求这种牺牲的情况下才是善的。”[4]333-334利他的善是建立在对他人有利或者说别人的利己基础上的。既然别人可以利己,为什么自己不可以利己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味肯定别人的利己,而反对自己的利己,要求我们自己一味无私奉献、承担对别人的义务呢?正如利他不能简单等同于善,利己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恶。在现实社会中,只要不犯法,一切利己的行为都不应受到指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走过了一条从“包”到“卖”的历程,其深层机制就是改变以往不和个人利益挂钩的公有制经济长期严重的亏损局面,通过分配、产权与个人利益紧密挂钩,扭亏为盈,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财富积累。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人的利己活动非但不是恶,而是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和社会财富的善。
由此可见,那种把善、恶视为固定不变的理性或欲望、利他或利己的客观品质的观点是简单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行不通的。
二、善恶不应由苦乐情感决定
历史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善不在于生命的客观内容,而在于生命所产生的快乐情感。这种观点称为快乐主义伦理学。它以苦乐定善恶,认为人类乃至一切生物都普遍地追求快乐,快乐或免除痛苦是唯一被绝对欲望的东西,主体的快乐情感不管是怎样产生的,都是绝对的善,反之为恶。快乐又具体分为肉体的快乐和理智的快乐。古希腊苏格拉底的门徒亚里斯提卜将肉体的快乐视为人生的目的,鼓吹纵欲主义;柏拉图高扬理智的快乐,强调禁欲主义。伊壁鸠鲁对两者有所折中,他所崇尚的快乐是肉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只有这种快乐才是“善”。这种快乐是由人“既自然而又必要的”欲望满足(如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带来的。针对柏拉图的禁欲主义和理智快乐,他指出:“如果抽掉了嗜好的快乐,抽掉了爱情的快乐以及听觉与视觉的快乐,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能够想像善。”[5]肉体感性的快乐是一切快乐和善的基础。“一切善的根源都是口腹的快乐,哪怕是智慧与文化也必须推源于此。”[6]但他又指出:肉体的快乐是暂时的、肤浅的、不稳定的,精神的快乐才是长久的、深刻的、稳定的。快乐的善必须与理智相结合:“我们说快乐是最高的善时,我们并非指放纵不羁的人的快乐以及一般感官的享乐而言……乃是指肉体能摆脱苦痛,心灵能摆脱烦忧而言。并不是丰盛的酒食、男女的淫乱和珍贵的物品能造成优越的生活,只有清醒的理性才可以做到。理性研究我们所做和不做的事情之种种原因,并可排除那种搅扰我们心灵的成见。”[7]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伦理学对以后的伦理学发展有重大影响。古罗马时代的卢克莱修,16世纪的托马斯·莫尔,17世纪的霍布斯、洛克,18世纪的休谟、爱尔维修、霍尔巴赫,19世纪的边沁、穆勒等人,无不有所继承。如爱尔维修说:善应当与人的本性相统一。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凡是使人得到快乐的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边沁宣称:快乐本身就是善,而且是唯一的善;痛苦本身就是恶,而且是唯一的恶。其它的一切之所以善仅仅是就它有助于产生快乐而言。边沁所肯定的快乐偏重于肉体快乐,因而被人斥之为“猪”的伦理观。穆勒继承了边沁善即快乐的思想,但又指出:这种快乐是“比动物的嗜欲更高尚的心能”的快乐。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康有为、严复受西方快乐主义伦理观的影响,也以苦乐作为决定善恶的标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说:“去苦求乐”乃“人道之至”,“立法创教,令人有乐而无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乐多苦少,善而未尽善者也;令人苦多而乐少,不善者也”。严复《天演论》导言之十八说:“乐者为善,苦者为恶,苦乐者所视以定善恶者也。然则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必有所乐,始名为善。”
人们天生地喜欢快乐,讨厌痛苦。将快乐视为善,将痛苦视为恶,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仔细推敲,却发现并不稳妥。快乐为什么会产生?在一般情况下,快乐是生命体满足了功利目的之后的产物。与其说快乐为善,不如说可欲为善、功利为善。所以,“快乐并不是自身即为善,而是善被达到的一个信号”。[4]229一方面,满足了生命体需求的功利可以产生快乐,另一方面,事物超功利的形式也可以带来快乐。在这种情况下,将带来快感的物质形式叫做“善”很牵强,叫做“美”则更合适。苏格拉底指出:“美就是快感。”[8]33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指出美是“一眼见到就使人愉快的东西”。[8]66德国沃尔夫(1679—1754)指出:“产生快感的叫做美,产生不快感的叫做丑。”“美可以下定义为:一种适宜于产生快感的性质,或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完善。”[8]88鲍姆嘉通指出,美就是“感性知识的完善”。[8]142无论美是“快感”还是“引起快感的事物”,“快感”都是美的决定因素。苦乐毋宁说是美丑的决定者和对应物。以苦乐定善恶,容易与美丑混淆起来。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快乐都是善,比如吸毒、淫乱等等。快乐只有在符合法律和社会道德的情况下才是善的。而杀身成仁所带来的肉体的痛苦毫无疑问是善而不是恶。[9]
三、善即包含私欲的公意、肯定自利的公利
因此,善、恶的评定标准应当从苦、乐以外去寻找。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说“真”是对外在客观规律的符合,那么“善”则是对主体生命目的的满足。主体的生命目的,通常叫“意志”、“意欲”。满足了生命“意欲”,维持了生命存在,自然就被有意识的生命体判认是善,所以,“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生命的最高意欲和终极目的是生存。所以,西方哲人认为“合目的”即善。这里的“目的”即生命主体的生存目的。满足生命存在意欲的对象是利益,所以说,“善者执利所在”。①《管子·禁藏》。原文为“势利所在”,“势”通“执”。从善恶的起源来看,“一个生命体的生存就是它的价值标准:凡是增进它的生存的就是善,威胁它的生存的就是恶”。[10]由此出发,满足个体生存目的(私欲)的私利既可能是一种善——当它不妨碍其它生命个体的生存目的实现的时候;也可能是一种恶——当它危害其它生命个体的生存目的实现的时候。为了保证人类社会每一个个体生命目的或生存意欲的实现,让每一个个体认可的善都得到确认并达成共识,个人的生存必须以不危害其他人的利益为前提,克制私欲私利,走向公意和公利。于是,善就从私欲走向公意,从自利走向公利。苏格拉底认为,对于任何人有益的东西对个人来说就是善。他将善的知识称为“一种关于人的利益的学问”,而“一切可以达到幸福而没有痛苦的行为都是好的行为,就是善和有益”。这种观点成为西方伦理学史上的一种重要思想。“我们称一个人为善的,是当他对自己的生命的塑造符合人的完善的理想、同时推进他周围人的幸福的时候;我们称一个人为恶的,是当他既无心愿也无能力为自己或他人做任何事情、相反却扰乱和损害他周围的人的时候。”[4]212这种包含并肯定着每个个体私欲的“公意”、包含并肯定着每个个体私利的“公益”便是善的本质。爱尔维修从肯定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出发,认为道德善应以公共利益为标准。卢梭提出“公意”为善的思想:“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11]善即社会公意,说得通俗些即善是社会普遍认可、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在现实中,社会公意既可以国家法律的形态出现,也可以道德习俗的形态出现。黑格尔指出:“公意、普遍意志即是意志的概念,法律就是基于这种普遍意志的概念而产生的特殊规定。”[12]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奎进一步分析说,国家应当是“公意的行使”,神圣的国家通过少数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应当体现着社会公意及其所代表的共同利益,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个人服从国家其实就是服从自己。[13]而在专制国家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因为专制国家的法律主要是源于最高统治者的私意,为维护其专制统治服务的。与显性的明文规定的国家法律相比,社会自然形成的道德习俗往往潜存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无法精确统计,较少明确公布,因而大多是隐形的。不过国家为了便于对国民进行道德教化,往往在法律管辖不到的地方代表社会公意或国家利益树立道德规范,推行价值理念,宣扬意识形态,奖倡社会风尚。当代美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伦理体系在任何时候都只是占优势的统治集团认为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在当代美国另一位社会学家萨姆纳看来,道德不过是比服装样式更为固定的更有强制性的社会风习而已。[14]这时,道德习俗就变得有迹可循起来。
由此可见,道德善不是事物的客观品质,而是客观事物中凝聚的人类公意。善、恶体现了人与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殊的关系。17世纪荷兰的斯宾诺莎指出:“善与恶既不是事物又不是活动,所以善与恶就不存在于自然之中。”[15]178“善与恶只是关系,因此毋庸置疑它们必然属于思想存在物”,而不属于“实在存在物”,它们“只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15]127
人类具有超越历史和国家、民族的社会公意,这就构成了善恶的普适性和共同标准。一般说来,平等、公正、民主、自由、自尊、自爱等等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度都是广受民众欢迎的善,而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度都是广遭民众唾弃的恶。这是没有疑义的。因此,人类才有了普适价值,各国人民之间才可以打交道。同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度、民族又有不同的社会公意,同一种行为、活动引起的善恶判断也就不同,这就决定了善恶的相对性。比如人类的利己活动、性行为,如果得到当时当地社会公意(道德、法律)的认可,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简单地把利己活动、性行为说成善或恶,都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善恶的相对性。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公意,因而,同一种人类的行为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会受到不同的善恶评价。比如女子抛头露面在大多数世俗国家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在某些国度则被视为伤风败俗,大逆不道。在公共场合穿上罩袍,是伊斯兰教对女子的服饰规定;最近法国正考虑通过一项法律,对在公共场合穿伊斯兰罩袍的女子罚款700欧元。萨科齐总统称,伊斯兰全身罩袍是“束缚贬低女性、让其屈从的形象的象征”,在“法国领土上不受欢迎”。[16]同一国度、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公意,因而,同一种人类行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受到的善恶评价也不尽相同。比如“文革”时期课以重罪的“投机倒把”分子,在改革开放时期则被视为“搞活流通”的能人。这里,最值得防范的是用一种固定的、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观点看待某一行为或事件的善恶。
善是一种社会公意,而这种公意往往由国家的法律来体现。因此,安身立命,必须具有法制意识,不做违法乱纪的事,这是做人的底线。善作为社会公意,还体现为法律之外的道德习俗,因此做人还必须顾及大众的、流行的道德评价。道德习俗给人类行为规定的活动范围比法律要严格,不违法的行为未必符合道德善,所以,在守住法律底线之外,还要恪守社会道德。当然,这也许活得太沉重。孔子曾说:“大德不逾闲(规矩),小德出入,可也。”倒不失为我们对待社会道德规范的一种通达态度。常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法律、道德会因时因地而变化,善恶又一次呈现出可以相互转化的相对性。因此,人生万一走错路,毋须绝望。时过境迁,就可以开辟人生的新天地。
[1]张建华.推到红墙——克里姆林宫最新档案解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65-168.
[2]培根.培根论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5.
[3]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41.
[4]包尔生.伦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95.
[6]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09.
[7]李仲融.希腊哲学史[M].上海:开明书店,1940:223.
[8]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祁志祥.美丑观:悦情为美,痛苦为丑[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61-70.
[10]爱因·兰德.客观主义的伦理学·自私的美德:利己主义的新概念[M].纽约:新美国世界文学文库,1964:17.
[11]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36.
[12]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33.
[13]赵修义,等.现代西方哲学纲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39.
[14]克莱宾.理想的冲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9.
[15]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6]英国《每日电评报》记者.穿全身罩袍女性在法将被罚款[N].参考消息,2010-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