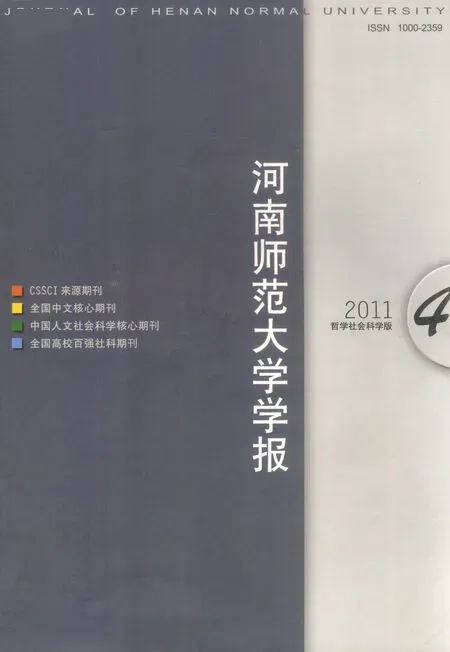从山巅之城到门罗主义:被误读的神话
——美国早期孤立主义辨析
2011-04-12袁胜育
袁 胜 育
(上海政法学院 国际事务系,上海 201701)
从山巅之城到门罗主义:被误读的神话
——美国早期孤立主义辨析
袁 胜 育
(上海政法学院 国际事务系,上海 201701)
对美国革命前后几十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们常常以“孤立”“不卷入”“中立”来概括。这似乎是一个普遍流行的神话,然而却是一个被误读的神话。首先,美国从来就不是孤立主义者,从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最初年月起,美国就有着一种积极的对外政策,这一点,浸透在美国人的清教理想和社会文化之中。其次,即便是将孤立主义定义为不介入欧洲政治事务,也仍然是夸大事实。一个从宗教情怀到社会文化都浸染着“积极的”对外取向的国家,是不会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再次,建国初期美国对欧洲的政策与其说是因为实力不济而不得不“敬而远之”,毋宁说是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主动做出的取舍。
美国外交;孤立主义;告别演说;门罗主义
对美国革命前后几十年,世人在提到这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往往想到的是“孤立”“不卷入”“中立”之类的词语。在人们看来,约翰·温索普所谓的“山巅之城”,就是要保持美国这块“乐土”的纯洁性,以免受到腐败、堕落的欧洲的玷污[1]。重申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孤立主义内核的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反对承担外部的义务,最典型地表达了美国人希望置身于这个腐败世界之外的愿望。门罗主义则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孤立主义和与世隔绝的传统。诸如此类的说法得到广泛认可。在对美国对外政策早期的历史的叙述中,存在着一个将美国当作一个孤立主义和被动的国家来看待的神话。如在基辛格看来,“在本世纪初之前,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倾向于孤立主义”,直到美国国力日渐强大,以及以欧洲为重心的国际秩序逐渐瓦解,美国才“不情愿地涉入了世局的漩涡”[2]。尼克松则在其最后一本著作中,将美国称作“唯一一个没有对邻国进行帝国主义占领历史的大国”[3]。而大多数美国人大概也会同意,贯穿美国的历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构成美国外交政策基础的根本准则首先就是孤立主义,孤立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中心原则[4]。
如果说这些算得上是对美国建国初期对外政策的一种简单化甚至是粉饰性的论断的话,那么,一些学者对这一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论述显得要贴近事实得多,那就是认为孤立主义只不过是反映了当时美国军事经济实力都不强大,弱小的美国需要保护自己。此外美国也想利用自己远离欧洲大陆的有利地理条件,孤立于欧洲纷争之外,避开欧洲国际纷争的牵累和危险,避免卷入欧洲的战争,专心致志地加强本国的实力。孤立主义也并非只包括消极的战略防御,也包括积极的战略进攻。对欧孤立主义和大陆领土扩张并行不悖[5]。
但是,即便是上述对美国建国初期的对外政策较为贴近事实的论述,似乎也存在着误读。首先,美国从来就不是孤立主义者,从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最初年月起,美国就有着一种积极的对外政策。这一点,浸透在美国人的清教理想和社会文化之中[6]10-11。其次,也正如罗塞蒂所指出的,“如果人们不十分严格地将孤立主义定义为不介入欧洲政治事务……它仍然是夸大事实并得出美国对外政策是孤立主义的结论”[6]10-11。一个从宗教情怀到社会文化都浸染着“积极的”对外取向的国家,是不会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再次,建国初期美国对欧洲的政策与其说是因为实力不济而不得不“敬而远之”,毋宁说是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主动做出的取舍。
一
对美国外交历史、传统和本质的误解最初开始于对17世纪30年代定居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的认知。在一些学者看来,孤立主义的历史“同英国在北美大陆首次殖民一样古老”[7]。最初来到美洲的移民,大多数就是为了逃避欧洲的战祸、饥馑以及政治和宗教迫害。“这些挣扎上岸侥幸成活的人除了被迫的原因外,不会再返回欧洲了”[8]。
然而,即便这可以被看作促使早期欧洲移民背井离乡来到美洲的动机,那它也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这些动机还包括“物质利益和乌托邦希望”[9]。“使命和金钱,或者是像一些历史学家更倾向于表述的,理想主义和自身利益,在差不多500年里,一直被美国人视为他们成功的原因。从一开始,他们就以宣称他们是在传播文明准则和赚取利润来证明他们开发北美大陆以及大半个地球的正当性”[10]5。
“即便是在这个国家最初的岁月里,许多杰出的美国人相信,美国肩负着一个使命:充当其他人的榜样,并且成为那些被政府专横统治着的国家的人民希望的灯塔”[11]。以温索普为代表的清教徒们并不是孤立主义者,他们是全球革命主义者。他们逃离迫害他们的旧世界,目的是要在美国建立这个理想中的宗教领地。清教徒不是要寻求永远脱离这个旧世界,他们“在荒郊旷野中开拓事业”的目的旨在建立一个向大西洋彼岸发起反攻的基地。正如清教徒思想研究学者佩里·米勒曾经说过的,“清教徒移民并不是要从欧洲撤退:这是一个迂回进攻”[12]7-8。
此外,吸引欧洲人走向一个并未开发和驯服的国家的梦想是发财致富的机会。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从海外贸易和西部土地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使得定居者“对赚取美元比对拯救灵魂更感兴趣,将更多的心思花在获取广阔的土地而非拥挤的村庄上,将更多的激情放在个人发财致富而非集体的福祉上”[10]10。因此,在早期开发北美大陆时期,美国外交的另一个关键主题也呈现出来:这个国家的繁荣和成功,有时甚至是它的生存本身,与远隔重洋的地方所发生的事件息息相关。这样,从一开始,美国人就不曾将对外关系与他们个人的生活方式区别开来;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环节。一方面,他们不可能孤立于欧洲的动乱之外。另一方面,他们也是重塑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关键。他们的财力和人力,使得西班牙以及随后的英格兰和荷兰得以取代意大利和德国的城市,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来自北美的皮毛、烟草、糖和鱼,取代亚洲的香料,成为欧洲贸易中最有价值的产品[10]7。
因此,从一开始,贪得无厌、个人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现代精神就构成了美国社会的基石。这种贪婪利己的个人主义是盎格鲁-美国人实现领土扩张的强大动力。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动机存在,还存在一些更“高尚”的理由。挤占他人领土的盎格鲁-美国定居者相信,他们正在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标,即他们将自己看作英国文明的先锋,要领导人类走向未来。殖民者在扩张的同时也将“生活在那里的异教徒和小偷们带入人类文明,并建立一个可以控制和太平的政府”[12]11-13。正如杰斐逊在1801年所写,美国的扩张应该被理解为事实上是不受约束的:无论我们今天的形势可能如何将我们拘囿在我们自身的限制内,一旦我们人口的迅速增殖超出这些限制,并涵盖整个北美大陆,如果不包括南美大陆的话,成为说着共同语言由相似的政府形式和法律治理的人民,这种情况将不可能长久下去。看着这块大陆呈现出斑驳杂陈的状况,我们也不可能满意[10]52。
二
1796年9月19日,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说》,提出了他著名的忠告:“在对外国的关系上,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是:一方面扩大我们的商业关系,同时尽可能少地和它们发生政治联系。……如果我们卷入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13]华盛顿的这些话被公认为早期孤立主义政策的依据[14],被称为美国外交中孤立主义思想的先声[15],被认为把传统的孤立思想上升为了方针政策[16]56,“为美国外交规定了孤立主义的准则[17]。然而,“华盛顿并不是替一项后来被称为‘孤立主义’的政策背书,那只不过是一项容许美国打造其实力的一项临时措施”[18]。这篇演说的真正主旨,只有在“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才可能加以理解。
一般认为,美国人具有一种共同的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但在1790年代期间,对于自由主义,以及一直被称为“共和主义”的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至少出现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愿景。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主义者提出的是一个将美国置于一个可靠的财政基础之上的庞大的计划,旨在将大部分资金置于一小部分(多数是东部的)商人和金融家的手中,在他看来,这些人能够为了国家的财政利益对这些资金加以最好的利用。他的目标是与詹姆士·麦迪逊和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共和主义者的偏好背道而驰的,后者代表中部和南部农业集团利益,他们从重农主义立场出发,主张加强农业投资,让每一个美国人都成为精于耕作的农夫[16]47。汉密尔顿以英国为模式在美国建立一个财政体系,这在麦迪逊看来毫无疑问意味着“君主政治即将到来,汉密尔顿及其‘财政主义者’、‘亲英分子’的追随者正密谋终结美国的共和政府”[12]104-106。
如果说汉密尔顿对美国的愿景,带给他的是对他视为世界上目前已知的或者是可能存在的最为成功的自由派政府(也就是英国)一种强烈的亲近感,那么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对美国的愿景则引导他们寻求与英国和英国式的政府分道扬镳。
当英国和革命的法国发生战争时,汉密尔顿派联邦主义者和杰斐逊派共和主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裂痕进一步扩大了。对英国的憎恨激发了杰斐逊派对法国的亲近感。然而,与杰斐逊对法国大革命的维护有着更大关联的,是他同汉密尔顿在国内所进行的斗争。因为,无论杰斐逊对法国大革命的智慧和正义有什么样的信念,他所关注的是对它的成功或失败的认知将可能对自由派的共和主义体制在美国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法国政府)的确立和成功对于我们自身坚持不懈,防止沦落为英国宪法那种半途而废的体制是必不可少的”。杰斐逊担心,如果大革命看来并没能在确保法国人的自由方面取得成功,将增强“英国专制制度热心的信徒在这里”的力量,也就是将增强汉密尔顿的力量[12]110。
在17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杰斐逊及其共和党似乎代表了美国人中的多数。基于对在美国自身反抗英国的斗争中法国所给予的援助的记忆,美国人对于法国的友爱之情,就像对英国人的敌意一样,自然而然地油然而生。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美国人对法国的同情得到极大的增强。1793年,当法国使者埃德蒙·热内来到美国寻求美国的支持时,他受到美国人热情洋溢的欢迎,以至于热内敢于越过华盛顿政府直接向美国人发出呼吁[12]110。
美国的亲法热潮以联邦主义者为代价使共和主义者的力量得以增强。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反对汉密尔顿及其假想中的君主制主义者阴谋家的“民主社团”,以保卫“自由和平等”。共和党人的报纸指责华盛顿总统处于英国的邪恶影响之下。共和党人利用国内这种情绪,试图为他们的领导人托马斯·杰斐逊赢得总统职位。华盛顿政府已经获悉法国图谋在西部和南部挑起分离运动,驻费城的法国公使警告说,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美国人必须在与法国的友谊或者冲突,甚或战争之间做出选择——公开呼吁美国人民击败联邦主义者,把选票投给杰斐逊[12]113。当此之际,华盛顿发表的告别演说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就是旨在击败杰斐逊的选举企图以及与之相联的危险的亲法国的共和主义学说[12]113。因此,华盛顿在这篇演说中对与其他国家永久结盟提出的告诫,与当时的这场政治论战有着直接的关联,华盛顿在这里所指的“其他国家”“显然是法国”[18]173。也就是说,美国人必须摈弃的是他们对法国“充满热情的偏好”[12]114。
后世的美国人往往引述华盛顿的这番话作为避免与外国结盟的理由。然而,即便是后来美国确曾出现过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也只不过是因为“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们往往被那些历史所教导或预示的信条所影响”[19],而与华盛顿的真正思想无关。《告别演说》的主题是有关共和国国内政治健康的。他将共和党人少一点中央集权、多一点民主共和主义的要求与血腥的和破坏性的法国大革命的共和主义相提并论。华盛顿暗示,如果共和党人在下一次总统选举中上台,同样的命运将降临到美国人的身上[12]113。
因此,即便是华盛顿在其著名的《告别演说》中涉及了美国的对外政策,那他所主张的也不是赞同孤立主义,而是以外交政策为脚本进行的一场有关这个国家的基本特性的斗争。
三
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发表致国会的咨文,其中提出的一些原则被后人称为门罗主义,其主要内容为:美国对欧洲列强各国事务不加干涉,欧洲列强“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企图”都将会被看作对美国安全与和平的威胁。门罗主义往往被看作继承了华盛顿给后任留下的不干涉欧洲事务的原则[20]。“门罗宣布的原则实际上是扩大了的孤立主义”,“不仅强调美国一国对欧洲的孤立,还追求整个美洲的‘集体孤立’”,不再只力求不介入欧洲事务,还要从美洲这个“集体孤立圈”中排斥欧洲势力[16]57。门罗主义被看作美国走向独立于世界政治之外的美国理想和具有历史渊源的非殖民化和不干涉主义的相当漫长道路上的一个路标[21]。
19世纪上半叶的时代特征是封建主义的旧世界与资本主义的新世界并存并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门罗宣言”的性质要从这个时代特征中去理解[22]。门罗主义产生于欧洲拿破仑的失败以及战胜国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安排开始了一个新的保守反动的时期的背景下。1815年后,欧洲绝对主义的君主制由于害怕自由主义的传播,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对于日益开放和民主的美国而言,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呈现出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景象。在这场冷战式的全球对抗当中,美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主要参与者,美国的领导者和公民们都积极支持自由派革命。
这个时期欧洲的反动甚至刺激了英国人的情感,毕竟后者保持着一种自由的立宪君主制。1823年,英国首相坎宁向美国驻伦敦公使提议,两国应该签署一份联合声明,宣称美国和英国将一起反对法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控制西半球的前西班牙殖民地的任何尝试。坎宁的提议推动了门罗在1823年12月发表声明,即后来闻名的门罗主义。门罗在咨文中表达了对希腊人会“在斗争中获得成功并且恢复其作为世界各民族中平等一员地位”的“强烈希望”。他还公开质疑:神圣同盟是不是觉得可不受拘束地“在同样的原则”——维护君主合法性的原则——基础上到处干涉呢?这是一个“所有政府体制与他们不同的独立国家都关心的问题,即使那些最遥远的国家,而且肯定没有一个比美国更为关心”。明白地说就是,美国认为,欧洲对共和制政府的干涉镇压是对美国自身安全的威胁。出于这种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他宣布,美国不得不担心欧洲事务。“对于地球上的那个与我们交往频繁并且是我们祖籍发源地的地区所发生的事务,我们总是焦虑不安和利益攸关的旁观者”[12]173-174。
因此,与其说门罗宣言是一份宣布正式放弃任何卷入欧洲事务愿望的咨文,倒不如说它是对美国在欧洲事务中的利益的一次直截了当的表述。门罗的咨文不是一种西半球孤立主义的宣言。从重要的方面讲,它是象征国际共和主义者团结的一个声明。门罗咨文的真正目的不是划出地理上的界线,而是划出意识形态上的界线[12]175。
四
在门罗总统之后的20年里,美国一度放慢了在大陆的扩张,那么,这是不是因为受到孤立主义的掣肘呢?不是,它同样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反映了其政治性质的话,那美国的蓄奴制,像美国民主和美国资本主义一样,必定会同样是影响19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不仅仅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它还是一个蓄奴者的国家,是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两种截然不同并最终冲突的国家利益观的这样两个独立和相互敌对的社会。美国对外政策反映了其自身混杂的政治制度。从19世纪20年代到内战的美国对外政策路线,—直由围绕着蓄奴制的斗争而形成[12]182。
应该说,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有强烈的扩张主义倾向,但是,在北方看来,美国向南方和西南方的扩张,将使蓄奴制被成功地移植到新获取的土地上,进而威胁到宪法中北方和南方达成的微妙平衡。不仅新的蓄奴州会加入联邦,而且宪法的五分之三条款也会使南方人得到在众议院和选举人团中更大的代表权。因此许多北方的联邦主义者反对获得新领土,他们不仅害怕蓄奴制的传播,而且担心政治平衡会发生不可改变的倾斜,使之越来越偏离以东北部为基地的联邦主义而偏向以南部为基地的杰斐逊共和主义,担心南方不断扩大的“蓄奴势力”会有主导联邦政府的危险。
正因如此,1819年密苏里危机爆发之际,正与西班牙谈判《泛大陆条约》条款以及北美西班牙领土割让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满足于以塞宾河为界,从而把后来成为得克萨斯州的大部分领土排除在外。私下里,他透露了他的考虑。“作为一位东部人”,“我不愿意出现一个没有限制蓄奴制的得克萨斯或者佛罗里达”。正如门罗对杰斐逊所说的,“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能够阻止”美国占领它所想要的大量西班牙领土。相反,困难“完全是国内的,也是最具有痛苦和危险倾向的”。“在西部和南部进一步获取领土”,有可能“威胁到联邦自身”,因为它会导致另外一场围绕蓄奴制的地方冲突。在这种情势下,门罗相信,扩张将是与国家利益相悖的,不是因为得克萨斯没有价值,而是因为美国政治的分裂性质使其难以消化。美国不能扩张,因为它无法决定它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12]201。而一旦它弥合了国内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国即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猛烈的扩张惯性。
对早期美国外交的历史考察表明,从“山巅之城”到“门罗主义”,美国人曾追寻并自然而然幸运地享有的光荣的孤立,被证明既不光荣,也非孤立[23]。如果说存在着一个关于早期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时期的话,那么它只是一个神话而已。领土和实力扩张从一开始就成为不容回避的美国历史事实,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野心深深根植于美国人的性格之中[24]。
[1]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184.
[2][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5.
[3][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M].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5.
[4]Daniel S. Papp,Loch K. Johnson,John E. Endicott,American Foreign Policy:History,Politics,and Policy,New York,2004:45.
[5]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1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346-347;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35;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国际关系史(近代卷·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4;唐贤兴.近现代国际关系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54;刘德斌.国际关系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3-74;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
[6][美]杰里尔·A. 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周启明,傅耀祖,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7]Donald F. Drummond,The passing of American Neutrality,1937-1941,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1955:1.
[8]Thomas A. Bailey,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1958:22-23.
[9]Eugene R Wittkopf,Charles W. Kegley, Jr.,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attern and Process,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27.
[10]Walter Lafeber,The American Age: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 since 1750,New York,1989.
[11]Daniel S. Papp,Loch K. Johnson,John E. Endicott,American Foreign Policy:History,Politics,and Policy,New York,2004:72.
[12]Robert Kagan.Dangerous Nation.Alfred A.Knopf:New York,2006.
[13][美]亨利·S. 康马杰.美国历史文献[M].北京:三联书店,1989:94-95.
[14]刘绪贻,李世洞.美国研究词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35.
[15]唐贤兴.近现代国际关系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55.
[16]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
[17]王玮,戴超武.美国外交:1775-2005年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7.
[18]John Lamberton Haper:American Machiavelli: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origins of U.S. Foreign Poli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77.
[19]Ernest R. May,Lessons of the Past: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vx.
[20]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国际关系史(近代卷·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2.
[21][美]沃伦·I. 科恩.共和制帝国的创建(1776-1865)[M]//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周桂银,杨光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73.
[22]李庆余.美国外交史——从独立战争至2004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17.
[23]Loch K. Johnson,Seven Si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2006:6.
[24]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M].肖蓉,魏红霞,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31-132.
[责任编辑孙景峰]
K712
A
1000-2359(2011)04-0244-05
袁胜育(1964-),男,汉族,湖北武汉人,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系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研究。
2011-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