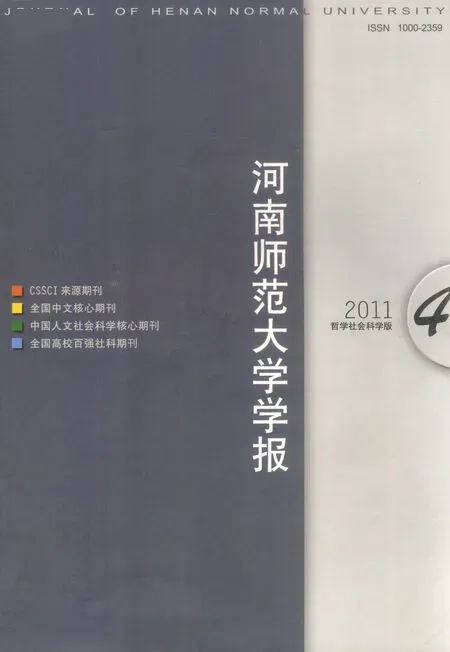文本概念的旅行及其核心要素的生成
2011-04-12梅启波
梅启波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文本(text)在一般意义上是指按语言规则结合而成的字句组合体,它可以是一个句子,也可以是一篇文章,甚至是一本书。它的印欧语词根“texere”表示编织的东西,如纺织品(textile)、建筑师(architect)一类的词便是由此而来。文本一词在晚期拉丁语(textus)和12-15世纪中古英语(texte)中开始表示文章的结构、主体。在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转向的背景下,文本理论开始兴起和传播,可以说文本理论和概念的产生是对应于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语境的,文本理论从发源地产生,到被挪用,实质上是一个被吸收、被规化、非历史化到新的地域的动态生产过程。本文将从萨义德理论旅行的视角考察文本理论及其概念的变迁,分析该概念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的传播中是如何生成,及其核心要素是如何逐渐被发现与增长的。
一、从作品向文本的迁徙:封闭自足的文本概念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出现了从作品研究向文本批评的转向。众所周知,这一理论转向的背后是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深刻变化:由传统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与之相应,西方文艺理论出现了许多以文本的语言性特征为思考核心的文艺理论流派,诸如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派、英美新批评派以及结构主义文论等。文本在这些理论那里成为一种自足自律的本体论结构体系,从作品走向文本成为一种必然。
在理论史上,虽然20世纪初兴起的俄国形式主义没有明确使用“文本”这个概念,但他们在研究中提出的“文学性”等理论,实际上已将文本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这为文本概念的提出和界定奠定了一块理论的基石。布莱克曼(J.M.Broekeman)专门写了一本《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的著作,描述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旅行的路线图,从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文本这个概念的旅行和生成路线。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苏联政治形势的变化,形式主义受到批判而逐步式微。雅格布森从莫斯科到布拉格,开始借鉴语言学理论,用音位分析研究诗歌。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他们是将形式主义的思想在“索绪尔语言学框架中加以严格的系统化”[1]。布拉格学派的形成代表了形式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过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结构主义的兴盛于法国,是因为当时法国巴黎聚集了一批研究者,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将索绪尔的语言学应用于文学研究。如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神话研究,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研究,热奈特的叙事功能研究,巴特的叙事层次研究等。在莫斯科的形式主义看到了文学语言的重要性,而结构主义则关注的是文学文本的深层规则和结构。形式主义走向结构主义,在于借鉴索绪尔语言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学,认为文学批评主要应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即研究文本的语言、结构层次等方面的特点。
俄国形式主义的文本观念是:文本是一种陌生化的语言客体,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是文学性;新批评的文本观念是:文本是语言的有机整体,文学文本的本体是其肌质。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明确提出了“文本”这个新概念。罗兰·巴特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和文章,将文本与作品区分开来。巴特在《形象、音乐、文本》(1968)中指出文本的语言特性:“作品可以由语言外在多样性的技巧来界定,而文本则彻头彻尾的就是与语言同质:它就是语言且只能通过语言而不是自身呈现。换句话说,文本只能通过作品和创造感受:文本即是意义。”[2]巴特在《从作品到文本》(1971)中进一步明确区分了作品和文本的关系。巴特否认作者对作品的决定作用,他认为文学作品并不是作者的个人产物,文学作品接近所指(signified),而文本则是对符号和语言的接近和体验。巴特认为:“文本则由语言来决定:它只是作为一种话语(discourse)而存在。文本不是作品的分解成分;而恰恰是作品才是想象之物。”[3]当然巴特在其他文章,诸如《作者的死亡》(1968)、《S/Z》(1970)以及《快乐的文本》(1973)中都曾提及文本与作品的区别。按照巴特的观念,作品与文本的差异有四点:(1)在本体层面,作品是一个实体,一个可见的实体,而文本则只能在生产中被感知;(2)在文类层面,作品只是意识形态产物中的文学这一类,而文本则不只限于文学,还包括其他各种艺术以及文化产品;(3)在符号层面,作品限于所指,而文本则是一种纯粹的能指游戏;(4)在阅读层面,作品是一种文化消费,作品带给读者的只是一种愉悦,而文本是一种游戏、劳动和生产,文本带给读者的则是一种快乐和极乐。总之,作品是作家创作的客观实在,而本文是文学作品的语言构成,是具有某种潜在意义的结构。在区分作品与文本区别的基础上,巴特对文本做出基本界定:文本是对符号的接近和体验,文本就是语言游戏。从作品向文本转向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语言和符号是文本概念的第一核心要素。正如瓦·叶·哈利泽夫说的:“文本是言语单位本身井然有序的组织结构,这一观念在文学中最为根深蒂固。”[4]
既然文本是由语言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那么结构就是文本概念的又一大要素。结构是文本内在稳定的秩序,是文本各个部分和层次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结构有如文本的骨骼、架构,结构的规则和逻辑决定文本的特性。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本语言的形式因素,或者说结构是凸现文学性的一种本体性因素;新批评认为文本是一个充满悖论与反讽的有机整体;结构主义认为结构不仅是文本的构造物,而且本身就构成了文本规则、秩序和逻辑。韦勒克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中的形式和结构概念》一文中考察从“形式”到“结构”的发展,论述了新批评、形式主义对形式的研究,认为传统的对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已站不住脚了,他建设性地提出了以文本的结构,也就是“内部研究”作为批评的方向。因此,在从作品向文本迁移的过程中,语言和结构构成了文本概念与批评的核心要素。
二、文本向互文本的延展:敞开的文本概念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后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以及现象学和阐释学的兴起,文本的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这可以说是又一次大的理论旅行。1966年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巴特的研讨班上在介绍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时,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概念。1969年,她在《符号学》一书中正式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5]克利斯蒂娃还提出“现象文本”和“生成文本”概念的区分,她认为“生成文本”积淀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所以当现象文本与之建立联系时就会形成一个能容纳历史、文化的网络。在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以及阐释学的这一系列文本概念中,最经典的还是1973年巴特在《文本理论》中所作的界定。他指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文本;其他文本存在于它的不同层面,呈现为或多或少可辨认的形式——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过去引语的重新编织。”[6]巴特用“文本分析”方法代替早期的“结构分析”,他认为后人对前人文本的解读反过来构成并不断地构成前人文本的一部分,他强调读者要致力于倾听文本中的多重声音,以揭示处在互文性中的文本,使文本与语言无限相连通。
互文性表明文本不仅是语言的编织构造,其生成也是与读者关系密切的,文本可以说是在与读者的互动对话中生成的。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是读者阅读和感知的主要模式,读者在阅读或阐释文本时,通常必须汇集一个以上的互文本来加以审视。“互文性”的英文“intertextuality”一词来自拉丁语“intertexto”,本意为“交织”。在《文本的快乐》(1973)一文中,巴特分析了文本的生成过程。巴特将文本比作编织加以形象地说明,他认为:“文本(Texte)的意思是织物(Tissu);不过迄今为止我们总是将此织物视作产品,视作已然织就的面纱,在其背后,忽隐忽露地闪现着意义(真理)。如今我们以这织物来强调生成观念,也就是说,在不停的编织之中,文被制就,被加工出来;主体隐没于这织物——这纹理内,自我消融了,一如蜘蛛叠化于蛛网这极富创造性的分泌物内。”[7]《文本的快乐》主要说明文本不再是面纱,其背后亦无隐藏的真理,文本的生成在于语言符号滑动和浮沉不定,在于读者阅读的游戏之中。
与此同时,在德国、波兰等国家兴起的现象学、阐释学也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提出自己的文本观,特别是对读者的重视。在阐释学看来,文本的解读与有一定视域背景的读者相关。迦达默尔认为在主张文本的规定性和开放性方面现象学美学家英伽登采取“图式化”方式对文本进行分析是出色的。英伽登认为艺术作品作为一种“意向性关联物”只是一种图式化的抽象存在,充满无数的“不确定点”和“空白点”,有待通过读者的想象性阅读才得以确定化。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已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文艺阐释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8]德国接受美学家伊瑟尔的文本理论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在《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1976)一书中区分“第一文本”与“第二文本”,认为文本具有一种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伊瑟尔借助英伽登的“空白”和“不确定性”概念,认为意义不确定性与意义空白是文本召唤结构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提出“文本的隐含读者”,这一概念标示出读者内在于文本的特征,也意味着文本潜在的一切阅读的可能性[9]。因此,读者也是内在于文本的核心要素之一。
三、超文本和泛文本的出现:扩大化的文本概念
超文本和泛文本是理论旅行到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一类概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特别是现代信息科技的发展,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开始在西方蓬勃发展。在这一理论语境下,传统的文本概念开始受到挑战,文本概念也显得驳杂,出现了超文本和泛文本等概念。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的文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纯文学文本,可分析其民族、阶级、权利、性别、身份等经济学、社会学的问题;另一类文本则是网络文学、电影、电视,或者是更广泛的诸如广告、时装、居室装饰等更广泛的文化文本。
1962年美国学者泰德·纳尔逊创造了“超文本”(hypertext)这一术语,他对“超文本”作的界定是非相续著述,即分叉的、允许读者作出选择的、最好在交互屏幕上阅读的文本[10]。可见超文本是一种扩大化的文本概念,是语言学继续向符号学深入发展的产物。超文本是采用文学语言,以及直接诉诸人的感官的符号和媒介(如视觉,包括图画、造型艺术作品;听觉,包括声音信号、音乐;或者视听多种感官,如戏剧、影视、网络媒体等),以超链接的方式建构的充满交互性的文本。这样一来,文本概念范围明显扩大,文本意义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背景,甚至进入了文化学领域,因此这种文本也被称为泛文本。可见超文本与泛文本的概念界定存在一定差异:泛文本是从文本形式、内容,以及背景的广泛出发,而超文本是从文本链接,以及媒介构成出发。
强调审美可以说是文学文本概念的基本特征。20世纪初文学批评就是要摆脱社会、历史的批评,转而追求具有审美特征的文学性。俄国形式主义从词语的构成性出发,探讨文本的文学性。现象学和阐释学文论则要让文学性呈现于读者参与其中的文学活动。英伽登认为:“文学的艺术作品不是为了增进科学知识而是在它的具体化中体现某种非常特殊的价值,我们通常称之为‘审美价值’。”[11]我们可以看到,从早期形式主义到现象学,其批评关注点无论是文本内部语言,还是外部的读者,其立足还是在于文本的审美。那么超文本和泛文本强调的是什么呢?20世纪60年代,巴赫金在《语言学、语文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中的文本问题:哲学分析之尝试》中将像超文本、泛文本这种由多种符号链接的文本定义为“有联系的符号综合体”,但是巴赫金强调人文科学始终要立足于文本,他认为:“如果在文本之外,脱离文本来研究人,那这已不是人文学科。”[12]可见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种文化批评的文本概念已扩大到整个人文学科领域,泛文本、超文本等概念的出现实际是对传统“纯文学”的质疑,它使得学界开始重新思考文学文本概念的界定和其核心要素。
在后现代主义和文化批评看来,文本除了语言、结构、读者、审美等核心要素外,还与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以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詹姆逊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将文学活动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生产。如伊格尔顿认为文本是由一般生产方式最终决定,作家借助一定审美形式和相对独立性的文学生产方式加工而成的审美意识形态。在詹姆逊看来文本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他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出“元批评”的策略,“我们研究客体与其说是文本本身,毋宁说是阐释,我们是借助这些阐释来面对和利用文本的”[13]。而且他明确指出了这种阐释应该是以文本的意识形态阐释为前提。其实,巴赫金早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中就提出符号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他说“哪里有符号,哪里就有意识形态”。他认为“在话语里实现着浸透了社会交际的所有方面的无数意识形态的联系”[14]。因此以符号构成的文本,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批评那里,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具体化,而意识形态则是后现代超文本的核心因素。
综上所述,从文本理论和概念在20世纪西方旅行的路线和历程来看,文本概念是在旅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其传播路线图是:俄国——布拉格——巴黎——德国——美国,最后走向全球化。最初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文本理论无疑具有真理性,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则致力于文本结构的建构和消解,而现象学、阐释学将读者的加入无疑使得文本理论和概念得到丰富,全球化背景下后现代主义和文化批评的意识形态研究又对传统文本理论提出挑战。由于不同地域的各个文本理论流派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出发点存在差异,而从这些各异的出发点来阐述文本概念往往会发现文本的不同侧面,以及文本不同的内核要素:语言、结构、读者、审美,以及各种意识形。文本概念正是在这种持续的理论旅行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对我们而言,在界定文本概念时,我们必须要历史地看待文本概念的发展,全面考虑其核心要素。
[1]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424.
[2]Roland Barthes.Image-M usic-Text[M].London:Fontana Press,1981:39-40.
[3]巴特.从作品到文本[J].文艺理论研究,1988(5).
[4]瓦·叶·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00.
[5]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G]∥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947.
[6]罗兰·巴特.文本理论[G]∥风格研究文本理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302.
[7]Roland Barthes.The p leasure of the text[M].Oxfo rd:Black well,1990:64.
[8]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9.
[9]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20.
[10]George P.Landow.Hyper-text2.0:the Convergence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 ry and Technology[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3.
[11]罗曼·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154.
[12]巴赫金.文本问题[G]∥巴赫金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00-325.
[1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
[14]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G]∥巴赫金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