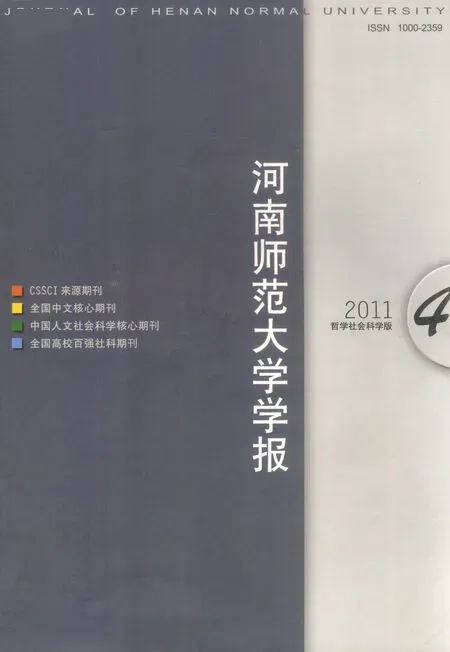刘心武小说中的启蒙话语
2011-04-12郭庆杰
郭庆杰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河南濮阳457000)
新时期启蒙叙事沿袭了五四启蒙文学的路径,面对着沉浸于苦难中的民众进行精神疗救和进行自我反思,刘心武是新时期初期承续近代以来启蒙传统的代表作家。新时期启蒙思潮萌生于“文革”后的社会文化环境,人们普遍感受到政治体制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因此,呼唤启蒙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伴随着政治变动,其时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民众的强烈认同,使启蒙价值得以体现。刘心武准确地抓住了历史蒙难后的社会普遍心态,承担了人性反思的历史使命。20世纪90年代以后刘心武以社会人生、世态人情构筑的宏大叙事不如当年轰动,但是作为曾经剥离政治文化的桎梏而发掘美好人性,探寻人格尊严、自由精神的先锋者,刘心武一直关注弱者的生存体验,维护底层边缘小人物的人格尊严,成为作家社会良知和文学精神价值的守护者。
一、遍布伤痛的生存图景
启蒙叙事的合法性基础即世界存在着普遍的精神苦痛,新时期文学萌发的启蒙言说将政治事件所引发的苦难与对民众的心灵救赎相联系。那时,各种“伤痕”铭记着民族心理的创痛,成为最典型的文化意象和时代符码。刘心武搜检当代中国尤其是在“文革”中所经历的各种苦难,描摹着苦难的具体状貌,在文学世界里构造出一幅幅遍布伤痛的生存图景。他首先感受到的是政治独尊的社会语境中的种种苦难,并预先把这种伤痛记忆作为前提提供给读者。《班主任》表达的是“文革”给中学生的教育造成精神毒害的悲情故事,《醒来吧,弟弟》、《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大眼猫》等篇目历数了青年们精神困惑的苦痛心理,《我爱每一片绿叶》和《如意》提供了中国当代政治环境中人性正常的需求被抹杀、尊严遭受蹂躏的种种事实。
新时期文学率先表达政治苦难,在社会道德层面进行灵魂重塑和精神拯救,当以人性自由为核心的文学启蒙精神深入人的心灵世界时,人们就会察觉政治文化并不能涵盖人性的全部内涵,而文化热潮的兴起带来了更为深广的人性认知,导致政治苦难关照下的伤痛主题不再惹眼和突出。虽然“伤痕文学”的轰动效应已经过去,大众的政治热情消退,但是刘心武对伤痛的关注却成为他的思考定式,并内化在其心灵深处,更为凝重。《立体交叉桥》、《钟鼓楼》从现实居住空间问题,返回到历史场景中,呈现了这一具体的生态群落所经历的“社会性苦恼”;《5·19长镜头》等纪实小说选取了与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社会问题,揭露了生活背后的各种心灵隐忧;《私人照相簿》则以家族史事为线索,隐含着对中国现代历史背景中的家庭悲欢离合和人事沧桑的喟叹。
政治苦难的发掘和述说与新时期国家意志诉求同步,刘心武表达了强劲的社会改造的冲动。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边缘人生生存状况的关注,他的创作从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开始进入对心灵世界的审视。他密切关注为社会所漠视的群体,探寻各种切实的社会问题,他的笔触总是伸向多数平凡的民众,作品保持着强烈的现实批判能力和生命质感。《站冰》、《泼妇鸡丁》、《榆钱》、《京漂女》、《民工老何》等新作对城市中的孱弱和边缘群体的生活现实及精神状态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刘心武凭借着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延续了巴尔扎克的社会风俗研究传统,进行着社会现实作品创作,体现了他在公共领域理性原则下扩展私人空间的持续努力。
刘心武的小说在新时期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承接了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在社会现实的逼仄中勾勒出民族魂灵,甚至被视为当代政治文化的泛文本。与五四时期有着广阔的中西文化背景的作家相较,刘心武更强调社会关怀,显现出自觉的政治身份的皈依。
二、师者形象与底层人物
政治苦难成为新时期文学启蒙叙事的文化前提,作家的启蒙意识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变动直接相关,承载启蒙价值理念的人物命运也深刻着政治历史变迁的烙印。刘心武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空间总是应和着时代变迁。按照角色功能,其人物形象基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承担着启蒙理念的知识分子形象,另一类是被启蒙的底层边缘人物。
新时期初期,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迫切需要反思历史,重新审视传统历史观念,这时智者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因此,知识分子形象被满怀期待着,注定要被塑造成拯救国家民族于愚昧和苦难的时代英雄形象。刘心武以浪漫和激情塑造了《班主任》中的张老师形象,在小说中他被赋予了精神救赎者的崇高地位,突出了其过度符码化的特征。而其后的《醒来吧,弟弟》中的“哥哥”则是对失去理想目标的年轻人进行精神疗救的导师和兄长形象。他希望唤醒的不仅仅是“弟弟”,而是借助“弟弟”这一角色在小说中发挥其文学的“广场”效应,从而达到对社会的启蒙效果。显然,这样的师者形象具有传达理念的工具效能,但并不具备充分的人格魅力和审美价值,最终也无法为大众所信服。
新时期文学中启蒙理念的表达不只是知识分子对底层百姓进行单向传输,也有不少启蒙者的反省和自思。《班主任》之后的作品中,知识分子并不总是满怀自信、踌躇满志的启蒙者角色,他们同样是需要不断自思和反省的群体。在道德平台上、在完美人性的标尺前,刘心武揭示了知识群体的精神生态、性格缺陷与病态心理,甚至在被启蒙者面前,他们也并不总是占据精神优势。而这样的反思,自《如意》开始越来越突出,小说中一号主人公是身处底层的石大爷,在芸芸众生中,地位卑微的守门人却有着完整而健康的人性表达、人格尊严和真挚的人情观念,而生活在他周围的众多教师,却显得平板、暗淡、伪善和猥琐。在《我爱每一片绿叶》、《立体交叉桥》等作品中的教师形象不再是智慧的拥有者和道德的完美者,他们都是充满了矛盾和困惑的普通人。刘心武对师者的反思越来越深入,不断表达对他们不足之处的痛心,甚至嘲讽。
而对于另一类身处底层的形象,刘心武则体现了一如既往的精神关注。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各种有着现实苦痛和精神创伤的弱者形象,他们被各种观念和权力话语排斥和压制,被忘却和遮蔽。新时期文学初期,刘心武进入了宋宝琦和谢惠敏的心灵世界,就发现了他们是启蒙者需要关注的精神受害者,是隐蔽在阶级论视野之外的精神弱者。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这样的人物形象成了刘心武笔下理解和救赎的对象。他们不乏物质满足,精神却无所依托。这类人物形象被他视为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他们跨越时代界限,超出年龄性别,即便芸芸众生也具有整体意义。
传统的人文道德和政治视野成了刘心武阐释当代中国文化进程的意义载体,但他的思考定式也成为突破时代、超越自身的重轭,他的作品在新时期的社会急遽变动中成为短暂的巡视。面对人物的精神苦痛,刘心武总是努力挖掘其社会现实原因,习惯以道德伦理介入作品,这使得他的小说世界中人物之间的精神差异逐渐弥合,获得了超人的道德优势。他的小说中有不少冲破束缚的小人物形象,他们不断寻求人性自然自主的发展,在社会语境中寻求自己的立身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这些人物形象,刘心武并不单以启蒙姿态进行精神观照,在他看来,这些底层人物身上也不乏传奇色彩和浪漫气质。刘心武小说设置了社会弱者,但是面对这些具体形象,道德立场冲击了他的批判姿态,他并没有把弱者形象与被启蒙者完全等同,他们可能在生理上受虐受苦,但不一定就损害他们的精神高度。小墩子(《小墩子》)、甘福云(《蓝夜叉》)等普通底层人物身上潜藏着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诉求。在作品中,人性的表达和改造与国家、民族的集体主义表达连接在一起,因此,这些个体形象蕴涵着民族现代化的寓言,在集体主义话语中,他们更是作为形象的集合体,而不是单个的形象来进行精神诉求的。
20世纪90年代后的社会结构变化和文化转型改变了人的价值定位,如果说刘心武对弱者形象的塑造隐含着国家民族意愿,那么此时的弱者形象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弱者”,而且是文学世界中的边缘形象,他们的生存需求和话语权力经常被遮蔽。刘心武关注的对象没有改变,但是对象与社会结构的定位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国家民族的主人翁转化为被漠视的弱势群体,从社会的中心滑落到了边缘。刘心武对这些形象的描摹,潜在地担负起与社会存在的普遍认知的抗衡。《民工老何》中的老何作为20世纪90年代在城乡交界间生存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个体,有着与社会互动衍生的烦恼,城市化进程吸引甚至诱惑了村民,同时也给他们的精神带来强大的压力,老何及其儿女们正面临着这种转换中的压力。他们在逆境中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执著追求。作家依然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注和审视,难能可贵的是,他写出了这些生活困窘的底层民众,依然秉持着美好、善良的人性,生活虽则艰苦但人格却不卑微,显示了足够的自信和尊严。
刘心武的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标记,他是在一元化观念、一体化的机制中逐步释放个人空间,在社会的背景下争取个体发展和自我生存的空间的。他有着浓重的政治情结,关注的是政治语境中的边缘人物。他把政治语境中的宏大叙事渗透在巷弄的日常生活中,把历史感转化为特定的民间叙事,在平淡无奇的叙事中表达人性的丰富多元和复杂共生。
三、空间意象的启蒙隐喻
启蒙文学思潮更侧重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任何一种意义阐释又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形式结构。刘心武的创作虽然并不有意突出形式特征,但是在阐释意义时不自觉地形成了自己的言说模式,包括结构、时空等各种叙述要素。刘心武的小说以独特的受限制的空间传达作家的启蒙理念。刘心武的作品空间意象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常常被封闭,处于其中的人们在精神上经常有被监禁,且又无从寻找伸展的感受。城、楼、长廊与鸡蛋壳是刘心武作品中颇具典型意义的空间意象。
刘心武在许多小说中讲述了大量的城与楼的故事。与老城联系在一起的是灰色而混杂的普通人生活,被城市的累积压抑在底层的普通人心态,以及为冲破压抑和寂寞所作的无力挣扎,“我洞见了普通人心灵深处的一种最淳朴的渴求与一种最浑黑的寂寞以及试图冲出这种寂寞的暴烈挣扎,我鼻子发酸”[1]204。如果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是通过知识分子唤醒大众的启蒙,从而确立知识分子的启蒙地位的话,那么,刘心武作品中对启蒙的解读已经转换为普通大众知识分子凭着共通的人性对美好、善良以及纯真等精神品质的渴求,来实现其启蒙目的的,即使这种渴求非常微弱和单薄,刘心武也认为这是最为真诚可贵的。在当代中国普遍削平知识等级观念、强调阶级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身份逐渐淡化,而普通大众的自主意识在不断增强,启蒙不再属于某一特殊阶层,也无法为知识阶层所特有。当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各种工农运动,知识分子阶层对一般民众的认同是史无前例的,刘心武对人性和人本的追求正是基于这种现实环境,同时,也是对五四启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语境中产生的新诉求的体认。
城、楼、院的空间意象设置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启蒙任务的转化。鲁迅当年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中国社会像“铁屋子”的意象,象征着封闭和压抑的传统家庭结构。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中有许多作品强烈抨击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和中国传统观念。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社会在逐渐瓦解家庭观念的过程中,试图用假设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家庭”来替代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当代社会伦理结构的改变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也影响了刘心武的空间认知。呈现在他的作品中的空间结构由闭合的家庭开始向社区过渡。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运动打破了传统的楼、院的家庭设置,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传统的楼、院的空间结构被不同的家庭分割,形成许多互相瓜葛又互相独立的家庭集合体。显然,传统的自足的家庭观念很难有效地在当代社会的家庭成员间得以贯彻,社会主义集体观念在当代生活中更具权威性,而互相居住在一起的家庭集结又是松散的,缺乏统一的意志观念。面对着这样一个空间结构,人物既能获得较大的活动空间,同时也会因内在的繁杂,变得更加茫然和缺乏稳定性。
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要求打破“铁屋子”的黑暗主要从变更造就“铁屋子”的社会环境开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反抗,直指上层社会。而刘心武小说则着力于表达既定空间内人物存在的合法合理性,其生活空间成为他们存在的依据,决定了他们的生活状态。他的作品描述这种存在,而不是揭示造就这种生活状态的不合理性。90年代后的作品甚至津津乐道于这种自足的生活状态,而对于打破自足空间总是隐隐地表达出遗憾和落寞,《小墩子》、《立体交叉桥》等作品都有类似的表达。刘心武进行全新的文体试验的“现代派”代表作《无尽的长廊》,在文本设置的假定情境中,进行精神漫游时,选取的空间意象是鸡蛋壳。这个虚拟的精神驻足空间无意识间展露了刘心武心底的深层表达,鸡蛋壳与“铁屋子”相较,铁屋子是冷酷无情的,阴暗而寒冷的,而鸡蛋壳却不同,它“内壁如珍珠般光润莹白,绝无一纤尘垢,使我浸泡于纯洁的氛围中”[2]。到头来,这些看起来非常坚固的空间意象,却在设置障碍和保护之间的挣扎中化为乌有,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人们心灵的确定概念又不时地隐约闪现,成为尴尬和荒诞的存在。“人们往往为自己的心灵挖掘出深深的护城河,然而到了关键时刻,护城河边却无战事,袭人变得轻而易举,沉沦仿佛风到花落……”[1]445
刘心武作品中空间意象的呈现和变异与他对世界的认知、体验和解读有关。刘心武是忠实于自身经历和体验的作家,他的作品首先是对过去生活的记录,对自己生活的回忆。“我”在小说叙事中的地位外表看来只是一个叙事者,但是从功能来看,若缺少这个叙事者,所有的人物形象、所有的故事都将缺乏叙事基础。“我”在叙事构成的深层次上,确定了作品的叙事基调和价值设定。
四、政治情结与问题意识
描述当代中国的苦难图景以确立新时期启蒙话语的合法性,通过师者形象和底层人物讲述启蒙故事,以各种空间意象呈现启蒙文化语境,构成了刘心武立体而丰富的启蒙叙事形态。文本的呈现取决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对世界的认知,刘心武启蒙言说的方式和限度取决于他以政治视角审视世界和以问题意识引发思考的方式。
《班主任》虽然质疑了阶级论建构的宏大叙事,开始从社会政治层面下延至生活世情,但不可否认它之所以能够引起当时人们强烈关注的原因,也是以往的政治化话语和阶级斗争思维的延续。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遗毒”、“精神创伤”等社会政治话语下的解读,而对其中的精神创伤代表如谢惠敏,在宏大政治叙事中,只关注到政治给她带来的伤害,却遮蔽了她作为女性形象否定女性气质的不正常心态,性别压抑在强大的政治叙事前被忽略了。作者只把她纳入到性别模糊的社会领域,成为社会话语的承担者,自语被代言功能完全遮蔽。作家难以舍弃载道之文,表现出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从而限制了他对人性的深入探寻和挖掘。他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启蒙意识,但并没有明确启蒙的价值内核。
问题意识使刘心武对题材的选择大多采取近距离的社会观照,通过陈述现象表达超现实的精神关怀,刘心武笔下的人物形象对启蒙之光的渴求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鲁迅小说中的被启蒙者形象往往受苦很深并精神麻木,所以,被启蒙者的处境与心灵是合辙的,既在社会底层又在精神苦难中,但在刘心武笔下,身处社会底层的并不一定就是精神卑微者,因此受虐、受苦不一定需要拯救,真正需要从人性上进行拯救的是处于苦处而不自知的人群。伤害在精神上,这正是五四启蒙文学所努力表达启蒙的合理合法性的再现和延续。他在描绘处于人性困境中的人们时坚信:只要有了美好理想,就具有了无限抬升的力量,就可以完成启蒙的拯救任务。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在人性、人情的平台上自然无法解决,况且诉诸人心的启蒙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他的作品甚至简化了人性困境的难度,刘心武比鲁迅要乐观,因此,他所提供的启蒙路径也由此而失落。
刘心武在难以贯彻始终的启蒙路途上调和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差异,也适应了知识分子和大众间的对立逐渐消隐的社会现实。首先,他化解了政治语境中因强烈对立和尖锐冲突形成的狭小空间。其次,他打破了革命话语造就的序列等级制度。空间上的安排无疑使刘心武的作品获得了人物间平等的充分理由,进而,开始解构集体主义话语的一体制,消解“我们”话语的统治性和权威性,复原鲜活的独异的个体形象。刘心武作品中的平民生活史在获得广阔的现实社会空间的同时,也将尖锐的文化冲突和矛盾转化为平民世界中的具体现象和问题,但刘心武只提出问题,并不努力追问社会问题背后的文化原因和探究人性的困惑,因此,这些问题并没有深化人性的认知,它在细碎的市民生活圈子中只会变得平淡和泛化,只能消解现实中存在的文化矛盾和人性悖论。
刘心武的小说所呈现的社会历史感在市民阶层的巷弄间的表达,事实上以人物群像提供了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历史脉络。当中国当代政治提供的集体主义的公共自由成为历史尘埃时,个人自由之声浮出水面,深受体制拘囿的中国民众,生活在巷弄这一半封闭和半开放的空间里,他们需要挣脱既受限制又相对开放的生活环境的束缚。在极度张扬公众普遍意志的政治自由向追求个体满足的个人自由倾斜时,在都市文明的现代自由和驻守于乡村文明的集体自由间,这种心态却是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城市化不彻底、政治权威借用公众名义侵略到私人化的生活空间的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产物。刘心武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特定时期的人性表达,并努力寻找这一群体的人生趋势和人性可能空间,但它恰恰表明了新时期中国启蒙路径的复杂和困顿,刘心武所作的努力只是穿过一道拯救的窄门。
[1]刘心武.刘心武文集·四牌楼[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2]刘心武.刘心武文集·无尽的长廊[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