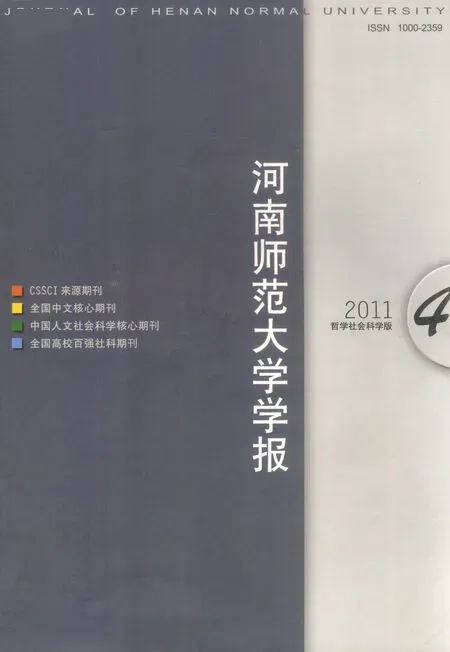期求和谐
——曹禺戏剧的一种伦理向度
2011-04-12陈永明
陈 永 明
(南阳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期求和谐
——曹禺戏剧的一种伦理向度
陈 永 明
(南阳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曹禺剧作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期求和谐的伦理倾向:在人的悲情怜悯中期求畅享人伦之和,在人生境遇的叩问中寻求文化之和,在与社会时代价值同构的诉求中探索社会之和。曹禺期求和谐的伦理诉求,成就了曹禺剧作系列鲜活而深刻的人物形象,映照出剧作家复杂而隐秘的情感世界,也导致了他自身令人感喟的戏剧性人生。
曹禺戏剧;期求和谐;伦理向度
文学的伦理价值作为人类社会古老的审美命题,体现为人类伦理道德借助审美形式实现自身存在的一种结果。曹禺戏剧始终围绕人的生存境遇进行伦理价值的创造性艺术建构,呈现出畅享人伦之和、追寻文化之和、探索社会之和的强烈伦理倾向,在剧作的深层结构和作家的身心隐秘世界里到达了一种自我丰盈、自我抚慰、自我救赎的“和谐”状态。
一、人伦之和
本着对人的生命本真最原始、最崇敬的热爱,曹禺高扬文学的伦理旗帜,在其创作中用敏锐、悲悯的眼光捕捉生命历程中说不清、道不明的悲情境遇,通过表现生命生与死的挣扎而博弈于神秘的命运,勘剖“恶”与“非恶”,在对个体生存的伦理思考和诗性表现中,流露出高度的人性关注与强烈的伦理关怀倾向。“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1]183。曹禺的戏剧着眼人类而直指人性深处,深切关注和执拗追索宇宙奥秘和人生况味。他指出写人“要写好多面,要从他的表面写到他的内心”[2]12。其剧作以丰满鲜活的艺术形象深刻揭示了人物性格在特定历史情势下蜕化的无奈性与非我因子,从而实现“恶者”由“恶”向“非恶”的流转。
《雷雨》中的周朴园作为始乱终弃者、专制家长、资本家这类“扁平人物”,无疑是“恶”的典型。但曹禺将其放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流变中来写,他则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家庭悲剧的制造者和承受者,在他身上承载着“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暂时不能实现”的时代悲剧性以及曹禺深切的悲悯之情。周萍尽管犯下双重乱伦罪孽,曹禺却希望“化开他的性格上一层云翳”,“要设法替他找同情”[1]189。《北京人》中曾皓拼命攫取愫方的青春热情的行径固然卑鄙自私,但也透露出曹禺对其处于精神孤寂、行将就木的可悲境地的同情。曹禺对管家婆曾思懿也表示一定的理解:“她也有她的难处。她为人惹人嫌恶,但这个‘家’是她支撑着。”[1]587《原野》中的焦母凶狠残暴、老辣刻毒,也是“恶”的形象,但她又是父债子还的承受者,遭受了顷刻之间失去儿孙的致命打击。曹禺对《日出》里的“坏蛋”也“无意中便流露出这种偏袒的态度”,“我深深地憎恨他们,却不由自主地怜悯他们的那许多聪明,奇怪的是这两种情绪并行不悖,憎恨的情绪愈高,怜悯他们的心也愈重”[3]48。曹禺对剧中人物生存境遇倾注的人文关怀突破了人伦道德的简单是非,其笔下即使有不赦之恶的人物也在展现人性丑恶的悲剧历程中,成为“错综复杂”的丰润“圆形人物”。这些人物作为剧本中能够激发读者进行伦理观照的“意义召唤结构”,也饱含着剧作家对人的生存及其伦理价值的审美思考。考究曹禺剧中“祛恶”倾向的伦理根源,既有曹禺对生命本真的悲悯,更蕴藏着他为求自身人格完善和心灵和谐的“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
这种迫切需要的情感表现为曹禺心灵镜像“映照”在剧中的“一种感情的憧憬,一种无名的恐惧的表征”[1]183,是其试图寻求情感“宣泄”与精神“抚慰”,达到身心和谐而对“人伦之和”的艺术畅享。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是欲望,而欲望是一种对另一个自我意识的对象性关系。个人主体只有在另一个对象化了的他人镜像关系中认同自己。拉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具有审美认识意义的镜像理论。具体到戏剧人物的认识上,镜像理论可用来阐释那种借助戏剧人物之间相互映照而将其所隐蔽的人生与命运虚像化地补充出来的艺术现象。曹禺通过制造镜像互补的审美认同机制,不仅使其剧本中的人物相互映衬与补充,而且使剧中人与剧作家之间相互映照与抚慰,在期求家庭伦理和谐中,用剧中生命去理解、去抚慰另一种生命真实,从而构筑了一种超越伦理理性、突出生命感觉的戏剧结构,达到艺术表现与伦理对话中的生命感觉共鸣,实现剧作客体与作家主体之间相互映照的内在和谐。
一是父子镜像互补关系。曹禺承认其父“和《雷雨》中的周朴园有些相似”[4]8,《北京人》中的曾皓“就有我父亲的影子。我对我的父亲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我爱他,也恨他,又怜悯他”[1]586。这种复杂的父子情愫映照在他对剧中“父辈”们的塑造上:周朴园“外厉内荏”,既有自私冷酷、蛮横残暴的一面,又有他内心的痛苦无奈及对侍萍款款深情的一面;《原野》中的焦母在刻毒凶狠的背后,则是风烛残年惨遭不幸。在另一层意义上,《雷雨》中周萍说他恨父亲,甚至希望父亲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子辈”们的这种“仇父”情结源于其长期受封建专制父权威压的恐惧,也有其幼年缺失母爱的创伤性体验。于是便有了周萍与继母的畸形爱恋,当他试图通过与四凤的恋爱来摆脱与蘩漪乱伦之罪恶感时,其罪孽不亚于30年前的周朴园,其懦弱卑怯恰如彼时的父辈,此时的子辈即是彼时父辈的镜像;同样,侍萍与四凤、焦母与大星、曾皓与文清、高老太爷与克定,等等,他们两代人的命运发展也都是呈镜像互补与映照态势的。这种镜像构成了戏剧一种前涉性或后设性的叙事结构,丰富和深化了戏剧人物的艺术底蕴,也反映了曹禺对封建礼教下人伦道德的深切焦虑与人生悲情境遇的终极关怀。
二是男女镜像互补关系。周萍等子辈们的精神苦闷与性格“云翳”,是其父辈们在特定历史境遇下人生经历镜像的前涉性映照。如果说这种映照在一定程度上是曹禺出于伦理考虑而对父辈们家庭人伦道德关怀的艺术书写,那么曹禺剧中阉鸡似的男性与美丽的女性所形成的镜像互补关系,则是曹禺幼年生活境遇和情感经历的映照与宣泄,是其补偿自身缺憾的戏剧幻象。曹禺剧中礼赞的女性形象有两类。一类是天生具有牺牲精神的善良女性,以愫方、瑞珏、侍萍、鸣凤等为代表。一类是追求自我的“雷雨的”现代女性,以蘩漪、花金子、袁园等为代表。以最“雷雨的”蘩漪为例,她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上演一个女性内心挣扎与自我作战的残酷悲剧,是对“天地间的残忍”的蛮力释放与生命探险。曹禺认为她“是值得赞美的”,“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更值得人佩服”[1]185。曹禺塑造具有牺牲精神和开放性格的女性,与周萍、曾文清、焦大星等人“阉鸡似”的性格相互映证,也以一种召唤式的戏剧结构与曹禺创作心态构成互补。她们应剧作家自我拯救的心理需求而幻化为戏剧意象,这种意象与曹禺“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的性情特质相映照,隐含着曹禺通过艺术创造对其自身创伤进行抚慰与补偿,最终达到人格完善与身心和谐的强烈欲求。
二、文化之和
在叩问人生境遇时,曹禺剧作在中西文化的浸染与渗透中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与本能欲望,为人物冲破“牢笼”实现自我救赎与本质充盈提供可能,极大地丰富了剧作的文化审美内涵,也体现了曹禺回归传统伦理文化的倾向。
曹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剧作家“注视、解读并有选择地接受一个自成体系的基督教文化,以悲悯的心态看待悲剧中的所有人物”[5]。《雷雨》中“原罪”的忏悔救赎、《原野》中的“不以暴力抗恶”、《北京人》中的“重构精神的家园”等,无一不是对宗教教义的阐释,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曹禺笔下的悲剧人物在梦幻般的戏剧结构中走向肉体死亡和精神毁灭,他们以忏悔、救赎、不可知的神秘、爱人、遵从基督教义、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使剧作散逸着浓郁的宗教气息。曹禺执著地探究人类存在的奥秘,悲天悯人地思考着人生要义与命运,希望凭借宗教观察世态人生,构建人类精神家园,借以超越人生绵延不绝的苦痛与无奈。这无疑是曹禺对“人样的生活”的宗教救赎,体现了他追求人类“诗意的栖居”的乌托邦理想与世俗道德化倾向。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儒释道思想对曹禺的戏剧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日出》卷首对老子《道德经》的引用就是要抨击违背天道的“人之道”,反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剥削制度,这与道家所推崇的“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的社会理想是相通的。而曾被曹禺释为自己创作原动力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恰与道家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哲学相契合。道家崇尚自然的生命和人性,倡导“大文明若野蛮”。体现在《雷雨》中的“蛮性”、《日出》中的“夯歌”、《原野》中的“野性”、《北京人》中的人类祖先“北京人”,不仅是曹禺创作的原动力,而且还是其批判造成人类生存悲剧的文明社会的精神武器。
“每一种文化形式一经创造出来,便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成为生命力量的磨难”[6]。没落官宦家庭出身的文化熏陶、传统封建文化的教育与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在曹禺身上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注定使得曹禺的文化心理呈现出斑驳的色彩。曹禺基于对生命的伦理直感,在批判代表封建礼教与宗法制度的“狭笼”和“坟墓”的同时,又不自觉流露出回归传统文化的倾向,除了表现在《北京人》中对士大夫文化的留恋与欣赏,更集中体现在对人物的情感倾向上。曹禺塑造了侍萍、愫方、瑞珏、丁大夫等具有传统文化美德的女性。他说:“像愫方这样秉性高洁的女性,我是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词来赞美她们的,我觉得她们的内心世界是太美了。”[4]38继《蜕变》之后,曹禺陷入与妻子郑秀及情人方瑞之间的婚外恋情不能自拔,他也承认愫方“是根据我的爱人方瑞的个性写的”[2]9。这里我们肯定曹禺对愫方这类“舍身爱人”的传统女性的美化有私情因素,但也不可否认儒家文化仁爱思想对曹禺的影响。愫方“温厚而慷慨”,心甘情愿为文清及其家人耗尽自己的青春,瑞珏“以身殉爱”,即使临终之时依然宁静而无悔。这都反映了曹禺在伦理维度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与回归倾向。
三、社会之和
曹禺在“人样的生活”与“春梦”的探寻中,尝试着探索人的利益诉求与社会公平道义的动态平衡,期求找到心灵和谐与利益共享的理想社会,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他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乌托邦式的伦理思考。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模式一直回旋在曹禺的创作中。钱谷融说:“在《雷雨》里,周冲是一个奇异的存在,一个‘不调和的谐音’。”[7]说周冲“奇异”是因其心中充满了诗意的遐想,对爱与自由及平等博爱的向往,对人间公平正义的追求;说他是“不调和的谐音”是因其生活在充满欲望罪恶、黑暗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可以想见,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即使他不意外触电而死,那个充满幻想的周冲也不会再现了,以至于蘩漪气急败坏地说“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像我,你——简直是条死猪!”“你还是你父亲养的,你父亲的小绵羊”。其实周冲只是曹禺的一个“春梦”而已。《日出》中的方达生被论者认为是幼稚病患者,其实他作为作者伦理道德力量的化身,具有反抗黑暗、拯救弱者、崇尚劳动的精神,且能付诸行动。曹禺之所以没让他像周冲一样偶然死亡,恐怕也是想给黑暗中绝望的人们一些反抗的勇气,并让他为作者的理想社会继续探索。《原野》中花金子与仇虎私通,看似旧情的炽然与泼野的肉体爱恋,实则是她把实现爱情梦想与人生理想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仇虎身上,寄寓着她对去“地上铺满黄金的地方”过“人的日子”的追求,尽管“天外边”是遥远的,“金子铺的地方”是朦胧的,可它是她自我救赎的捷径与梦想。这种单纯而执著的追求散发着原野泥土的芬芳,也浸润着作家乌托邦式的伦理关怀。
囿于时代环境和自身的认识,当时的曹禺还未能给笔下人物找到明确的社会出路。无论周冲、方达生,还是花金子,都只是曹禺充满诗意的艺术幻象与最深挚的憧憬,寄寓着他对真善美的乌托邦社会的无限渴望和对丑恶社会现实的极端憎恶,寄寓着他的欢喜和失望,是他幼稚多感、饱尝愤懑与痛苦的灵魂的补偿与抚慰。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深受儒家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影响的曹禺创作了系列关心民族命运的载道之作,如《黑字二十八》、《蜕变》、《艳阳天》,开始了他艺术创作与人生之路的转折。新中国建立后,曹禺还创作了《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作品,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曹禺告别了过去那个富有诗人气质、执著追问人的命运的自我,他以全新的姿态融入到社会主义新的生活当中去了。遗憾的是,他在“文革”中屈辱自保,失却坚执高蹈的精神气节。这固然是特定时代的社会悲剧,但深潜在曹禺身上的文化伦理的双重性与软弱性更是导致其悲剧的重要因素。这对穷其一生探索“人样的生活”,期求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社会和谐的伟大戏剧家曹禺来说,不能不算是个让他身心痛苦的悲剧。
[1]曹禺.曹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曹禺.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J].剧本,1982(10).
[3]曹禺.曹禺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48.
[4]田本相.曹禺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5]王列耀.宗教情结与华人文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86.
[6]刘小枫.现代性中的审美精神[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416.
[7]钱谷融.《雷雨》人物谈[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53.
I206.6
A
1000-2359(2011)04-0188-03
陈永明(1973-),男,河南信阳人,南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专项任务(2011-ZX-342)
2011-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