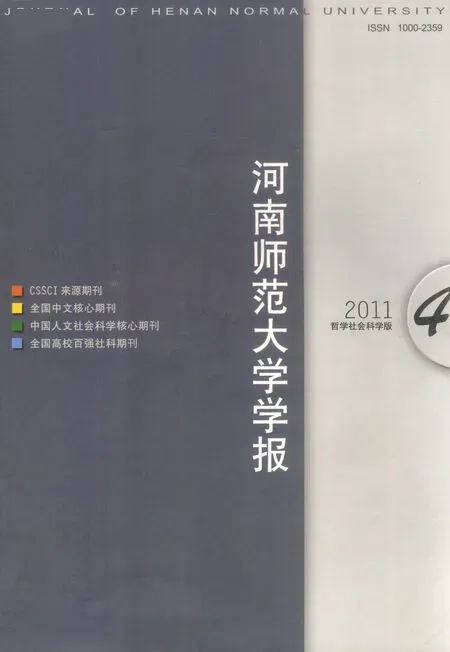试析作品中创造性的界定
2011-04-12张晓敏
张 晓 敏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试析作品中创造性的界定
张 晓 敏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作品内在的创造性是著作权法律关系发生的依据和正当性基础。在著作权领域,创造性涵盖在独创性判断之中,但是,由于缺乏独创性的具体标准,作品受保护的范围无法明确界定;功能性作品的出现甚至挑战了作品独创性的底线标准。独创性标准的坚守是著作权立法的目标追求,有利于界定私域与公域的界限;同时,独创性程度、实质性相同的排除、智力投入及创作意图的考量是独创性标准判定的因素。
创造性;著作权;作品
一般认为,创造性是著作权客体受保护的实质要件和逻辑起点,是建构著作权权利基础的核心。在著作权领域,创造性涵盖在独创性标准之中,由于其内涵的不确定性和标准的不统一性,独创性标准备受争议并遭到质疑。为了使保护和鼓励创新的知识产权立法目的得以贯彻如一,并合理地界定私域与公域的界限,著作权领域既要恪守独创性标准又要对独创性以恰当的界定。
一、创造性是著作权正当性之基础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旨在调整因创造性智力成果产生、利用和保护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鼓励创新是这一制度的根本动机和价值追求。著作权主体所享有的法定时间内的排他性的专有权利,一是基于权利主体的创造性劳动及其创新成果的产出,二是基于创新成果控制权的稀缺性而获得的市场青睐。
首先,根据劳动价值论,创造性智力成果来源于人的创造性脑力劳动,创造性劳动的价值度量要由个别劳动时间来衡量,创造性劳动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了智力成果的创造性价值,这种劳动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表现出智力劳动产品——作品使用价值的个性化和异质性,是取得著作权的核心。同时,在社会需要的层面上,智力成果专属使用权的交换价值取决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程度,消费者对创新成果的偏好是创造性智力成果基础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这种由社会需要决定的创造性智力成果的市场价值,是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内所具有的价值。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量上取决于社会对某一种生产物已经在数量上确定了的需要,它反过来制约着创造性智力成果交换价值的价值量。因此,著作权赋予作品产权化保护正是来源于创造性劳动和劳动成果的创造性。“确信一个付出了智力上劳动和努力的个人创造者有权享有其劳动果实,确立了解释知识产权正当性的基础”[1]。
其次,知识产权作为专属支配权具有法定的稀缺性。法律之所以通过特许权的形式赋予知识产权权利人以排除他人免费复制和使用的垄断权利,限制了不特定人接近智力成果信息资源的自由,从而人为地创设了知识产权的稀缺,是源于知识产权作为特许权控制下的知识产品所体现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创造性价值,能够满足人们对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的需要,并以商业化应用带来经济价值。法律通过权利界定拟制的稀缺,保障了知识产权特许权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回报,“通过这种人为创造的稀缺,在实现对知识创造者产生更大收益的过程中,知识产品的生产却被相应地激发了”[2]189。从这个意义上说,著作权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获得了私权禀赋和正当性源泉。
二、创造性是作品受保护的内在依据
人的活动不仅是自由自觉地有目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而且是以人的情感、智慧、价值和理想,按照美的规律来超越既有的给定,构造再造物,创造有意义的、不断发展的生活世界。因此,创造的过程凸显了人类的理性和精神指引,创造性是人的活动的固有属性和内在本质。创造性强调人的认识的能动性和创新性,注重主体创造力在客体中的凝聚以及独创性新成果产生。著作权领域虽然以独创性定位创造性,但在作品不同的表现形式中依然会体现出程度不同的创造性,并决定着作品受保护的依据。
首先,创新成果的超越性。突出创新成果的前所未有性和开拓性,表现出人类认识的始创造甚至零起点,具有独树一帜的领先性,是最高层次的创造性。人的活动表达着自主超越性向度,人所具有的内在的不断追求超越既有经验存在及生命境况的冲动,是创造性的原动力。如原创性作品,作为作者基于首次创作行为直接产生的作品,打破了原有的思维定势和思想框架,提出新问题,把握新方向,开拓新领域,体现了质的飞跃,是著作权高强度的保护范围。
其次,创新成果的差异性。体现创新成果在原有成果基础上的差异性和进步性,表现出人类认识的再创造和非重复性更新,是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推进,在原有形式上的显著性变化和更胜一筹,是前人已有的成果的实质进步及优越胜出,表现出弃旧图新的变革,代表了人类不断超越自身的发展向度。人们锲而不舍地自我完善,是创新活动的不断向前递进的内在尺度。例如演绎作品等二度创作的作品,在已有作品中增加了新的独创性表达,体现了可区别性的显著变化,依然是可著作权的表达。
三、作品创造性认定的困境
著作权将作品保护限定于独创性范围已成为各国立法的共识,但独创性的认定,尤其是独创性中的创造性成分的高低却大相径庭。英国法官认为,著作权法不要求作品必须是原创的或唯一的,只要求不是对另一作品的复制或抄袭。在美国,要求作品是由作者独立完成,并且必须具备少量的创造性。法国最高法院则将独创性解释为“表现在作者所创作作品上的反映作者个性的标记”[3]。个性则是创造性的表现。在德国,认为作品应具有一定的创作高度,它是著作权保护的下限。我国著作权法将独创性作为界定作品的内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且有创作性的,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由此可见,我国著作权立法中对独创性的界定包含了独立完成加一定的创造性,独创性应涵盖对作品质和量的两方面的规定。
尽管独创性作为作品受著作权保护的基本条件已经被世界各国所认同,但由于各国在立法上无独创性的具体判断标准,作品受保护的范围缺乏明确的界定;同时,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功能性作品等新的作品形式不断增加,独创性能否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底线标准再一次受到挑战。
(一)潜意识再现
世界上不存在无中生有的作品,任何作品都与前人的文明成果具有传承关系,或多或少地借鉴人类文化遗产,并受当代人智慧的启迪。人们的创作活动离不开以往经验的积累,包括其他作品中吸收的经验。当作者在潜意识中埋藏了前人某些独特的表达因素,通过记忆、经验再现于自己的作品时,如果这种表达仍在著作权保护期内,作者无意识地复制了在先作品的表达形式,此时,如何认定该作品的创造性?尽管衡量作品中借用在先作品受著作权保护的分量与著作权保护程度密切关联,著作权独创性理论仍然无法准确判断他人作品中的再现部分与作者独特表达或重构的区别,此类作品独创性质和量的规定性亦难以把握。
(二)二分法下的改头换面
思想与表达二分法作为著作权法域中的重要原则,强调著作权法保护只能及于思想的独创性表达,而不保护思想本身。由于思想是通过表达表现的,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通过附载在作品中的特定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尽管思想具有积累性和继承性,一种新思想很难同公有领域借用的思想截然区分,但一个包含着作者独创性新思想的表达的作品,与一个利用旧思想做出新表达的作品相比,必然体现出较高程度的创造性。当有人利用了作者具有独创性的新思想,并对这种新思想的原创性表达做了改头换面的修改后把它当做自己的作品,由于著作权法并不禁止同一种思想具有多样化的表达方式,此种作品的创造性成分如何界定?在目前盛行的学术论文检测技术中,似乎通过了所谓论文抄袭检测系统,该论文就堂而皇之地打上了独创性或独立完成的标签,免除了侵权责任。对表达的弹性解释,降低了作者写作的成本,“使作者能够不受约束地抄袭自己的前人”[4]。
(三)功能性作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作品种类的扩大,数据库等功能性作品进入著作权的保护范围,著作权的独创性标准受到了挑战。数据库作为一种服务于用户特定需要的有组织、可共享的数据集合,具有可访问性的检索工具性质,它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是其内容的选择或编排体现独创性。《TRIPS协定》第10条之二规定:“数据或其他材料的汇编,无论采用机器可读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编排构成智力创作,即应予保护。”一方面,由于数据库可能来源于对一些事实材料的汇编,其创造性程度之低使作者能够轻易地满足,著作权却能够给予所谓“创造性的火花”的保护。同时,按照“辛勤收集原则”(industrial collection principle),作者制作相关数据库过程中的辛劳付出或实质性的投入被作为判断数据库受著作权保护的条件,独创性品质来源于某种智力技巧的运用,独创性标准便被降低。另一方面,“电子数据库的内容贮存在数字化媒介(CD-ROM、网页等)上的顺序是由其驱动程序决定的,这种编排的技术性考虑多于创作性考虑,很难满足独创性的要求”[5]。而数据库的功能性和实用性目的是其财产价值的基础,数据库规模越大选择编排的独创性越小,甚至有人担心数据库的独创性要求会导致数据库制作者成本的增加,阻碍数据库产业的发展。数据库受著作权保护可以突破独创性的要件吗?
四、创造性在著作权保护中的恰当认定
创造性的判定在著作权领域始终是模糊不清的,许多国家著作权法基于独创性对作品进行界定时,仅要求最低程度的创造性,甚至是“创造性火花”“微小的创造性痕迹”。尤其是对于一些功能性作品创造性成分如何考量,成为立法和司法的一大难题。鉴于此,有学者提出降低创造性标准,适当降低对数据库独创性的要求[6]。还有学者主张以信息产权理论的“投资回报”替代知识产权理论的创造性标准[7]。创造性标准的坚守是著作权立法的目标追求和基本价值取向,是不可动摇的基石;创造性在著作权保护中的恰当认定有利于私域与公域界限的划分。同时,增加创造性标准的可操作性也是司法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独创性划定了私域与公域的界限
由于人类思想的传承性,任何作品的创作都离不开公有领域的素材,即便是一种新思想的表达也会或多或少地留下前人思想成果的痕迹,如果不加区别地把它们一并划入权利人的保护范围,将是不合理地挤占公共资源,并妨碍公众利用作品的空间,从而阻碍科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者独立构思或在前人成果启发之下完成的新的表达形式是作品独创性的构成,这种独创性来源于作者智力的创造性劳动,也是作者取得法律上的垄断利益的唯一依据。独创性从理论上划定了专有与公有的界限,将作品受保护的范围限定在含有一定程度创造性的部分,以区别于非创造性的公有领域的素材。作者因创作获得了法律激励机制下的控制权和利益,作品的新思想在作品发表后融入公共资源库,丰富了公众可接触的信息源,也为公共利益的实现以及他人的后续创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二)作品独创性判断的主要因素
1.独创性程度。从理论上说,一部作品只要是作者独立完成并赋予独特的个性表达,并且不是对已有作品的复制抄袭,就能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对象,而不论其创造性程度的高低和价值的大小,作品的创造性程度与获得著作权保护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需要强调的是,首先,作品仅仅是作者独立完成,并不一定具有创造性,“仅凭独立创作本身并不能保证作品的质量,因为独立创作的作品也可能是低劣、平庸而毫无价值的文化渣滓”[8]。因此,通过独立的创造性劳动并打上独创的个性烙印的作品才是著作权保护的对象,对作品独创性考量必须内含最低程度的创造性。其次,作品的著作权受保护的强度关联着作品的创造性程度,作品中创作性成分越少,受保护程度就越低。作品受保护的价值判断来源于作品的创造性,一定的创造性程度是作品独创性的内在追求。数据库这类功能性作品也只有在素材的选择、编排、分类、检索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独创性才能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
2.实质性相同的排除。尽管著作权法不排除不同主体就同一客观对象的独创性表达而产生的雷同作品,但却阻止将他人作品中的独创性部分当作自己的作品的抄袭行为。对于“借用”他人享有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的行为,如果借用的是作品的创作思想则不在保护之列;如果借用的是作品思想的表达,则要看被借用作品表达的保护范围,该保护范围即为作品中的原创性成果,此时,适用“实质性相似”认定方式。即看借用者是否实质性复制了被保护作品中的独创性表达,两者是否存在质和量上的“可区别的变化”,同时,借用者是否有机会接触到受保护作品的这些特定的表达,两者是否达到了实质性相似的程度,进而判定是否侵权。“体现在著作权作品中表达的特定化程度越大,其他作品与该作品的区别程度就越大,即相似性的减少是排除实质部分或实质性相似的标准”[2]702。可见,被保护作品的独创性程度,是确定借用作品与受保护作品法律上相似的关键,吸引他人借用的理由更多来自成果的创新性,独创性程度越高,诱使他人抄袭的可能性就越大。“值得抄袭之处, 即是值得保护之推定证据”[9]。对于潜意识再现受保护作品的独创性部分,美国法院认为:“被告是善意地忘记了自己的作品来自原告的作品,这种‘无辜复制’仍可构成侵权。”[10]值得借鉴。
3.智力投入及创作意图。作品的创造性只能来自作者非技巧性、非机械性的智力创作劳动,这种智力性投入是衡量作品独创性的一般标准。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创作意图应包含在智力投入之中,作者经过独创性探索,找到了独特的构思,从而确定了作品中特定化的表达主题和内容,这是一般智力创作行为的必经阶段。但是创作意图作为主观的创作动机属于思想的范畴,不能成为著作权保护的理由。只有将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通过表达形式表现出来,浸透在最终完成的作品中,具有创造性的创作意图才能在作品中体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当作品的独特表达来自创作意图的贡献时,创作意图就构成了作品独创性的一个核心要件。此时,创作意图成为佐证作品创造性的因素。但是,美国学者大卫·尼默提出的将创作意图作为独创性的要件时,“意图检测是一个排除性而不是包含性检测,因为当将其应用于一个创作作品(作为毫不费力作品的对立面)时即是一个不相关的问题”[11]。即如果能明确证明作者没有创作意图,便可以否定其作品的独创性。从这个意义上,创作意图可以作为判断作品独创性的要素。从包含性检测标准来看,“智力投入”还包括作者经过独立思考、智力判断,将思想感情融入创造活动,运用聪明才智独立完成智力成果,作者投入智力创作劳动须最终凝结在作品上,作品中蕴涵的差异化和个性,体现着创造性的量的规定性。这些构成作品独创性的智力投入是作品可著作权的依据,也是作品创造性的印证。
[1]冯晓青.“增加价值”论:知识产权正当性的一种认知模式[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2]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3]姜颖.作品独创性判定标准的比较研究[J].知识产权,2004(3).
[4]波斯纳.法学与文学(增订本)[M].李国庆,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20.
[5]薛虹.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63.
[6]唐广良.计算机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73.
[7]骆电.传统著作权法上创造性要求面临的挑战与回应[J].法律适用,2010(5).
[8]韦之.略论作品的独创性[J].经济与法,1993(3).
[9]Tina Hart,Linda Fazzani.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M].Beijing:Law Press,2003:148.
[10]孟祥娟.版权侵权认定[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97.
[11]L.Ray Patterson.Nimmer’s Copyright in the Dead Sea Scrolls:A Comment [J].Houston Law Review,2001:38(2).
[责任编辑孙景峰]
TheProperDefinitionofCreativityinWorks
ZHANG Xiao-mi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The creativity inside works is the basis and legitimacy for legal relationship of copyright. In fact, creativity is covered in originality judgment from the point of copyright. However, due to lack of specific standard for originality judgment, the protection scope cannot be identified. Moreover, the bottom line of originality is challenged by the advent of functional works. Adhere to originality judgment is the target for copyright legislation, which also helps us bette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And there are three main standards for originality judgment which are the level of originality, the discriminating against substantially similar works and the evaluation of intelligence investment and creation intension.
creativity;copyright;works
D923.4
A
1000-2359(2011)04-0131-04
张晓敏(1958—),女,江苏武进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
2011-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