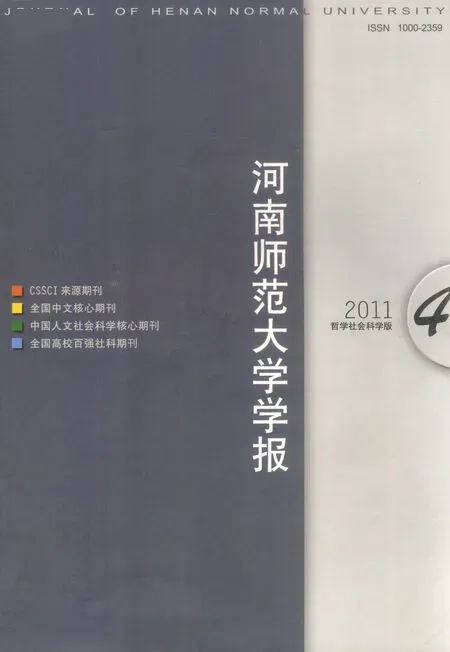论两岸关系中的台湾非政府组织
2011-04-12王运祥
安 然,王运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目前两岸关系虽日趋缓和,经贸文化往来日益频繁,可是大陆与台湾仍旧面临隔海分离的局势,建立统一和强大的中国仍旧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一、两岸关系现状
台湾问题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内战的遗留问题。两岸关系从新中国建立至今经历了相当大的波折与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949年至1978年。此阶段两岸基本上处于绝对的隔绝,甚至在武力上也是相互对峙的状态。以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为标志,其内容主要为商讨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并提出两岸三通、扩大两岸的交流,由此两岸关系迈入了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至2007年,这是一个对两岸关系的探索过程,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1978年大陆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美关系也步入正轨,台湾也在80年代宣布解除戒严,两岸的经贸、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从此开始愈加密切。可是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并非只有和平统一的主旋律。在李登辉、陈水扁当政期间,他们相继抛出“特殊国与国关系”“一边一国”论调,鼓吹台独,更有陈水扁的“去中国化”运动,使得两岸关系“剑拔弩张”,引发台海局势的动荡。到了2008年5月,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两岸关系才步入了第三个阶段,迈入了和平发展的新轨道。
自2008年以来,两岸双方抓住机遇,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关系呈现出共识增加、交流频繁,制度性协商谈判成效明显、和平发展态势逐渐稳固的良好局面[1]。目前两岸关系正呈现出和平发展的强劲势头,两岸各界大交流局面正在形成,且两岸的交往也正在向着制度化和机制化进程有序推进[2]。可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良好的大环境下,两岸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面临一定的阻力和挑战,“台独”势力依然存在,反“台独”的斗争仍需继续下去;同时也有来自国际上其他大国的干预,企图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的发展,控制台海局势。和平统一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毋庸讳言,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及未来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台湾民众当然也可以从中受益。两岸之间关系的改善,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台湾仍然有一部分人对大陆的怀疑。陆委会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在认知大陆政府对台政府的态度上,持“不友善”(43.4%)的要高于“友善”(37.3%);至于大陆政府对台湾人民的态度,持“不友善”(41.4%)与持“友善”(41.2%)的比例相差不大。由此可见,台湾民众对大陆政府仍保有警觉心[3]。
胡锦涛也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的十六字方针:“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足见“建立互信”是两岸关系能够稳健发展的重要前提。可是由于目前两岸的特殊政治状态,我们政府无法直接向台湾民众传达我们的意愿或是直接落实某些政策,因此建立互信需要另辟渠道,那就是依靠民间交流,依靠非政府组织(NGO)扮演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发挥桥梁作用。这样非政府组织依靠自身优势,既可以赢得民众好感,也可以有效传达政府意愿,在两岸关系的进一步稳健发展中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台湾NGO的发展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 rganization,简称NGO),又被称为“非营利组织”“民间团体”“慈善机构”“志愿组织”“第三部门”等,并在诸多文献中也经常被交互使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在其文件中指出:“虽然非政府组织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也有一些基本的性质符合一般的协议。一个非政府组织是一个非营利实体,其成员是一个或多个国家的公民或公民社会,而且其活动由其成员的集体意愿来决定,以响应其成员或与该非政府组织合作的一个或多个社区的需要。”[4]本文采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对NGO的权威定义。
1949年国民政府退至台湾,5月宣布“戒严令”,台湾进入戒严时期,对于政治、媒体和结社自由等有着诸多的限制。直到1987年宣布解除了“戒严令”,政治上才开始民主选举,言论和结社也趋向自由。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背景下的台湾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展现出充沛旺盛的活力。20世纪80至90年代成为台湾NGO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社会运动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开放。据统计,1988年刚解严不久,全国性社会团体的总数是822个,到1996年时已成长至2390个,成长了2倍之多[5]。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台湾NGO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规模,步入正轨,其数量更是增长迅速。在2000年政党轮替后,新执政党对于民间团体更加重视,推动台湾的组织参与国际事务,鼓励非政府组织对于国际社会的付出。根据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的统计,当前台湾地区的基金会和社会团体的总数共达16085个,涉及环保、人权、妇女和人道救援等许多方面,规模数量都相当可观。
台湾的NGO随着全球化的脚步逐渐开始走入国际社会,同时伴随着全球治理的需要,台湾的NGO也开始参与国际社会活动。而其参与国际事务的目的有两个:首先,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宣扬其NGO的立场和理念,在各自领域为台湾NGO谋求立足之地;第二,鉴于台湾进行所谓“外交活动”的特殊性,许多NGO被打上了政治烙印,一定程度上代表政府的观点,在国际上开展“外交活动”,以“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事务,提升国际能见度。但台湾NGO在参与国际事务过程中的表现也确有值得肯定的方面,涉及环境保护、人道救援、科教卫生等许多方面。下面笔者将以国际援助为例来概述台湾NGO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及贡献。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由两极格局向多元体系转变,由权力和利益而引起的区域间热战频频爆发,例如科索沃战争、卢旺达种族屠杀、海湾战争等事件。此外,由自然灾害以及生态失衡引起的灾难也随着全球工业的发展发生得愈发频繁,使得许多无辜的人面临生命的威胁。于是人道救援成为全球性的议题。非政府组织具有中立、非营利、不带有政治色彩之特质,相较于国际组织与主权政府更适合从事人道救援之行动[6]。台湾地区致力于推动国际人道救援活动,在台湾有30多个慈善团体在50多个国家进行急难救助。台“外交部”与“国际美慈组织”(M ercy Co rp s)、“海伦凯勒国际组织”等国际人道救援团体分别签署了合作备忘录[7]。台湾从事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NGO以“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影响力最大,其在国际人道救援事务中表现十分积极。2003年伊朗巴姆城赈灾救援事务、2004年南亚海啸救灾以及医疗协助、2005年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赈灾等事迹,皆可见其在国际救援事务上之贡献。而近50年来,红十字会所援助的地区遍及亚太、美洲、欧洲、非洲、中东北非等5大区域40个国家,而该组织在目前国际人道救援事务上拥有相当高度之专业经验,亦在人道救援事务上占有相当重要之地位[8]。再例如“慈济基金会”,它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国际援助,并成立了“国际急难救助基金”。慈济基金会在90年代期间的国际救援工作遍布五大洲,而受援国也多达40多个国家[9]。迄今已援助了70个国家和地区。对于受灾国家,除了提供粮食、衣被、谷种、药品的紧急援助外,还援助建房、建校、协助开发水源、提供义诊。关怀项目尽管有别,“尊重生命”理念却是始终如一 。
当然,台湾NGO的发展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一些是普遍性的,是国际上多数NGO在发展中都会遇到的,台湾NGO也不例外。首先,由于NGO的非营利性,它只能从有限的渠道获得资金来源;再由于其公益性,大量的支出又不可避免。因此,充足的资金来源和经费资助成为NGO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和保障。台湾NGO由于其数量庞大,组织规模又大小不一,有相当一部分的NGO都存在资金匮乏的问题,单靠政府的补贴是远远不够的,且政府补贴又无法顾及所有的NGO。较大规模的NGO,例如“慈济基金会”“红十字会”等,它们的运作机制已经十分健全,有固定的资金来源,同时,由于其享有的美誉,其获得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固定募捐资金也相当可观,经费充裕。可是大多数NGO还都达不到这样的条件与规模,有学者认为“欧美地区NGO资金来源多半来自私人捐献,但是台湾捐献风气未兴,亦是台湾NGO经费不足的原因”[11]。
其次,外界对NGO法律地位和管理的质疑。在发展中国家,一些有关NGO注册登记、行政管理、法制化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发达国家,NGO发展较为成熟,有相关法律来明确NGO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等,NGO具有国内法上的人格已毋庸置疑,但对于其是否具有国际法的主体资格则尚未明确,其主要争论在于NGO是否能够直接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和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台湾的NGO已具有相应的公法地位。在台湾地区有关NGO的法规有民法总则中的法人规定、人民团体法、免税法规和捐募法规等,将NGO纳入法律系统之下进行管理,也使得其更加规范化。可是由于台湾并不存在统一管辖所有NGO的主管机关,不仅不同类型的NGO的主管机关不同,就连同一类型的NGO也都可能存在不同的主管机关管辖不同层面事务。这样虽然加大了政府对NGO的监管力度,“但由于多头管辖,也容易造成管理层混乱、意见矛盾的局面”[12]。
再有,NGO成为问责的对象。以往的NGO都是以问责的主体身份出现来履行对政府、企业、其他组织的监督职责。但是,随着NGO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社会需要,世界各地的政府、企业、各类组织,甚至是媒体和公众也开始对NGO发出了问责的要求。全球治理下NGO的发展不全是积极方面,在其发展过程中自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表现在于组织活动和财政信息的透明度不高、政策判断依据和倡导的质量有赖于考证等。
除了以上种种NGO发展中都会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外,台湾NGO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也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归结为政治原因。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行政体系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享有主权。然而,实际情况是台湾尚未纳入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其有自身的行政组织、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且在台湾岛内更有“台独”势力渗透其中,鼓吹“一中一台”,企图宣称台湾是“独立的国家”。目前来看,现任的或历任的执政党派都未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抑或是高调宣称台湾独立,与大陆的关系也是时而缓和时而紧张。正是台湾政治上的尴尬地位,使其NGO在参与国际事务中受到了许多限制与约束。
三、两岸关系中的台湾NGO
1987年台湾宣布解除戒严,两岸关系逐渐恢复并趋向缓和。尽管两岸关系时而缓和时而紧张,可是两岸联系与交流愈发密切是不争的事实。在推动两岸交流与地区发展的进程中,NGO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两岸NGO所开展的交流与合作不胜枚举。
目前的情势是台湾仍然没有真正回归,因此两岸沟通多依靠民间交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要求的进步,两岸社会和人民都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和平发展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心声,这便促使两岸民间交流日趋繁荣。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2009年5月在厦门举办的首届海峡论坛上致词时也指出:“两岸民间交流是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两岸民间交流是两岸同胞增进了解、融洽感情的重要途径;两岸民间交流是凝聚两岸同胞意志、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13]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是当前两岸交流的主题和重头戏。除此之外,两岸的民间交流还在科技、教育、体育、卫生等各个领域开展,最大限度地实现两岸优势互补、互利双赢。
多年来台湾历届执政党都相当重视岛内NGO的发展,一直都在大力支持台湾的NGO能够参与到国际非政府组织当中,为台湾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提高台湾在国际舞台的能见度。台湾NGO的发展固然值得鼓励,可是受到了政治影响的NGO会丧失其自主性与非政府性,其开展的活动也不单纯是公益性质的,而是沾染了政治色彩的,更有甚者沦为了当政者的政治工具。这样的NGO不但打破了岛内NGO整体发展的协调性,同时也间接性侵害到了中国的主权。试图借参与国际组织的形式达到使国际社会承认台湾地位的手段虽然没有建立所谓“邦交关系”来得明显,但是其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
台湾某些台独分子试图利用一些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NGO来进行“外交活动”的行为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台湾利用这种所谓的“第二轨道外交”或是“非政府组织外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实不可行。
首先,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虽然在不断提高,但还不足以取代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活动中的重要性,国家主权目前还是无法取代的。官方邦交才是主流,非官方的邦交只能是外交活动中的辅助手段。“第二轨道外交”如何重要和有效,也不及各个国家对官方外交的首肯。
其次,“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是国际所达成的共识,只有个别小国是由台湾通过“金钱邦交”所换来的“邦交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认可无法同日而语。
再次,有着“外交”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过程本身就存在矛盾,台湾的执政者想要利用其开展“外交活动”不免增加了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资金来源、组织管理甚至是活动的接洽都需要依靠“政府”来帮助,这完全丧失了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失去了它的非官方色彩和公益性质,就不再能够称作“非政府组织”了,因此利用非政府组织开展“外交活动”本身就是个悖论。虽然被台湾部分人寄予厚望的“第二轨道外交”或是“非政府组织外交”自身便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大陆依然需要对这种试图看似合理却想要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方式提高警惕,杜绝这种企图分裂国家的行为。
总之,对台湾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也是希望能够做到知己知彼,有益于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对于台湾NGO事业的发展,大陆无疑是持支持的态度,NGO的不断进步与成熟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与成熟,是值得鼓励的,可是前提是需要坚持NGO自身的特质,保持NGO性质的纯净。而对于某些台独分子利用非官方的渠道,特别是利用非政府组织企图进行“第二轨道外交”则另作别论。但是鉴于台湾非政府组织这种社会政治力量的不断强大,提前做好防备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目前稳定繁荣的两岸关系得以延续,双方共同朝着更为积极方向努力,早日成为真正“统一”和“强大”的中国。
[1]董玉洪.国民党重新在台执政周年两岸关系发展综述[J].两岸关系,2009(5).
[2]王克群.近期海峡两岸关系评述[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1).
[3]宋兴洲.两岸关系的发展现况与主要挑战[M]//第12届中国科协年会第31分会场海峡两岸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2010:103-106.
[4]联合国文件.UN.DOC,E/AC,70/1994/5[Z].1994.
[5]顾忠华.公民结社的结构变迁——以台湾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为例[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9(36).
[6]刘俐吟.国际非政府组织与我国政府在国际人道救援事务伙伴关系之研究[Z].TASPAA伙伴关系与永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8.
[7]赵勇.台湾政治转型与分离倾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96-215.
[8]D.露易斯.非政府组织的缘起与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2005(1).
[9]王慧萍.大爱包容地球村——慈济国际人道援助1991-2000[M].台北:慈济文化志业中心,2000.
[10]慈济基金会.慈济国际赈灾[EB/OL].(2009-01-09)[2010-11-15]http://www.tzuchi.o rg.tw/index.php?op 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50:2009-01-09-00-33-26&catid=54:international-relief-about&Itemid=308&lang=zh.
[11]张隆盛,廖美莉.我国参与联合国重要活动之策略[EB/OL].(2001-12-17)[2010-12-12]http://old.npf.org.tw/PUBL ICA TION/SD/090/SD-B-090-007.htm.
[12]杨兰.香港、台湾、新加坡之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的比较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34.
[13]贾庆林.扩大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两岸合作发展——在首届海峡论坛上的致辞[J].两岸关系,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