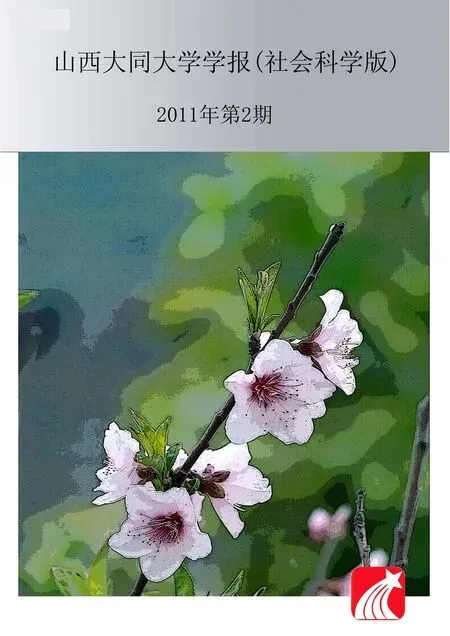北朝文化精神中的草原文化取向
2011-04-12蒙丽静
蒙丽静
(1.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2.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编辑部,山西 大同037009)
北朝文化精神中的草原文化取向
蒙丽静1,2
(1.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2.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编辑部,山西 大同037009)
草原文化特质是北朝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一方面,来自于北方游牧部落的北魏拓拔鲜卑集团对中原的儒家礼乐文化有吁求;另一方面,北朝的少数民族特质又有机地渗透到北朝文化的各个角落,其自由、尚武、劲健的文化品格对之后隋唐的文化风尚具有重要影响。
草原文化;审美取向;北朝文化精神
北魏是少数民族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建立的封建王朝,统治时间长达200年之久,这在隋唐以前是罕见的。其文化精神的定型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建设完成的,这种状况也一直持续到隋唐。不仅隋朝是北方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延续,就连辉煌的大唐帝国也流淌着来自于草原的少数民族的直系血脉,有着草原文化的遗存。草原文化的多元体对中古审美文化走向有着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却常常因夷夏观念而被学者忽视。对这样一种特殊时期的文化形态进行研究,就必须保持广阔的民族视野,才能揭示中古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
一、草原文化对儒家礼制的政治诉求与冲突
草原上的部落联盟制是北亚政治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史料表明,联盟中的每一个部落大人以独有的方式获得部落牧民认可后,就具有对自己部落的绝对权威性。部落内牧民以部落大人名为姓氏,“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独立地散居在属于自己部落的草原领地中。部落联盟制的领袖与诸部落之间的联盟是一种共有天下但又互有契约式的权利协作关系,这与草原游牧部落散居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有关。台湾康乐先生曾用符拉基米尔佐夫在《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对蒙古草原游牧部落的研究做比照,铁木真做汗王时,其部下宣誓:
(我们)立你做皇帝。你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得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如厮杀时违了你的号令,并无事时坏了你事呵,将我离了妻子家财,废撇在无人烟地面里者。
而铁木真也有着汗王的义务:
如果我是帝王,并是许多国家军队的先锋,那末,我一定会对部下尽义务,将许多马群、畜群、帐幕、女人、孩子和百姓都来与你们。在草原狩猎时,我与你们整治通道,构筑围场,并把山兽赶到你们方面去。[1](P28)
这种草原文化政治传统与中原的以伦常为基础的礼制传统截然不同,草原文化中部落下属的忠诚来自于对首领的神话般英雄式的崇拜、相应的契约以及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中原儒家文化中,帝王的合法性则来自于“道”,来自于以“天命所归”为依托的礼乐制度。契约随时可变,天命却不可违。在不断进入中原并接触到中原文化以后,修城筑邦的定居方式以及儒家的“万世一系”的帝王体系,对来自于北方草原文化体系的帝王来讲具有莫大的诱惑力。与草原散居的生活方式不同,农业聚居生活方式必须建立相应的秩序,才能确保政权的平稳。在物质资料稀少的情况下,在进行利益分配时,谁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人类对特权和利益最大化的追逐也永远不可能停止,一旦争执的双方力量发生变化,平衡将被打破。对于散居的北方少数民族来讲,草原残酷的弱肉强食法则只会造成部落间或部落内部的社会秩序更迭,战争后生存下来的会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但这种法则并不适合中原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劫掠方式在中原生活,后果就只能是战争不断,破坏农耕社会正常稳定的生活劳作秩序,将会对其生存造成毁灭性打击。农耕文化依附于土地,土地固定不变使得农耕文化更为注重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为了在土地上分工协作,更好地繁衍生存,以土地为基础的家族观念就显得格外重要。所以,以血缘为主“尊礼”的群体道德体系在中原地区的观念中占有绝对优势,而少数民族并不具有这样的观念。
公元220年,曹魏代汉,诘汾之子力微成为拓拔部落首领 (力微被后世的北魏王朝认为是北魏王业的奠基人,在位58年),不断扩大自己的部落联合体,建立了“帝室十姓”、“内入诸姓”、“四方诸姓”的部落体系和社会关系。“帝室十姓”的界限十分严格,不容外姓插手,而对“内入诸姓”和“四方诸姓”的管理则已经有了王权的倾向,一方面以军事强力来威慑与控制,如力微曾直接杀死不服从自己的部落首领,控制部落首领的立废;另一方面则以质任制度(即扣押人质,如部落大人长子等)作为牵制。以“帝室十姓”为核心的拓拔政治结合体并不稳定,当拓拔部落强大时就依附于拓拔部,反之,当拓拔部落呈现衰败时就独立或者依附其他强大的部落。这种强则为王弱则为奴的思维模式和利益分配模式,对统治核心内部的“帝室十姓”也有影响。从《魏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力微去世以后,其后继者却并没有重新树立起让人崇拜敬畏的威望,以至于40多年中就有12次部落首领的更迭,政治体系内部的不稳定直接导致部落的衰落。这种由内到外都不具备稳定性的草原政治文化特色,一直蔓延到北魏定都平城以后,以“谋逆”而引起的宫廷内部的战争多次发生。换一个角度说,中原士族的道德文化观念并不适合于评判草原的文化体系,对于承袭汉制的中原士人来讲是谋逆,而对于以拓拔部落的部落联盟政权形态为基础的北魏王朝来讲,“谋逆”可能就是极为正常的部落分裂、重新组合直至强大的合理程序。北魏初期的帝王个个骁勇善战,一方面,他们以强悍的能力率领各部落拥有天下,被“诸部大人”所共同尊奉;另一方面,作为领袖,他们同样有义务保障各个部落的权益,所以开国后北魏帝王对诸部大人大都直接分封极高的爵位,并给予相应的物质赏赐,这种文化深处的契约性思维模式并没有改变。契约是现世随时可以改变的东西,倘若首领不具备给予归属部落支持和保护的能力,契约就被打破,任何一个部落都有理由取代原来首领的位置。为了维持王朝的稳定和帝王的绝对权力,并把官吏的等级高下内化为每一个人都遵从的道德习惯,以“天命所归”的儒家的礼制就成为帝王最为向往和推崇的内容。任何势力的权力独立和僭越都被视为是对于皇帝专权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化是北魏皇帝对威胁皇权的潜在敌人的有目的的打击。北魏帝王权力绝对统一集中的要求与北朝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松散的政权体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种不可调和性在北魏立国推进汉化以后,主要表现为皇族势力与北镇府兵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北魏建国以后,历代皇帝都在推进儒家观念的教化,一方面是为了笼络中原人心,但更重要的就是要突破原有的契约式的政治文化传统,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治秩序,使自己的国祚绵长,然而文化传统的改变并不容易。
二、草原道德价值观在北朝文化中的体现
(一)女子位尊,婚恋自由社会风气 对于农耕社会来讲,男子完成主要的田间生产劳作,女子的任务是生育以及家庭内部的事务处理;而草原牧区的女子在家庭内承担的工作量几乎与男性是一致的。相比于农耕社会的女子,草原民族妇女在家中的地位更高一些,妇女亦像男子一样习射练武跃马驰骋。草原的财富以帐幕和畜产品为标志,女子婚后会获得一定的畜产品。一般而言,每家一个帐幕,而每一个帐幕中只能有一个女主人,而且即使是离开家的女儿也有资格从家产中分到相应的畜产品。与鲜卑同风俗的乌桓族的男子即便是杀死父兄也不会获罪,然而却不能伤及母亲,因为父兄之死只是本部落内部的事情,而母亲因有其出嫁前的族人替她报仇,这便会涉及到不同部落间的争执诉讼。[3](P214)这种社会现象,在北朝的历史文化中多有体现,从北魏道武帝拓拔珪建立“子贵母死”的制度以排除舅家势力干预夺权开始,到北方女主如文明太后、胡灵太后至唐朝武后的出现,大都有此风余波之嫌。北朝一夫一妻现象也较多,这不仅反映在社会生活中,而且还直接体现在北朝的诗歌创作中。南朝那种大量的视妇女为玩物的狎昵之作,在北朝文学作品非常罕见。另外,从恋爱婚嫁来看,北朝的妇女也较为自由。在乌桓鲜卑早期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嫁娶都是事先私通,除去相互恋爱较为自由以外,更可以确保女子的生育能力。女子出嫁可获得丰厚的嫁妆随男子而去,一般处理家中事务都由女子做主。这种风俗使得北朝女子在面对自己的感情时真挚大胆而热情,而且女子婚前选婿自由、婚后相妒成风、再婚以及婚外情比率大幅增多。北朝民歌和乐府中的爱情诗,都传达出清新真挚的爱情观念以及对爱情执着追求的审美风尚,为诗歌领域拓展了新的空间。
(二)重利尚实的价值观念 中原文化提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因此,以利益的收获作为行动的目的,在中原文化中是令人鄙夷的。但是,在早期的草原文化中,必须以获得辅助性的生活用品来维持生计,所以对于能够为家族带来利益的行为一律给予最高的评价。在《史记》中,司马迁非常鄙夷匈奴的这种不知礼仪没有节气的做法。有利就上,没利就退,在战争中,也不以正面拼杀为荣,能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一逃而散,这正是少数民族游牧生涯的主要战争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小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获。壮年之人有丰沛的体力能够从外部世界获得更多的资源,部落内只尊强者,这显然不同于汉族尊老爱幼的观念。因此,早期草原文化中并没有孝道之说。
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则瓦解云散矣。[4](卷110,《匈奴列传》)
这就是司马迁笔下匈奴人的形象。鲜卑部落也是不拘于礼仪,以劫掠为生。不管是匈奴还是鲜卑,他们都有着相似的做法。草原生存环境艰难,尤其是到冬季天寒地冻之时,成百上千头牲畜一起冻死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草原男子不为虚名所累,任性使气,置身于锋刃之间,他们所有的出发点就只能是为家人提供更多的生存机会,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中,能够担当起这份责任,为时刻陷于自然灾害以及面对不断战争的家人带回足够生活资料,就是有道德的表现。这种质朴务实豁达的价值观念,同样被带入北朝的文化体系中。
(三)尚武刚健的性格取向 草原经济的单一性决定他们必须以获得外界的辅助性产品作为生活的基本保障。获得的方式除了经济上的交换以外,最常见的就是武力上的掠夺,因此崇尚武功是草原文化的一个重要习俗,所谓“兵贵死”就是这种传统的真实的写照。“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加上北方苦寒的自然条件,使得草原民族必须具有强健的体质、剽悍粗犷的性格以及精于骑射的技能去完成扩大地盘、寻找和开辟牧场的任务。恶劣的生存条件使得崇尚武力成为草原民族天性中自然而然的因素,就像圣人是儒家崇拜并歌颂的对象一样,少数民族崇拜的是英雄。中原文化中的圣人制礼作乐,传承文化,是农业社会保持稳定并且健康发展的基石;而在冷兵器时代的草原英雄,则以骁勇善战的风格率领部族在不断的战斗中扩大自己的生活领地,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这种观念对于进入中原以后的士人文化冲击也很大。北方的少数民族就是籍此而获得了对中原的统治权,强烈的竞争意识使得拓跋鲜卑等少数民族具有尚武和刚健的审美取向。由北魏到北周至隋唐,尚武的社会风尚一直没有改变,与中原士族对门阀大族文化的敬重一样,北朝对于一门勇武的将帅家族也是充满钦慕。不仅男子如此,女子也多精通骑射甚至是带兵打仗,由此而出现以武艺为特征的射礼、围猎等游乐项目,甚至还进入到了国家的祭典礼仪中。尚武的社会风尚对文艺的影响很大,显示着阳刚之美的乐观豪迈气势直接进入了北魏的绘画、雕塑、诗歌等具体的艺术形式之中,“马”成为北朝代表精神特质的重要的艺术形象之一。
(四)悲壮苍茫的审美取向 北方的刚健勇武是主流的精神特征,然而战争中付出代价是不可避免的,杀伐之后的沉重和悲凉相伴而来。北方少数民族本来就生活在北中国高寒带区域,高远辽阔,雄伟的山脉陡峭绵延,最为艰难的是北方漫长的严寒冬季,生活资料严重短缺却无法补充。生活环境和方式,使得北方的气质掺入了悲凉的因子。在进入中原以前,北方游牧民族的丧葬活动也很简单,他们为战死的英雄唱着悲凉悠扬的挽歌,“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5]北方自然气象和文化精神的共同作用表现在文化审美取向上则是悲凉厚重。面对灾难和痛苦,常表现为克制和牺牲,透出一种北国大丈夫的气概,迥然相异于与同时期南朝面对灾难或离别时表现出来的痛哭流涕。除去文学作品中明确的表达以外,在书法、雕塑、绘画和建筑等领域均流露出这样的文化特质,比如魏碑体的凝重、雕刻佛像的雄壮慈悲等等,都显示出了北朝文化精神的这个基本取向——悲凉厚重。正是这个基本的草原文化精神,当南朝玄远的清谈以及文辞形式的华美袭来的时候,流淌在血液中的北朝草原文化特质始终无法放弃悲凉厚重的民族记忆,文风由此而远离浮靡。
草原的文化特质笼罩了北朝300多年,并且一直延续到隋唐。但在以往的文学研究过程中,几乎没有过多的涉及草原文化的因素。以少数民族为统治核心的北朝各代君主,不论怎样启用汉人建立具有儒家特色的社会政治体制,其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习惯都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文化习惯不仅影响着汉化后的少数民族士人,同样也影响着生活在北中国的中原士人,士人的审美风尚和生活习俗都会带上独特的地域特征。
人类的任何一种文化,作为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形态,都具有其特殊性,也有着缺陷性。历史上的任何文化的融合,不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都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破坏其民族的特殊性,另一面也打破其局限性。北朝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特性,在失去了它的生存空间后,其文化特质潜移默化地进入汉文化系统,使得汉文化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新貌。汉族士人文化和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士人文化在紧密接触中互相吸收融合,共同成为辉煌的隋唐文化的基石。
[1]康 乐.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从西郊到南郊[M].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
[2](北齐)魏 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王明珂.面对汉帝国的游牧部落[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南朝宋)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编辑 赵立人〕
The Pasture CulturalO rientation in the Cultural Spirit of Northern Dynasty
MENG Li-jing1,2
(1.School of Liberal Arts,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2.The Editorial Department,Journal of Shanxi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Pasture culture is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the culture of Northern Dynasty.First,the Xianbei people,a nomad tribe,needed Confucianism.Second,the culture of theminorities infiltrated every corner of the culture of the regime.Free,martial,and tough,were characters thathad great impacts on following dynasties.
pasture culture;aesthetic orientation;cultural spirit in Northern dynasty
K239.2
A
1674-0882(2011)02-0040-04
2011-03-05
蒙丽静(1971-),女,山西大同人,在读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