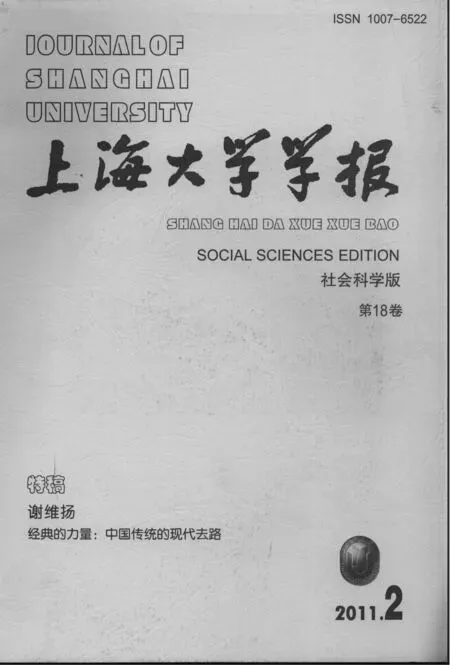清初在京贰臣文人社集唱酬活动探微
2011-04-12白一瑾
白一瑾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清初在京贰臣文人社集唱酬活动探微
白一瑾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自顺治元年至顺治三年,在京的仕清贰臣文人群体频繁举行唱和活动,并以“社集”标榜,已经有了文学社团的雏形。其唱和多为抒发对明朝故国的怀恋,抒写失节的痛苦和在异族治下为官的苦闷感,抒发南人仕北的思乡之情,纾解精神苦闷的寻欢作乐。贰臣士人们在此种同病相怜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模糊的群体意识。
清初;贰臣;社集
明清易代之际,以明朝旧臣身份再仕清朝、成为贰臣的士人,数量极为庞大,于清初政治文化各方面,影响力亦相当可观。但因道德上的争议,这一群体长期被边缘化,因而有很多内容值得重新发掘和思考。
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清初贰臣士人之间频繁的集会唱酬活动。特别是在甫经鼎革后的数年内,滞留在北京、已归降于清政权的部分贰臣,经常进行各种形式的聚会宴饮、诗词赠答。从龚鼎孳、曹溶、李雯等当时在京城的贰臣文士,在这段时间内的诗词作品即可以看出:宴饮唱酬之作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大多是与和自己遭际身份相似的贰臣友人的来往酬答;且以“社集”明确标榜,在某种程度上已具有文学社团的性质。
本文对从顺治元年(1644)五月,清政权接管京城,至顺治三年(1646)期间,京城部分贰臣士人的社集唱和活动,进行梳理和分析,希望揭示出清初贰臣这一特殊而有争议的士人群体,在身经鼎革兼丧失节操之后,所形成的这个群体独有的心态特征和群体意识。
一、清初在京贰臣文人的社集唱酬活动
清政权入京之后,宣布“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1]卷六“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1]卷六因而,大量滞留在京的明朝官吏,都改换门庭,再仕于清政权,成了“贰臣”。
就在这一年的初秋,在京的仕清士人中,兴起了以“秋日书怀”为主题的集体吟咏唱和。其中,龚鼎孳有《和雪堂先生遂初秋岳舒章秋日书怀诗十二首》,曹溶有《书怀同李舒章作三首》,熊文举有《甲申秋和同志杂诗》,李雯有《初秋感怀》、《和龚黄门写怀八首》。此次唱和的参与者,包括龚鼎孳、曹溶、李雯、熊文举、朱徽。其中,除李雯系以明诸生仕清外,其余几人都系两朝为官的贰臣。
顺治元年中秋,曹溶作《八月十五夜二首》。其后,龚鼎孳亦有和作《和秋岳八月十六夜诗》、《再叠前韵赠别秋岳》,李雯有《和龚芝麓十六夜作用原韵为赠》。
不过,上述“秋日书怀”与中秋唱和,只是一般友人间酬唱往来,尚不能算作真正的社集。真正具备社集形态的,是顺治二年三月十八日的韦公祠海棠之会。这次聚会规模相当大,且与会者明确以“社集”自称。主持者为袁于令,参与者有谢弘仪、龚鼎孳、李雯、朱徽、张学曾等,除袁于令、李雯二人外,其余参与者均系贰臣。李雯有《乙酉三月十八日袁京兆令昭招饮韦公祠同谢护军朱龚两都谏张舍人友公赋》。龚鼎孳亦有《社集韦公祠看海棠同诸子分韵》。
韦公祠之会的次日,李雯、朱徽、胡统虞复在龚鼎孳寓所聚会,李雯有《十九日集孝升斋和其原韵时同赋者朱遂初胡孝绪》。三月二十日,李雯、龚鼎孳、朱徽又在报国寺聚饮、观海棠,李雯有《二十日朱龚二黄门招饮报国寺观海棠即事》,这两次聚会,亦可算是韦公祠海棠之会的余波。
顺治二年四月八日,李雯、龚鼎孳、袁于令、谢弘仪、张学曾在天庆寺又有一次以“送春”为主题的聚会。龚鼎孳有《天庆寺送春和舒章箨庵尔唯诸子》,李雯则有《四月八日谢都护招饮天庆寺即事得元字》。李雯和龚鼎孳还分别有《风流子·送春》和《风流子·社集天庆寺送春用舒章韵》词作。
顺治二年的端午节之会。端午前一日即有社集,参与者中姓名可考的有龚鼎孳与朱徽。龚鼎孳有《南柯子·端午前一日社集和遂初韵》。次日,在龚鼎孳寓所聚会,并演《吴越春秋》,参与者有李雯、吴达、朱徽、孙襄。龚鼎孳有《五日李舒章中翰招同朱遂初孙惠可两给谏集小轩演吴越传奇得端字》,李雯有《端午日吴雪航水部招饮孝升斋看演吴越春秋赋得端字》。
顺治二年六、七月间,有送别因谏阻薙发及伪太子事而辞官的熊文举、朱徽南下之会。参与者有李雯、龚鼎孳、曹溶等。李雯有《送熊雪堂少宰请告南归》。龚鼎孳有《送雪堂夫子南归用古诗十九首韵》,曹溶有《送朱遂初都谏南还五首》、《送熊雪堂少宰四首》。
顺治二年中秋之会,中秋后一日在曹溶寓所举行,参与者有李雯、张学曾、钱士馨等。曹溶有《秋夜同照千稚农作》,李雯有《十六夜集秋岳斋即事同友苍上人张尔唯王照千钱稚农赋》。
顺治二年重阳之会。唱和者有李雯、袁于令和朱徽。此后,龚鼎孳亦参与赋诗。李雯有《九日和朱遂初黄门得重阳二韵》、《九日又和令昭》。龚鼎孳亦有《凫公舒章重九集饮有作遥和原韵》。
顺治二年冬,龚鼎孳、李雯、曹溶、袁于令在张学曾寓所聚会。龚鼎孳有《冬夜同秋岳舒章凫公集尔唯药房限韵》,曹溶有《冬夜社集张尔唯中翰药房分韵》。
顺治二年冬,王崇简自南方归来后,京城的贰臣为他举行聚会洗尘,参与者有李雯、李奭棠、张学曾等。李雯有《于尔唯贰公席上喜值敬哉南归同话而有赋》。
顺治二年冬,袁于令在寓所演《西楼记》传奇,所邀宾客有曹溶、龚鼎孳、陈名夏、金之俊、吴达、胡统虞、张学曾、李雯。其中除袁于令和李雯身份或有争议以外,均系贰臣。此次聚会,曹溶有《西楼曲赠令昭》及《令昭水部招同百史岂凡两少宰芝麓奉常孝绪太史雪航侍御尔唯舒章两中翰演自度西楼曲即席赋二首》。龚鼎孳亦有《袁水部招饮所著西楼记传奇同秋岳赋》。
顺治二年十一月三日,龚鼎孳为其妾顾媚寿而聚会招饮,曹溶有《芝麓以闺人初度招饮同社用前韵二首调之》。
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龚鼎孳生日前六日,还有一次社集,曹溶有《芝麓见招余以事不克赴二首》,不久又有《同社过集二首》。
顺治二年冬,以曹溶幼女初周,复有社集。曹溶有《幼女初周喜同社见过》。
顺治二年岁末,有送袁于令官清源之会,在龚鼎孳寓所举行,参与者还有曹溶、吴达。龚鼎孳有《袁凫公水部将之清源同秋岳雪航集小斋赋别》。
顺治二年岁末,又有送吴达南归之会,龚鼎孳、曹溶参与。龚鼎孳有《雪航席上同秋岳限韵》。
顺治三年元夕,龚鼎孳与曹溶饮于“无外户部”宅邸观剧。“无外”为谁,尚不可考;然此人在入关不久的清政权中任职于户部,系降清明臣的可能性相当大。龚鼎孳有《同秋岳观剧无外邸中重用赠雪航韵即席四首》、《同秋岳饮无外邸中》、《扫花游·元夕同秋岳作于无外邸中用周美成韵》。曹溶则有《无外户部席上观剧同芝麓限韵三首》。
顺治三年二月八日,曹溶、李雯、龚鼎孳还有一次送别聚饮,所送之客不详。曹溶有《仲春八日即席送客同舒章芝麓限韵二首》。
顺治三年二月十二日的花朝聚会。在曹溶斋中宴饮,参与者还有龚鼎孳、李雯、王崇简、赵进美、宋琬、张学曾。在这次聚会上,龚鼎孳有《花朝同敬哉韫退玉叔尔唯舒章岕庵社集秋岳斋限韵十体》,曹溶有《芝麓舒章尔唯敬哉玉叔韫退过集分赋》,李雯有《十体诗花朝社集秋岳斋限韵》。
其后不久,李雯以葬父而请假南行,龚鼎孳与曹溶聚会相送。龚鼎孳有《舒章请假南行同秋岳赋送四首》。
顺治三年三月的澹园唱和,参与者有龚鼎孳、金之俊、曹溶、吴达、刘余祐等。龚鼎孳有《春日同金岂凡少宰刘玉孺司马曹秋岳太仆吴雪航侍御讌集澹园即席限韵》。曹溶则有《澹园赏花同芝麓作二首》。
此后,顺治三年六月,龚鼎孳以父丧回乡守制,是年夏秋之交,李雯亦启程回乡。次年正月,曹溶以滥送贡监被革职回籍。在这三位文名最盛且最为活跃的贰臣文士离京后,鼎革后在京贰臣的群体性唱和,渐告一段落。
纵览鼎革后一段时间内在京贰臣的唱和,有两个特点:
其一,聚会唱和时已表现出群体意识,以“社集”自称。若韦公祠海棠之会中,龚鼎孳明确声称是“社集韦公祠看海棠”、“三月十八日与诸子社集其下”。天庆寺之会中,龚鼎孳亦云“社集天庆寺送春”。顺治二年冬张尔唯寓所的宴饮,曹溶亦称“冬夜社集张尔唯中翰药房”。而龚鼎孳为姬人顾媚寿,也明确标榜是“以闺人初度招饮同社”。可见在宴饮唱和的过程中,在京贰臣已经初步有了文学团体的雏形。这个文学小团体虽然并无固定的名称,但其成员比较固定,其间较活跃的主要成员有李雯、龚鼎孳、曹溶、朱徽、熊文举、袁于令、谢弘仪、张学曾、吴达等。其余若金之俊、陈名夏、胡统虞、宋琬、赵进美、王崇简、刘余祐等,亦偶尔参与。在重要的时令节日或某成员的特殊日期,往往会举行定期的聚会。
其二,除某些特殊情况(如以明诸生出仕的袁于令、李雯,在清朝通过科举入仕的宋琬)以外,这一文学团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都系由明仕清的贰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贰臣文社”。在甲申以后,仍滞留在清政权治下京城的士人,绝大多数是失节仕清者。他们既属同一群体,在精神上面临同样的困境,自然希望在与同类的社集唱和之中,寻求某种精神慰藉。
其三,次数极为频繁,且在社集时间选择方面煞费苦心。不仅在各种节令,若元夕、花朝、端午、中秋、重阳等,甚至还包括如三月十八日明亡“纪念日”这样的敏感日期,在京贰臣均有宴饮唱和赋诗的聚会。此种频繁的聚会宴饮,一方面说明这些贰臣心绪复杂、心情苦闷,对物候时事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情感倾诉;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在心理上,对于具有相似遭际的本群体成员,有极强的认同感乃至依赖性。
二、在京贰臣文人集会唱酬的主题与心态
在京贰臣的聚会唱和,主要有如下几个主题:
其一,抒发对于明朝故国的怀恋和身经故国沦亡、山河易代的痛苦。
清初贰臣士人群体之故国之思的抒发,具有群体性的倾向。贰臣士人们并不像时人所嘲讽的“切莫题起朱字”。[2]前集卷十他们并没有因为再仕新朝,而完全抹去对明朝故国的思忆眷恋,也并不忌讳将这种复杂而深厚的情感形诸笔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顺治二年三月十八日的韦公祠海棠之会。按照李雯《乙酉三月十八日袁京兆令昭招饮韦公祠同谢护军朱龚两都谏张舍人友公赋》所记,这次聚会的主持者为袁于令,参与者有龚鼎孳、李雯、朱徽、谢弘仪、张学曾。其中,龚鼎孳、朱徽、谢弘仪和张学曾均为贰臣,袁于令和李雯虽系以诸生仕清,却对仕清之事深感悔恨惭愧。因而此次聚会,堪称是一次纯粹的仕清明臣的聚会。
从时间上来看,此次社集正在三月十八日明朝灭亡一周年之际;所选择的韦公祠,又是晚明时代京城颇有名气的游览胜地。龚鼎孳在《满庭芳》“红玉笼云”词的序言中,对这次聚会的性质,有一相当明确的阐述:“韦公祠西府海棠,数本繁艳,甲于京师。春昔朝士宴赏,不减慈恩牡丹也。沧桑既变,而此花不改。三月十八日与诸子社集其下,感兴系之。”[3]卷二
可见,这是一次明确以追悼故国为目的的社集。而社集者所吟咏的内容,也以悼念亡明故国为基调。在李雯的长诗《乙酉三月十八日袁京兆令昭招饮韦公祠同谢护军朱龚两都谏张舍人友公赋》中,此种故国情怀的抒写,相当淋漓尽致:“呜呼韦公祠南古木多,海棠红雪堆高柯。暮春春寒作惆怅,阴风碧野吹坡陀。”虽然是海棠烂漫的春日美景,但在他眼中,却毫无半分美好欢愉的生机,而呈现出一派“春寒惆怅”、“阴风碧野”的凄冷哀愁景象。下文笔锋一转,开始直抒胸臆、长歌当哭地书写这些贰臣在故国沦亡一周年之际的怆痛悲慨心绪:“丧乱以来泪洗面,一朝一夕春风见。今年花开祗树林,去年矢及承明殿。触事难忘旧恨深,春草春花双紫燕。谁说开花不看来?看花正是伤心伴!家国兴亡若海田,新花还发故时妍。万年枝上流莺语,今日人间作杜鹃。”[4]卷一
“谁说开花不看来?看花正是伤心伴!”这些触景生情的“伤心人”,其伤心处不仅在于“家国兴亡若海田,新花还发故时妍”身经丧乱鼎革的故国情怀,也在于“万年枝上流莺语,今日人间作杜鹃”——昔日大明王朝“万年枝”上臣僚,已成新朝苟且偷生者——的惭愧苦痛。这些前明旧臣时时萦绕在心、难以抑制,却又是况味复杂、欲说还休的故国之思、身世之悲,在同病相怜的贰臣同人之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
四月八日天庆寺之会,聚会的原因和吟咏的情调亦与此相仿。以“送春”为主题,本身就代表了对于在甲申之春覆亡的明王朝的追悼。龚鼎孳《风流子·社集天庆寺送春用舒章韵》写道:“柔丝牵不住,眉尖小,一蹙又斜阳。问红雨洒愁,几番离别,绿萍漾恨,何代苍茫。子规说,麝迷青冢月,珠堕马嵬妆。”下片复云:“前欢真如梦,流莺懒风日,枉媚银塘。担阁背花心性,泪不成行。”[3]卷二暮春三月时,明朝灭亡;春已逝去的五月,清政权接管了京城。在贰臣们眼中,他们效忠过的朝廷如春光般倏然逝去,永难再回。“柔丝”牵绊,“流莺”献媚,都是枉然,春天还是毫不留情地一去不复返,只留下“红雨洒愁”、“绿萍漾恨”的一片狼藉,这“一春滋味”实在难以言说。
不仅是如三月十八日明亡“纪念日”这样的敏感日期举行的社集,即使是一般性的节令聚饮唱和,贰臣们的诗作也往往体现出追挽故国的情感倾向。
顺治二年五月端午,龚鼎孳在家中演《吴越春秋》传奇,招李雯、吴达、朱徽、孙襄等聚会。这次社集虽以“端午”为名,但其真正寓意,却远非一般的节令聚会所能概括。特别是所演以吴国覆亡为题材的《吴越春秋》之剧,显然是有所指:一方面是藉此挽怀明朝故国的灭亡;另一方面,是时南方奉明之正朔的南明小朝廷,亦处于即将覆灭的危境。且在座的五位贰臣成员,均系南籍,其隐秘的惆怅痛苦心境实在难以言说。龚鼎孳在《五日李舒章中翰招同朱遂初孙惠可两给谏集小轩演吴越传奇得端字》中写道:“歌舞场中齐堕泪,乱余忧乐太无端。”[5]卷十七李雯的《端午日吴雪航水部招饮孝升斋看演吴越春秋赋得端字》则对此阐释更详:“高会犹将令节看,素交风义岂盘餐。酒因吊屈人难醉,事涉亡吴泪已弹。生意尽随麋鹿后,乡心几度玉兰残。年来歌哭浑同调,颠倒从前非一端。”[4]卷三与会贰臣们无端“堕泪”的感慨,显然与“亡吴”的剧情,在他们心底激起的波澜有关。
其二,抒写贰臣自身失节的痛苦和在异族治下为官的苦闷。
除了亲身经历故国沦亡以外,贰臣士人还具有本群体独有的另一种遭际经历,那就是个人的降清再仕、丧失节操。他们原先的人生理想信念已经彻底崩塌,而且是被自己忍痛亲手毁灭。外部环境已是鼎革巨变、山河破碎,而自身又是大节已失、一钱不值。这种巨大的失落感、孤独感,使他们格外重视“同病相怜”之同类的存在,而失节后的惭愧悔恨苦闷等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低谷体验,也可以向这些具有同样痛苦经验和耻辱身份的友人放怀抒发。
在清军进入北京后的甲申当年夏秋之际,在京贰臣们已经开始有大规模的唱和活动。是时距离甲申国变方数月,贰臣士人们已是国破家亡,名节丧尽,几个月以来的经历恍如一场噩梦。因而其唱和的内容,在故国之思以外,已经开始有大量关于自身失节的愧悔情绪的抒发。龚鼎孳写道:“恨人怀抱本苍茫,愁对秋云万里长”,“百年出处高斋梦,满眼兴亡午夜心”,“南冠万死身何补,画角一声魂未收”,“铜驼蔓草秋仍碧,巾帼余生影自憎”;[5]卷十六曹溶有“三径蓬蒿惭故事,五更风雨失初心”,“百年失意真为夭,四海横流怅独存”;[6]卷二十九熊文举则有“沧桑浩劫真难问,萍梗□生更自猜。肠断孤臣羞汉节,苍梧龙驭几曾回”,“衣加东首愁无赖,乐操□音泪可憎。寂寞松烟龙蜕冷,攀髯何面拜诸陵”;[7]卷十九对故国的追忆,都是和失节的痛悔苦闷绞缠在一起的。
失节之痛以外,还有对自身处于异族治下,笑啼不敢、动辄得咎之凄惨尴尬处境的叹息。贰臣士人入清后仕途的波折坎坷,因身为失节汉臣而受到满清统治者不公正待遇的苦闷情绪,也只能在贰臣之间抒发。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顺治二年七月送别熊文举、朱徽的聚会。是时,在京的贰臣士人若龚鼎孳、李雯、曹溶等纷纷设宴赋诗相赠。以熊文举本人文集卷十八所收录的《南归舟次和龚芝麓都垣赠别》、《和曹秋岳侍御赠送还山诗四章》等,即可知对此略知一二。
熊朱二人之得祸去官,均与清初政治环境有关。“遂初曾疏论伪储,几蹈不测;予为薙发力诤冒险略同。”[7]卷十八顺治元年十一月,有自称崇祯太子者投嘉定侯周奎府,为清廷系狱;朱徽力辨太子为真,请“从容研质”,[8]卷九因而触清廷之忌。而清廷顺治二年六月下薙发令后,熊文举曾上《江南初下条奏事宜疏》谏阻,称“礼乐耕桑,不违其俗”,“行一政也,必其有便于民而后行”,[7]卷二十二亦为清廷所不容,两人不得不辞官回乡。
与其说与会的贰臣士人是单纯出于与熊文举的交谊而开展大规模的送别唱酬活动,还不如说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对熊朱二人因触异族统治者之忌而得祸,深有兔死狐悲之感。曹溶叹息“知人良独难,势去薰为蕕”,“得归万事足,多誉为祸枢。一身且莫保,遑惜梁栋徂”,[6]卷三龚鼎孳更以受宠而失宠的女子譬喻,“一朝蒙顾盻,光采惊邻妻。……命移颜色改,观者徒伤哀”。[5]卷一
顺治二年冬的张学曾寓所社集,也和贰臣们在清朝治下的仕途坎坷,有着密切关系。就在这一年八月,发生了御史吴达等人弹劾大学士冯铨贪贿的重大事件,冯铨与龚鼎孳甚至面诘于朝中,以“阉党余孽”与“流贼御史”[9]互詈。龚鼎孳、吴达等南籍贰臣,因此纷纷遭到处分:“处分已定,是非已昭,若淟涊苟偷,不即引退,则真寡廉鲜耻,无惑乎人言之诟讥矣”。[10]卷一
此次参与社集聚饮的龚鼎孳、李雯、曹溶、袁于令与张学曾,都是南方籍的仕清者。在这一朝廷对南籍贰臣的打击中,普遍处于人人自危和失望消沉的情绪里。所以这次聚会,实无多少欢娱可言。龚鼎孳写道:“天涯流落岁寒同,入夜清樽兴不空。无数遥烽迷去鸟,有情别泪到秋虫。灯前残菊如羁客,乱后绨袍饱朔风。莫倚荆高能意气,人今衰草暮笳中。”[5]卷十七通篇都是一派衰飒悲凉、低沉失望的气氛。曹溶则叹息:“黯黯尘途将岁暮,谁知管葛在人中。”[6]卷三十情绪亦与此相仿。
其三,是抒发南人仕北、远离故土的思乡之情。考察这个贰臣文学团体成员的籍贯就可以发现,南人占了绝对优势,地域文学的心态特征相当明显。李雯、龚鼎孳、曹溶、朱徽、熊文举、袁于令、谢弘仪、张学曾、吴达、金之俊、陈名夏等,都系南人。鲜明的地域因素,正是贰臣身份之外,这个文学社团形成和维系的另一重要基础。李雯《乙酉三月十八日袁京兆令昭招饮韦公祠同谢护军朱龚两都谏张舍人友公赋》:“江左才人二三子,折花微解朱颜酡。”[4]卷一曹溶《陈彦升招饮》:“北土寓公欢畅少,西京词客别离多。”[6]卷三十他们正如袁于令所自嘲的,不仅是“生于明而仕于清”,而且是“生于吴而仕于燕”,[4]卷五在失节的痛苦之外,也必然感受到远离故土的苦闷。而这种苦闷,也只有向具有相同处境的南籍贰臣友人述说。
李雯在作于顺治二年重阳节的《九日和朱遂初黄门得重阳二韵》写道:“江山烽火隔重重,故国荒台白露封。九月乡心纷木叶,两朝清泪落芙蓉。榆关猎猎渔阳鼓,燕市萧萧长乐钟。同是飘零吴楚客,强将黄菊慰秋容。”[4]卷三以中国传统,重阳节是怀乡和思亲的节日,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是也。而对于当下的李雯等“贰臣”来说,江山已经易主,自己身为南人,不仅是远离家乡为官,且身跨“两朝”,处境尴尬,此种怀乡思亲的情感也就倍加浓烈和苦涩。龚鼎孳亦有《凫公舒章重九集饮有作遥和原韵》:“四海交游纷落叶,百年生事一悲歌。紫萸黄菊愁无赖,潦倒深杯奈尔何。”[5]卷十七其心态之苦闷,思乡情绪之深沉,亦与李雯在精神上相通。
其四,是以纾解精神苦闷为目的的寻欢作乐。许多贰臣聚会并非文人清谈式的诗文唱酬,而是纵情歌酒美人、演剧欢宴,颇具寻欢作乐的色彩。若顺治二年冬,袁于令在自家演《西楼记》传奇,邀宾客观剧。袁于令是明末著名戏曲家,所作《西楼记》亦为一时名剧,故与会者颇多。是时盛况,曹溶《令昭水部招同百史岂凡两少宰芝麓奉常孝绪太史雪航侍御尔唯舒章两中翰演自度西楼曲即席赋二首》描绘颇详:“胜日联床佞酒筹,依然丝管坐西州。宫园法部人人艳,纨素新声夜夜愁。走马呼鹰余乐事,攀嵇慕蔺总风流。长安此后传佳话,轻薄名居最上头。”[5]卷三十可见此类聚会,无论是主办者还是参与者,都颇有些裘马清狂、任情纵欲的味道。
在国破家亡之后,还来举行这种清平盛世时的观剧宴饮活动,或予人全无心肝之感;然而它却是贰臣士人互通声气、纾解精神压力的重要方式。上述《西楼记》聚会中,观剧者之一的龚鼎孳《袁水部招饮所著西楼记传奇同秋岳赋》即清醒而辛酸地写道:“可怜蓟北红牙拍,犹唱江南金缕衣!”[5]卷十七所演出的是“江南金缕衣”式的晚明江南名士的脂粉风流,但身处的却是国破家亡、异族治下的“蓟北”。其尴尬凄苦之感,可以想见。这些贰臣们并不能藉歌酒美人、放情纵欲的欢愉笑闹,来稀释心中的深沉隐痛。
对于这一时期内在京贰臣士人们的社集聚会,以及社集吟咏中表现出的对亡明故国的怀恋,清政权的态度相当宽容。这是这一“贰臣诗社”能在数年内存在的外部原因。若特意在明亡“纪念日”举行的韦公祠社集,在文字狱盛行的康乾时代,是足以贾祸的。然贰臣们举行此类集会唱酬时,竟对此毫无忌讳;而其后也无人因此得祸。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清初在京贰臣社集唱和的时间,主要在顺治元年至顺治三年间。此时清政权入关未久,且国家尚未统一,统治者的关注集中在与南明及各地反清武装的军事征战上,而对文化思想方面的控制,尚提不上议事日程。故顺治一朝,文字狱并不怎么酷烈。而当时文学创作,正如宋征舆《书钱牧斋列朝诗选后》所言:“时鼎革未久,文字中或关涉时事,多触忌讳,诗歌中尤甚。”[11]卷十五可见顺治时代文化环境尚属宽松。
清初贰臣士人社集能够公开表达故国之思的另一个原因,是清政权入关时在道义方面进行“包装”,以明朝“盟友”形象出现,大力宣传“为明复仇”的论调。清人甫入京,即令臣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其后又礼葬崇祯帝后,将明太祖祀入历代帝王庙。顺治帝本人甚至认为:“明臣而不思明者,即非忠臣。”[12]953当时清统治者自身对于明朝的礼尊态度,亦为贰臣公开表示怀悼明朝的情感,提供了某种“合法性”依据。
三、在京贰臣集会唱酬活动中的群体意识
在京贰臣社集唱酬活动的另一重要意义是,在与处境相类的友人同气相求的交往与慰藉中,贰臣士人们开始形成模糊的群体意识。
“贰臣”虽系政治概念,但贰臣作为一个特定的士人群体,必然具有自身独特而无可替代的精神特质和群体意识。在此可以明末清初的另一有代表性的士人群体——遗民作为对照系加以说明:
由于贰臣这一特殊自我身份所具有的道德上的谴责意味,尽管他们面对着相同的生存环境,也必然形成相似的群体观念,但他们却不可能如遗民般毫无顾忌地公开标榜自我身份。身为明遗民,方文自称“匹夫有至性,可以贯真宰。况乃忠孝人,九死犹未悔”,[13]59黄宗羲称遗民为“天地之元气”,[2]后集卷二魏禧则以遗民为大厦将倾时以己身为砥柱的“刚确不挠之夫”,[14]都对自己的身份充满了自豪感。而贰臣的身份,却不但不是可以引以为傲的存在,反而如罪犯的烙印般是耻辱的象征。所以,他们的群体意识只能是以一种不易察觉的、隐藏的、卑微的方式呈现出来。有意识地与自身遭际地位相当的失节士人,在同病相怜、彼此理解的情况下宴饮酬唱、互陈衷肠,互相给予和获取可怜的心灵安慰,正是这种潜在的群体意识的表现方式之一。
李雯在《和曹秋岳侍御闲居诗》中写道:“自昔罹孔艰,良友知我心。蕨薇在何许?悠悠高山岑。失路惭訾食,沉忧托令音。”[4]卷一他在仕清以后,一直难以摆脱愧悔自责的心态,心绪长期抑郁苦闷。自己“失路”未能成为采薇全节之人,这一辛酸惨痛却又是不大体面的心灵痛苦,只能向曹溶这类同属失节者的“良友”来言说。而这段时间内,正是和他处境相当的贰臣友人们的往来,给了他相当大的精神慰藉。李雯在《中元日从先君瘗所还过秋岳曹侍御夜坐》中写道:“故人慰我频频酌,玉盏愁心敢细论”。[4]卷三他在和这些贰臣友人的频繁酬唱中,尽情地抒发着内心的苦痛和压抑。
而从李雯的几位贰臣友人来看,龚鼎孳《有触》:“但许称同病,悲怜意不生”,注云“为舒章也”。[5]卷五“同病”正是两人彼此心灵相通和理解的基点。王崇简《舒章至》则言“经岁犹然识泪痕,幽怀相向各声吞,惟予悲感心多愧,无复欢娱事可言”,[15]卷四李雯和他本人之悲抑心境可见。而陈名夏《李舒章中翰以亲丧未归有人言赋此慰之》痛惜李雯“君生不得志,父死敢言归?”“独慕云间鹤,偏留患难余”,[16]卷一亦颇有作为失节者的同病相怜之感。
贰臣士人这种交往对象的选择方式和范围,使得贰臣士人作为一个真正具有紧密精神联系,而非仅仅以政治立场生硬划分的群体,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逐渐形成。在此可对顺治三年春的花朝聚会作一剖析:
顺治三年二月十二日,曹溶在自己在京的寓所中举行以“花朝”迎春为主题的社集聚会。这次社集活动规模相当大,参与者包括龚鼎孳、李雯、赵进美、宋琬、张学曾,以及刚从南方回归不久的王崇简。曹溶有《芝麓舒章尔唯敬哉玉树韫退过集分赋》、龚鼎孳有《花朝同敬哉韫退玉叔尔唯舒章岕庵社集秋岳斋限韵十体》,李雯有《十体诗花朝社集秋岳垒限韵》,王崇简则有《春日曹秋岳社集龚孝升李舒章宋玉叔赵韫退别体限韵》,其诗体则包括四言诗、古诗、律诗、绝句、排律等。可以看到,这次聚会除了李雯和宋琬在明朝只是诸生,其贰臣身份尚有争议以外,其余几人都是以明臣身份仕清的贰臣。这足以说明这一聚会的实质,是度尽劫波的贰臣们在易代以后,自觉地以身份为纽带互相联系,并在群体中隐秘地寻求自我心灵安慰的过程。
龚鼎孳《花朝同敬哉韫退玉叔岕庵尔唯舒章社集秋岳斋限韵十体》对贰臣特有的此种群体意识,表达相当深入:在经历了“陵谷苍茫后,徒伤结客名”的沧桑巨变以后,他们的心绪大多被身负污名、遭人鄙视的孤独失落感笼罩,“身在千秋失,心孤百感生”。在这种处境下,“江左空三阁,天涯滞一檠。管宁今割席,伍举旧班荆”,旧日的朋好,多也因其失节而断绝往来,他们只有在处境相同的本群体内部寻求一点可怜的心灵慰藉:“握手当风叹,愁眉变徵声”。[5]卷三十三
花朝聚会的首要主题,是时节变化,对于春光的感慨叹惋。前文所述,“春”这一节令对于亲身经历了甲申国变的贰臣们来说,是一个相当意味深长的母题。甲申年的春光消逝,是和国破家亡的惨痛一起刻印到贰臣们心中的。两年后的顺治三年,春光重至,京城宫阙风景未改,而明朝故国却已是一去不复返,自己也已经是新王朝之臣属,此种今昔变化令人倍添感慨。以曹溶《芝麓舒章尔唯敬哉玉树韫退过集分赋》为例,若“燕麦凄然地,何令客子繁”等,都颇具此类亡国感慨的意味;而“萍梗怜同病,风尘讳独清”,“太息因才累,都输处士名”,[6]卷十五其处于异族统治下,同病相怜的心境可见。
花朝聚会的第二个主题,是庆贺王崇简北来得官,正式融入京城的贰臣群体之内。顺治二年,流寓江南的王崇简自淮上北还。顺治三年二月,授庶吉士。以王崇简本人在聚会上“脱巾笑此双蓬鬓,短袖新裁旧锦袍”[15]卷五的句子来看,他对于自己的授官是较为志得意满的。他的另一首同题五律云:“世变文章在,交真意气尊。莫悲寥落甚,吾辈幸相存。”[15]卷五对这些贰臣同好的友情极为珍视。
花朝聚会的第三个主题,是李雯以葬父而即将南归。李雯《十体诗花朝社集秋岳斋限韵》注云:“时将南归。”[4]卷四龚鼎孳、曹溶、王崇简等人都与李雯交好,对其仕清后的抑郁心境比较了解且深为同情。对于与会者们来说,此次聚会既是送别,又是为李雯排解精神痛苦,更是他们对自身相似处境和心灵压抑的宣泄。龚鼎孳写道:“庾徐失路因辞藻,苏李同时恨简编。世事衔杯都欲尽,莫将名姓借人传”,[5]卷三十四而李雯本人则叹息道:“念我失路士,踯躅微尘中。肌骨既销铄,毛羽无丰茸。促促若槛羊,啾啾非候虫”。[4]卷四其中所抒发的那种“失路士”、“槛羊”、“候虫”的凄促之状,正是与会的贰臣们所共有的感受。他在同题另一七古中写道:“天下才人不易得,穷途尚欲存风格。犹是凌云卖赋人,俄成离黍悲歌客。雁影春寒紫凤城,牛鸣日落铜驼陌。三年故国已荒陵,二月清明正寒食。薄宦何须苦死留,曳车终日畏王侯。人生失意当尽意,数子论文日不休。”[4]卷四
由甲申国变到这次花朝聚会,已过三年,在经历了故国荒陵的惨变之后,由“凌云卖赋人”而成为“离黍悲歌客”的贰臣们,通过“数子论文日不休”的本群体士人频繁的社集聚会,排遣着“人生失意”的痛苦。在“论文”社集的过程中,贰臣士人作为社会群体所特有的群体意识,也在滋长。
综上所述,甲申国变后的数年内,由明仕清之“贰臣”文士,在京举行的集会唱酬,是鼎革后颇具特色的一种文学活动。参与者不仅明确以文学社团自居,且在社团成员身份和创作心理等各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趋同性。其主要成员大多是南方籍,且大多系明清两代为官之“贰臣”;其唱酬作品,也很能体现出这个特殊士人群体在亡国失节以后的普遍性心态,包括:对于明朝故国的怀念,甫经鼎革巨变的痛苦怅惘;对于自身失节再仕的愧悔,和在清为官的苦闷隔阂;身处异地、远离故土的怀乡思亲之情;以及为纾解精神痛苦,而有意识地寻欢作乐。这些贰臣士人,在与本群体成员“同病相怜”的交往中,各诉衷肠,获取心理安慰,还逐渐形成了本群体所特有的隐秘的群体意识。
[1]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黄宗羲.南雷文定[M].清康熙二十七年靳治荆刻本.
[3]龚鼎孳.定山堂诗余[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李雯.蓼斋后集[M].清顺治十四年石维昆刻本.
[5]龚鼎孳.定山堂诗集[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曹溶.静惕堂诗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
[7]熊文举.雪堂先生文集[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8]甲申传信录[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9]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龚鼎孳.龚端毅公奏疏[M].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11]宋征舆.林屋文稿[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
[12]邹式金.牧斋有学集序,钱牧斋全集第八册附录[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3]方文.嵞山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4]魏禧.魏叔子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5]王崇简.青箱堂诗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
[16]陈名夏.石云居诗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
(责任编辑:梁临川)
A Probe into Beijing's Poetic Responsory Activity of Turncoat Official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AI Yi-j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During the time from the first year of Shunzhi to the third year,many turncoat poets in Beijing working as the officials in the Qing court frequently had a reunion,chanting responsory poems,which,having had the rudiment of a literary association,was called as the"society".The responsory content was mainly displayed asfollows:(1)expressing the nostalgia for the Ming Dynasty;(2)uttering the sufferings of compromising honor and the depression of holding an official post under the rule of foreigners;(3)conveying the homesick feeling of southerners working in the northern area;(4)presenting the merrymaking of relieving spiritual depression.It is during the process of freemasonry communications that these turncoat poets grew up a faint group ideolog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turncoat official;"society"
I209
A
1007-6522(2011)02-0077-10
10.3969/j.issn 1007-6522.2011.02.007
2010-10-22
白一瑾(1980-),女,四川都江堰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明清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