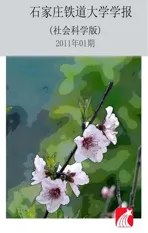试论西方语境中“反本质主义”文学认识的两个向度
——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
2011-04-12闫听,李森
闫 听, 李 森
(1.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2.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试论西方语境中“反本质主义”文学认识的两个向度
——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
闫 听1, 李 森2
(1.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2.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西方语境中,“反本质主义”思想在两个向度上影响着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一是以尼采、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对抗形而上学哲学的思路;一是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家族相似”的概念考察思路。反思二者,更加明晰文学本质作为一个价值问题的存在,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文化研究,在如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作出民主多元的文学理论建设才是关键所在。
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德里达;维特根斯坦
选择如题目所述的这两个向度来梳理西方语境中“反本质主义”之于文学理论的历史,是破费踌躇的。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可简言之为: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许多教材与专著对于从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的描述都可归纳为这样两个“转向”,即认识论方面与语言论方面。前者主要指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形而上学一元本质论的质疑;后者主要从语法规则角度对哲学思维本身进行改造。这两者反映到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上就形成了本文所述的下面两个传统。同时,不可否认这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都把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放在一起来研究。[1]也有论者撰文把维特根斯坦看做一个保守的解构主义者。[2]不过,统摄在文学理论的范围内来讨论问题,这两者还是在不同层次上给予了我们异于传统哲学化文学认识的诸多启示。
一、从尼采、海德格尔到德里达:颠覆形而上学的“摹仿论”文学本质
海德格尔曾说过:“恶劣而糟糕的危险乃是哲学化”。[3]他的意思显然是指向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诗入哲学的“本质思维”意味着文学认识被哲学规训的开始。[4]我想用海德格尔的“哲学化”指称对于文学的“本质主义”思维,包括“文学是什么”这样的提问在内均是“哲学化”思维之下的产物。那么对于这一“哲学化”文学认识的对抗、颠覆和瓦解的历史就可称之为“去哲学化”的历史,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说,“去哲学化”的历史就是一个“反本质主义”的历史。同时,这一历史又是分沿着多个路径,在不同理论家那里获得了不同的展开方式的。在这一历史的开端,尼采无疑是有代表性的第一人。
这里需要联系一下“文学”这个概念的演变历史,根据彼得·威德森在《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Literature)中的分析来看,奠定我们现代文学观念的关键是审美化的“大写的文学”的出现。而具有审美价值的“大写的文学”正是在这样两个大背景下发生的,韦勒克称之为:“这个词(指“文学”——笔者注)在1760年代之前已经经历了一个双重过程,一个是‘民族化’的过程……另一个是‘审美化’的过程。”[5]前者指的是文艺复兴以来建立民族国家,推崇民族文学的努力。后者指的是西方基督教等信仰衰微之后对于价值基础重建的努力。文学的情感性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代替了宗教的作用。而尼采,无疑是对于后者敏锐的预言家。尼采宣称的“上帝死了”正是对这种基督教信仰衰落的典型表述。尽管尼采的著述中没有直接论及文学本质的问题,但是其思想中拒斥形而上学、彰显生命维度的认识无疑对于我们从反本质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文学提供了帮助。[6]尼采曾言:“哲学家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世界的人格化。他力图通过自我意识理解世界。他力图达到同化,拟人化地解释事物总是使他感到快乐。占星学家认为世界服务于个人,哲学家则把世界看作一个人。”[7]
尼采的反形而上学思想对后世哲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后世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理解开出了一条新路,可以说,海德格尔、德里达等重要思想家无不是尼采思想的继承者和开拓者。而由德里达连接起来的——包括尼采与海德格尔在内——他们三者的关系则更加值得玩味。斯皮瓦克就此曾说:“海德格尔介于尼采和德里达之间,几乎在每一个场合,德里达都要写到尼采,而这时,海德格尔式的阅读总要被引发出来。似乎德里达通过研读和反对海德格尔而发现了他的尼采。”[8]
从对于形而上学的反思之中,后世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重要哲学家都渐渐地把所谓“哲学”作为人们思考进入世界的一个视角而非是唯一的绝对的视野。这种转向就内在地包含着“反本质主义”的思想因素。对于这一个继承性的传统,德里达有很好的说明:“我曾经,现在依然如此受到海德格尔式的那种肯定的吸引,它认为哲学本质上不是一般的思想,哲学与一种有限的思想相联,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联:它首先是一种古希腊的发明,其次经历了拉丁语与德语‘翻译’的转化等等,它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在西欧文化之外存在着同样具有尊严的各种思想与知识,但将它们叫做哲学是不合理的。”[9]9-10
因此进一步,德里达说:“哲学并非全部思想,非哲学的思想,超出了哲学的思想是可能存在的。”[9]12
这提示人们一种从“去哲学化”的角度来看待文学的可能性。而德里达本人的“解构”策略,正可以看做是对于“哲学化”文学认识的超出。
上文论述了诗入哲学即本质入诗的过程,其中核心就是认为文学的本质是摹仿。德里达首先针对摹仿论发难,论述这一点必须联系到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念,因为后者左右着关于摹仿论的形成。
在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中,“诗入哲学”的文学认识直接受制于亚里士多德奠定的真理观念,即符合论真理观。“亚里士多德这位逻辑之父既把判断认作真理的缘始处所,又率先把真理定义为‘符合’”。[10]上述“摹仿论”文学观正是符合论真理观的典型表现。作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真理论,其遭到了后世理论家的诸多批判。关于符合论真理观的内涵和表现均很复杂,海德格尔说传统的真理观念可以表述为:“真理是知与物的符合”。[11]208联系哲学史来看,这种“符合论”可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柏拉图的二分世界,承认存在着摹本与原型。二是认为基于这一种原型或客体(精神的或物质的),只能有一种陈述和认识与之相一致。海德格尔说这是一种假象:“仿佛这一对真理之本质的规定是无赖于对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的阐释的——这种阐释总是包含着作为intellectus[知识]的承担者和实行者的人的本质的阐释”。[11]210由这种符合论真理观所建立起来的文学认识同样奠基于二分结构之上,并且认为对于诗(文学)的阐释只有一种与原型的相符合,那就是文学的本质、真理。所以,符合论真理观就是一元论的真理观。
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里也对符合论真理观进行了解释:“这种真理观认为有一种知识因其与对象的本质完全符合因而是不可置疑的真理。”[12]这个简明扼要的解释同样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寻找一种与对象符合的知识,二是把这个与对象符合的知识当做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因此,生产这样的本质性的知识就成了传统哲学或说形而上学的基本思路。符合论真理观显然是“本质主义”在哲学思维中的典型表现,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从古希腊皮罗等人的怀疑学派就已经开始,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利奥塔、德里达和罗蒂等等后世哲学家均在自己不同的侧重点上质疑、批判这种哲学。实际上,这种把“存在”当做“存在者”来思的符合论真理观,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化”的过程。
而另一种,则是海德格尔反对前者而开创的“无蔽”的存在式的真理观。这一点在此不必多说,关于海德格尔的这种真理观的阐释(如《艺术作品的本源》等著作)国内多如牛毛。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认为以上两点均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即使海氏拒斥柏拉图开创的形而上学但是其“无蔽”的真理观仍是“形而上学的隐秘返乡”。在根本上二者均是建立在二分结构即摹本与原型之上的一种摹仿观。对于思考文学问题,德里达认为两者都是误断。在《文学行动》中,德里达通过对马拉美的《摹仿》、阿尔托的残酷戏剧和卡夫卡的小说的分析,证明“文学”是不摹仿什么的摹仿,只有文学和戏剧所表达和意指的东西脱离了逻各斯式真理化的暴政,“文学”这个概念本身才在历史中清晰起来。因为文学这个能指并没有终极的所指,更不存在一个终极的原型,有的只是差异性结构。在对于马拉美的分析中,德里达说:“马拉美就这样保留了摹仿(mimesis)的差异结构,但却摒弃了柏拉图式或形而上学的解释。……那个摹仿者最后没有了被摹仿者,那个能指最后没有了所指,那个符号最后没有了对象,它们的运作不再包含在真理的进程之内,相反,它却包含了真理。”[13]96-97
德里达反复用马拉美的话提醒人们:“读者,摆在你眼前的是,一件书写的作品……”[13]329以示必须脱离开文本之外的终极所指来看待文本本身。
在对卡夫卡的小说《在法的前面》的分析中,德里达针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道:规定着“文学是什么”的法原则是什么呢?也即“是谁决定、谁判决,又是按照什么标准,说这篇叙述属于文学呢?”[13]124德里达给出了四点理由:“第一条公认的意见是,我们都承认我刚刚读到的文本有它自身的同一性、独特性与统一性。……这种公认的第二条实际上与第一条是分不开的,即这篇文本有一位作者。……第三条公理或前提是,在这篇以‘在法的前面’为标题的文本中,事件是被叙述出来的,而这种叙述属于我们所说的文学。……在这里,我加了引号的‘在法的前面’这一短语是一篇故事的标题。这是我们要补充的第四条前提。”[13]122,123,125,126
这四点理由均是出自《在法的前面》这一文本,但是这些确认它为“文学”的理由均不在我们上述所说的哲学化的认识范围之内。因为在根本上,这四点均没有以文本之外的终极原型来界定文学。文学这个能指本来就没有本然、固定的所指。德里达说:“什么是文学?(what is literature?)”这一问句的内在矛盾就在于后者否定前者,即“文学”否定了“什么是”[13]因此,德里达认为文学应该这样来理解:
“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要讲述一切,无疑就要借助于说明把所有的人物相互聚集在一起、借助于形式化加以总括。然而要讲述一切同时也就是要逃脱禁令,在法能够制定法律的一切领域解脱自己。文学的法原则上倾向于无视法或取消法,因此它允许人们在‘讲述一切’的经验中去思考法的本质。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13]3-4
这就是德里达借用卡夫卡的小说来喻解文学本质的根本目的。文学既没有一个实体也不是天然存在的。规定着文学是什么的法原则是一套历史性的建制,这套建制的虚构性决定了其内涵是空空如也的。因为“没有内在的标准能够担保一个文本实质上的文学性。……如果你进而去分析一部文学作品的全部要素,你将永远不会见到文学本身,只有一些它分享或借用的特点,是你在别处、在其他的文本中也能找到的,不管是语言问题也好,意义或对象(‘主观’或‘客观’的)也好。甚至允许一个社会群体就一种现象的文学地位问题达成一致的惯例,也仍然是靠不住的、不稳定的,动辄就要加以修订。”[13]39德里达的这些言述无疑成为了“反本质主义”理论视角下的文学观的代表,对于哲学化文学理论的超出使德里达深刻地注意到了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性规约的存在。讨论文学问题决不能脱离开现代民主制度和社会文化语境,这一点也已成为文化研究所倡导的历史化、地方化知识建构的内核。德里达代表了承接尼采所开创的反思、颠覆形而上学一元论、理性中心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路径的文学认识思路。与这一思路相应的是以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家对于语言问题的批判研究,其中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对于“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观与“家族相似”性的本质理解
这里所谓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观,主要指以《哲学研究》为代表的对于日常语言的批判研究。其中对于“反本质主义”文学认识有关键影响的是其“家族相似”说,这里无意全面评析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只重在阐明维氏观点是如何影响“反本质主义”文学认识的。①
维特根斯坦在分析“游戏”这一概念时说: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我们称作‘游戏’的活动。我指的是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球类游戏,角力游戏,等等。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不要说:“它们一定要有某种共同之处,否则它们不会都叫做‘游戏’”——而要看看所有这些究竟有没有共同之处——因为你睁着眼睛看,看不到所有这些活动有什么共同之处,但你会看到相似之处、亲缘关系,看到一整系列这样的东西。[14]
进一步,维特根斯坦在下一节说: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说法来表达这些相似性的特征;因为家族成员的各式各样的相似性就是这样盘根错节的:身材、面相、眼睛的颜色、步态、脾性,等等,等等。——我要说:各种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
“家族相似”说的基本内容就如上所示,当然,因为维氏的哲学写作方式比较特殊——格言,警句式的——他往往是从具体的例子入手引人思考,前前后后所举的很多例子就不在此一一呈现了。但基本思路就是:想用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来对以往哲学认识中那个所谓的同一性的、整体划一的实体化“本质”提出质疑,比如他在开篇所述的奥古斯丁的图像化语言本质论(§1—§64)。从中我们看到:维氏不承认世上事事之间都有着所谓独特的、足以区别于其他的“本质”,至少,维氏认为很多概念、范畴是说不出来其独特于其他的“本质”的。如果是一物或许可以,比如苹果和梨之间的不同,我们尽管一目了然但是却难以说出其中的本质区别,尽管它们确有不同之处。如果非要明确其中根本——也好办——我们至少可以诉诸科学的实验分析,构成苹果和梨的元素总有不一样的,这可以确证其不同本质的存在。但是如果是正义呢?是理性呢?对于这些抽象的概念就很难说明其中区别于其他的所谓“本质”了。可以说以往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基本都是在处理这些类似于正义、理性等等的超级概念的。但是维氏却明确说:我们有一种幻觉,好像我们的探索中特殊的、深刻的、对我们而言具有本质性的东西,在于抓住语言的无可与之相比的本质。那也就是句子、语词、推理、真理、经验等等概念之间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可以说——超级概念之间的超级秩序。其实,只要“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用处,它们的用处一定像“桌子”、“灯”、“门”这些词一样卑微。
这段话非常明确地否认所谓“超级概念”。如果这些如“语言”、“经验”和“世界”的超级概念有它们各自所能被理解和指涉的内容,那么它们就一定和普通概念一样。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语词——“知”、“在”、“对象”、“我”、“句子”、“名称”——并试图抓住事情的本质时,我们必须不断问自己:这个语词在语言里——语言是语词的家——实际上是这么用的吗?我们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
维氏这种哲学观对于以往的形而上学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颠覆。对于“文学”的形而上学化(“哲学化”)的解释就是把“文学”作为上述如“语言”、“经验”和“世界”等这样的超级概念来思考的。那么在维氏看来,之所以对于这些概念的思考出了问题,是由于这种“哲学”思维本身的问题所导致的。因为语言中的词语和概念,它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这些超级概念正是形而上学用法所造成的假象。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考察维氏对于形而上学的颠覆性认识,这一点集中体现了维氏的哲学观:“哲学研究:概念考察(研究)。关于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它没有弄清楚事实(事质)研究和概念考察之间的区别。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总是表现为一个事实问题,尽管它其实是一个概念问题。”[15]
这段话微言大义,维氏认为哲学应该做的就是概念考察研究而非对于事实(事质)的科学化的分析。这个意思就是哲学研究不是对于某个事质的研究,关于某实存之物的研究那是科学要做的事情。比如上述所举出的克里普克对于水的本质的分析,通过科学实验就是H2O这个结构。但是对于诸如“正义”、“真理”等等概念你是无法用科学来分析研究的,这就是哲学要做的事情。所以维氏说:我们的考察不可能是科学考察,这是对的。……这些问题当然不是经验问题;解决它们的办法在于洞察我们语言是怎样工作的,而这种认识又是针对某种误解的冲动进行的。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靠增添新经验而是靠集合整理我们早已知道的东西。哲学是针对借助我们的语言来蛊惑我们的智性所做的斗争。
也因此可以这样说,科学增加人们的新知识,比如知道了水的本质就是H2O。而哲学是通过概念考察的方式对人们早已熟知的意义和道理等问题进行澄清,在维氏看来就像是医生治病一样:“哲学家处理一个问题;就像诊治一种疾病。”②并且这种澄清和考察不是找到以往形而上学所预设的那个现象背后的本质来获得的,而是“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式”。所以如果你错把本是概念问题的研究当做事质问题来研究,那就会造成一个形而上学的假象,这正是形而上学本质论的致命之处。比如当人们追问“文学是什么”的时候,会错误地以为“文学”是客观存在的一物,人们要做的就是找出其背后独特性的、甚至是永恒的“本质”所在,但这样必将是失败的。“文学”应该是语言和概念问题而非事实(事质)问题。形而上学化的文学认识把概念研究和事实(事质)研究混同了,正是这个假象虚构出了规定文学的独特性的甚至永恒的“本质”。而事实上,文学不过是具有一些“相似性”③特征所组成的类的集合,像“游戏”这个词一样。依维氏之见,我们真正要关心的问题应该是“文学是什么”这一表达方式本身。要使“文学是什么”这一问句不成为一个形而上学假象所制造出的“伪问题”,必须首先杜绝科学化的事实研究的干扰。其次,在文学一词所使用的具体语境中辨析其用法,这正彰显了历史化、地方化与语境化的概念考察方式。维氏的“反本质主义”思想之于文学认识的核心启示应在于此。当然,维氏哲学并没有直接针对文学来说,但是其颠覆形而上学本质论的思想直接影响到了对于文学认识的变更。还应多强调一句的是,维氏认为哲学研究就是概念考察,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说的哲学问题根本上就是语言学问题。20世纪理论界的语言学转向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由此就认为哲学问题就是语言学问题是武断的。同理,文学理论的问题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问题,否则对于文学理论的建构只需要编著一部更详尽的字典便可做到啦!简言之,维氏的反本质思想提示我们:把概念考察和事实(事质)研究相混同,这既是以往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本身的迷雾所在,又是“哲学化”文学认识的盲见。
综上所述,维氏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本质论,改变哲学的目的和任务,把哲学与科学、物理学与语言学等区分开来。这同时也是在颠覆和改造“哲学化”的文学认识,为文学理论的反思和建构提供了新的视野。“文学”这一概念在维氏那里应像“游戏”一样,归入“家族相似”的认识中。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正是这个家族的内部成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的本质是某种关系之维中的“相似性”,而非固定化的某个区别于其他的独特的“本质”。但是更近一步来说,文学的这个“相似性”又如何考察、确证呢?这个就不是维氏哲学要论述的问题了,毕竟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根本兴趣并不在文学研究方面。但是由维氏的哲学观还是能获得一些解答的启示或线索:一是维氏在解释“家族相似”时说的“不要想,而要看”,这颇似现象学所推崇的“回到实事本身”。因为维氏有言:“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在那里,不解释也不推论。——既然一切都公开摆在那里,也就没什么要解释的。而我们对隐藏起来的东西不感兴趣。”
二是,维氏对于“生活方式”的论述,这一点又类似于德里达论述卡夫卡小说时所问的:规定文学的法原则是什么。但维氏的哲学观似乎更倾向于说:
哲学不可用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因而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因为它也不能为语言的用法奠定基础。它让一切如其所是。它也让数学如其所是,它不能促进任何数学发现。对我们来说,“数学逻辑的首要问题”也是个数学问题,就像任何其他数学问题一样。
这提示我们哲学化的文学认识不能统筹关于文学的概念和定义的历史,更不能左右文学认识而变成独尊的文学理论形态。西方古老的“诗学”形态和现今所谓的“文学理论”,包括中国古代文论,它们都在不同的阶段内对文学进行解释但也都是“一种解释”。哲学之于文学认识应该让文学如其所是,而确证文学的真正根基绝不是“哲学”所能提供的,比如德里达对于文学本质的四点认识。如果说,德里达是用其一系列“解构”策略拆解了形而上学化的摹本与原型的“摹仿论”文学本质观,那么维特根斯坦就是通过澄清和改造哲学本身的思考和提问方式,来否定作为文学本质根基的哲学依据的。
三、“反本质主义”的启示:文学本质作为价值问题
主要阐述了“反本质主义”形成的两个重要路径:尼采、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反形而上学思路和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家族相似”的概念考察思路。这些论述都有一个根本的关涉点和立足点,那就是文学理论。
“反本质主义”之于文学理论的真正影响是使文学回归一个“词”。正如伊格尔顿所言,文学就是历史上人们称作文学的东西。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课堂上被当做文学来教授的东西。这样,文学理论就应首先回归概念考察。也就是对于文学这个词进行“词义”的考辨。回归其所生成的历史语境,并对之进行“事件化”的理解这是“反本质主义”题中应有之意。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在历史上规定着文学称谓的是什么力量呢?文化研究所能给出的答案大约就是意识形态,就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所奠定起来的思想意识。德里达承接尼采的传统拒绝文本在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他要求一切回归“书写”,而文本之外空无一物。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在声明传统哲学命题的无意义之后,给出了“回归生活”的路径。承接上文所述,维氏不过是在说其实世界上本没有哲学问题,传统哲学所关注的问题要么是在不能提出问题的地方产生怀疑而变得无意义[16];要么就是把本为概念的问题误解成一个事实问题而找科学去解决。因此这些哲学问题其实本不存在,有的只是我们不能明晰的把握语法规则所造成的误解(command a clear view of the use of our words.-our grammar is lacking in this sort of perspicuity.)。④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回归生活,生活让一切如其所是。如此传统哲学就自然消失了,哲学问题的真正解决就是其自行消失。人生问题的真正解决就是让人问不出这样的问题,正所谓:“人生问题的解答在于这个问题的消除。”所以维氏才说:任何理解我的人,最终都会发现我的这些言述是无意义的。这就像你已登到高处之后就可以把梯子扔掉了。哲学回归生活,文学就应该回归文本。怎么理解这个文本呢?或许就应该是活生生的被写作者不断创造出来的作品。这些世代流传的鲜活文本召唤着文学理论的本质诉求,又不断地颠覆这些本质称谓。韦勒克所谓“透视主义”的理解正体现出这样的辩证法:
“存在一种结构的本质,这种结构的本质历经许多世纪仍旧不变。但是这种‘结构’却是动态的:它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读者、批评家以及与其同时代的艺术家的头脑时发生变化。这样,这套标准体系就在不断成长、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总是不能圆满地实现。但这种动态的观念并不意味着只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17]
韦勒克、沃伦一方面认为文学或诗的本质就是其“决定性结构”,另一方面又指出这一结构的“动态”性质,是在历史中不断地被人们认识与生成的。所以,韦、沃才强调要用“透视主义”的方法综合这种标准,即处理好“一”与“多”,“变”与“不变”的关系,在相对中寻求不变的确定性,在确定中看出其发展变化来。这样便能既反“绝对主义”,又反“相对主义”。但韦勒克在《批评的概念》中还是显示出了布尔迪厄所谓的追求绝对理论的雄心:“我们必须回到建立一种文学理论、一套原则体系、一种价值理论的任务上来,”[18]18实际上如前所述,这无疑也是一种政治性的体现。因为“一套原则”是用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一种价值”是用来判定好文学和坏文学的。可见,这样的价值判断其实也不并与文化研究所揭示的“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相矛盾。更何况韦勒克还说:“文学理论与价值判断并不直接相关,这种观点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8]5可见问题并不出在建构本质性质的理论上,而是出在民主和霸权问题上。
德里达在描述“解构”的两难处境时说:解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因为“不能逾越这一阶段就意味着仍然要在被解构的系统的内部领域中进行活动”。[19]德里达反复强调“解构”本身是一个肯定性的过程,解构形而上学同时也尊重形而上学,打破二元对立的同时也承认二元对立存在的权利。否则正是走向了解构真义的反面。解构根本上就是在处理无法解决的矛盾而达成的一种妥协,体现出了一种直面异质性(heterogeneous)的勇气。解构的这种肯定性彰显了一种民主。并且在德里达看来文学本身就是西方民主制的产物:
“在西方,处于比较现代形式的文学建制是与讲述一切的授权联系在一起的,无疑也是与现代民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说它得其所哉地依赖于民主,而是在我看来,它与呼唤民主、最大限度的民主(无疑它会到来)的东西是不可分割的。”[13]4-5
因此,历史地看,本质问题本身就是价值问题,无论文学理论还是文化研究。如何能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中国当代文学知识的价值建构才是关键所在。不过,这种文学理论建构是什么呢?是否是德里达所谓的文本写作?还是借鉴维氏所谓的真正的哲学就是取消哲学呢(就像扔掉梯子一样)?或者说,这种文学理论建构能超越“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范式吗?这一点或许正如余虹所说:
“未来文学理论的基点在哪里?也许只有当我们真正拥有了一种新的意义理论,并切实地重建了一种较为可信的‘能指—所指—存在’的关系之后,这一基点才会显现。”[20]
注释:
① 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语言游戏”说和反本质主义的哲学论述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争论,本文在此只是立足维氏文本,阐明其“反本质主义”的基本思想对于颠覆形而上学的“哲学化”文学认识的意义,并不涉及其他。
② 此处译文,根据此页下的注释,笔者略有改动。
③ 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维氏的“相似性”和共同性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说:“相似性的确只能通过性质的共同性来定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解释一个一般概念时所需要的那种相似性只能通过全总的、贯穿于属于其的所有事项的性质上的(甚至于成分上的)共同性来得到解释”。详见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解读(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62
④ 根据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 Basil Blackwell, 1958, §122.p.49.笔者对译文做了改动。
[1]Simon Glendinning. On Being With Others: Heidegger, Derrida, Wittgenstein[M]. Routledge, 1998.
[2]陆扬.维特根斯坦:保守的解构主义者?[J].天津社会科学,2007(3).
[3]海德格尔.从思的经验而来[M]// 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158.
[4]拙文.反思本质思维如何进入文学认识[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1).
[5]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M].钱竞、张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6.
[6]余虹.艺术:无神世界的生命存在——尼采的艺术形而上学与现代性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5:(4).
[7]尼采.哲学与真理[M].田立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79.
[8]斯皮瓦克.德里达《论文字学》译者前言[M]// 陈永国.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6.
[9]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10]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M].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北京:三联书店,1999:247.
[11]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2]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
[13]德里达.文学行动[M].赵兴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4]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8.
[15]Ludwig Wittgenstein. Remark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M]. Basil Blackwell, 1980:167.
[16]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1,104.
[17]勒内·韦勒克、奥斯丁·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73.
[18]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M].张金言,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19]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M].何佩群,译.包亚明,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89.
[20]余虹.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J].文艺研究,1996,(3):12.
Two Trains of Thought in Anti-essentialism Literature Theory in Western Context——Derrida and Wittgenstein
YAN Ting1,LI Sen2
(1.School of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2.School of Music,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nti-essentialism in literature theory knowledge construction has two ways: one is the thinking of withstanding metaphysics, represented by Nietzsche, Heidegger and Derrida. The other is the concept investigation of “family resemblance”, represented by Wittgenstein. Reflecting on the two ways, we can know deeply that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is a value judgment. Whether in literature theory or cultural theor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w to develop democratic and pluralistic theory construction in recent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
anti-essentialism; literature theory; Derrida; Wittgenstein
2095-0365(2011)01-0075-08
2010-12-28
闫 听(1985-),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I10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