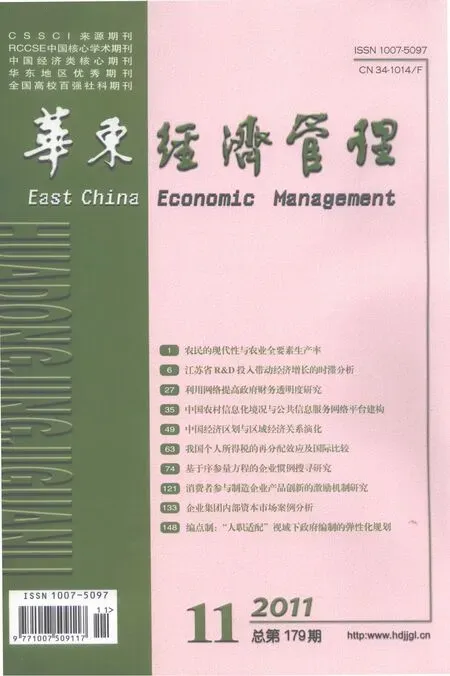晋升激励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2011-04-12田伟
田 伟
(1.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 南京 210004;2.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一、引 言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已有很多,最近的研究越来越集中于地方政府治理和地方官员激励的视角。而围绕经济增长的主题,从政府(官员)治理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国区域增长差异、粗放型增长方式以及城乡收入差别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绩效问题的经济学文献也开始出现,由此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张军等,2008)[1]的基本框架。
已有的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文献大多遵循以下两条逻辑路径:一是将地方政府本身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通过抓住1979年后中央——地方关系变革的主线(即财政分权改革),考察在财政收入激励下,地方政府具有怎样的行为特征,以之对中国财税制度的增长绩效进行分析 (如,Oi,1992[2];Qian and Weingast,1997[3];Qian and Roland,1998[4]; Jin 等,2005[5];刘雅南等,2009[6]等)。二是以地方官员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考察现有的官员治理制度如何影响着地方官员的激励结构,进而对中国官员治理制度的增长绩效进行研究(如,周黎安,2004[7]、2007[8]、2008[9];张军等,2007 (a)[10]、(b)[11];徐现祥等,2007(a)[12]、(b)[13])。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Chinese Style)分析框架的提出,上述第一条逻辑路径(即,基于财政收入激励考察地方政府行为)占据着对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主流地位。然而,由于该分析框架虽然可以成功解释中国在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但对于与高增长相伴随的某些“不好”的方面却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周黎安,2004)[7]。为更加深入地揭示地方政府的激励来源,从官员个体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地方官员治理制度的经济绩效这条逻辑路径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经济学者的关注。杨其静和聂辉华(2008)[14]以及周黎安(2008)[9]指出,以地方政府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类似于传统微观经济学在分析企业行为时将企业处理成一个“黑箱”,并没有涉及到地方政府内部的运作过程以及更为微观的官员个体行为的分析。事实上,中国政府部门自20世纪80年度初期开始实施行政首长负责制(由1982年宪法规定),行政首长对于政府事务负有主要责任,因此行政首长个人的激励与偏好对于政府目标的形成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主导作用。在这个背景下,如果以官员个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分析地方官员治理制度对于地方官员行为的影响,有利于揭开地方政府这个黑箱,更为深刻地考察地方政府激励结构的形成过程。
在中国地方官员治理制度中,与晋升激励相关的制度安排尤为重要——由于政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相比具有目标多任务型(multi-tasking)、绩效难以衡量性以及官员注重政治声誉与社会地位等非货币化效用满足等方面的特征,因此在公共部门一般采取弱激励的固定工资制,对于地方官员的奖励也以精神鼓励为主(王永钦等,2007[15]),这使得晋升激励往往构成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设计中最具激发力量的一种激励手段。所谓“为政之要,在于用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如何在晋升制度设计的引导下促进官员激励结构的优化成为地方官员治理问题的核心。基于此,遵循前述第二条逻辑路径的经济学文献大多从晋升制度进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出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问题加以阐释,本文即尝试对这一部分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一个综合的考察。
二、晋升激励的增长绩效研究
(一)“援助之手”与晋升激励问题的提出
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之所以在中国政府治理的经济学研究中受到关注,主要源于相关文献对中国地方政府“援助之手”行为的讨论。与俄罗斯及东欧等转型国家相比,中国地方政府被认为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伸出了更多“援助之手”(helping hand,Frye and Shleifer,1997)[16]——地方政府不仅会积极推进地区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Che and Qian,1998[17];Jin and Qian,1998[18];杨瑞龙,1998[19];张维迎,1999[20])、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洪银兴等,1996[21];张军,2007[22]),而且具有充分的激励为居民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张军等,2007(b)[11])。究竟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地方政府扮演了与其他转型国家的地方政府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角色?为什么在同样是转型体的其他国家,地方政府却往往被利益集团所“俘获”,具有了“攫取之手”(grabbing hand)的行为表现呢?
有关中国地方政府的“援助之手”行为可以从财政分权理论中找到初步的解释。由于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构成1979年后中央—地方关系演变的主线,因此早期的文献也倾向于从财政分权,进而财政收入激励中寻找“援助之手”问题的答案 (如,Oi,1992[2];Qian and Weingart,1997[3];Qian and Roland,1998[4])。基于财政收入激励的文献抓住了1979年后中国政府间关系制度演进的主线,其结论也得到部分经验证据的支持(如,Lin and Liu,2000[23];陈抗等,2002[24];Jin 等,2005[5])。然而,它们并不能够回答以下一个关键问题,即,为什么中国的财政分权可以促使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而俄罗斯的分权却为地区利益集团所“俘获”,成为了“攫取之手”呢 (Shleifer,1997[25])?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0)[26]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模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他们认为,对转型国家而言,仅仅是财政体制的分权尚不足以为地方政府提供充分的“援助之手”激励,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之所以取得一定的绩效,原因在于中国在财政分权的同时,保持着官员晋升的集权特征,这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在努力追求地区财政收入的同时,具有“向上负责”的激励导向,因此也不会为地区利益集团所“俘获”以争取更多的“民主选票”。
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0)[26]对于中国地方政府“援助之手”的解释使得经济学者开始关注晋升激励在引导地方官员行为中的作用,自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0)[26]之后,经济学文献开始从晋升机制进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其所伴随的一系列现象进行阐释。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学文献中还普遍出现了“中国式分权”的概念(傅勇、张晏,2007[27];陈刚等,2009[28]),用以描述中国经济转型所具有的“晋升集权”与“财政分权”相结合的特定制度安排,并认为“中国式分权”可以成为解释与中国经济增长相关问题的一个制度方面的重要特征。
(二)相对绩效考核与晋升激励的增长绩效研究
晋升的“集权”为中国地方官员提供了“向上负责”的激励导向,从而为中央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在保持对地方官员任免权威的同时,中央还主要通过相对绩效考核方式具体决定地方官员晋升(Li and Zhou,2005[29]),由此在政府部门模拟出标尺竞争(yardstick competition,Besley and Case,1995)[30]机制,制造了中国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共识和强大激励(见:张军等,2007(a)[10];张军,2008[1];徐现祥等,2007(a)[12])。虽然如此,相对绩效考核对于地方官员激励会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利影响。相对绩效考核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扭曲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代理人相互拆台的行为与中国地区间的市场分割
在相对绩效考核方式下,代理人之间存在相互拆台的可能,并且这种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行为甚至会走向某个极端,即,只要有利于抬高自己的相对位次,代理人有时不惜以损失自己的绩效作为代价。针对这种情况,Lazear(1987)[31]认为,通过适当降低支付的不均等程度可以有效减少因相对绩效考核而带来的恶性竞争。可以发现,虽然Lazear(1987)[31]的观点应用于私人部门减少恶性竞争的行为可能有效,但对于公共部门却不会起到十分明显的效果。由于公共部门主要以政治晋升而非货币作为对绩效较高者的支付,而晋升位置本身具有稀缺性(零和博弈的特征),这便使得降低支付不均等程度的方式在公共部门并不具有多大的操作空间。
考虑到相对绩效考核带来代理人之间相互拆台的情形,周黎安(2004)[7]在Lazear and Rosen(1981)[32]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政治锦标赛”(Political Tournament)的中国地方官员竞争模型,揭示了相对绩效考核引发中国地方官员合作困境的根源,对中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以及重复建设问题进行了一个基于晋升激励视角的解释。周黎安(2004)[7]虽然较好地解释了中国区域间合作的困难,但依据其基础模型,在政治锦标赛模式下,官员之间不存在相互合作的空间,我们因此也无法单纯从的晋升激励角度去理解中国部分地区(如长三角)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合作的倾向正变得越来越强烈的现实①。
徐现祥等(2007(a))[12]扩展了周黎安(2004)[7]的思想,认为为追求政治晋升概率的最大化,地方官员选择地方市场分割还是区域一体化将“因条件而异”。具体而言,当地方官员的努力具有正外部性或正溢出效应时,地方官员会理性地偏好于区域一体化,从而将正溢出效应内部化,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以及更高的晋升可能性;反之,当存在负外部性或负溢出效应时,地方官员会理性地偏好于区域间市场分割,从而将负外部性内部化,以免殃及自身经济增长以及相应的晋升可能性。此外,区域间一体化程度会随着正外部性的增加而增加,当经济体内的正外部性达到一定程度时,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区域一体化行为可以建立起全国统一开放的大市场。
徐现祥等(2007(a))[12]构建的理论模型能够从晋升激励的视角对中国部分地区市场分割以及部分地区市场整合同时存在的现象进行解释。皮建才(2008)[33]则在得出与徐现祥等(2007(a))[12]类似结论的基础上,将主流文献在构建相对绩效考核下晋升激励的理论模型时所采用的“代理人—代理人(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研究层次拓展到“委托人—代理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层次。从而使得过去文献所关注的地方“自下而上”的整合上升到强调中央政府在区域市场整合乃至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作用,使得晋升激励与区域市场整合问题富有了更深的政策含义②。
2.初始禀赋差别、地方官员行为的异质性与中国区域增长差异
王永钦等(2007)[34]指出,由于中国各地区初始禀赋的差别较大,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扭曲官员激励,导致不同地区地方官员行为的差别,进而加大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距:一方面,相对绩效考核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代理人面临的冲击或风险是共同的,而若代理人受到异质性随机冲击的干扰时,基于相对绩效考核激励方案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Gibbons and Murphy,1990)[35]。由于中国地区间初始禀赋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各地区在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别增加了相对绩效评估标准中的噪音,因而会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对绩效考核的激励效果。另一方面,在相对绩效评估方式下,较富裕的地区更多地享受着先天的优势和收益递增机制的好处,这就使得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地方官员不能在相对绩效评估的机制下获得激励。所以落后地区的官员在相对绩效评估中会处于先天不利的弱势,在晋升无望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他们寻求其他的替代办法进行补偿,如贪污腐败,或者“破罐子破摔”等,这将造成落后地区越来越落后而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因地区初始禀赋差异而造成的地方政府行为异质性的问题在财政分权理论中得到过深入的探讨,这些研究大多验证了在财政分权激励下,中国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会较不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更多地向地区经济增长伸出“援助之手”(张晏等,2005[36];王文剑等,2008[37];Zhang,2006[38])。对比财政分权理论的相关研究文献,除前述王永钦等(2007)提出的一个简单推论外,从相对绩效考核进而从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系统性理论及实证研究尚不多见。田伟、田红云(2008)[39]构建了一个地方官员晋升博弈模型,考察了相对绩效考核方式之下中国地方官员行为异质性的问题,从而对王永钦等(2007)[40]的推论进行了一个机理分析。但由于缺少地方官员行为的微观数据,他们的实证检验部分显得略为粗糙。
3.预算软约束、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与增长可持续性
在相对绩效考核引发的晋升锦标赛下,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有可能恶化,而企业的软约束问题则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周黎安,2004[7]、2007[8]):一方面,晋升锦标赛下的地方官员具有强烈的追求政绩的动机,为追求政绩最大化,地方政府有突破预算约束的冲动。而在“中央或上级政府不可能让地方政府陷于财政破产的境地”的预期之下,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会进一步恶化,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发生。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虽然企业等微观行为主体已获得相当大的决策自由,但由于地方政府仍然拥有部分重要资源的配置权以及行政管理权力,企业在融资以及获得土地、能源等要素方面会受到地方政府因素很大的影响,这使得企业(包括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会间接服从于地方政府的需要(田伟,2007[41]),“协助”所在地区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中胜出,由此而恶化了企业软约束的问题。
转型时期“软约束”的存在使得地方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这对宏观经济稳定性与增长的可持续性都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就其对宏观经济稳定性造成的冲击来看,软约束的存在使得地方投资具有了强烈的“单向”扩张特征,无论是在经济繁荣阶段(“过热”时期)还是在衰退阶段(“过冷”时期),地方投资似乎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单向扩张的倾向。方红生和张军(2009)对1994-2004年中国24个地区面板数据的研究后就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中国地方政府有75.16%的概率在执行扩张性政策,而在经济繁荣时期,地方政府执行扩张性政策的概率为63.78%。地方投资的单向扩张倾向使中央政府制定的宏观稳定政策难以得到很好的贯彻与落实,紧缩性政策常常因为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而体现不了应有的效果。地方投资冲动也因此构成引发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最初根源(应宜逊、林奇,2006[42])③。在对宏观经济稳定性产生冲击的同时,地方的投资冲动也是导致中国增长驱动因素中的投资——消费结构失衡,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过度依赖于投资驱动的低效率模式的一个重要体制根源。有关此,在相当多的文献中已有过深入的讨论(如:吴敬琏,2006[43]),我们这里不再赘述。
4.“合谋”与代理人选择参照系的成本
相对绩效考核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前述三方面扭曲成本为国内已有的经济学文献所关注。以下我们考虑另外两类扭曲成本,这两类成本虽然对经济增长不会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但由于不利于政府质量的改善以及官员素质的提升,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某些间接的不利效应,值得我们在后续研究中加以关注:
(1)相对绩效考核与“合谋”(collusion)的成本。Mookherjee(1984)[44]和Dye(1984)[45]发现,相对绩效考核方式会促使代理人之间合谋,共同降低努力程度,并且,与产品市场的合谋相比,相对绩效考核下的合谋由于代理人之间行为的相互可监督性而更难被打破(即,这种卡特尔越牢固)。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地方官员具有的一些行为特征,如政绩造假的“合谋”行为④——相邻地区地方官员之间对于对方的政绩造假行为“见怪不怪”,采取一种默认的态度,同时自己也参与政绩造假的活动。此外,越是到基层政府,相邻地区地方官员“政绩造假”合谋的可能性似乎会越大,虽然这种合谋也许是“心照不宣”式的。理由是:越是到基层政府,相邻地区地方官员的行为越是容易被相互监督,从而“卡特尔”的牢固性相对较强(当然,我们的这个推论并没有获得经验研究的证据,但在后续的研究中或许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⑤。
(2)相对绩效考核与代理人选择参照系(Choice of Reference Group)的成本。在相对绩效考核方式下,代理人总是倾向于选择能力较弱者作为自己的参照系,而在同一个参照系中,有能力者也往往容易遭受排挤。“能者被排挤”的现象在中国公共部门并不鲜见,许多真正有能力的官员虽然能够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可,但同时也会受到不少同级官员的“冷眼相待”,更有甚者,有能力者在做出一定实绩后反而可能面对许多的诽谤和中伤。在极端情况下,能力较弱者甚至还可以通过“游说”上级政府,影响有能力者的政治晋升,这不仅严重挫伤了有能力者的积极性,对于干部队伍整体质量的提升也将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
(三)“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对晋升激励增长绩效的研究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相对绩效考核或标尺竞争的有关文献为晋升激励的研究提供了“地方官员竞争”的分析框架。基于这个框架,我们可以融合中国转型期“晋升集权”与“经济分权”的制度特征,在“中国式分权”的大背景下讨论晋升激励的增长绩效问题。与前面纯粹从政治晋升视角出发考察晋升激励增长绩效的文献相比,将晋升集权与财政分权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会使得对晋升激励的讨论更趋完善。
为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讨论晋升激励的增长绩效问题,首先必须将晋升集权与经济分权对官员激励的影响加以融合。一些经济学文献对此进行了尝试,如,刘瑞明等在其一系列研究文献中提出“政治控制权收益”的概念(刘瑞明,2005[46];刘瑞明,2007[47];刘瑞明、白永秀,2007[48]),认为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主要来源于追求政治控制权收益。所谓“政治控制权”,简单来说即处于一定政治位置的官员所能控制的资源数量。当一个官员所控制的资源越多越有价值时,他所享受的“政治控制权收益”越大,表现为更大的名誉满足、更多的福利、更多的“在职消费”和灰色收入以及更高的反监督能力等等。政治控制权收益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官阶”的上升(纵向晋升激励),二是财政分权的经济激励(横向的“自我晋升”激励)。通过政治控制权收益的概念,刘瑞明等将财政激励容纳在一个基于政治控制权收益的晋升激励的框架下进行讨论,进而在“地方官员竞争”⑥的分析框架中讨论了“中国式分权”背景下晋升激励的增长绩效问题。
本文对财政分权与晋升集权在同一理论框架中的结合提出两点看法:
第一,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收入也可能构成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⑦。例如我们可以从许多省、市政府所制定的目标责任制考核项目中发现,对于下级政府必须完成的财政收入增长率本身就构成了对地方官员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所谓的追求财政收入激励与追求政治晋升激励并不冲突,而且前者可视为是后者的一项重要内容。如,薄智跃(Bo,1996)[49]基于中国省级官员1949-1994年升迁数据的研究后发现,与地区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央更关注地方上缴的税收——上缴税收越多的地方官员越可能获得提升,而少交税的地方官员甚至可能被降职。
第二,从官员个体的视角出发,财政收入不仅仅是一种激励,更多地可理解为是官员在追求政治晋升时所受到的地区财力方面的约束。即,在政治晋升的激励下,为追求政绩最大化,地方政府会扩大经济建设事权的要求,而地区财政收入作为经济建设职能的一个经济约束,地方政府只有为弥补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财政支出,才会产生增加相应财政收入的要求。因此财政收入与其说是一种“激励”,倒不如说是地方官员在追求政治晋升过程中所受到的经济方面的“约束”。我们这个观点得到有关经验数据的支持,如,马兹辉(2008)[50]发现,地方官员之所以追求财政收入,正是因为一定的财政收入可以支持一定的财政支出。而傅勇和张晏(2007)[27]在对“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实证分析时也隐含了这样一个假设。
我们的上述两点看法在王贤彬、徐现祥(2009)[34]以及傅勇(2008)[51]的理论模型中得到部分体现:王贤彬和徐现祥(2009)[34]构建了一个转型期中国地方官员的经济行为模型,这个模型一方面将财政收入作为地方官员追求效用最大化必须满足的预算约束(即,将财政收入更多地看成是地方行动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将地区须向中央上缴的部分财政收入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部分归入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从而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中同时考虑到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对于官员行为模式的影响,据此对中国地方政府偏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援助之手”(抑制官员私人消费)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机理分析。傅勇(2008)[51]则假设,地方官员的效用来自两个方面:增长业绩(GDP增长)和公共物品供给。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来源于扣除向中央上缴比例后的地区财政收入。预算约束被用于两部分:一部分被用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吸引资本流入进而追求地区增长业绩,另一部分则被用于向本地居民提供公共物品。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傅勇(2008)[51]构建了一个中央与地方博弈的斯塔科尔伯格(Stackelberg)模型,结合地方政府竞争(以财政支出竞争为手段)的逻辑,讨论了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偏好于基础设施建设,但对于科教文卫等项目的支出不足)的激励根源以及改善这种扭曲性支出结构所可能具有的福利含义⑧。
总的来看,虽然不同的文献存在着不同的尝试,但最近出现的刻画“中国式分权”的理论模型大多将财政视为一种手段。与早期强调财政激励的文献相比较而言,这些文献更强调晋升集权进而晋升激励在引导中国地方官员行为中的作用。
(四)“隐性治理机制”的增长绩效研究
除相对绩效考核外,中央还通过一系列“隐性治理机制”(Huang,2002)[52]——如官员异地交流、任期限制等——对地方官员进行治理,这一系列治理机制设计的目的旨在降低官员腐败水平以及防止地方违背中央意志等现象的发生。与相对绩效考核相比,隐性治理机制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官员政治晋升的治理制度,但由于它们会对晋升激励产生某些“间接”的影响,因而也受到相关经济学文献的关注。
隐性治理机制间接影响晋升激励的具体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这些制度的实施会进一步放大或缩小相对绩效考核的激励效应——如,官员异地交流制度就被认为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降低因代理人相互拆台而产生的扭曲成本,有效促进地区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及官员之间的经验交流(刘本义,1998)[53]。再例如,徐现祥等(2007(b))[13]发现,地方官员的“交流效应”服从于现行政绩考核方式所能够提供的激励导向,其结果是“从产业发展取向看,官员交流效应是通过在流入地采取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取向实现的”。就这个角度而言,异地交流制度(在降低代理人相互拆台的扭曲成本的同时)也可能使得转型时期地方投资冲动的扭曲效应得到进一步的“放大”,由此而加剧中国经济的粗放增长。
新近出现的有关隐性治理机制增长绩效的研究大多是基于计量分析的方法,对隐性治理机制的增长绩效进行定量识别,为“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徐现祥等(2007(b))[13]基于1978—2005年间中国省长(书记)的交流样本构造了一套省长(书记)与省区相匹配的面板数据,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省级官员交流对流入地经济增长的影响(省级官员交流促使流入地GDP增长约1个百分点)。张军等(2007(a))[10]同时识别了异地交流与任期限制的增长绩效,发现:①异地交流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存在地区效应的差别(异地交流制度在东部地区带来的增长效应要高于中西部地区)。②官员的在任年数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呈现出由正到负的倒“U”曲线的特征,同时在任年数的增长效应也存在着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官员在任期内比中西部地区官员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正面作用更大)。徐现祥等(2010)[54]以省长晋升为省委书记作为政治晋升的样本,识别出晋升激励的增长绩效会因地方官员年龄及任期的差异而产生差别,年龄越大,政治激励的作用越小,而任期的适度延长则有利于政治激励作用的发挥。
可以发现,虽然这些文献为“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但由于缺少更深层次的机理分析,其结论对于理解“隐性治理机制”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整体”效应却启发有限。如前文以异地交流制度为例所探讨的那样,“隐性治理机制”完全可能会是一把“双刃剑”,在短期内有利于增长“速度”的提高,但在长期内却可能对增长的“质量”产生种种不利影响。如何在理论研究中识别出“隐性治理机制”影响晋升激励的具体作用途径,通过开展更为深刻的机理分析,对“隐性治理机制”的增长绩效加以系统性考察,这或许是后续研究有可能获得突破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研究展望
如何从地方官员个体视角出发,通过考察晋升制度对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政治—经济”的分析,这正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者的关注。前述对已有文献的考察表明,相关研究在以下几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拓展:(1)在理论研究方面:应体现出“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景,将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融入同一个理论框架,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的两条“平行”开展的逻辑路径能够获得统一。(2)在实证分析方面:应尽量以地方官员调研的微观数据为基础,对官员行为进行直接的测度。现有文献大多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角度间接衡量地方官员行为,由于缺少公开的制度外支出数据,基于这种方法得出部分结论可能令人质疑。(3)在指导实践方面:应考虑将“代理人—代理人(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分析层次上升到“委托人—代理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层次,使得相关研究具有更加深刻的政策含义。在这方面,皮建才(2008)[33]进行了一个有意义的尝试,但其讨论仅仅限于地区市场分割问题,如何在晋升激励增长绩效的理论研究中系统性地引入中央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对于推进实现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增长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 释]
① 针对该问题,周黎安(2004)提出经济竞争与政治竞争的“混合竞争”假说,认为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区域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但前提是这种合作不改变地方官员之间在政治上的相对位次(即,“经济合作的政治激励约束”)。
② 在具体的建模思路上,皮建才(2008)对比了中央采取的两种不同绩效考核方式(“总量相对绩效考核”与“增长率相对绩效考核”)对于区域市场整合的影响效应会存在怎样的区别,据此对两种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比较。
③ 郭庆旺和贾俊雪(2008)构建了一个中央与地方在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上的博弈模型,考察了地方的投资冲动冲击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具体作用机理。
④ 周黎安(2007)指出,跨地区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谋在中国目前的晋升体制下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威胁。原因在于,在锦标赛式竞争模式下,官员通过竞争胜出所能够获得的利益要远远高于因“偷懒”合谋所能够获得的利益,因此与合谋相比,高度竞争才是一种常态。我们认为,官员之间究竟是合谋还是竞争,除了取决于官员对两者利益的对比外,还取决于官员对两者成本的比较,若上级政府对官员合谋行为的监督不力或惩处不严(即合谋的预期成本较低),则合谋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倾向。我们所举的“政绩造假合谋”也许就是一个现实的案例。
⑤ 我们这里主要讨论了横向相对绩效考核的情况,在纵向相对绩效考核(周黎安,2005)下,是否也会存在政绩造假的合谋现象呢?即,当某一任官员发现前任官员政绩造假后,是否也会“自觉地”对前任的虚假政绩进行掩盖呢?我们认为,在相对绩效考核下,官员进行合谋的动机是存在的,某一任官员掩盖前任的虚假政绩,并在此基础上继续“造假”,这种行为倾向在现实中并不罕见。
⑥ 基于政治控制权收益的地方官员竞争类似于周黎安(2004)提出的“混合竞争”的假设。
⑦ 地方财政收入由一般预算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基金收入)两大部分构成。一般情况下,上级政府会在年终对下级政府本年度完成的“财政收入增长率”进行考核,同时也对一般预算收入(含国税地方留成、地税收入、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等)进行单列考核。
⑧ 其实证检验见:傅勇和张晏(2007)。
[1] 张军,周黎安.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 Oi Jean C.Fiscal Reform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Corporatism in China[J].World Politics,1992,45(1):99-126.
[3] Qian Yingyi,Weingast Barry R.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1997,11(4):83-92.
[4] Qian Yingyi,Roland Grard.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5):1143-1162.
[5] Jin Hehui,Yingyi Qian,Berry Weingast.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 Style[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1719-1742.
[6] 刘雅南,邵宜航.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差异[J].经济学(季刊),2009,(8).
[7]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6).
[8]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
[9] 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 张军,高远.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7(a),(11).
[11] 张军,高远,傅勇,等.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J].经济研究,2007(b),(3).
[12] 徐现祥,李郇,王美今.区域一体化、经济增长与政治晋升[J].经济学(季刊),2007(a),(6).
[13] 徐现祥,王贤彬,舒元.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7(b),(9).
[14] 杨其静,聂辉华.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J].经济研究,2008,(3).
[15] 王永钦,丁菊红.公共部门内部的激励机制:一个文献评述[J].世界经济文汇,2007,(1).
[16] Frye Timothy,Shleifer Andrei.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Grabbing Hand[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2):354-358.
[17] Che Jiahua,Qian Yingyi.Insecure Property Rights and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Firm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113(2):467-496.
[18] Jin Hehui,Qian Yingyi.Public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 of Firms: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113(3):773-808.
[19] 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J].经济研究,1998,(1).
[20] 张维迎.区域竞争与私有化[J].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1999,(20).
[21] 洪银兴,曹勇.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功能[J].经济研究,1996,(5).
[22] 张军.为〈为增长而竞争〉而写[M]//张军,周黎安.为增长而竞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公司、格致出版社,2008.
[23] Lin Justin Yifu,Liu Zhiqiang.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00,49(1):1-21.
[24] 陈抗,Arye L Hillman,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J].经济学(季刊),2002,(2).
[25] Shleifer A.Schumpeter Lecture:Government in Transit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41(3):385-410.
[26] Blanchard O ,Shleifer A.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China versus Russia[R].MIT Working Paper 00-15,2000,
[27] 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 ,(3).
[28] 陈刚,李树,余劲松.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关于中国式分权的一个假说及其验证[J].南方经济,2009,(7).
[29] Li Hongbin,Li-An Zhou.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1743-1762.
[30] Besley Timothy,Case Anne.Incumbent Behavior:Vote-Seeking,Tax-Setting,and Yardstick Competi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5,85(1):25-45.
[31] Lazear Edward P.Pay Equality and Industrial Politic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7,97(3):561-580.
[32] Lazear Edward P,Sherwin Rosen.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1,89(5):841-846.
[33] 皮建才.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下的区域市场整合[J].经济研究,2008,(3).
[34] 王贤彬,徐现祥.转型期的政治激励、财政分权与地方官员经济行为[J].南开经济研究,2009,(2).
[35] Gibbons Robert,Murphy J Kevin.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o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J].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1990,43(3):30-51.
[36] 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5).
[37] 王文剑,覃成林.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J].管理世界,2008,(1).
[38] Zhang Xiaobo.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in China: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Inequality[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6,34:26-713.
[39] 田伟,田红云.晋升博弈、地方官员行为与中国区域经济差异[J].南开经济研究,2009,(1).
[40] 王永钦,张晏,章元,等.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J].经济研究,2007,(1).
[41] 田伟.考虑地方政府因素的企业决策模型——基于企业微观视角的中国宏观经济现象解读[J],管理世界,2007,(5).
[42] 应宜逊,林奇.中国经济周期的特点与宏观调控改进思路[M]//刘树成.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3]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44] Mookherjee Dilip.Optimal Incentive Schemes with Many Agents[J].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84,51(3):443-446.
[45] Dye Roland A.The Trouble with Tournaments[J].Economic Inquiry,1984,22(1):147-149.
[46] 刘瑞明.晋升激励、政治控制权收益与区域可持续发展[M]//白永秀.区域经济论丛(一).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47] 刘瑞明.晋升激励、产业同构与地方保护:一个基于政治控制权收益的解释[J].南方经济,2007,(6).
[48] 刘瑞明,白永秀.晋升激励、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J].南开经济研究,2007,(5).
[49] Bo Z.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996,5(12):135-154.
[50] 马兹辉.中国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J].管理世界,2009,(3).
[51] 傅勇.中国的分权为何不同:一个考虑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的分析框架[J].世界经济,2008,(11).
[52] Huang Yasheng.Managing Chinese Bureaucrats:An Institutional Economic Perspective[J].Political Studies,2002,50:61-79.
[53] 刘本义.党政领导干部的交流与探索[J].组织人事学研究,1998,(3)
[54] 徐现祥,王贤彬.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