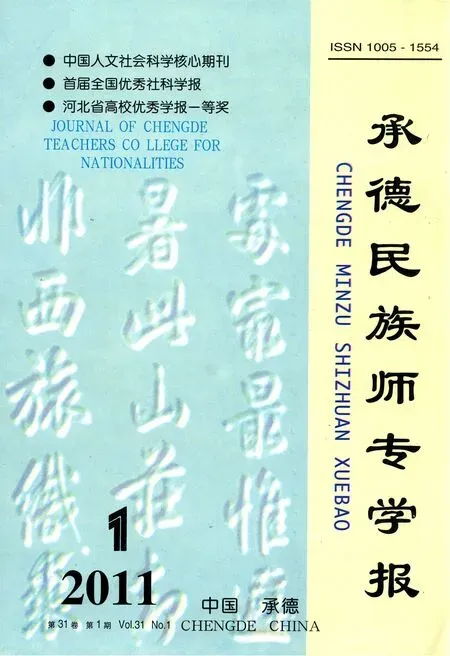《文艺阵地》对抗战时期文学论争的介入及其理论建构
2011-04-12熊飞宇
熊飞宇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400047)
《文艺阵地》对抗战时期文学论争的介入及其理论建构
熊飞宇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400047)
抗战时期,社会的剧变,对于新文学的发展和变革提出新的要求,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实主义,二是文艺大众化、旧形式和民族形式。其中有关现实主义的讨论是基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而文艺大众化,则指向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文艺阵地》是茅盾主编的一份大型的综合性文学刊物。对于上述问题,都曾积极介入并展开充分的探讨和争鸣,极大地丰富了抗战时期的文学理论。
《文艺阵地》;现实主义;文艺大众化;旧形式;民族形式
《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一份大型的综合性文学期刊,1938年创刊,1942年终刊。其主编,名义上一直为茅盾所担任,实际上却先后由茅盾、楼适夷、以群、罗荪等人执编。借助这块阵地,中国左翼文化人士以积极而活跃的战斗姿态,在创作与理论两方面大有斩获,与《抗战文艺》一道,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两大刊物。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论争,《文艺阵地》可谓无役不与,围绕现实主义,文艺大众化、旧形式和民族形式,展开讨论和争鸣,在理论上作出卓越的建构。
一
抗战的爆发,使中国和中国人民面临着重大而艰险的历史巨变。在这个历史巨变中,文学艺术必须作为一种巨大的反映力量和反拨力量,给予这种历史现实以有机的影响。从“新现实主义”的提出,到“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贯彻,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至尊,再到“民族革命现实主义”的倡扬,现实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现实语境中,展现出不同的面目特征与精神特质,最终从国外无产阶级文论的束缚中,艰难地蝉脱出来,重新接续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再度呼应了抗战新形势的要求[1]。《文艺阵地》则见证了这一结果的诞生。
所谓“现实主义”,简而言之,就是广泛、多面而正确地描写现实生活的倾向。在李南桌看来,只要是一个作家,广义地说,必定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因此无须紧抱死守某一主义。如果非要勉强命名的话,可称之为“广现实主义”[2]。在《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论》中,祝秀侠对这一论题作了初步的阐释与建构。1.题材。茅盾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中指出“抗战文学的题材,应当广博而复杂,什么都有。”抗战有积极的样貌,也有消极的样貌。在内容上,既需要激昂慷慨、悲壮英勇,也需要嬉笑唾骂。前方与后方,是战时整体的两面,不可偏废。国内的题材固然重要,国际的题材也必不可少。总之,社会背景、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复杂多变的,由此带来的主题广泛性、多样性,正是现实主义抗战文学的主要条件之一。2.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是客观认识与主观感情的统一。抗战文学在匆促间披挂上阵,露出两个破绽:一是作品的理论化与原则化。只有主观充溢的感情,没有表现出客观事实的复杂性,没有具体反映出真实,沦为观念论的俘虏。“差不多”现象和理想概念化也就漫衍开来。二是只写乐观的一面,忽略了艰难悲观的事实。抗战的现实是悲喜剧交织的伟大场面。抗战的最后成功,要经过无数可悲的事实。粉饰现实,将虚伪的感情注入作品中,不是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正如沈起予在《悲观的文学》中所说:“在抗战的昂奋的时候,带哀感的文学就一定无好处吗?”3.热情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高耸入云的“主题积极性”。积极性是站在作品现实性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即必须依附于现实的真实本质,而不单由观念所决定。作品勉强积极化,扎上积极的尾巴,并不就表示意识的正确,相反则会导致公式主义的泛滥。4.抗战文学不应该忘记“文学”。在抗战文学的河流中,浮泛着大量标语、宣言、政论式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在现实表面滑行的结果。抗战文学并不是粗枝大叶的。首先要关注的是艺术性。从表面上看,艺术性只属于创作方法,而其实是创作过程的全面显示,是文学的本质。其次是典型性。典型一方面固然是概括相同的人物而抽出它的一般性特征加以深化、扩大;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个别的特殊性和个人的性情。最后是健全的世界观。现实主义要求有积极的态度,正确而深刻地透视现实的本质倾向,及其多样性、关联性、活动性,藉此坚定抗战的意识,洗炼行动的战术,使抗战文学向更高发展。因此,文学工作者必须把握创作过程和生活过程的相互关系。首先作为一个现实的战士而生活,参加到现实的斗争中,渗融在现实最深的内容里。其次学习一切伟大作家的艺术手法,接取一切现实主义的文学遗产,增加抗战文学的艺术性[3]。
祝秀侠的观点,还明显地带着发轫时期的散漫。经过一个时期的进展,洁孺最终结晶为“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论”。前者用现实主义统摄抗战文学,后者则将现实主义置诸民族革命的语境。新时代和新文艺,要求文学现实化、中国化和大众化,要求文学水准向上和向前。因此,建立新的完整的中国文学形式,创造具体的系统的中国文学基本方法,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有了必要。
这种完全中国的方法与形式的创造,存在于如下两个契机:一是有机地摄入人类成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吸收、融化,并与民族革命的现实相联系;二是把握中国民族革命的现实,加以有机的概括,使之透过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而显现,并获得现象的健全性与明了性。
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由三个方面组成。1.民族革命的内容占优位,成为民族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在艺术创造上吞没其它的东西,而是在调谐的基础上归于统一。2.这里的现实主义,不仅是动的现实主义,而且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合流,是两者在新基础上的创造。革命的浪漫主义,作为一种非常强烈的力量,有机地渗透于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之中。3.这种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是完全“中国”的。它把过去一切时代中国文学的累积作了质的提高、深化和净化,引领中国文学,在民族革命的精神上、思想上改造并教育中国的现实群众;而且在创造的基础上,模铸中国的典型,描写中国的性格,丰富中国文学的形式,创造中国文学的风格,革新中国文学的姿态。
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体现出三个基本特征。1.机敏地结合中国大众的斗争,指引抗战文学在实践的斗争和宣传中,发展创作,培育理论,使中国文学的批评活动、理论活动和创作活动,获得特殊的姿态和实践的意义。一方面指导创作实践,一方面指导生活实践。2.要求全体文学工作人员,一致站立在民族革命的世界观上面,深刻地了解中国历史现阶段的性质3.是一个有机的艺术方法的整体。它不仅是作家实践和认识的方法论,更主要的,它还是一个表现的方法论。总之,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在政治、文学、样式的意义上,都具有深远而切实的指导意义[4]。
玄珠认为,五四以来写实文学的真精神就在于,它有一定的政治思想为基础,有一定的政治目标为指针。其间客观的社会政治形式屡有变动,写实文学的指针也屡易方向,但作为基础的政治思想却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民族的自由解放与民众的自由解放[5]。正是在此基础上,“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在战争的风风雨雨中,茁壮成长起来,并以坚稳深固的英姿,让这一政治思想发扬光大。
二
如果说有关现实主义的讨论是基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那么文艺大众化,则指向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文艺大众化,简单地说,始自五四平民文学的要求,1927年前有革命文学的倡导,抗战时期有大众文学的推进。具体表现为:1937年文艺的“通俗化”问题的讨论;1938年“文协”关于“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提出;四十年代“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以及解放区文艺大众化运动火红的展开[6]。抗战时期成为这一运动至关重要的发展阶段。其理论探讨与实践成果,《文艺阵地》都有充分翔实的反映。
文艺的大众化,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大众文艺。因此,文艺大众化,不止是一种政治的革命手段,也是一种文艺的革命手段。它具有政治和文艺的双重目标。革命文学大众化,就是为使革命文学能够深入和普及到大众里边,所要完建起来的一种文学革命的工作。抗战建国的文艺实践,一方面是革命文学的实践,另一方面,则是文学革命的实践。文艺大众化,既是抗战建国中文艺的中心工作,也是文化艺术领域中的民族革命工作。文艺大众化,要求文艺工作者,不但在理论活动、创作活动上战斗起来,而且必须深入到大众里去推行、传播。
文艺大众化的推进,必然撞击到语言和形式两个层面。就语言而论,则有大众语问题的生发。近代语言学有两个努力的方向:一是趋向单纯,是解析的,宜于理论;二是趋向繁复,是完形的,适于文学。大众语,是大众创造的总集,富于生动的形象性,存在于人类认识所及的任何地方。作为国语或官话的反面,大众语包含着方言和俗语。前者是地方性的,后者是阶层性的。文艺,为了能够与大众向上的生活亲切地配合,必须铲除文字上的壁障。因此,一系列运动,如识字运动、语文运动、拼音文字运动等,都要获得广泛的开展。于是,拉丁化运动、普及教育运动、政治宣传工作,文化上的一切动员问题,都同文艺大众化密不可分。没有文艺大众化,做不到文化上的总动员;没有文化上的总动员,也达不到文艺大众化。大众化不是文艺的降低,而是文艺的提高;不是贬值,而是加价。文艺大众化是更进一步、更深入一层的现实主义。
就形式而言,第一个问题是旧形式的利用。所谓旧形式,是指散在民间,还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口碑式的文艺形式,而非无条件地指一切旧日的文学形式。旧形式,并不意味着完全陈旧,它是新文学家用来区别于欧化形式的一种说法;旧形式也并不完美,因为文化生活的低下和积年注入毒素的原故。
齐同首先批判了“应用旧形式”的错误。“应用”意味着,把旧形式生吞活剥地拿来,添上抗战的内容。他力主“利用”,因为利用首先含着取舍。利用要加以必要的拣择、审慎的处理,其中扬弃作用是不该忽视的[7]。利用旧形式,在仲方先生看来,是以“旧瓶装新酒”为主体。它有两种意义:一是翻旧出新;二是牵新合旧。两者汇流,将产生民族新的文艺形式[8]。然而,对于此种说法,向林冰却不以为然。在《关于“旧形式运用”一封信》中,他代表“通俗读物编刊社”,从两个方面加以辩驳:1.旧瓶装新酒本为 “旧形式运用”的拟语,强分为二,似可不必。2.“利用”为实用主义观点,“运用”更妥。在运用的概念下,从适应大众低级欣赏力,到克服大众的低级趣味;从运用旧形式配合大众启蒙运动的开展,来创造新形式;由大众化内容的增长,加深其与旧形式的矛盾,从而促进与新内容合致的新形式的建立[9]。
旧形式载新内容这个课题,是“9·18”之后所提出的大众化文化运动的一个具体发展。对于这个课题,存在着两种错误见解:一是根本不能适应;二是完全能够容纳。第一种见解,取消了旧形式在现阶段抗日战争的新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把旧形式看作是与新内容绝对对立而不相容的东西。第二种,推崇旧形式“十全十美”,无条件地夸大其适应的效能性,结果产生不良影响,即人们将满足于旧形式,而放弃建立新形式的主观努力与创造,忽略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伧俗的形式中,很难产生大众的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10]。
那么,文艺大众化和利用旧形式二者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大众化文化运动,一方面需要文化人更密切地接近大众的生活,运用和创造大众的日常语言,以便更能适合大众的需要和理解;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在某一个时期内,需要运用旧形式,并通过旧形式,去取得更显著的效果。而旧形式在客观的历史法则制约之下,仍能某种限度地适应新内容。旧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它会在新内容的推动下,发生蜕变。文艺大众化,其最高目标,就是要通过旧形式的利用,达到文艺的大众化,充实和发扬抗战力量,同时使文艺获得质的提高,陪伴并参与抗战建国的前途发展。对于旧形式,要有惊动与修改的胆量。旧形式的“同时克服并保留”(恩格斯语)不能一蹴即几,一下即成。首先得有大量作品的产生,在此基础上,努力铺砌作者与批评者不断交往的过程,即作者的尝试、改进、自我检讨与批评者的分析、批判、理论光照。其次,对于“旧人”也要不遗余力地争取[11]。
三
第二个问题则是民族形式的建立。文学上民族形式的创造,是文学的历史传统(包括口头文学与写的文学)的接受,渗透到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以完成文学的政治的历史任务,并使文学本身发扬光大一种运动与口号。
就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而言,有载道和言志两派。载道以儒家思想为传统,言志以佛老思想为本质。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就是儒家思想与佛老思想的交流。中国传统文学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表现上层建筑的政治的基调;一是表现下层社会基础的生活的基调。由此形成中国文学民族形式的传统:一是文学的全体主义(totalism),表现为混沌笼统的概念与对情节的关注;二是必须注意中国社会的殖民地性质。殖民地的大众文学,有其一般性与特殊性。中国革命的力点,已经由反日反汉奸转移到反帝反封建上,因此,这时期中国大众文学的主要内容,是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文学,反帝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主义的文学。它以殖民地人民大众的立场,观照抗战现实的每一角落,予以批判与赞扬、打击与发扬、无情的暴露与热烈的高歌。在此基础上,巴人的结论是:1.民族形式必须从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学中生长;2.学习当以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形式为依归,向民间的生活形式突进,再转化封建文学的形式为真正的大众文学形式;3.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文学形式将是而且应该是无限、复杂、多样的发展[12]。
民族形式问题,引发了激烈而持久的讨论,杀伐之声,不绝于耳。针对陈伯达、艾思奇、郭沫若、光未然、向林冰、胡风等人的观点,王实味以《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和新偏向》为题,展开集体清算,最终认为:民族形式,就是进步新文艺在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应用,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反映民族的现实生活,使它成为新鲜活泼的、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13]。这里,气派是民族的特性,作风是民族的情调。特性是作品的内容,情调是属于作品的形式。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既是民族形式的集中体现,也是现实主义大众文学的最高特征。
然而,文艺大众化的结果,是否就是指向通俗文艺?艺术产生于“俗”。《诗经》直接产自大众的民间文艺,《离骚》则是一个不得意的文人迫入大众之后所产生。民间文学有两大特色:一是无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都保持着与大众智识水准的一致;二是手段多用白描,其形象化中一点观念的渣滓都没有,而义蕴却最多,因此能把一时一地的意境完全防腐地保存下来,供给不同的时代作不同的解释。而“雅”不仅代表了艺术的幽美与艰深,也表现时代生活壁垒的界限。为了保守某种生活,就不能不倡导“雅”。同时,文艺入庙堂,是文人把去出卖、换取功名的结果,这一换,文艺只剩下残渣。在历史上,“雅”常会遭遇贫困,需要不断有人从民间拾取一些新的质素,一俟文艺潮流变化,便挤进去,从而挽回文艺的颓运[14]。
文艺大众化是文化整体变化的必然。革命文艺大众化的工作,一方面是形成了报告文学、朗诵诗、街头剧等的运用;而在另一方面,则是利用旧形式的通俗文艺运动。这是文艺大众化的两条平行路线,互相辅助、互相配合,并路而进。大众化和通俗运动并不是迁就、降级与退缩,而是提高。这提高不仅在于外形,也在于内质。运用旧形式的通俗文艺的目的,就是要用一种新的革命的东西,去代替封建的民间文艺;就是用一种游击队式的民间文艺,去代替义和团式的民间文艺。它并不要求文化人或作家另造一种文化,而是原有文化的扩大与更新。文艺大众化首先要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在大众生活和文化状态的改善过程中,文艺大众化是其中最有力的环境,并由此而穿上政治性的衣裳,成为抗战巨流中的一支。从另一角度上讲,文艺大众化并非去教育大众,把文艺还给大众,才是文艺大众化的最终目标。总之,简单地把大众化与通俗混用,是极其有害的:直接的可以影响到大众化,间接的可以影响到整个抗战。
现实主义,以及文艺大众、旧形式和民族形式,一直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的主要线索,在抗战的语境下,不但未曾中断,相反却获得了新的内涵和发展。《文艺阵地》对这两个问题的介入与建构,既丰富和深化了抗战时期的文学理论,同时也为它们的演变,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有效的考察视角。
[1]靳明全,宋嘉扬.论中国抗战文论中的现实主义之深化[J].文学评论,2005,(3)
[2]李南桌.广现实主义[J].文艺阵地,1938,(1)
[3]祝秀侠.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论[J].文艺阵地,1938,(4)
[4]洁孺.论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J].文艺阵地,1939,(8)
[5]玄珠.浪漫的和写实的[J].文艺阵地,1938,(2)
[6]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148.
[7]齐同.文艺大众提纲[J].文艺阵地,1939,(3)
[8]仲方.利用旧形式的两个意义[J].文艺阵地,1938,(4)
[9]向林冰.关于“旧形式运用”的一封信[J].文艺阵地,1939,(3)
[10]杜埃.旧形式运用问题[J].文艺阵地,1938,(2)
[11]黄绳.关于文艺大众化的二、三意见[J].文艺阵地,1939,(11)
[12]巴人.民族形式与大众文学[J].文艺阵地,1940,(6)
[13]王实味.文艺民族形式的旧错误与新偏向[J].文艺阵地,1942,(4)
[14]穆木天.文艺大众化与通俗文艺[J].文艺阵地,1939,(8)
The Debates on Literature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Front of Literature and Ar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Xiong Feiyu
(Chongqing Research Centr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society mak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New Literature,specifically in two terms:firstly,realism;secondly,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traditional and national form.The debates on realism are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imes,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refer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people.The Front of Literature and Art is a voluminous comprehensive literary journal edited by Mao Dun,which responds to such problems actively and debates about them fully further.All of these have greatly enriched the literary theory in this period.
The Front of Literature and Art;realism;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traditional form; national form
I206
A
1005-1554(2011)01-0020-04
2010-12-25
熊飞宇(1974-),男,四川省南江县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重庆抗战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