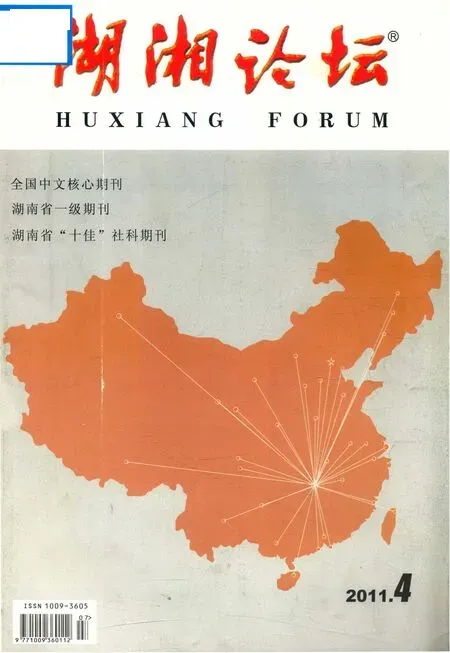论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同构*
2011-04-11李建华方华堂
李建华,方华堂
(中南大学,湖南长沙410083)
论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同构*
李建华1,方华堂2
(中南大学,湖南长沙410083)
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在生成过程、主体承担、功能作用上都是具有同构性的,从变更行政文化入手来提高政府效能不失为一种合理选择。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在生成时间、生成空间和起点上都是交织的,同时政府效能的建设主体与行政文化主体也是同样的,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类同的作用体现在维护政府合法性及有效回应社会需求作为自己的价值旨归,都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都是政治建设的一部分。
行政文化;政府效能;同构
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具有同构性,这源于它们衍生于政府生态这个共同的物象,从而二者同源、同象、同功成为可能。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同构促使二者的互镜顺理成章,联姻则进一步规训二者往更高阶段有序发展。“同构”是一数学用语,原意是指保持结构的双射,其中一个态射联动着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态射,两者构成一个恒等稳定的结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子化的事物之间联系愈来愈紧密,各个学科交叉融合,打破了原有的隔离,学科界面呈现重合,学术用语也被不断移植到其他学科,“同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引入了社会科学。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同构,它着意于不同事物立基于相同的生长起点,表现在生成具有同源性,体现于生成过程的同构,包括生成起点、生成时间、生成空间、生成的主体以及由此衍生的作用于功能。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同构就是这种源头上的同构,它们以政府生态为共同源头,在同一生成主体下衍生出相同的生成起点、生成时间、生成空间以及相似的功能作用。
一、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生成过程具有同一性
从生成起点上来说,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都是伴随政府生态而与生俱来,它们的生成过程拥有同一肇始点,即政府的出现。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生成起点在于政府的产生与存在,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无论是封建社会的家国一体,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前中期纯粹管理型的行政国家,抑或后资本主义时期的服务型政府,我们不难发现,自国家、政府产生的那一天起,也就宣告了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正式存在,由于二者的结构性互嵌,政府的产生不可避免地同时伴随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出现。行政文化作为政府管理的灵魂,它处于政府形成过程与成长过程中的潜层次与隐层面,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导引作用,既包括行政管理主体在行使行政职能时自发形成的行政文化,也包括由于行政管理客体对政府的预期与回应而反作用于行政主体而促使其按照公众期待所型构的行政文化,但无论何种形成机制,行政文化都要归因于政府的存在。由于政府存在的模式有多种,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于是行政文化也就有了优劣之分,这种所谓的优劣并非是恒久的指谓,它意指行政组织中的文化样式能否与当下环境中各种能量地输出、输入及转化相匹配、相符合,契合则是优良的行政文化,反之则是阻碍行政管理发展进程的落后的文化样式。此种当下环境中能量地输出、输入与转化是指政府从诞生之日起,其存在模式的不断翻新与政府生态的推陈出新,行政文化也不断重塑自我从而与各个时代的社会现实相吻合,从这一点上来说,行政文化具有历时性;然而从行政文化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分析,行政文化的各种形式在各个阶段初期其主体无疑都是优良的,它能够有效的为政府行为指引方向,尽管期间也伴随着低劣的、阻碍行政管理向前发展的颗粒。从生成过程的肇始点上来说,政府效能亦是政府产生的衍生物。自政府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政府有效与无效,高效与低效的问题,尽管表现为统治、管理、治理、服务等多种形式,但是这都难以改变政府效能从政府产生而发端的事实,这也是政府效能附属于政府存在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只有政府产生了,才有政府效能这个问题意识;并且,只要政府产生了,就必然会出现政府效能这个问题,尽管其不一定以“政府效能”这一专用术语来指代。从上述分析可知,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确实生长在同一共相点上。
从生成时间上来说,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产生具有同步性。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在生成过程上不仅具有相同的生长起点,而且二者在产生的时序上也具有同步性,是一种伴随政府产生而出现的共时性产物。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自政府相应的模式产生以后就必然伴随而生,二者出现并没有先后之分,不是行政文化的出现才引致政府效能的出现,也不是政府效能的面世导引行政文化的面世,二者不存在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或时滞先后的线性关系。以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外显性很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例,在其产生之时,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也以相应的形式同步产生,虽然它们当时的面目与后资本主义时期的行政国家以及现实期的服务型政府下的政府生态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二者依旧是同步产生的。因此,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由于结构性互嵌,二者在产生时序上是同步的。
从生成空间上来说,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都具有地域阈限。我们在通常意义上分析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时总是一个宏大的指谓,是抽象的集合体,即剥离出差异而求同的结果,其实,若是深究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真实镜像,那么就会发现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并非是适用地域范围广泛的专业术语,相反,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都是区域性的,都有自己适用的阈限。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巨大,它们不仅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表现不同,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表现相异,而且在同一时期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其表现也大相径庭。“美国的行政文化通常表现为民主、自由、积极、奋发的特色,德国的行政文化表现为重法、守纪、严正、整齐的特色,英国的行政文化则有尚典、守旧、泥古、重名的色彩。”[1]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缘于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使动者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易受地域风俗文化影响的人。文化作为人类群体在生活过程中的一种形成符号、表征价值和传达意义的集结物,它起到一种社会规范的作用,是人与人交互作用的产物。行政文化作为文化的子类,它在拥有表征自己本质属性的殊相的同时,最普遍的还是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共性的东西,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若是剥离出各个时代的特性而以同质的时空观来解构,行政文化是一种纯粹主观建构的产物,它的形形色色取决于生活在该特定区域里的人,它也因此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区域性特点的烙印,体现为具有区域阈限的行政文化。政府效能与行政文化相比,其建构范围与行政文化相当,完全立基于行政文化的生成空间。政府效能究竟呈现何种态势,要与政府生态的诞生地域有直接关联,尽管可进行效能标准的移植,但是,这种移植绝不可能完全照搬,它必须综合考量地域状况与空间特质,以此对政府效能标准进行自由裁量。这就突显出地域空间对于政府效能的作用,犹如行政文化受地域限制一样,二者都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生成空间界限。
从历史惯性上来说,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都具有历史因袭性。影响行政文化的因素很多,诸如历史习惯、地理环境、社会制度等等,行政文化一经形成便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在一定时间内难以改变,尤其是在以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我国为甚,人们深受历史积习的影响。行政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支,其历史惯性主要缘于行政文化是一种内生变量。一国行政文化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虽然也在发展变化,但这种过程极为缓慢,它往往瞄准行政体系的核心特质,较少涉及那些稍纵即逝的行政观念与态度,更是拒斥当前的舆论热点。行政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我演化的过程,它是一个独立的自变量,其变迁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进程,强加的政策引导由于比较突兀,很难对接成功。多年来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一直难以跳出“膨胀—精简—膨胀”的怪圈,就是这种状况的鲜明写照,因为行政文化改革滞后,软件建设没有跟上硬件建设的步伐。政府效能的历史因袭性更为明显。根据行政文化历史发展阶段及其特点,可将我国行政文化分为“伦理型的行政文化范式、制度——伦理型的行政文化范式、法治型的行政文化”[2],即使如此,每一阶段的行政文化并非是完全割裂的,而是陈陈相因的。政府效能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如制度因素、技术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从各种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可发现,制度、文化、心理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甚至是保守性,而技术发展虽说是日新月异,但其无论如何飞速,也难以跳出一定时间点上的物质条件限能的制约,因此,政府效能受这些趋稳因素的影响,其发展变化也是较缓慢的。所以,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从历史惯性上来说都具有历史因袭性,成为二者同构的因子之一。
从产生的功用上来说,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具有同等的功用阈限。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功用集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于一体,而且,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都服从服务于政府合法性这一终极价值,是政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中予以论述,本部分主要阐述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同构的又一个表现,即功用阈限。鉴于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在生成空间上具有地域阈限,它们的功用阈限也就不难理解。尽管公众对政府效能的建构有影响,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政府效能很大程度上都是政府在自说自话,这种自说自话表现在:一方面,尽管来自世界各地高效能的政府行为的强制性同构的压力与规范性同构的吸引力,然而一定程度上,现行的所谓高效能的政府行为在其应然意义上并非就是最优结果,而是一种次优结果或者折中的结果,它是世界各国以及各区域性的“政府合谋”的结果,甚至是共同蒙蔽或敷衍各自民众的一种手段。很多人也许对此难以理解,但是我们联系一下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人”假设以及官僚制理论或许就会清晰明了。“经济人”假设意指个体不管处于何种情势之下,在人的本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即以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出发点,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它是个体行为处事的原始动机。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人布坎南认为,在公共决策中进行的决策并非是根据公共利益进行的选择,而是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安东尼·唐斯在《官僚制内幕》中也提出了一个中心假设,即官员们都是理性人、经济人,追求效用和自身利益最大化。公共选择学派的相关理论一再昭示政府都是自利性政府,追寻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一论断出发也就很好理解“政府效能是各国以及各区域性‘政府合谋’的结果”的观点,由于所谓的效能标准并非是最优的,因而具有效果阈限。另一方面,政府效能是政府加强自我建设的一种形式,是证明自己合理存在的依据,其证实方式往往是自我的一种无绝对强制力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剖析,效能的高低都以自己设定的标准进行检测,公众由于对政府事务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因而也难以真正了解内幕,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效能在中央政府制定的抽象、粗略的考核指标下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来细化本地的考核标准,各国政府效能的比较更是难以真正量化细分,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效能在各个区域也就有所差异,呈现出区域政府效能的阈限。而行政文化作为影响政府效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鉴于其也有自己的生成空间,它的功用阈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建设主体具有一致性
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源于同一个物象即政府生态,政府的存在是它们产生的源头,而且更进一层,不同的政府生态也会产生不同的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综观政府模式在各个不同阶段所呈现的形态以及在各自形态下产生的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时期的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皆产生于对其有决定性的政府模式之上,政府生态为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共同起源。在主客体间的映射上,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都映射出社会现实,这突出表现在行政生态理论。按照美国行政学家弗雷德·W·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的观点,影响公共行政主要有五个因素,即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与政治架构。他将行政模式分为融合型的农业型行政模式、棱柱型的过渡行政模式、衍射型的工业型行政模式,这三种模式分别映射传统社会、农业向工业过渡的社会以及现代工业社会的行政现象。分别对应于各个社会形态的现实状况,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呈现出与农业社会、过渡社会以及工业社会所具有的特质。因而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具有共同的生长点,同时又都映射出共同的社会现实状况,具有共相性,亦即在产生根源上,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都衍生于政府模式,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都映射社会现实。下面,我们就详细分析一下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同构的几个表现,即生成过程具有同一性,建设主体具有一致性,拥有类同的功能和作用。
主体是认识与实践活动的承担者。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建设的主体呈现一致性,都是行政组织(包括行政管理者)与扮演受动角色的社会大众,其中,行政组织(包括行政管理者)作为行政主体,是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建设的主主体;社会大众作为环境主体,是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建设的从主体。之所以将行政管理者成为主主体是因为在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建设中,二者的地位与作用是有分殊的。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成型与推进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行政管理者在行政管理实践中的认识、提升与身体力行,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本文不同意部分学者将社会大众排除在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建设主体之外的观点,因为尽管社会大众在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建设中并非起到中心作用,但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任何一国政府绝对不可能无视社会大众的反应,社会大众的任何回馈都会得到政府管理人员的回应,包括作为与不作为,此种角色在当下参与型文化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社会大众也是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的建设主体,只不过其作用不如行政组织明显而已,我们姑且称之为从主体。相应地,由主主体推动而形成的行政文化是一种微观的行政文化,由从主体力行的行政文化则是一种宏观的行政文化,“宏观层面的行政文化是指现行社会中普遍流行的观点、思维模式以及价值取向等,它的主体不局限于行政主体中的成员,更多的指社会民众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微观层面的行政文化是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为背景的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所形成的精神文化形态,是关于一切行政活动的行政意识、信仰、价值观、道德观、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心理倾向、传统习惯等因素的有机整体。”[3]即行政文化的成型一方面是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实践与社会交往活动获得行政认知,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大众对行政实践的反馈与期许形成行政期待。政府效能的建设主体与行政文化主体也是一样的。规范的、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除了政府部门自己设定指标进行评估外,也少不了社会大众的测评,二者的协同方能成就有效能的政府。
三、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具有类同的功能及作用
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类同的作用体现在维护政府合法性及有效回应社会需求作为自己的价值旨归,都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都是政治建设的一部分。
一方面,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都是以有效回应社会需求为价值旨归。随着社会的进步,个人主体性的发展,政府的祛魅成为必然,政府已经很难像以前一样单向度的制定法律法规,然后让群众无条件的服从与遵守,而是必须与公众进行互动,进行双向交流与信息沟通。公众应该有权提出公共决策议程设置,并参与决策讨论,最后结果应当体现公共理性协商所达成的共识,由于公共决策影响到利益相关者的生活,所以与公共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众应当有权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发挥各自的角色作用,具有充分而对等的发言机会,从而使决策集思广益,引起共鸣并获得支持。现代社会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公共治理取代政府管理,在公共治理的背景下,治理主体渐呈多元化,治理客体对象不断扩展,治理机制和工具的得以变革。这种状况使得政府必须对民众要求作出及时正确的回应,倾听群众的呼声,真实体现出当下的集体意向性,型构柔性的社会结构。因而政府必须将对社会的有效回应作为自己决策的活水源头,只有公众的积极参与,才能群策群力,才能防止部分人的短视与盲目。特别是现代社会利益矛盾错综复杂,不同人群的利益矛盾,不同阶层的利益矛盾交织在一起,合理省力的解决方式只能是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对话、进行商谈,而这必须要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如此一来不仅能够反映民意、集中民智,还使制度法规能够被群众很好地遵循,减少了政策执行中的协调成本,降低了行政成本,最重要的还获得了群众的认同,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无疑都是以维护政府的合法性及有效回应社会需求为终极目标,价值负载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都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当代公共管理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顾客导向、私营部门管理方式和竞争机制的引入、注重结果和产出、注重绩效评估和效率,在这种大环境下,行政体制改革往往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优先选择。在行政体制改革实践中,政府的职能转变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政府生态由最初的统治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转变,再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并伴有后现代公共行政的思想因子;政府权力得到了更为明确的界定,为权力运行限定了边界;行政程序的法律界定表征着由重实体法转向重程序法,因为权力的运行必须以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方式进行,阳光行政是必然归宿。放眼全球,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服务运动勃兴,各国政府都在积极推动政府创新,在此大背景之下,我国也不例外,党中央、国务院一直要求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转变政府职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改变政府包揽过多、伸手过长的状况,只管掌舵、不要划桨,以实现依法行政和提高行政效率。要取得行政体制改革的成效,跳出“精简——膨胀——精简——膨胀”的怪圈,不仅需要改革政府效能等行政管理的显性构件,更为重要的是改革行政管理的隐性构件行政文化,只有软约束层面的要素得以提质改造来联动硬性的政府效能的提升,才能真正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向前发展。
此外,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都是政治建设的重要构件,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必要工具。可以说,政治建设最为重要的是在政治领域推进民主化与法治化。在政治建设的民主化方面,我们知道,“民主政治的稳健构建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社会发展为条件,成熟的政治文化为支撑,完善的制度安排为保障,同时也离不开本国主导的民主话语体系。”[4]在政治建设的法治化方面,首要的是必须要有一部“良法”的存在,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历史上,我国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态度:人治与法治。“儒家有‘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说,希望有圣君贤相出而德化万民,治理国家;法家有‘任法不任人’之说,强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5]P404实际上,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主要是人治在起作用,人们的法治意识比较淡漠。但是,随着近些年来法治观念的普及,现在我国已经克服了要不要实行法治的问题,法治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法治是专制、独裁的死对头,意味着权力屈从于法律,它保障个人权利,限制公共权力。“一个民主的社会必须是法治的社会……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保障和重要标志。”[6]P124政治现代化则主要涵盖政治权威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专门化、政治参与的民主化,其中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包括政治过程的法治化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很明显,政治建设与政治现代化都离不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可以被定义为:公民对自己国家的政治体系所采取的基本价值、信仰、观念、态度和取向。[7]P70一国的政治文化相对稳定,虽然也在发展变化,但这种过程是极为缓慢的,它瞄准的是核心价值,而非那些稍纵即逝的观念、态度,更非是当前的舆论热点。“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它是一个独立的变量,与经济的关系应是一种自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而非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如此之说,并不意味着政治文化的演变不受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而是强调,政治文化与经济发展不是果与因的线性关系,它有着自身独特的演化路径。”[8]治文化的变迁除了受一国历史传统因素的影响,还受制于政府政策的引导。阿尔蒙德和维巴将政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者文化。[7]P76村民文化通常出现在贫穷的、教育水平低下的社会中,在那里人们的聚焦点只在本人狭隘的圈子内,如只关注家庭、村庄,对较大范围的政治体系则孤陋寡闻。臣民文化能够意识到较大范围的政治体系,但并未参与其中,其身份只是一臣民。参与者文化则可以运用自己的各项权利积极融入到政治体系之中。由于行政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子类,行政文化创新与政府效能提升是行政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构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行政文化是政治建设的重要构件。政府效能亦是如此。政治现代化必然要求政府管理的现代化,政府管理现代化最明显的标志无疑是良好的政府效能。所以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必要工具,因此也就有了类同的功能和作用,是二者同构的表现之一。
[1]于健慧.基于传统视域的行政文化的反思[J].行政论坛,2007,(5):43.
[2]何永红.中国行政文化的范式分析[J].行政论坛,1999,(6):14.
[3]撒承贤.简论政府效能与行政文化[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6):122.
[4][8]李建华,张效锋.论我国民主政治建构的基本维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155,156.
[5]孙哲.权威政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6]赵震江.中国法制四十年(1949—198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7]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M].娄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D0
A
1004-3160(2011)04-0056-05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研究》[项目批准号:08JZD006]的研究成果之一。
2011-05-10
1.李建华,男,湖南桃江人,中南大学、湖南城市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伦理学、公共管理学;2.方华堂,男,湖南衡阳人,益阳市公安局局长、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谭桔华